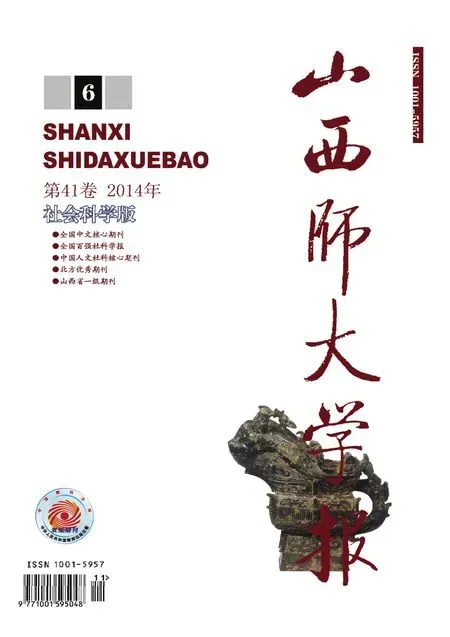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思辨性言说及其文化成因
2014-04-11杨朝蕾
杨 朝 蕾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阳 550001)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风日炽,佛学肇兴,掀起继先秦之后的又一股思辨风潮。其时文士暂时走出具体繁杂的表象世界,去沉思隐藏在其后的本质与始因,创作出诸多思虑精湛的论作,在思辨中体会觅得真谛的纯知性乐趣。思辨性言说成为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主要言说方式。所谓思辨性言说,即在理论表述时,通过概念、范畴的建立,以抽象的言语形式,阐明不同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然而,与西方哲人单向的线性逻辑表述不同,魏晋南北朝论家擅长思辨与诗性的联姻,在整体上追求一种不同既往的言说方式,为其思辨性言说注入艺术的精魂,使之与诗意性相融合,使苦涩的理论变得丰润而可爱。
一、思辨性言说的主要方式
(一)诠量轻重,遮其所非——遮诠式言说。遮诠与表诠是语言中的两种表达方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解释为:“遮诠,即从反面作否定之表述,排除对象不具有之属性,以诠释事物之义者;表诠,乃从正面作肯定之表述,以显示事物自身之属性而诠释其义者。”遮诠式言说为大乘中观学派所擅长的思辨方式,龙树《中论》中的“八不缘起”即采用此种言说方式,通过否定“生灭、断常、一异、来出”等实体性概念来反显超越名相的最高实在。作为鸠摩罗什高足的僧肇,对“三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熟稔使其化中观学派的般若思维方式为己用,灵活运用遮诠式言说方式创作了《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与《涅槃无名论》。从这四篇论的题目,就可见其遮诠式言说之端倪。其论中更是随处可见遮诠式言说,如《般若无知论》对圣智的描绘即是从“不是什么”中彰显其“是什么”,曰:“然其为物也,实而不有,虚而不无。存而不可论者,其唯圣智乎”[1]1804,将本身就是抽象难以言述的对象“以破为立”。宋代的净源法师在《集解题辞》中称:“昔者论主生于姚秦,遮诠虽详,表诠未备”,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僧肇受到中观论法的影响。在他看来,唯有祛除对真相的遮蔽,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因此,运用遮诠法解空,才能不胶着于表相。
堪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理性思维的英雄”[2]7的王弼,亦为遮诠式言说的大家。他认为“名号生于形状”,在为《道德经》中的“道”定名时,从形名角度转化为“无”,其《老子指略》曰:“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3]195此处,王弼对“无”的描述多处运用否定词“不”,没有从正面对其进行论述,其特征是无形无象,无法命名,所以就是“无名”,“无名,则是其名也”[3]53。
(二)二元相关——对举式言说。老子擅长用“正言若反”的语言表达形式描述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转化,这种思维方法,被张东荪先生称为“相关律名学”或“二元相关律名学”, “即这种名学注重那些有无相生,高下相形,前后相随的方面”。[4]365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沿袭《老子》中“正言若反”的语言表达形式,通过列举大量对立概念进行论辩思考,如形名、温凉、宫商、炎寒、柔刚、一多、恩伤、古今等。除此之外,亦以“四象”与“大象”对举,以“五音”与“大音”对举,以“四象”与“五音”代表“个体”,而以“大象”“大音”指代“一般”,二者既对立又辩证统一。
与正反对举相类似的是中观学派所讲的“有无双遣,不落两边”。张东荪先生指出:“我以为印度哲学上的这种论式是‘双遣法’……此法是以相反的两概念先使其同时皆非,但亦可使其同时皆是。如有与无,一与多,既非有又非无,同时却又非非有与非无,同时非一非多,而又同时即一即多。此种论法亦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亦即所谓‘超腾’(aufheben)。”[5]247僧肇深受中观思维的影响,在其论中多处运用“双遣法”进行论证。如“不迁,故虽往而常静。不住,故虽静而常往。虽静而常往,故往而弗迁;虽往而常静,故静而弗留矣”(《物不迁论》),将“往”与“静”这对矛盾对立,又使其统一于同一事物中。
(三)链体推进——因果式言说。链体结构在《老子》中已多处使用,如:“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可拆解为两个长句:“为者败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执故无失。”但拆解后的链体结构和原句相比,原句并不仅仅是表达一种思想的简洁方式,而是以无声的、结构的方式表达思想的第二个层面,也就是说两个句子之间并非是平行并置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对立面,共同构成一个存在着的界域整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种结构在论体文中亦较常见,有助于建构立体的论辩空间,也增强了文章的逻辑严密性。
魏晋南北朝论体文中的链体结构具有逻辑推进功能,根据其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单链推进。从形式上看,与顶针句无异,每一句都以上一句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再以此为前提,推出下一句,与传统逻辑中的连锁推理相似。但连锁推理是复合推理的省略形式,是建立在类属(属种)关系基础上的。[6]344此处句子的推导关系却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句式为“……,故……”,不妨称其为因果推理。如慧远《明报应论》曰:“知久习不可顿废,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权其轻重。轻重权于罪福,则验善恶以宅心。”《三报论》曰:“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另一种为双链推进,论证中双链并行,二者纵横交错,构建起立体的思维空间。王弼是运用链体推进的高手,较之先秦典籍中的链体推进,王弼将其进一步系统化,甚至将其用来结构全篇。如上文所引的《老子指略》开端部分即为双链推进式论述。
二、思辨性言说的特点
(一)概念缺乏确切含义。概念是对事物共性的抽象概括,反映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是最基本的理性思维形式。“构成哲学概念的四个标准,即名词化,有固定形式,用于普遍性论述,以及用作判断的主词或宾词。”[6]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士在进行论体文创作时,脑海中没有盛满西方的哲学话语和方法,因此他们不会像我们似的一说到“思辨”,首先想到的就是概念是否明确,他们重视的是“正名”。冯友兰指出:“盖一名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之要素或概念也。”[7]52以王弼“无”概念为例,在《老子》中,“无”共出现一百多次,但大多数为形容词或副词,并非哲学概念。到了王弼的《老子略例》与《老子注》中才将其发展为哲学概念,他的贵无论是由老子“有生于无”发展而来,曰“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又将道称为无,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然而,“无”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征,王弼依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阐述。因为“无”与“道”这类范畴型概念,“它本身只是一个无穷的意义场,随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的阐释而不断发展,一旦给它规定一个明确的意义,那就不是它了”[6]。所以根本无法用西方的那种稳定而明确的定义方式进行阐述。
刘笑敢先生认为,“哲学问题的讨论是靠哲学概念还是靠副词描述,是靠比喻和寓言间接表达还是靠理论论证,这是哲学逻辑思维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8]如果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魏晋南北朝论体文,可以发现较之先秦诸子著作的寓言说理,魏晋南北朝文士在抽象思辨能力方面已有很大提高,叙事性寓言在魏晋南北朝论体文中已较少出现,理论论证增多。但其概念的阐释仍较多地采用遮诠的方式,因此,贵在意会、领悟、直观把握,而无法用确切的语言进行界定。在冯友兰先生看来,概念可分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中国哲学的概念是用直觉的方式获得的,而西方哲学的概念则用假设的方式获得,“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7]22。西方哲学的方法论是理所当然地由正的方法占统治地位,而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则理所当然地是负的方法占统治地位。[7]298如何晏、王弼论中的“无”,慧远论中的“神”无不如此。对于这种范畴性概念,往往无法用单一的定义去限定其内涵,因其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有机生长的意义场,充满张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多义性与模糊性。如果一定要按现代性的知性思维对其进行概括,反而容易陷入独断的境地。
(二)判断缺乏鲜明形式。概念按照一定形式相互联结起来,就构成判断。张东荪认为,由于汉语的主语(subject)和谓语(predicate)的分别极不分明,“遂致中国人没有‘主体’(subject)的概念”,“谓语亦不成立”,“没有tense与mood等语格”,“因此遂致没有逻辑上的‘辞句’(preposition)”。[9]“中国哲学更注重判断认识与生活实际的关系(名实关系),而不大注意判断概念与概念的关系以及句式本身的清晰性、稳定性、程式性。”[10]227古汉语中的判断往往借助于词序与虚字来构成,如“……者,……也”,“……,……也”等。在西方人看来,其判断缺乏明确形式。霍布士指出:“有些民族没有和我们的动词‘is’相当的字。但他们只用一个名字放在另一个名字后面来构成命题,比如不说‘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动物’,而说‘人,一种有生命的动物’;因为这些名字的这种次序可以充分显示它们的关系;它们在哲学中是这样恰当、有用,就好像它们是用动词‘is’联结了一样。”[11]41这正道出古代汉语的表述特征。因为缺乏明确的判断形式而使复杂的判断句式出现多义化倾向。如王弼《老子指略》曰:“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由于没有逻辑连结词,其涵义就可以作不同理解,可以构成不同的判断形式。
判断形式的这种模糊性,使之意义缺乏确定性,却也使之具有更丰富的内涵,而充满诗性特质,但又因其多义性而容易产生歧义,使所言之理缺乏准确性与严密性。究其缘由,魏晋南北朝文士沿袭前人的思维方式,认识到“言”与“意”之矛盾,在他们看来“言不尽意”,“言尽而意未了”,因此对于判断形式的明确化缺乏内在的兴趣与热情。
(三)推理缺乏清晰过程。任何推理都是由前提和结论两个部分组成,前提是推理的出发点,结论是推理的目的,任何推理都是完整而确定的过程。推理的前提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推理的结论则只有一个。所以,推理必须采取句群或句组的形式。但古代哲人崇尚简约,在言意关系中,推崇得意忘言。按照道家的思想,“道可道,非常道”,也就是说道不可言,只能悟。语言的作用不在其确定性,而在其暗示性、启发性。冯友兰先生指出“……中国哲学的语言何以是提示性的而并不明晰。它不明晰,因为它不代表用理性演绎得出的概念。哲学家只是告诉人们,他看见了什么。因此,他所述说的内容非常丰富”[7]22。尽管魏晋南北朝玄学与佛学提升了其时文士的逻辑思辨能力,但他们在提出新的命题时,往往都是单句,而非句组或句群。也就是说他们将自己感悟的结果以简练的语言概括出来,而省略其推理之过程,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经过严密的推理即得出如是结论,没有大前提、小前提,甚至没有逻辑联结词。
何晏注《论语》提出“思其反”的论辩方法,《论语集解·子罕》曰:“夫思者,当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为远。能思其反,何远之有?言权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何晏所谓的“思其反”是针对“道”与“权”的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由用以求体,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使纷纭万变的现象归属服从于总的原则;另一方面,再由体而及用,从抽象返回到具体,通权达变,掌握神而明之的应变能力”[12]122。何晏在《道论》中提出其贵无论玄学系统的基本范畴“有”与“无”,“有”是由具体现象提升出来的,包括圆方、白黑、音响、气物、形神、光彩等自然界的物象,也泛指各种人事。而“无”则无形无名,是从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即为道,“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来皆有所有矣;然犹谓之道者,以其能复用无所有也”。然而,终究没有讲清“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这一命题是如何提炼出来的。按照其“思其反”的方法,本来是应该由“用”以求“体”,但他却弃其“用”,单拈出“体”,省略其求之过程。于是,体就成孤悬之体,无法得知其用及由用求体之推理过程。
语言是思维的外化。“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十分注重‘辨名析理’。他们的理论形态和理论思维尽管大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思辨性特征,但从其思维倾向看,与先秦道家一样,仍然是通过名辩的逻辑过程而排斥具体知识或名言,旨在肯定直觉性思维。[14]145”直觉思维重视体悟,与逻辑思维之不同在于其是综合的、具体的,而逻辑思维重视推理,是分析的、抽象的。在魏晋南北朝论体文中多比喻论证与断语警句,是其时文士直觉思维的表现。“推理式的思维以‘A是B’的命题为中介进行演绎论证,而比喻例证的两点论的思维方式缺乏严格的‘A是B’的结构,而以‘A犹如B’那样的公式进行‘比类取象’和‘援物比类’。”[13]魏晋南北朝文士通过比喻论证进行说理时,A与B是异质的,通过体悟与联想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只是若干可能存在的联系中的一种,突出的是主观性,而忽略了二者之间联系的建立过程,即推理过程。范缜在《神灭论》中以“刃”与“利”来比喻“形”与“神”,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体现出的是范缜“取象以尽意”的主观意图,将客观的存在转化为主观的认识,用具体的物象来论述抽象的道理,其间不存在推理的过程。
三、玄佛论风与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的思辨性言说
一般而言,中华民族长于形象思维,短于抽象思辨,但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特殊,其时玄学、佛学的兴盛使文士对哲理的探讨近乎癖好。其时,理性思辨亦具艺术性,成为诸多文士生命中的一部分,甚至达到废寝忘食、累病谈死的境界。不管是孙盛与殷浩舌战,“往返精苦”,“至暮忘食”,还是嵇康与向秀笔战,就养生问题而互相论难,表演精彩的“双簧”,他们对“论”的热爱,对“理”的执着,皆表现出“理知性的认识愉快”。
汉魏之际复兴的名理之学,继承先秦名实之辨而又有所发展。王弼明确指出:“夫不能辨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强调辨名言理与定名论实的重要。其时文士以擅长名理著称者甚多,如钟会“精练名理”,嵇康“研至名理”,阮侃“饬以名理”,卫瓘“清贞有名理”,等等。甚至有文士以先秦名家的逻辑命题作为论资,如西晋爰俞“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由此可见其时文士对逻辑思辨的由衷热爱。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玄学的辨名析理完全是抽象思维,从这一方面说,魏晋玄学是对两汉哲学的一种革命。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从两汉到魏晋,觉得耳目一新,这是因为玄学的精神面貌和两汉哲学比较起来,完全是新的。……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15]44。蒋凡先生也在其《〈世说新语〉研究》中谈道:“玄理清谈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发展,特别是对于理论思辨,曾起了推动进步的积极作用。”[16]69二者皆注意到魏晋时期玄学对抽象思辨的重视及其对士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玄学论辩是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理的论争,重视以理取胜,必然讲究思辨性。王晓毅先生曾从逻辑学角度,将魏晋名学方法分为两个基本层次:一是“校实定名”的方法,一是辨名析理的方法。前者产生并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以“名”、“形”、“实”为范畴,后者是指“通过比较概念的异同,研究概念之间的联系,以达到分析事物规律的目的”。[17]110名实方法侧重于概念研究,名理方法则侧重于运用判断和推理,二者是魏晋南北朝论体文运用较多的论辩式言说方式。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全面输入,使得其时崇佛文士与僧人的理论思维水平进一步提高。佛教中的“论”,《佛学大辞典》解释为:“佛自论议问答而辨理也,而佛弟子论佛语,议法相,与佛相应者,亦名优婆提舍。三藏中之阿毗达磨藏也。”[18]2636阿毗达磨,梵语Abhidhqrma,汉语亦作毗昙、阿毗昙,译为无比法或对法,是智慧的别名。因三藏中之论藏诠显学者之智慧的缘故,虽涉于大小乘论藏之通名,而常指小乘萨婆多部之论藏。
中土第一个组织系统翻译有部毗昙的僧人是东晋释道安。在他所组织翻译的各种经籍中,除了一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是属于般若类以外,其他的十三部一百七十八卷都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经典。道安强调学习毗昙是读懂经典的基础,要研习般若学,也必须掌握毗昙学中的数法。作为道安得意弟子的慧远,受其师的影响,对毗昙学甚为重视。后来他在庐山请僧伽提婆重译《阿毗昙心论》,对弘扬毗昙学起了重要作用。慧远在《阿毗昙心序》中介绍说,法胜“以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迄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曰心”。并指出《阿毗昙》相当的深广幽奥,一般很难探究其内涵。故汤用彤先生说:“《毗昙》学之大兴,实由于慧远徒从也。”[19]249堪称的论。
吕澂先生在《阿毗达磨泛论》一文讲了阿毗达磨藏之来历,又论大乘阿毗达磨曰:“后世观《庄严经论》及《摄大乘论释》,皆解阿毗达磨意义有四端:其一对法,谓以四谛道品等说,趋向于涅槃;其二数法,谓以思择法门数数分别法相;其三伏法,谓说论议能伏他异诤;其四解法,亦称通法,谓释规式通晓文义。”[20]2364由此可见,阿毗达磨采用的论辩方法甚多,而慧远受其沾溉,在创作的论体文中灵活运用各种论辩方法,义理丰富,造诣甚高。[21]
东晋南朝文士受佛学影响,创作了大量佛理论文,诚如刘师培所云:“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以刘琰、王濛、许询为宗。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又西晋所云义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慧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郄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均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22]56在玄学与佛学的碰撞、交涉过程中,玄学亦受佛学之影响,在论述裴頠《崇有论》与佛学的关系时,普慧先生指出,“由当时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我们便会认识到他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尤其是佛教‘论’的影响。比较《崇有论》与佛教的‘毗昙’之文,就可清楚地发现这一点。除裴頠之外,其它玄学家的议论文在对概念的分析上、在对论点的推理和思辨上也受到了佛教的潜在影响”。[23]东晋孙绰、罗含、周续之等人,南朝谢灵运、颜延之、宗炳等人之佛理论,注重概念分析与推理思辨是佛理论的重要特色,显然是受佛教之影响。
总之,魏晋南北朝论体文思辨性言说的增强,表明其时文士受玄佛论风的影响,思维得到深化和精确化,思想和语辞产生张力,使理性思辨审美化、艺术化。
[1] (清)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5] 张耀南.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6] 张汝伦.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范畴错误”[J].哲学研究.2010,(7).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8] 刘笑敢.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J].中国哲学史,2002,(1).
[9] 张东荪.从中国语言构造上看中国哲学[J].东方杂志,1936,(7).
[10] 马中.人与和:重新认识中国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
[11] 胡适.先秦名学史[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
[12] 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13] 徐通锵.思维方式与语法研究的方法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1).
[14]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1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 蒋凡.世说新语研究[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8.
[17] 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8]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书店,1991.
[19]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0]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6.
[21] 杨朝蕾.简论毗昙学对慧远论体文的影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2).
[22]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3] 普慧.佛教对中古议论文的贡献和影响[J].文学评论,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