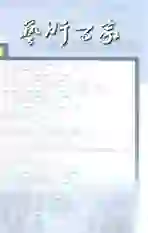艺术原创的生态性:味与魅力
2014-04-10姜耕玉
姜耕玉
摘 要:艺术原创作品应该是一个生态系统。它表现为艺术本源的本真深邃、形象的结实饱满以及艺术结构的生命张力和整体平衡。形象根于作品结构之中,艺术整体结构的多维深度的自然和谐,是形象发生魅力的深厚基础。趣味是“灵魂的微笑”,是艺术生命的形态表现,于独特的趣味表象之中包裹着味之深意或美的内质,“味外之旨”,即是上乘的作品境界。味或魅力,是复杂的生态的艺术形象整体结构的效应。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原创;本源;艺术生态;趣味;味质;魅力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艺术原创是个体的创造活动。一部原创的优秀作品,是充满活力与个性的创造主体的深度显示,它是以呈现形象世界的趣味生态为基本标识。只有达成艺术形象存在的生态性,才有产生艺术美与魅力的可能。艺术魅力,首先是生态魅力,而原创提供了艺术生态的最大可能。艺术生态是一个生态系统,也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具体表现为艺术的本源性、形象的结实饱满以及艺术结构的生命张力和整体平衡。
魅力是艺术传媒与审美接受的出现的概念,我们为某一艺术形象所诱惑、所惊叹、所震撼、所折服、所陶醉,这即是艺术的形象与趣味发生的魅力。而一部作品具备优良的艺术生态结构系统,是其味和魅力发生的首要条件,艺术魅力是形象系统的整体效应。艺术魅力一旦被人们感受,可以理解为娱乐与审美的最高境界。
一、艺术本源:人类生命与灵魂的诉求
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基本层次的需要理论看,艺术属于第五个层次“自我实现需要层次”,即人的精神层面。人的“自我实现需要”的精神活动,是内在的、心理的、灵魂的活动,艺术属于满足人的精神需求的基本层面。卡西尔说:“艺术可以包含并渗入人类经验的全部领域。在物理世界或道德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自然事物或人的行动,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会被排斥在艺术领域之外,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抵抗艺术的构成性和创造性过程。”①与宗教、科学、历史、哲学相比较,艺术家是在最低处歌唱。因为艺术以无所不包的感性的形象世界,不仅贴近世俗、亲近人类,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而且人们从艺术中可以获得比宗教、哲学等领域更为丰富多样的精神需要。这就是艺术的特质与魅力所在。人生在世,不光是生命的个体,而是有种种负荷的精神个体。尼采有灵魂三变说:“……灵魂苟视其力所能及,无不负也。如骆驼之行于沙漠,视其力所能及,无不负也。既而风高日黯,沙飞石走,昔日柔顺之骆驼,变为猛恶之狮子,尽弃其荷,而自为沙漠主,索其敌之大龙而战之。”“狮子”能“破坏旧价值(道德)而创作新价值”,“然使人有创作之自由者,非彼之力欤”,故“狮之变而为赤子”,“赤子若狂也,若忘也,万事之源泉也,游戏之状态也,自转之轮也,第一之运动也,神圣之自尊也。”②“骆驼”标示人生在负重与艰难跋涉中的灵魂痛苦,“狮子”标示人的反抗与创造精神,“赤子”标示创造者的真诚、激情与超脱的自由心灵。从艺术本源考察,骆驼式痛苦,狮子式奋起,只是艺术之起因,如秋风起于青萍之末。而赤子之心,才是打开通往艺术之门的钥匙。叔本华称:“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凡赤子皆天才也。”③骆驼——狮子——赤子,可以理解为从感受者的灵魂变为创造者的灵魂的实现。艺术天才即赤子若狂若忘的状态,颇近于激发灵感的艺术状态,艺术天才的灵魂,皆赤子式灵魂也。尼采的灵魂三变,即骆驼、狮子、赤子,也可理解为人的灵魂的三个向度,由此展示了人的灵魂的脆弱与强大、痛苦与超脱,由此生命和灵魂作为艺术本源,提供了形象创造中灌输生气的可能性。真正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是纯粹的、本源的。艺术形象的物性,只有被生命精神和灵魂照亮,才能变得充盈起来。生命和灵魂作为艺术本源,概言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人性源头守护说,一种是入世的孤愤—发愤说与酒神—日神说。
首先看人性源头守护说。荷尔德林说:“美,人性的美,神性的美,她的第一个孩子是艺术。”即是说,“在艺术中,神性的人青春重返,再获生命。”然而,这一理想主义的艺术的实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荷尔德林举出希腊艺术为例。然而,把“人性的美,神性的美”视为艺术之母,却是独到精当的。荷尔德林说:[HK18*2][HT5”,5K]
从摇篮时代起就不要去干扰人吧!不要把人从他本质的紧密的蓓蕾中驱赶出来吧!不要把他从童年的小屋里驱赶出来吧……让人知道得晚一点些,在他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会成人。人一旦成为人,也就是神。而他一旦成了神,他就是美的。④ 荷尔德林认为,人性、人的本质之美,寓于摇篮时期的蓓蕾之中、童年的小屋里,他呼吁不要去干扰,让人性的美好蓓蕾自然生长。只有保持人的天性,他才会成为人,才会有神性的美。这种不入俗流的乌托邦主张,其本意在保持人的本真与纯粹的本质,具有守护艺术本源的纯洁性的重要意义。因此,它成了很多诗人、艺术家信奉的艺术准则。中国明代李贽就提出“童心”说,并且有比较完整的论述:[HK18*2][HT5”,5K]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⑤ 童心即真心,李贽这么解释,显然更具有艺术创作的普遍意义。然而,真心又不等于童心,只是本于童心,即“心之初”。李贽主张“童心”,不是回到人之初的童子时代,而是不忘并保持心之初的本真,即荷尔德林崇尚的“人性的美,神性的美”。这就是“最初一念之本心”对于人的一生的价值。人一旦失去“最初一念之本心”,就毫无“真心”、“真人”而言。尼采所说“赤子之心”,也是根于“最初一念之本心”。李贽打出“童心”说的旗帜,意在从人性的源头上,“绝假纯真”,守护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这与荷尔德林呼唤“不要把人从他本质的紧密的蓓蕾中驱赶出来”相一致。然而,以异端自居的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又不同于诗人荷尔德林,他的“童心”说,是在现实的反抗封建礼教与批判“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中提出来的,是在对假人假言假文为什么盛行、而真的作品反而湮灭无闻的追问中立起来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说由此闪现艺术本源的理论光芒。历代不少哲学家、艺术家提倡皈依人的天性、本真。“真心”、“本心”亦列入诸种教义,中国佛禅有“心源”之说。尤其是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之后,人的异化不可避免,这也更加显示这些观点的重要意义。本文由此提出守护说。这一说乍看似乎是乌托邦主义,而对于艺术来说,却是灵感之源,即使这一源头在上苍,也是必要的,也要仰天而望。守护本义是虔诚的,艺术有责任守护人类精神的那一片净土,即人本有的精神家园,也有力量唤醒人们瞻顾那曾经拥有或失去的美好的东西——人性的美。endprint
再来看孤愤—发愤说与酒神—日神说。此两种观点虽有很大区别,但,以艺术起于感性为纽带而可归为一体。正如尼采所比喻,人的灵魂首先是无所不负的沙漠骆驼,作家、艺术家当然是愤然而起的狮子,并具备赤子之心。而引起天才的创造冲动欲望的,还在骆驼式的痛苦,与从痛苦中奋起的亢奋。这从中国古典作家的经验中足以得到论证。司马迁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⑥这也是受尽酷刑的太史公在谈创作《史记》的切身体会。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赞同司马迁的观点,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⑦。清代二知道人在评点《红楼梦》中则提出“孤愤”说:[HK18*2][HT5”,5K]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⑧ 孤愤与发愤两词相通,对于创造者的灵魂,又有先后之别。孤愤,不单单贴近骆驼式痛苦,同时结郁甚深,独具个体性与文人的情怀。可以从引发灵感发生的创作状态,去理解孤愤,而一旦郁结勃发,即发愤也。所谓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正是对发愤而为之的描述。自己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物,有许多欲语而不能语之事,蓄积已久,势不能遏,一旦有了时机,就一吐为快。《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称为哭:
[HK18*2][HT5”,5K]
《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书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王子言曰“别恨离愁,满肺腑难淘泄。除纸笔代喉舌,我千种相思向谁说?”曹子言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意(味)?”名其茶曰“千芳(红)一窟”,名其酒“万艳同杯”者;千芳(红)一窟,万艳同悲也。⑨
刘鹗疏忽了一个主题词,“窟”,谐音“哭”,应该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发愤也好,哭也好,都是因为痛苦而发。所谓喷玉吐珠,召回云汉,是说天才的创造者把痛苦磨砺或孕育成了珍珠的本领。哭,诚然会要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但一旦进入形象创造,这种狂放的悲痛,则是立于艺术创造过程之上的标志性符号。发愤、哭,固然属于情感的范畴,但同样可以说,心在哭泣,灵魂在哭泣。作家、艺术家的主观情感,一旦渗透到作品形象之中,势必会变得隐蔽起来,因此,姑且称之为发自内心的声音、灵魂的声音,更为贴切,也更为切入艺术本源,这样也可以避免创造的心灵与真实情感之间的纠缠。尼采认为“艺术的持续发展是同日神和酒神的二元性密切相关的” ⑩,他甚至把酒神冲动与日神冲动看成为艺术的根源:[HK18*2][HT5”,5K]为了艺术得以存在,为了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一种心理前提不可或缺:醉。醉须首先提高整个机体的敏感性,在这之前不会有艺术。B11 尼采将日神与酒神都列为“醉的类别”,“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画家、雕塑家、史诗诗人是卓越的幻想家。在酒神状态中,却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于是情绪系统一下子调动了它的全部表现手段和扮演、模仿、变容、变化的能力,所有各种表情和做戏本领一齐动员。”日神是光明之神,支配着内心幻想世界的美丽外观。日神冲动借助于视觉的幻觉能力,以获得梦的形象世界为满足,突现外观的全部喜悦、智慧及其美丽。酒神状态,是“整个情绪系统激动亢奋”,是“情绪的总激发和总释放”。酒神冲动是通过音乐和悲剧的陶醉,是痛苦与狂喜交加的癫狂状态,可以理解为艺术体验的巅峰状态,是具有形而上的悲剧性深度的艺术状态。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称“日神的梦艺术家”和“酒神的醉艺术家”B12。“梦”和“醉”都是本能性的、非理性的。“梦”是借外观的幻觉自我肯定的冲动,“醉”是借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二者对立而又相互平衡,日神对酒神的放纵无度起有抑制作用。中国有“李白斗酒诗百篇”之说,李白之狂放不羁,从“醉”意中得诗。深受西方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李金发,更称其诗“是个人陶醉后引亢高歌”。吴道子借裴将军舞剑,挥毫作画,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亦通于酒神冲动,也带有日神因素。中国艺术讲究一个“情”字,“发愤”、“哭泣”,没有达到酒神“醉”的极地,正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制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中国书画,颇得日神精神。中国书画运笔用墨洒脱自如,呈现着幻觉智慧的美丽世界。苏东坡称吴道子画佛,“梦中神受”,“梦中化作飞空仙,觉来落笔不经意”。这种梦中得画,是梦艺术家对幻觉能力的无意识发挥。尼采的酒神冲动与弗洛伊德的力必多转移说有相通之处。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本身就是艺术家的‘白日梦,是他们不能满足的欲望的转移和升华。”B13弗洛伊德的观点,切入艺术与生命本能的关系。性与生命意识,是艺术表现的重要方面,本文没有把生命本能当成艺术本源,是因为灵与肉是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没有生命意识的精神,势必变得空洞,也不会有痛苦。尼采称酒神“醉的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B14,并且确认其“醉”与日神之醉一样,是一切审美行为的心理前提,是最基本的审美情绪。“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B15弗洛伊德也没有离开“自我”、“超我”谈“本我”,他的“白日梦”说,其艺术价值主要在于发掘和发挥了无意识、潜意识的作用,使艺术家、作家的形象创造在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无限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提供了生命精神的形而上的艺术实现的可能。
二、艺术生态的形象与结构的特征 艺术家、作家能否拥有并深入艺术本源,直接决定其所创造的形象的生命质量与形象世界的生态性。正如海德格尔对梵高的画《农妇的鞋》所作的描述,首先,表现了鞋的物性。农妇穿着鞋站着走着,是作为工具而发挥作用,鞋以质料—形式结构而成为纯然之物,农妇在“在劳作时对它们想得越少,看得越少,对它们的意识越模糊,它们的存在,也就越真。”再则,纯然之物是自我包容的,这即是艺术形象的特质。艺术家的才华和本领就在于将形而下的物的艺术转化成形而上的精神的形象。“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现出来。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的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集着对面包稳固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战栗。这器具归属大地,并在农妇的世界得到保存。正是在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中,器具才得以存在于自身之中,保持着原样。”B16海德格尔借梵高所画农妇的鞋,旨在阐释“这一存在者从它无蔽的存在中凸显出来”。本文借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存在的思想,描述艺术形象的生态特征。艺术原创形象是以始初与鲜活、结实与饱满为基本特征。生态的艺术形象依仗于自身的独立性,特别指向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JP2]把表现对象作为纯然之物的真的存在。那种先入为主,一开始就把对象视为任我支配的奴隶,势必失去形象的自然生命力。过去文艺“工具”论,搞“主题先行”,使艺术形象失去了自主性,同时也失去了物的本真性。作家、艺术家把创造的艺术形象当做独立生命体,首先还是要把所创造的形象的物质载体,视为有生命的个体,并且尊重这种生命个体。只有尊重艺术,尊重艺术表现对象,才不会随意去支配它、扭捏它,才有使它保持真的存在的可能。所谓始初与鲜活,就是形象的本真存在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曾被人碰过的毛茸茸、活脱脱的形象体。[JP]物一旦融入自我而进入作品,就灵动起来,成了存在者的存在。物作为表现对象包容自我,这一艺术化的过程,同样要尊重所创造的形象,顺其自然,不能把主观感情强加给形象,甚至肢解和扭曲形象。正如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中特别强调,“只取其事体情理”,“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在叙事艺术中,人物形象在故事情节、戏剧冲突与细节、场景中生长丰满起来。这一艺术过程有着一定的长度,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的,任何走捷径而省略了某一过程或环节,等于破坏了艺术结构的生态平衡,受到影响或损害的是人物形象。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说:“境地愈稳,生趣愈流。”人物形象的结实和饱满,是一个自然成熟的艺术过程,是在对形象有序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描绘中生动丰满起来的。《红楼梦》在复杂庞大的情节结构中创造的众多人物,个个栩栩如生,堪称“圆的人物”(福斯特语)。“圆的人物”,即是结实饱满的形象指称。上述对农妇被磨损了鞋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的描述,则显现了农妇的世界。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鞋里“聚集着无怨无艾的焦虑”,“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并“隐含着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战栗”。这足以表现出画面形象的充盈。形象根于作品结构之中,艺术整体结构的多维深度的自然和谐,是形象发生魅力的深厚基础。艺术生态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之中。每一种艺术形象都要有扎实的铺垫与刻画,往往是在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中成长、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这即称为艺术过程,任何艺术形象,包括短制单一的形象都不能绕过这一艺术过程。譬如,希腊雕塑《维纳斯》,她端庄的体态与微微扭转而站立的姿势,脸部的典雅美。我们看到的,不单是她脸部的美的笑容,甚至还感觉到她微微扭转中腰际也发出微笑。罗丹称之为“古代神品中的神品”。这种独有的魅力,是形象的结实饱满所致,而形象的神韵,却是由质料与线条的感性效果中产生的。应该说,从质料与线条到维纳斯的典雅之神韵,十分遥远,艺术家运用神工妙斧,进行许多铺垫、链接与整合,才使女神形象呼之欲出。所谓她的腰际发出微笑,正是动态平衡的艺术效果。没有相对的稳定与平衡,各种艺术环节上的资源和潜能,就没有机会得到利用和发掘,这样艺术形象也会因为某个侧面的缺失而丰满不起来。艺术生态是艺术创造过程中呈现的一种气象或气息,它既是艺术家创造出来、并始终把握住的艺术境界,又维系和催动着艺术家的直觉想象与整个作品形象创构的运作。考察《红楼梦》这部鸿篇巨制的艺术生态特征,可谓虚中写实,真中见幻,曹雪芹即是在这虚实、真幻的叙事氛围中,展示驾驭纷繁复杂系统结构而游刃有余的大气和天才。自开篇第一回大荒山上女娲炼石补天遗落下来的一块无用的石头说起,经过“枉入红尘若许年”,化为通灵宝玉在尘世走了一遭,最后宝玉又被僧道携回青埂峰下。曹雪芹这一灵感来源,如此虚幻的“石头记”结构寓意,冠结并浸润全书的整个故事结构,这可理解为《红楼梦》整体结构的生态之源。而在现实人物故事的具体描写中,曹雪芹又严格依照事体情理,追踪蹑迹,从深入揭示贾宝玉和大观园女儿们各自的性格、命运及其相互关系中,展开庞大复杂的情节结构网,获取情节发展的内在依据。整部小说一树千枝,一源万派,路转峰回,山断云连,迷离烟灼,纵横隐现,突现了情节结构系统的自我调节与完善,不断取得艺术生态平衡。譬如,《红楼梦》第二十九回中,林黛玉病了,宝玉来探望,黛玉心头笼罩着金玉良缘的阴影,不由流露出来,惹出贾宝玉砸玉之事。这个细节,不仅对宝黛爱情的发展,起有推动轴心的作用,同时吓着两院丫头,惊动了贾府老祖宗及凤姐、宝钗等,既表明这块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又突现宝玉在贾母心目中的位置,还隐现宝、黛、钗之间的爱情角遂之跌宕起伏。宝、黛之间口角砸玉,牵动诸多人物关系与纠葛的波澜,亦可成为艺术结构系统的信息反馈。这一反馈调节机制,发生了推动与抑制的双向作用,而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艺术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在艺术叙事的过程中是由多种方式得以体现。曹雪芹的好友脂砚斋有一则眉批:“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传粉,千皴万染诸奇。”B17这段脂批,十分准确地描述了曹雪芹以天才的变化多端的叙事方式,创造了庞大复杂的情节结构的独特富丽、巧夺天工的生态系统。所谓艺术生态的自我调节能力,即是艺术叙事在对情节结构整体的驾驭中而不露痕迹的鬼斧神工。“佳园结构类天成”,只有形成作品结构的艺术生态系统,才会有艺术形象的结实与饱满。艺术魅力是作品各种复杂功能体系所产生的整体效应。而艺术生态结构为表现复杂饱满的形象与艺术直觉的创造力,提供最大的空间。譬如,毕加索的《牛头》,看起来很简单,但你却说不清楚它的意义指向,只觉得简洁而有意味。毕加索的创作灵感,源于自行车龙头和坐垫,是把二者拼合用青铜塑成牛头。这种奇思妙想式的创构,无疑是生态性的,成了充满张力的艺术形式,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符号,象征性的生命形式符号,由你去想象。因此说,艺术生态结构系统是开放式的,乃至不确定性的,神龙式的若隐若现,不是清晰透明的。中国艺术创构讲究浑然一体,“返虚入浑”(司空图语),“大浑而为一”(刘安语)。“大浑”本身就显现艺术生态特征,具有最大的包容性,甚至包含着神秘性。大作品往往都带有些神秘性,因为“我们从来只见事物的一面,另一面是沉静在可怕的神秘的黑夜里”B18。艺术生态结构,当然应该包容着这种神秘,反言之,荡溢着这种神秘迷离的氛围的艺术结构,才是生态的。艺术的生态魅力,是以包容性与生成性为特征的模糊美。endprint
三、艺术生命形态:趣味与味质
好作品与好酒一样,总是以味显现其质地和品质,“味”是鉴别一篇作品高低优劣的直觉印象。印度古典理论家檀丁在《诗镜》中曾以“蜜蜂得到花蜜而醉”来阐释“味”,强调“味”感性特征。“味”作为一种属性,是艺术品的品质与成色,伴随着艺术品的诞生而出现,犹如花粉的色泽和芬芳,在未被蜜蜂发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艺术作品中,味与趣是分不开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的生命力,总是以独有的趣味呈现出来。譬如,潘天寿画的《鸡雏图》,黑白两只小鸡,闲立或打盹,妙合天趣,自是一乐,真正给人以“手无缚鸡雏之力”的感觉。味,是一个宽泛的模糊性概念。一篇作品的味道,首先是由形象引起的直觉感受,但其深味,不单是耳目感官的快适,更有耐人寻味的感知,所谓“味外之旨”,即是不落言筌的形上之至味。德里达将阅读比做揭开一幅油画下面掩盖的另一幅更可贵的画B19。这种言外之深意或“另一幅更可贵的画”,是能产生艺术语境的效果。犹如好酒是由陈年老窖酿出来的,酒窖之酵母,是味中之味。而艺术之味,是靠艺术家、作家的形象体验来酿造的。审美意象是一种情感的精神的形象。好的艺术品得力于生意盎然、趣味横生的形象与意境的创造,于独特的趣味表象之中包裹着味之深意或“味外之旨”,“味外之旨”即是上乘的形上境界。这种味,可称为味质,而味质是相对于趣味而言,可理解为趣味的内涵。如果画图示意,可简括如下: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同小说“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B20,把“趣”视为俗文学才有,是一种传统的偏见。趣味,并非只是浅层次的娱乐。罗丹有一段话,十分重要:[HK18*2][HT5”,5K]艺术,也是趣味。艺术家一切的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是对于房屋、家具……人类灵魂的微笑,是渗入一切供人使用的物品中的感情和思想的魔力。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能有几个人,感觉到住房与家具应合乎趣味的需要呢?B21
[TP
罗丹把趣味与“灵魂的微笑”联系起来,视为艺术的必然表现,这一观点非常深刻。罗丹所感叹的他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能把趣味摆到应有的艺术位置,仍然切入今天的创作实际。究其原因,这固然有艺术表现趣味的难度,更重要的,还在于艺术观念尚未得到根本转变。为什么梁启超抑低小说“乐而多趣”,其旨在强调“熏”、“浸”、“刺”、“提”的载道功能,似乎“趣”有碍于功能表现。如此把趣与道对立或分割开来,把趣归入浅层次娱乐,这种观念,恰恰掩盖并障碍了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从上述图中可看出,趣味是艺术生命的表现形态,而功能是作品和艺术形象所产生的审美效应。如果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让理性挤压了形象的趣味形态,甚至无视于艺术的趣味表现,这样的形象创造势必因阉割了趣味形态而显得扁平或不健全。趣味形态,是艺术形象的生态性的凸显。只有尽力发掘和刻画作品形象的趣味形态,才能彰显形象的生命光彩与结实饱满的特质,才能引起艺术魅力效应与功能效应。
[JP2]趣,是一种生气和灵机,也是黑格尔所说“心灵中起灌注生气作用”B22。自古诗文之道有理、事、情、景四字,但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这是从使诗文增色的修辞层面上而言。从艺术形象创造的生命元素与生态元素方面考察,明代袁宏道的“真趣”论,值得重视。袁宏道继李贽之后,提出文学要“独抒性灵”。他说:“真人真作,故作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语,唯会心者知之”。B23趣,是人的天性、灵性的体现。只有“任性而发”,才能调动起性灵之趣,并使得之以美丽展示。李贽在提出“童心”说时,也有过“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B24之语。袁宏道将“趣”视为“童心”、“真心”、“真情”的标识,他对“趣”之妙处的欣赏和描述,是对高级的审美形态的肯定。他反对“寄意玄虚,脱迹尘纷以为远”的倾向,认为这种脱离世俗与人的神情的趣,只是“趣之皮毛”,由此强调“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推崇“童子”与“山林之人”之趣。“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目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这即是“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山林之人,无拘无缚,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袁宏道称道“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B25,是指童子之趣。袁宏道所论“趣”的核心价值,在于追寻了“趣”的发生的源头,从返归自然、返归人的本真方面,对“趣”作了深入论述:从趣的表现形态看,趣美出于自然,惟自然,才有深趣;从趣的形式的成因看,趣,依附着人的本性之真,只有发自人的天性、“性灵”之趣,自由绽放之趣,才会带着生命本色烂漫伸展。童子之趣,则是返依人之初的本真意义上的趣,具有纯粹的原生态的特征。从“童子”到“山林之人”,都是“虽不求趣而趣近之”。这即是说,趣,不是刻意可求,只要保持一颗童心,不背上思想文化的重负,就有“近趣”的可能。趣,就包孕于童心之中。人类并非要回到童年,也不可能回到童年,而是要在不停地去蔽中拥有和保持童心之真、之趣,这是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之所在。[JP]趣,有俗趣与雅趣之分。“雅趣”是指带有文化意义上的“趣”。文人视野中的野趣,可谓雅趣的变奏。古人所说“生趣”、“意趣”、“天趣”、“逸趣”、“情趣”、“形趣”、“真趣”、“机趣”等,各有审美价值取向。譬如,南宋“米家山水”的“墨戏”,是借线条流转与墨色浓淡来写意显趣,以墨趣表达意趣。法常的三联轴《观音·猿·鹤图》,尤其是猿,很有生趣。苏东坡题《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则是一派形趣与逸趣的场面。周邦彦词句“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是真趣,亦是天趣也。一方面,我们要摆脱文化重负,回到人的本真之源去找回真趣,另一方面,趣,又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文人的个性与修养。袁宏道所说“性灵”,大概是指人先天的灵性与后天的灵性的合一,而后天的灵性,就折射着人的质素和智性。他主张“淡”,意在淡中求真趣。他既称“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又说“唯淡也无不可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B26。趣,得之自然,任乎情性,表现为淡的不可造性;而付诸艺术形式,需要通过艺术创造赋予淡以质感,加大其表现力,“大都入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B27,这又表现为淡的可造性。米芾在评论北宋巨然的山水画的“平淡天真”时,称之为“老年平淡趣高”B28。如此“天真”之“淡”中见“大趣”、“高趣”,折射着画家的胸襟高远。又如元代以“逸品”著称的倪瓒作品,草草简淡之笔中逸趣横生,却是一种任乎情性、纵笔自如的高浑大趣之境。这都可以视为袁宏道所谓性灵之“淡”不可造与文中之“淡”无不可造的有力例证。趣,作为心灵本真的自由显影,是艺术形象创造中个性表现的基本内容之一。袁宏道说:“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B29明清小说在文字描写的口语化中,十分重视对人物个性刻画与讲故事过程中趣的氛围的渲染。尤其是清代言情小说,对人物的情性、情趣的发掘,成了心灵逼真的表现。譬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称大观园是“女孩子天真烂漫的混沌世界”,着力展示了少女们的丰富情趣和活泼快乐的天性。曹雪芹的好友明义有评诗云:“怡红院里斗娇娥,娣娣姨姨笑语和。天气不寒还不暖,曈昽日影入帘多。”B30这首诗最早透露《红楼梦》成书时所展现的青娥红粉争艳斗俏、情趣盎然的场面。小说中描写大观园女儿们斗俏取笑的形式,表现为雅谑。雅谑,也是谐谑,“更多的是愉快和机智的放肆”B31。这恰到好处地展现女孩子的天真烂漫和灵秀之气,而每位女子都有自身的方式,即使透过笑的细节,都能把每个人的个性区别得十分鲜明。曹雪芹对大观园少女们的天性灵趣的尊重和发掘,无疑增强了她们最后被毁灭的悲剧价值。即使表现同一个人的笑,也不尽相同。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婴宁》,全篇有26处写婴宁的笑,有遇面捻花含笑,有倚树孜孜憨笑,有初见微笑,有户外嗤嗤笑声,有客前忍笑,有叱叱咤咤,放纵大笑,还有与王生相见时,她且行且笑,边说边笑,乃至“笑极不能俯仰”。种种笑姿,发乎情性,出乎自然,是这位少女在不同场合里真实情态。小说中这样写道,她“善笑,[JP2]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显然是对婴宁纯真灿烂的笑的美的认同。笑,虽为形趣,却耐人品味。按照封建社会中“淑女”标准要求“笑不露齿”,而蒲松龄写婴宁无拘无束的笑,正是在远离世俗、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妇女的桎梏中而闪现心灵的光辉。当然,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性格各异,即使表现“有身如桎,有心如棘”,同样可以张扬自由和真趣,关键在作家、艺术家对人物的体验与认知。[JP] 至于由心灵的机智而产生的趣,包括袁宏道所说“谐谑”,包括运用借喻、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而产生的情趣、谐趣、机趣等,只要是人的本性与性灵的自由抒发,同样属于“任性而发”的“真趣”范畴。譬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红娘善于周旋、成人之美的倚门卖俏、调笑谑语,则是她心灵的智慧的表现。金圣叹称红娘“如从天心月窟雕缕出来”B32,这种“灵襟”、“慧口”,更藉助于她的灵性的发挥。与西方幽默、滑稽相比,红娘的调笑谑语,属于自然清纯的一类。幽默、滑稽,“摹仿偶然的事件以及情况、性格的荒谬可笑”B33,在更大程度上制造笑或喜剧的效果,但同样依赖于作家、艺术家的“真心”。幽默也产生趣味效果。西方人的幽默更多的借助于姿势与动作的夸张而造成这种效果。谐谑是滑稽的一种,在简单的谐谑中,却很少纯粹滑稽的东西,更多的是愉快和机智的放肆。“对谐谑来说,什么都是愚蠢的、可笑的,但是只有它自己不可笑也并不愚蠢。幽默却是自我嘲笑。”“幽默,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嘲笑,通过滑稽戏和谐谑而表现,一个人在幽默中允许自己打诨说笑,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可笑的,也想描摹自己的可笑之处:他的谐谑大部分都是挖苦揶揄,因为感到了侮辱……”B34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以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为例,认为他的装疯卖傻,说出打诨式的可笑又粗野的谐谑,是智者哲人对人类弱点与愚蠢的嘲弄,他的笑,是对自己以及对人们的同情的微笑。这一分析是深刻的,阐明在优秀作品的幽默和谐谑中,具有深刻的内涵或弦外之音。中国式的幽默,就像赵本山的农民的诙谐,大都是语言上的幽默,借助于汉语修辞效果,如谐音、双关语、反语等,用暗示的手法,在机智、含蓄、轻松的情境中造成一种逗人发笑的趣味。幽默情境可分为悬念、渲染、反转、突变四个环节。幽默可以同时借助一些道具,比如卓别林的拐棍和帽子。中国的喜剧片小品,更多的是借助夸张、反转、突变,造成一种幽默情境。趣味作为艺术生命形态的表现,离不开艺术形象创造的真、新、蕴而闪现光彩。如果说谐谑与幽默的生命在于真诚,分量或质量在于蕴含,那么,审美诱惑还在于新奇。任何一种趣的形式,都要求独创,失去新鲜与个性的东西,味同嚼蜡,就谈不上审美趣味。趣味,主要通过形象和情境表现出来,它是形象的生命形态的完备体现,是高级的感性形象的层面。如果这一层面表现薄弱,势必就会削弱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影响形象的艺术传导功能。因为功能层的作用,依赖于魅力效应,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审美诱惑自然产生的。 (责任编辑:徐智本)[HT]
① [ZK(#]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② 尼采《察拉图斯德拉》,转引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叔本华《意志及观念之世界》,转引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荷尔德林《论美与神性》,《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⑤ 李贽《童心说》,《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118页。
⑥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序》。
⑦ 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⑧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3页。
⑨ 刘鹗《老残游记·自序》。
⑩ 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日神和酒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和狄奥尼苏斯,都兼司艺术。
B11 尼采《偶像的黄昏》,《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9页。
B12 同⑩。
B13 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B14 同B11。
B15 同⑩。
B16 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李普曼编《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392页。
B17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页。
B18 转引《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99页。
B19 J.Derrida,Writing and Difference, Univ of Chicago Press,1978.p65.
B20 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历代文论选》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页。
B21 罗丹《罗丹艺术论》,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10页。
B2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页。
B23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小修诗》,《叙陈正甫会心集》。
B24 李贽《容与堂本〈水浒传〉回评》。
B25 同B23。
B26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三,《叙呙氏家绳集》,《行李园存稿引》。
B27 同B26。
B28 转引伍蠡甫《中国名画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B29 袁中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七,《听朱生说水浒传》。
B30 一粟《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B31 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中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B32 转引《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眉批。
B33 转引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赫斯列特《英国的喜剧作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B34 同B31,第93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