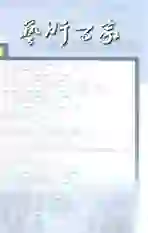时尚产业:符号生产与市场操控
2014-04-10王列生
王列生
摘 要:时尚生产是符号生产,时尚产业是以符号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链条。时尚符号的重要存在特征之一就是它所链接的是人的物性欲望或物的人性意象,而非超越物质的意义、价值或精神诉求。在文化产业的谱系内置中,时尚产业无论就其产业规模还是其高额回报,都处在产业形态的高端位置,时尚产业的从业规模、利润总量、产业链长度、制度完形状况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波及面,几乎都为文化产业其他类目所无可比拟。毫无疑问,这一激进文化形态对日常生活境遇而言乃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所能虑及尤其所应谋划的问题焦点在于,面对汹涌而至的时尚消费以及这一消费事态的全球化市场拓展,我们如何在中国问题背景和中国利益立场去全面审视时尚产业的事实、真相和驾驭姿态,并由此获得助推中国时尚产业的知识支撑,从而为那些“知其然”的产业操控者们提供“知其所以然”的背景参考方案。
关键词:文化;时尚产业;符号生产;艺术市场操控;知识支撑;意义;价值;精神诉求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在文化产业的谱系内置中,时尚产业无论就其产业规模还是其高额回报,都处在产业形态的高端位置,其情形往往为那些所谓“内容生产至上”或者说“内容为王”论者始料未及。巴黎抑或伦敦,甚至新兴经济体内的上海抑或加尔各答,时尚产业的从业规模、利润总量、产业链长度、制度完形状况乃至对整个社会生活的波及面,几乎都为文化产业其他类目所无可比拟。虽然美国时尚产业形势始终逊色于欧洲大陆,但我们依然能阅读到资料呈现的“作为一项产业,1900年的纽约非常可观,单是女性上衣生产就雇佣了18000工人。也就在那个时候,国际女装公会(ILGWU)成立,它是现行服装公会UNITE(Union of Needletrades,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的先驱,后者成立于1995年并与混纺制衣公会兼并”,①而其中披露的消息在于,至少在那个时代,其产业辉煌绝非娱乐业所能望其项背。类似事态如今已经跨越欧美的所谓时尚帝国边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高速崛起新兴经济体热拥中的现实,其中当然首先包括我们站在中国利益立场所观察到的激进中国时尚潮流。毫无疑问,这一激进文化形态对日常生活境遇而言乃是大势所趋,而我们所能虑及尤其所应谋划的问题焦点在于,面对汹涌而至的时尚消费以及这一消费事态的全球化市场拓展,我们如何在中国问题背景和中国利益立场去全面审视时尚产业的事实、真相和驾驭姿态,并由此获得助推中国时尚产业的知识支撑,从而为那些“知其然”的产业操控者们提供“知其所以然”的背景参考方案。
一 尽管时尚生产从孕育、发展到高潮经历过漫长的时间洗礼,但成熟的时尚产业直至19世纪下半叶才真正形成,这一方面是因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生产和扩散制度形成于那一时期并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巨大稳定性”,②另一方面则更因为“这一时期活跃于欧洲的服装企业迅速增加而且融合。欧洲市场可能已经形成,而这一进程显然已经寓示着欧洲消费市场的出现”。③庞大的中产阶级以其不可抗拒的巨大消费容量,不仅残酷地淹没小众贵族社会时尚生活的封闭、自恋、矫情和惶惶不可终日的身份特权感,而且也在激荡中冲洗出消费社会的大众日常生活价值秩序以及这一秩序支撑起来的开放性时尚潮流。与此相一致,则是时尚消费市场化和时尚生产产业化时代的历史转型,则是“棉纺和棉织在工厂中大规模的机械化和聚集化,诸如裁缝铺的建筑幸存,已然某些制衣和纺织家庭生产史的残留证据”。④历史的演绎姿态从来就在于,旧有的生存格局和生活方式被新的转型形态所取代,其中既包涵政治利益替代和经济利益替代,也包涵社会型制和文化风貌的替代,而时尚产业在那一时代节点的勃然兴起,不过是这一替代过程中的具体案例之一而已。随着资本属性拓殖与资本布控功能更加强大,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和市场对时尚生活空间的兴趣和覆盖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由此带来的时尚消费浪潮及其所卷起的高额剩余价值利益诱惑,直接推动着时尚产业的产业发展规模和产业链延伸长度以几何级数倍增方式迅速增长。这样的增长态势下,资本及其所开拓的市场,不仅将传统手工艺的时尚版图完全纳入其布控范围,而且还在大工业和新要素基础上打造其规模化巨量生产航母,由此形成传统与现代叠加的时尚工业体系,以及因承载这一体系而获得全球时尚辐射力及世界市场牵引力的所谓“时尚之都”,被时尚史家描述为“亦如巴黎是‘十九世纪的世界都市,纽约无疑是二十世纪的世界都市。在纽约,未来存在于现在,超越现实的未来被打造为具体、物质以及当下,这是一个自然结果并必然成为涤荡殆尽的世界,与此同时,人造风景开始仿形为自然的畸形”。⑤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可以在大工业背景下把握时尚产业的扩张版特征,那就是:以资本财团为中心的利益控制体系在时尚产业发达国家逐步形成,并通过合法化的“显在形态”与潜规则的“隐在形态”建构起自我循环的产业制度。无论罗兰·巴特形而上分析的诸如“如果我们意欲在其总体中捕获能指的结构,那么这是一种有效的差异,由此,就必然会一再涉及限制性问题,首先是在制度层面,然后是在syntagm层面”,⑥还是乡村由仁夜形而下叙事的诸如“时尚能被作为包含各种组织的一种制度来予以审视。这些组织共同再造着时尚形象,而且在重要的时尚城市中使时尚文化经久长存,譬如巴黎、纽约、伦敦以及米兰”,⑦无非都是指涉一个共同的对象事实,那就是时尚文化符号处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已经被纳入非自存性制度框架,也就意味着它不仅不是想象中的诗意符号自由,而且更是管制中的异化符号压迫。在这个“管制中的符号压迫”事态中,无论是时尚消费者身份的所谓“不仅仅谈论他的服饰,而且还谈论他的家居,家中的陈设与装潢,汽车及其它活动,根据这些东西有无品味,人们就可以对它们的主人予以解读或进行等级、类型的划分”,⑧还是时尚偶像身份的所谓“杰克·肯尼迪的现代雅致对时尚世界发生了长久影响”,⑨他们的命运都被制度功能的魔绳牢牢牵系,其不乏虚荣的出场及其符号狂欢与陶醉,其实都是制度场域成功实现的有效确证。一句话,时尚存在于时尚利益链的显性抑或隐性规制之中,时尚制度逐步成为时尚利益乃至时尚生活方式的强大保护伞。然而,当文化产业的大潮涌动到伯明翰学派崛起的20世纪后半叶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知识谱系绵延全球的21世纪之初,时尚产业作为其重要产业构成部分,事态本身又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变化,而且最重要的变化恰恰就在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命题的所谓“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⑩正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乃至消费全球化的提速过程中深刻地改变着既有的相对稳定的边际经济秩序,也就是超越于以边际垄断为经济场域前提的“对于现代市场社会,经济学和社会学接受了那些批判性的共同主张,每一种主张都裹挟着市场秩序和个体行为的理性”,B11代之而起的主流经济形态,就是全球化无孔不入所带来的“全球自由贸易的出现为开放的世界性市场奠定了基础”,B12继而也就必然出现跟进性的文化产业而且尤其时尚产业对于主流经济形态的存在性嵌位,当然也就迫使我们在全球生产和全球消费的视角重新审视时尚产业的内在逻辑与外在景观,至此,仍然停留在鲍德里亚“作为一种生产力体系的需要体系和消费体系”B13问题拟置水平来解读时尚产业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因为文化全球化表象层面的诸如“1990年代,亚洲时尚成为一种刮目相看的全球趋势,改变着亚洲内外的人们的看法与穿戴”,B14蕴藏着极为复杂同时也极为丰富的时尚产业事态真相。这种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以传统的“时尚之都”为核心标识的垄断性时尚生产格局及其对时尚消费被动性的资本布控,逐渐在时尚生产的全球性分工重组与时尚消费主动性对时尚产业命运的主宰中失去昨日辉煌,时尚与西方、时尚与贵族性以及时尚与符号霸权之间的必然逻辑及这些逻辑所支撑着的时尚帝国,B15在全球化、大众化、消费化、多元化甚至后现代化中轰然坍塌,更加广泛同时也更加充满竞争活力的时尚消费者、时尚生产企业和时尚产业分工共同建构其崭新的民主时尚世界。时尚文化的全球激变与时尚产业全球格局重新定位,经历了一系列博弈与一系列新的利益主体崛起争雄的壮烈故事,最具有讨论意义的,当推70年代以后传为奇迹的“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世纪以来雄风正盛的“金砖五国”(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其时尚产业的拓殖速度、影响深度与波及广度,已经足以改变全球时尚产业的生产布局与时尚份额配置比,从而也就决定了当代时尚史乃至未来时尚史必须改变其书写方式与叙事路线。就时尚产业全球转型升级而言,关键还不在于事实局面的诸如“在缺乏复杂精密的全球体系的情况下,这种变化不可能出现——受控于东西商业中心的体系——以确保式样美观并且数量可观的时尚商品按时抵达零售连销店,而且往往是恰好发生在格局布控好之后六个星期”,B16而更在于真相层面所深层隐匿着的那种“问题在于,市场进程既很少刻板均衡地生产,亦很少有效资源分配地生产”,B17以及那种民族文化意识形态抵抗的诸如“西方的支配性,如同其政治一样侵略性地显示其文化实力,尤其是殖民地区,被陈腐的异国观贴上标签,视其为‘它者。因其如此,它者也就从未充分同化于支配性文化”,B18内在地制约着对时尚现场的单边主义征服,进而也就客观形成推进全球时尚新格局和世界市场多极化竞争的持续动力,时尚产业由此全面进入弱势传统与多元崛起互动共存的时代。正是由于时尚产业全面进入互动共存时代,才会不仅给后起时尚产业国家、时尚产业城市或者时尚产业企业留有产业准入的良好时机,而且也迫使强势时尚产业国家、强势时尚产业城市或者强势时尚产业企业在挑战面前重新规划其竞争发展战略。就前者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是“2004年,百事可乐在一次区域广告竞赛的多边市场中,推出了九位香港和台湾的流行明星,就在同一时间里,hallyu,或者说韩潮,集结了一批新的亚洲——韩国孪生名流。亚洲主要报纸和杂志的娱乐版面充斥着流行明星小故事和形象,引来远近邻居的流行风暴式参观”;B19就后者而言,我们所看到的则是“希尔曼公司(The Hillmans)于1986年关掉了他们两个商店,转而仅仅专注于生产Ritva Kariniemi牌外套,其贴牌超过了23个国家的300多家商店,自1987年起每年的资金流转量都会翻番,其中对外销售达到60%,该公司由此于1991年因出口而获得女王奖励”。B20只要涉身者不为诸如thereotical exoticism等类似狭隘情绪的困扰,就不难发现,多极化全球时尚利益格局是一个多赢的产业升级国际化平台,它在时尚市场大规模拓展的同时,也给先行与后起时尚产业各方带来资金流通效应、技术升级效应、平台聚集效应、人才竞争效应、消费激活效应以及利润漫溢效应等。
二
时尚生产是符号生产,时尚产业是以符号生产为核心的产业领域和产业链条。问题在于,时尚符号区别于一般意义符号的诸如“符号象征着特定观念生成或修饰的某种内容”,B21也就是说,与一般符号作为去物化意义指涉或意义象征所不同,时尚符号的重要存在特征之一就是其去意义指涉的物性呈现方式,它所链接的是人的物性欲望或物的人性意象,而非超越物质的意义、价值或精神诉求,抑或完全与人隔绝开来的物自体,所以鲍德里亚将其描述为“美丽的逻辑,同样也是时尚的逻辑,可以被界定为身体的一切具体价值、(能量的、动作的、性的)‘实用价值向唯一一种功用性‘交换价值的蜕变,它通过抽象化将光荣的、完善的身体的观念、欲望和享乐的观念概括为它一个——且由此而当然地否定并忘却它的现实直到在符号交换中耗竭。因为美丽仅仅是交换着的符号的一种材料,它作为价值/符号运作着”。B22沿着这个思路去认识和把握时尚符号生产,就必须从一开始既自觉规避单一物恋主义理解向度的“对物的占有和操控欲望导致对人的欲望化占有与操控……例如,‘纪实电视(Reality TV)文化就将其影响和巨大利益建立在人的商品化之上”,B23亦自觉规避完全意义价值观理解向度的“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别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因此,时尚只不过是我们众多寻求将社会一致化倾向与个性差异化意欲相结合的生命形式中的显著的例子而已”。B24穿越现象的存在坚甲,进入时尚符号生产的事态真相,我们就不难发现,即使在文化产业的框架里,时尚符号生产也就是一种大大相异于诸如电影生产、电视生产、工艺品生产、美术商品生产及音乐唱片生产、旅游纪念品生产等的生产类型,它与其他类型既有叠合生产属性亦有非叠合生产属性,其最大差异性特征就在于,时尚符号生产乃是一种融物质塑型、审美想象、欲望诱引、市场逐利等诸种目的性为一体的复合型行为过程,因而作为产品形态的时尚符号也就同时呈现为非意义的物质结构、直接意义的审美结构以及间接意义的价值结构,而这种物质结构、审美结构与价值结构涵存事态的时尚符号本体(甚至可以表述为载体与本体的直接同一),不仅为时尚涉身者增加了诸多现场判断的幻觉甚至误判,而且也给时尚产业生产主体增加了更多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市场销售等关键环节的操作性障碍。就现场判断幻觉甚至误判而论,之所以会出现诸如“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在他们抨击资本主义以及他们的可能性选择想象中,给予着装也许完全不可思议的重要地位”,B25或者所谓“仅在民主时代能感受到完美的时尚,唯此存在着共识以及强大、广泛和可持续的对现代意识形态基本价值的牵系:平等、自由和人权”,B26就因为他们总是把本体构成的某种结构,无条件地提升至对于本体存在属性、本体存在状态或本体存在价值的一般性讨论,从而也就必然产生局部放大或盲人摸象的片面性且极端化叙事后果。就关键环节的操作性障碍而论,由于创意论者过分强调时尚的意义指涉及其在大众文化场域中的观念冲撞效果,尤其因此而漠视时尚符号的物性须臾不可分割及其在身体生产时代时尚符号功能的全面欲望呈现,导致文化产业浪潮被动卷入者容易将时尚产业冲动性地悖离于社会和市场经济,悖离于产业经济学描述得已经十分成熟的基本规律与基本要素,悖离于诸如边际效应测算、成本价格换算、市场风险分析以及产业链接口功能保障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产业运行常规技术工具,浪漫主义地驰骋其思于人文抒情意味的诸如“如果创意产业的技术停留在创意产业内部,其影响力将被限制和减少,伦敦变得毫无竞争性。如果运用其创意内容及其创意管理,贯穿于整个经济,让整个社会从中受益,那么领导者的殊荣将在本世纪来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就是挑战”。B27因此,在粗线条地了解时尚符号的存在复杂性与生产歧义性之后,就能较为理性客观地看待时尚产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命运,即一方面它是具有高附加值且大规模市场拓展的产业领域,另一方面在这一产业领域中时时伴随着非预期性的高风险与市场危机。这意味着每一种产品都将有可能巨额获利于技术细节变化新异效果的诸如“‘奇异态概念能在两方面适用,或则涉及到外国时尚式样或罕见时尚式样。在规范的社会活动中时尚奇异式样的具体体现(跨越所有文化),乃是产生‘颤慄的一种有效方式(激动得发抖或轻微触动),因为时尚制度建立在奇异符号与熟悉符号的关联与紧张关系中,而奇异外观作为展示技术总是更加有效”。B28同时也意味着每一次生产过程都将充分考虑在全球竞争中利用价格优势以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标杆,如所谓“有关这一产业里存在价格/生产形成标准的论断,获得了时装生产公开告知价格的支撑。人们甚至可以在生产者为了推广宣传而做公司简介里,随时能看到这样的价格,以下即来自印度公司的简介:‘男式半袖短衫,一只扁平口袋,百分之百棉织品(92×98),染制需2.8美金,印制需3.1美金。此处所看重的,既非时尚亦非衬衫的‘外观,而是生产方法及其布料品质。显然,其所期待的,就是时尚投入来自买家”。B29甚至还意味着每一家时尚公司(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广告商)或时尚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参与者(投资人、设计师、模特、记者等),都有机会走向他们超级预期的那种“里奇·马拉摩提(Luigi Maramotti),极为成功的马克斯·麦瑞时尚集团(Max Mara)的主席。马拉摩提来自一个可以上溯至1850年的制衣家庭,如今他的企业拥有6亿英镑的年营业额,且在世界各地拥有超过一千家店铺”。B30而在案例叙事的反面,同时也就意味着遭遇风险的诸如投资失败、设计失败、经营失败、生产失败、销售失败甚至细节性的某次T台展演失败。每一种失败较之其他纯物质制造的产业领域而言,都不仅存在着更多导致失败后果的原因非确定性,而且存在着更加致命的产业生存摧毁性。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时尚产业所从事的时尚符号生产,是所有涉事和参与环节的集体生产成果,时尚学将其陈述为“服装生产涉及物质服装的实际制造过程,换句话说,时尚生产涉及所有帮助建构时尚观念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则将时尚处置为一种集合产品乃是一项广泛参与的任务,涉及到文化生产的方方面面而非具体产品的即时制造过程居主导地位”,B31即是强调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或失败都会给时尚生产以及时尚符号产品带来无可估量的负面后果。集合性虚拟本体及其所呈现出的现象事态非确定性,使得所有参与要素都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位置,并且其复杂的博弈后果直接决定着某一要素方是否能获取超级预期的高附加值利益分成,否则就将不得不承受高风险所带来的失败苦果或严重利润亏损后果。譬如,价格/成本形成机制及其利润份额分配比例,几乎贯穿于时尚符号生产的全过程和所有要素方面,因而经典经济学的约定分析方式就会始终盯紧供需关系结构变化,盯紧价格弹性的所谓“在发生重大变动的场合,我们从较大的产量和较高的价格进行计算。用P表示价格,Q表示购买数量,我们看到,弹性是[SX(]ΔQ/P[]ΔP/P[SX)]这个比率的倒数测度在既定需求条件下价格对供给数量的反应”。B32但微观经济学家所归纳的这样一种比例曲线变化关系,甚至他们面对宏观市场计算收益时所使用的通用型手术刀“需求的价格弹性”与“供给的价格弹性”,B33在时尚生产、时尚消费和时尚经济场域中往往出现功能失灵,不仅不能有效地计算基于供给结构关系的价格和收益,而且也不能有效地指导基于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市场预期和产业调控,甚至当人们对时尚市场进行探索性数据分析时,不仅这些数据所指涉的经济事实其所指真实性疑问多多(例如时尚消费不景气就不一定代表经济不景气或者消费马车的拉动力不足),而且有限的基本数据究竟能获取多少以及如何给予随机抽样都困难重重(例如短裤在单位时间里究竟如何在日常消费状况中统计其可分离性时尚消费量),1947年前后潮起潮落的迪奥新装事态就曾经让研究时尚市场的专家沦于难置一词的窘境。B34当事态延展至全球化与后现代性高度叠加的今天,出现解读窘境的几率以几何级数增长,时尚产业所蕴藏的高风险危机,对每一个产业环节和要素方都是必须时时予以警惕的残酷挑战,时尚社会学家在举证各种风险义项时,甚至还不放过极为细微事态的所谓“问题之一在于,市场双方的行为人常常生活于不同的世界,对时尚持有差异性见解,所以此时当地的雇员就成为中介人。而其后果之一则是变得讨论的规范化话题愈来愈少而交往困难却越来越多。时尚,如同其他审美话题一样,难以用抽象概念来讨论,更多地要求对图像进行解释。在这一案例中,问题被进一步加剧,因为对许多参与者而言,英语并非他们的母语,但商务用语却恰好是英语,当然,这显然是英国的服装连锁店,但情况同样真实地存在于瑞典的服装连锁店”。B35至此,则给所有时尚产业研究者及实践者的告诫就在于,千万别心潮激荡地一味亢奋于时尚产业的高附加值,随时都要拉紧高风险这根绳。
三 要想在新的时尚世纪将时尚产业做大做强,B36尤其要想在做大做强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提升高附加值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减少高风险所带来的种种危机,至少就中国问题背景或中国知识立场而言,切要处必须完成三大产业条件配置,或者说为中国时尚产业发展满足最基本的配置功能产业制度条件,那就是:(A)产业制度运行的风险资本配置功能,(B)产业制度运行的资源聚集配置功能,(C)产业制度运行的市场激活配置功能。不是说这样的配置就足以实现功能谱系完形,而是说它们承担着产业大厦崛起的基本支撑任务。之所以强调风险资本配置功能,一个简单的文化背景事实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视时尚为奢侈别名或者曾经彻底将其纳入意识形态声讨对象的国度而言,B37尽管时尚文化价值转向已经呈现生机渐露的新世纪景观,即时尚意识、时尚生活方式、风靡大都市的各种时装展以及电视节目对世界时尚潮流的实时传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化正能量价值判断的精彩生活内容,但离建构起普世价值支撑的现代时尚制度及其这一制度所支撑的全方位时尚生活现场,无疑还有较为遥远的距离。时尚逆反心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必然会形成时尚制度建构的障碍力量,必然会使一部分人及其所携带的雄厚资本对时尚产业望而却步,这足以构成资本进入时尚产业的文化阻抗风险。B38进一步就在于,一旦缺失身份合法化、秩序规范化、政策工具功能化乃至产业边际清晰化,实际上也就堵住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等不同资本进入时尚产业的入口,这不仅因为它们自身进入时尚产业领域其实就是一次风险资本身份转换的投资涉险过程,而且还在于它们进入时尚产业领域的效益命运,要么取决于其信贷是否能“抓住最小可控风险之上的较大安全缓冲”,B39要么取决于其投资是否能“保证参加竞争的障碍不会大于刚好抵消风险和投资费用的必要程度”,B40从而也就要求决策者从一开始就必须自觉意识到,一切资本形态在进入时尚产业之际都必然是基于风险评估的条件性进入而非无条件性进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激情冲动下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绩而将这种进入行政指令地处置为非条件性资本事态,将一定会因资本风险的随机性爆发而自食其果。更进一步则还在于,时尚产业具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重国籍存在特性,因而其资本进入就既不能单纯按照虚拟经济投资运作亦不能单纯按照实体经济投资运作,需要基于时尚制度和时尚产业运行规则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复合投资技术方案,而不是在这些方案取得有效支撑之前,权力意志或者欲望意志地一头扎进某一拟置性时尚产业项目,甚至所谓创意区域意义的时尚产业园区,盲目再造其所在区位那种“时尚创意经济”或者“时尚文化产业”大词乌托邦,而这样的大词乌托邦往往是悖离产业经济学最朴素规律的文人修辞产物。由于它是虚拟经济,投资主体在产业规划和投资取向过程中,必须最大限度地寻找创意潜力、观念生产力和时尚文化的背景知识储备条件,将切入点精确定位到诸如“创意产业和文化经济的投资,既有其基本规律亦有其分析目标……创意产业投资根据不同的市场形态”。B41由于它同时又是实体经济,从而使得其投资取向及其产业运作模式大大相悖于诸如文化产业中的电影产业、音乐产业或者演艺产业等,直接导致资本进程回归到产业经济的常态而非变异性的虚拟态,并且会因切实的回归而让时尚产业投资主体甚至会在古典经济学的知识谱系内,密切关注诸如“不混同利息率与资本对于产业的全部利益。利息率定于资本最后加量的利益;以前各加量的利益几乎可以较大至任何比例”,B42或者所谓“垄断者贪心的唯一限度是购买者提高价格的意愿和能力”,B43当然更会斤斤计较于现代经济学知识视野的诸如“经济自信源于所有的投入诉求能被其产出所确证:Ax
四 如果以上所述的认识目标和实践道路都成为时尚产业未来中国发展中的已然条件,是否就意味着中国时尚产业一定腾飞无疑呢?未必。虽然时尚产业通常被归类至创意产业,虽然创意产业据说即将进入人类生产力空前解放的所谓“创意经济时代”,或者说人类将很快面临一个人类主体性绝对主宰“社会—自然”博弈关系的所谓“创意社会”,虽然他们梦想般诉说着诸如“其实创意经济时代需要的只是一种世界观的改变。创意力不像是矿产一样可以触摸,也不可囤积或掠夺,甚至无法买卖。我们必须开始意识到创新能力是一种公共产品,像自由或安全”,B56或者“创意产业概念——与创新、驾驭风险、新商务与新起点、无形资产以及新技术的创意性应用等联系在一起——已经发展出很宽泛的新起源”,B57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除了我们要在观念上充分认识创意的时代特征和重要选择向度外,还必须将时尚产业的生存与发展嵌位于现场事态,并在总结线性轨迹经验与教训基础上,切实谋划其与全球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与有效处置方案,至少应充分明晰设计有效处置方案的关键点或切要处,否则就会在关于创意的高谈阔论语境中不经意间失去时尚市场份额和时尚产业竞争力。最重要的关键点或切要处,在于如何面对全球化提速的世界市场格局主动谋划本国时尚产业恰配性国际分工,并于全球竞争平台逐步扩大后发时尚产业国家的时尚消费市场份额。逼近这一目标,要求时尚产业行动方案规划实施进程中必须清醒地意识到:1.行动方案规划实施过程应始终充满全球市场整体意识。2.行动方案规划实施过程应努力做到时尚产业制度与国际接轨并由此获得时尚产业制度运行的域外延伸与全球张力。3.行动方案规划实施过程必将是一个应对激烈竞争并逐步在竞争中取得话语权和产业优势的长期过程。毫无疑问,没有全球市场整体意识的时尚符号生产,不管其产品多么吻合生产者自身的目的性诉求,或者在地缘文化边际内多么吻合麦尔考姆·巴纳德(Malcolm Barnard)时尚交往功能定位,亦即所谓“按照符号学模式,无论服装设计师、着装者还是观众,都不是以意愿提供意义的唯一来源,而是这些角色之间协商谈判的结果,……带着他们自身的文化体验与文化期待,承载于意义生产与交往的服装中。意义得以提炼,尔后,则通过交流过程,相对权威形态得以建构”,B58都无法实现现代时尚产业在大工业背景和大数据时代的规模化绩效目标。这中间隐存着两个条件限制:其一是如果符号生产及其时尚产品的意义指涉不能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和认同,那么符号意义的可接受性及符号产品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可通约性,就会在作茧自缚中形成孤岛文化效应,而这显然悖离于天下大势和文化全球化潮流及其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亦即悖离于“理解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方法依赖于对认同空间变动着的构成成分和它们的相伴随的策略的理解……认同构造正是全球体系的历史性的动力部分”;B59其二是时尚产品销售既受制于国内市场亦受制于国际市场,而且WTO全球贸易规则使得国内时尚市场同样受到全球时尚产业的布控和倾销,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时尚产业实际上只存在全球时尚市场一个竞争平台。处在这个平台的时尚产品,一方面要面对存在转型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充分实现其产业化。文化及其产业(或者说创意产业),也就从事物象征的逻辑转移到事物本身的逻辑”B60,另一方面更要面对受到“事物本身的逻辑”所控制着的“根据麦迪逊(Maddison)的统计,在相当长时期,世界(所有产品总和)出口额的增长率几乎平均比‘世界国民生产总值高出一倍。这种贸易增长高于世界生产的情况不仅出现于1820年至1913年期间(只统计了工业化大国),也出现于1950年至今”。B61也就是说,世界市场已经成为一切现代产业不可逃离的宿命,世界文化市场顺理成章地演绎为一切文化产业的基本存在条件,于是时尚产业的发展也就只有到世界时尚市场竞争格局中拼搏这唯一的“华山一条道”。总体而言,虽然在全球时尚消费和世界时尚市场份额占有的竞争格局中,的确能像帕明德·巴库(Parminder Bhachu)那样,不无欣喜地发现一些亚洲时尚经营者或时尚设计师成功于欧洲时尚市场,发现“他们正在繁育新的时尚地理,以及新的颠覆主流国家流行的风格,这是一个对欧洲时尚风景重新设计的过程”,B62但在绝对优势情况下,都是先发时尚产业强势国家、强势企业、强势品牌以其铺天盖地的强势时尚产品,淹没后发时尚产业弱势国家的时尚消费和时尚市场,至少就当代中国时尚生活境遇而言,广为称道并且众所乐购的大多是欧美时尚思潮汹涌而至的品牌如路易斯·威登(Louis Vuitton)、克里斯丁·迪奥(Christian Dior)、可可·香奈儿(Coco Channel),如潮流High-Tech Fashion、Hip-Hop Fashion、 Italian Futurist Fashion等。因此,后发时尚产业弱势国家必须从产业方案规划实施之初,就在全球市场整体意识作用下寻找产业机遇,使所有技术路线实施细节都能与全球时尚市场动态保持有效链接,最终在较长时期的学习和跟进之后获得具有创新竞争力的超越。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大词宣言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B63毫无疑问,没有时尚产业制度的国际接轨,以及接轨后制度运行的域外延伸与全球张力,无论我们有多么高调的诸如“打造时尚产业航母”的走出去口号,无论我们有多少种时尚品牌战略及其占领国际时尚消费市场的技术方案,其结果将一定与良好动机背道而驰。这一判断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现代时尚产业在先发时尚产业强国之所以能持续性地高速推进,甚至在推进过程中令人意象不到地成为躲过诸多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乃至军事占领等天灾人祸的特殊产业门类,就在于坚实稳固且运行规范的时尚产业制度起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就在于大多数时尚学家都精确地把握到的“时尚学首先聚焦的,就在于它是制度化的时尚体系。要想将时尚作为制度来分析,我们必须寻求其体制特征,其所卷入的各种类型劳动者,每一个人都完成其自己的任务。时尚是一个制度、组织、群体、各种生产者、不同事物及其广泛实践的系统,所有这一切都对时尚生产作出贡献,而这是与服装或穿戴相区别的,其体制的结构特性确保着设计师创意行为的合法进程”。B64虽然现代时尚产业制度一般认为是19世纪中后期最早成熟于法国巴黎,但是经过“时尚世纪”(a fashion century)的延伸过程,这一刻度已经覆盖并且实际支配着主要时尚符号生产大国,甚至其制度末梢在被动性时尚消费国家也已经有零散性的神经单元,不断地递进着主体制度框架的各种生产信息和市场执行指令,就仿佛“到20世纪末,印度尼西亚北萨摩垂的巴塔克(Batak)文化中,已经有个别设计师承包商,试图销售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用本地原材料制成的西方流行时尚”,B65或者在北京出版其发行量超过欧洲大陆的中国版巴黎时尚杂志(据说中国版的《Vogue》每期销售量都在百万册以上)。全球时尚生产、全球时尚市场和全球时尚消费潮流,如今就在这一成熟的非政府组织和行业性自稳结构的时尚产业制度操控之下,而且其显在制度框架和隐在制度维系总是功能叠合性地发挥出强有力的支配力量。如果细究其框架和维系,就不能发现:它既包含诸如产权保障体制、资产评估体制、原料配给体制、价格商谈体制、标准核裁体制、生产分工体制、市场准入体制、消费监管体制、跨国贸易体制、零售扩张体制以及利润分配体制;亦包括诸如偶像塑造机制、观念扩散机制、品牌烘托机制、风格推介机制、设计创新机制、社会诱导机制、符号阐释机制以及潮流漫溢机制。这些体制机制有些由官方主导,有些则由行业主导,或者体现为“显规则”的契约形态和合法化权威文本形式,或者体现为“潜规则”的行业惯例和由行业制约所产生后果的个体自律。总之,诸如此类的制度框架功能,支撑、保障和维护着时尚产业全球时尚市场运行的公平性、效率性、开放性、竞争性、稳定性、创新性和可持续性。它在残酷地让企业破产、投资失败、品牌淹没甚至偶像沉沦的同时,更多地创造着神话般的诸如“现代时尚的黄金时代,曾使得巴黎人的高级时装业成为产业中心:新奇事物生产与小规模制衣所模仿的焦点”,B66甚至更广泛同时也更具体地支配着产业后果形态的诸如“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产业一直按照家庭轨迹发展,那些沿着下河东区苹果街(Drchard)和桑葚街(Mulberry)经营那些小工厂的贫困外国移民的后裔,后来开始在第七大街建立较大的公司”。B67一切都是时尚制度的显形后果抑或隐形后果,因而所有后发时尚产业国家要想建立起民族时尚产业体系,就必须与既有的先行体制状态接轨,融入到体制运行的进程中。在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 阿里克斯·格雷斯(Alix Grès)以及玛德琳·薇欧奈(Madeleine Vionnet)成为全球拥戴的名流时,美国作为后发时尚产业国家,即使小有名气的诸如阿德里安(Adrian)、巴尼·卡西(Bannie Cashin)、克莱尔·麦克卡戴尔(Claire McCardell)都无可同日而语,更何谈无数默默无闻的生产商、经营商、零售商和设计师,于是他们只得从制度复制、尤其是时尚展示制度和时尚生产制度的复制开始,而且还屈受参加模本时小心翼翼地给法国人付费的压抑,以确保更加真切地了解时尚制度运行的全部真相和各种原委,并且最终成就了当代强大的时尚美国或者作为新的时尚之都的纽约。中国时尚产业的真实窘况大约相当于80年前的美国,时尚制度复制实际上也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如模特选拔培训体制基本成型、季节性时装展对异域目光已经有所吸引),但困难恰恰在跟进性的第二步,就是如何使本国的时尚产业制度尽快完成功能框架塑形,然后能够在世界时尚产业平台和全球时尚市场空间延伸出这一功能框架的域外张力。B68例如如何使中国时尚创造依托富有支撑力的跨境营销体制,到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巴黎、伦敦、纽约、米兰和阿姆斯特丹去开拓其零售布局,时尚社会学知识谱系将这一时尚体制进化过程,表述为生产市场和投资市场为时尚零售商闯牌子,也就是一方面要解决“中国时尚制造”在国际时尚产业格局中面临的问题,如“由于工厂拥有设备类型和所有工人的技术状况、生产商总喜欢生产专业化,而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两个进行相同供货的竞争者将订购种类相近产品的可能性”,B69另一方面则要解决“中国时尚制造”在全球时尚市场营销中时尚储备的跨境贸易问题,如“贸易按照价格机制的基点来进行,当然其中的价格竞争是具体的。这种自动机制或许部分由计算机程序来控制完成,意味着你可以买入储备和将时尚储备卖出,但是你并不能直接影响这些交易……技术制度建构起来以后,使得市场操控可以按照理论方案进行”。B70总之,无论是独资、合资或者贴牌加工,无论零售经营、连锁经营还是跨境贸易,无论中国时尚消费市场的国际化份额垄断、国际时尚消费市场的中国时尚产品竞争缺席以及中国时尚符号生产与销售的弱势出场,都要求正在努力建构中的中国时尚产业制度,必须迅速实现支撑力接轨基础上的全球张力,否则就无所谓时尚产业“走出去”,更坏的结果只怕是“站起来”B71都成问题。毫无疑问,竞争只会随着时尚市场开放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激烈,而在竞争性和合作中时尚产业弱势国家想要获得公平产业竞争地位,就必须逐步取得时尚话语权以及受其制约的时尚产业分工中的某些优先权。时尚话语权虽然包含在时尚生活现场和时尚产业结构的方方面面,但主要的义项编序还是突出地显形为:1.时尚观念话语权,2.时尚产品价格话语权,3.时尚符号阐释话语权。就时尚观念话语权而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情景在于,一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并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每年在境内外市场直接时尚消费多达数千亿美金之多,而且其消费行为往往被诱惑于诸如法国的时装和香水、意大利的皮鞋及其他皮革制品、瑞士的钟表、美国的娱乐大片和商业体育流行文化、希腊人的休闲方式以及伦敦名目繁多的创意设计等等。这种诱惑后果,B72不仅表现为超过十亿计的庞大人群,于日常生活境遇中直接抑或间接、显在抑或隐在地将自己的身体管理、身体装饰和身体符号具身化,委身于拥有时尚观念话语权的他国、他地、他人或者总称性的“他者”,并由他者决定自我的“身体叙事命运”而进入未知性情境真相,即所谓“西方的时尚设计师定期进行新流行风格公告,其中一部分得以流行。通过努力影响时尚编辑,设计师们大量扩张其新形式的社会公示,并在时尚杂志和时尚报纸中获得广泛播撒,以致力于劝说那些旧时装的消费者群体去买新的样式。与此同时,时尚产业期待那些有决定性影响能力者,将设计时尚转换为街头时尚”,B73而且在“委身”之际还常常购买到以本土文化资源为时尚生产原料的“时尚替身”,也就是“哑巴吃黄连”地集体体验“时尚制度从‘他者形象和时尚中掠夺‘外来的技术和符码”,B74因为这些技术和符码很可能就恰恰来自中国。因此,只有当我们从诱惑对象“转身”为诱惑主体,我们才有可能获取时尚观念话语权,以符号生产的想象力优势驰骋时尚潮头,才能确保中国时尚产业的竞争先机。就时尚产品价格话语权而言,由于时尚产品价格从某种意义上主要由“议价”(talking price)来确定,而非完全根据价格成本要素和价格成本原则进行法律严格监管下的计量换算,就仿佛一件小尺码的高端时尚“比基尼”,其万元美金单价的价格神话,无论如何也无法镶嵌进“费施理想价格指数”(Fisher ideal price index)测值路线的B75“丛林法则”甚至“海盗法则”很大程度上仍然左右着时尚产品定价权,贴牌生产方式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贴牌者拥有点石成金的任意议价操控权。后发时尚产业国家如果最终不能参与国际时尚市场的价格博弈,就一定会因时尚产品价格话语权的丧失而阻碍其时尚产业发展。较之时尚观念话语权获取的复杂社会文化构成要素,中国时尚产业在争取产品价格话语权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条件优势: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为以人口红利带动的无限市场潜力,决定了我们可以在内需增长基础上建立中国时尚制造与先发时尚产业国家之间的价格谈判主导机制,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为以经济高速增长红利带动的巨大时尚购买力,决定了我们可以站在买方市场的有利位置,寻求包括中国时尚产品合理价格定位的国际时尚市场产品价格话语权。很显然,只要我们将这两大红利有效转换为中国时尚产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先决优势条件,则拥有时尚产品价格话语权当指日可待。就时尚符号阐释话语权而言,必须首先明白的一个直观道理就是,时尚符号阐释(包括广告、媒介宣传、潮流激活、形象展示以及专家深度剖析等等在内的广义阐释)是时尚扩散的前提,时尚扩散是时尚市场在被诱惑中时尚需求欲望漫溢的前提,时尚需求欲望漫溢则是拉动时尚产业生产力高度解放的前提,这是时尚产品供需关系逻辑结构大异于其他产品供需关系逻辑结构之所在,供方在最大限度地诱惑出需方时,也最大限度地建构起驱动自身的强大消费力量和虔诚拉车的“骆驼祥子”社会群体。B76由这个逻辑关系出发,中国时尚产业要想获得促进其全球扩散效果的时尚符号阐释话语权,将不得不尽快拥有权威时尚杂志如《女士杂志》(Ladys Magazine)、《艺术、文学、商业、时尚及政治宝典》(Repository of the Arts, Literature, Commerce, Fashion and Politics)、《巴黎时装精选月刊》(Monthly Selection of Parisian Costume)、《英国妇女家庭杂志》(The Englishwomans Domestic Magazine)、《服装与时尚杂志》(Journal of Dress and Fashion)、《先生》(Esquire)、《时尚》(Vogue)、《妇女着装日报》(Women Wear Daily)直到《i-D》等,将不得不尽快拥有权威时尚编辑如E.W.契丝(Edna Wodma Chase,曾担任《时尚》(Vogue)的主编)、南茜·怀特(Nancy White,曾担任《卖场》(Bazaar)的主编)、凯瑞·登万(Carrie Donovan,曾担任《纽约时代》(New York Times)的时尚编辑)、埃尔萨·柯伦斯切(Elsa Klensch,曾策划并大获成功地主持CNN的《流行》(Style)和《绝对时尚前沿》(Full Fronted Fashion)等,)将不得不尽快拥有具备影响甚至统治国际T形台的超级名模如娜米·坎贝尔(Naomi Cambell,一位当代黑人名模)、简·施瑞普顿(Jean Shrimpton)或者特威吉(Twiggy,20世纪60年代英国最红的女模特,以身材极瘦和爱穿迷你裙而名噪世界),将不得不尽快拥有富有吸引力的时尚博物馆如时尚与纺织品博物馆(the Musée de la Mode et du Costume & the Musée de la Mode et du Textile)、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The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英国时装画廊(the Gallery of English costume)、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装学院(the Costume Institute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时尚工艺学院博物馆(The Museum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京都时装学院(The Kyoto Costume Institute)等,将不得不尽快拥有基于专业博物馆和其他展示空间并具有极大冲击波的时尚展览如“时尚与超现实主义”(Fashion and Surrealism, 1987)、“胸衣:让身体更时髦”(The Corset: Fashioning the Body,2000)、“蛇蝎美人:世纪末法国的时尚与视觉文化”(Femme Fatale: Fashion and Visual Culture in Fin-de-Siècle France, 2002)、“伦敦时尚”(London Fashion,2001)等,甚至将不得不尽快拥有时尚研究专家如齐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麦尔考姆·巴纳德(Malcolm Barnard,)、吉尔斯·李普维特斯基(Gills Lipovetsky,1944-)、维拉瑞亚·斯提尔(Valerie Steels,)、狄雅娜·科瑞妮(Diana Grane,1933-)等,总之,包括如上述及在内的各种涉及时尚符号阐释的社会要素,都是时尚文化的符号指涉甚至时尚生活在场状态的参与者和创建者,当然也就必然成为作为时尚符号生产的时尚产业的引领力量和驱动力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后发时尚产业国家来说,能否有效整合这些力量,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和何种规模完成这一整合,将极有可能成为产业成败的重要判断标志。endprint
五 在文本的叙事进程中,之所以直到讨论话语权问题仍然避开时尚设计师在时尚产业中的要素地位,不但不是有意疏淡,而且更在于用心良苦地意欲凸显,从而在专门讨论中将其置于产业运行的核心驱动力要素以及产业制度存在的非稳定性结构要素,而且在于这两大要素身份,既功能性地链接时尚产业的符号生产,亦功能性地链接时尚市场的符号消费。如果将这一议题嵌入政治经济学知识谱系,就不难发现,时尚设计师身份本身可以多向度地指涉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将其嵌位产业经济学知识谱系,则它既关乎成本价格,亦关乎生产效率,至于将其嵌位于微观经济学知识谱系,它又可以身兼二职地成为供需关系结构中生产拉动力量与消费拉动力量,并在双向推动中产生时尚市场核聚变。简而言之,没有时尚设计师面对生活进行时所产生的创意灵感与诱惑能力,则激荡变化的时尚思潮以及物化形态的全部时尚市场利益谋划行动,将彻底不复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时尚学家敏锐地注意到了时尚史对时尚设计师价值判断的非公平性,即所谓“没有作者讨论设计师或者说时尚创意者在时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时尚设计从未被认为是合法化职业,传统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上层阶级妇女身上,集中于她们奢侈的服装”,B77但当这样的注意仅仅建立在“设计师:时尚的拟人化”(Designers: The Personification of Fashion)这样的命题平台,就显然狭隘于所议身份意义创建的人文关怀而忽视了其价值驱动的经济制约。时尚设计师的身份悲剧性在于:处在身份追逐时代它不过是贵族等级制度的行业仆人或者说作坊里的裁缝,因受制于总体社会境遇的“在数个世纪里,服装总体上遵从地位等级制度,每一社会身份的成员,其着装都适应于所在等级地位,传统的力量阻碍着身份的混杂和对服装特权的篡夺”,B78他们甚至不被称为“服装设计师”或“时尚设计师”而被称为“作坊里的裁缝”,B79地位低下且大多按照贵族们的强制性新鲜要求去进行被动性技术加工。到了身体生产成为时尚符号主旋律的时代,亦即到了公共性置换意识形态性,以及自由消费权利置换等级地位安排的时尚民主时代,他们虽然被理性地尊重为“时尚设计师在世界上占有特殊地位,其智慧和想象力不仅在如何使人形象好中起重要作用,而且在创造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做出了重要贡献”,B80却又在大产业制度的非条件性安排下,不仅技术分工出生产岗位身份名称的诸如“辅助设计师”(assistant designers)、“制样师”(sketchers)、“定型师”(patternmakers)、“布料师”(drapers)、“成衣缝纫师”(finishers)、以及“样品抽检师”(sample makers)等,而且即使是大牌时尚设计师也同样不得不在资本权利和产业制度控制下带着镣铐跳舞,就仿佛作为品牌型时尚企业,克里斯丁·迪奥(Cristian Dior,1905-1957)麾下的那些时尚设计大腕,如让·阿赞思(Jean Ozenne)、罗伯特·皮古特(Robert Piguet)、皮尔·贝尔梅因(Pierre Balmain)等,他们的才华、创意和熟练技术都不过是以优秀时装设计师的岗位身份,受雇于或者说被支配于迪奥家族企业以及其所愈来愈具有延伸长度的迪奥时尚产业链。B81因此,当我们完全站在时尚产业研究的立场去讨论包括时装设计师在内的时尚设计师在产业结构中的要素功能,必须从一开始就坚决悖离其身份研究的传统叙事语境,而且尤其坚决走出身份政治或者身份意识形态的价值结构,暂时性地文本悬置诸如“法国的时尚制度化,导致两大设计师群体的边际切分,恰如划分出一部分人消费最新的时尚,而另一部分人则模仿其他阶级的时尚所为”,B82抑或涉事当代身体策略之际的所谓“今天似乎取得了胜利的身体没有继续构成一种生动矛盾的要求、一种‘非神秘化的要求,而只是很简单地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成了神话意愿、教条和救赎模式”。B83也就是说,我们将朝着形而上指向的反方向进入时尚产业经济学事态,在产业链或者产业结构谱系中寻找时尚设计师的特殊功能定位,并由此展开其要素配置真相的学理阐释,从而追问何以时尚设计师既具有供给拉动力量亦具有需求拉动力量,或者换句话说,追问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助推时尚产业进展的变量要素而非常量要素。之所以时尚设计师在时尚市场中既具有生产推动力量亦具有消费拉动力量,是因为它既是生产最大化得以实现的基本杠杆亦是消费最大化得以实现的基本杠杆。时尚市场的均衡游戏,其最核心的游戏内容就在于这一基本杠杆的起落变化和均衡协调,杠杆两端的参与广度、参与长度和参与深度,都不过是游戏热闹景观的“乌合之众”,B84而让这些被反流行文化论者诟病的“乌合之众”集体转身为“消费大众”,B85就在于基本杠杆的社会组织功能与经济激活功能,在时尚设计师的能量聚变中得以有效匹配。在产业经济学视野里,投资者是否投资以及产业是否成为产业,是以清晰的利润计量目标作为行为前提的,从而也就必然以竞争性市场结构作为利润计量的测算边际和思考问题的大背景,即必须既要有消费测算路线和方式的“相对于预算限制,每一个消费者都努力使其效用最大化,一般而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在于B87在这两个模型里,均存在变量不确定性以及测算非关联性,当然也就意味着时尚产业投资者如果按照这些计量模型问题域去进行投资决断,就不仅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使决断更加缺乏比较和平衡的交互换算关系,更何况时尚产业无论是消费面还是生产面,都难以直接嵌位至反映一般产业状况的所谓“消费者效益最大化”和“生产者效益最大化”,其结果就必然给时尚产业投资决断和产业助推变得极为困难且极为缺乏清晰的抓手。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时尚产业投资的资本拥有者,在他们决断是否以及如何进行时尚符号生产和时尚市场操控之际,就会顺利成章地将决断意志集中定位于时尚设计师这一产业内驱要素和市场结构力点,定位于消费经济学家清醒意识到的“这种消费并非必须直接依赖于商品生产”,B88定位于时尚生产与时尚消费的双向非确定性。当时尚产业的投资决断,面对双向非确定性而生犹疑,时尚设计师及其身份能量就成为消除犹疑的动态关键要素,而除疑的效果如何,则完全取决于对这一动态关键要素的功能发挥程度。就消费拉动向度而论,要素功能在于时尚设计师的理念、想象力以及基于物载的符号呈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有效调动欲望的诱惑力,B89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欲望的诱惑将消费大众“被抛于”设计化社会情境游戏诸如“通过对身体着装,以生产特定现实的、社会的和符号的效果”,B90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得设计化社会情境“被抛”演绎为“符号商品世界”(the world of signal commodities)的消费事态,即将时尚符号生产最大限度地转换为消费欲望强烈指向的“所有对象皆可被选择为商品形式,拿钱去交换而非商品本身,就仿佛为行贿而支付(道义价格),或者如出卖古玩这种不能再生产的物品”,B91或者在跨文化境遇波涛相逐地刺激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度假小屋、游泳池、出国旅游、高品质的衣服、大把的钞票以及两辆私家车,这些都是美好生活的标志”,B92抑或基于消费经济的“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整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B93就生产拉动向度而论,要素功能在于时尚设计师的理念、想象力以及基于物载的符号呈现,是否能够有利于各生产要素的功能实现以及进一步的整合利用,是否能够有利于更多的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等,愿意为潜在的消费市场利益承担非确定性巨大失败风险,是否能够有利于产业链延伸以及延伸过程中关联性产品大批量跟进,诸如此类的牵系不仅存在于极为表层的诸如“在自动化和高技术的今天,人的因素仍然在时尚中是不可替代的要素。对所有有效信息的分拣、接受、否决和转化,都有待个体的创意智慧”,B94而且更存在于诸如“数年时间里,英国的棉产业征服了世界,不仅毁灭了印度次大陆的本土棉产业,而且毁灭了产业赖以存在的原材料”,B95抑或事态更具纠结的“毫无疑问,在设计师的高水平创意和高度承诺与确保各方面都接受的公共关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一致。而且从现存的脆弱且实际上破旧不堪的那些基础设施中就可以看到破产景象,即只要设计师的观念不能成为通行的标准或规范,或者至少成为期待圈的一部分。这一情况,将时尚设计搁置到社会学家乌尔瑞奇·贝克(Ulrich Beck)所谓‘危险工作的境地”。B96综合起来就是,资本及其携有者在市场投资决断中,就会很精明地研判作为产业功能要素之一的时尚设计师及其设计理念、设计方案,有时甚至细节地从诸如“衣箱秀”(trunk show)或“规格书”(tech pack)中窥视其对生产指向的潜在拉动影响,而又同样细节性地从诸如“诱惑力”(seductive power)或“时尚预测”(the prediction of fashion)等蛛丝马迹中猜测其对时尚指向的潜在拉动张力,并最终形成以投资目标、投资规模、投资方式等为关键内容的产业行动方案及进一步的产业运行实际状况。很显然,只要承认这一产业要素具有如上所述的双向非确定性影响力,就决定了它在产业结构中具有变量地位而非常量地位。而进一步的追问则在于,就时尚产业而言,这个变量不仅不是某个生产环节或消费环节的变量,而且是整个时尚产业和时尚市场的核心变量或者说总体性变量,它在时尚产业经济分析或者时尚市场计量建模中,其地位甚至超过通常意义上微观经济学或产业经济学对价格、价格指数的功能定位。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价格、价格指数都是市场均衡分析或产业运行测算的变量法宝,无论一般性分析的“理解竞争性经济的一个基本点是,竞争价格反映了社会成本或稀缺性……边际成本比率等于价格比率,所以相对价格就反映社会的这种转换比率”,B97还是技术化测值的“科诺斯价格指数为Pk(支出)函数”,B98其法宝的法力从来处于弹指灵验的神功状态。然而,正如本文前此已经述及,其法力在解读或者描述时尚市场的边际效益状况或时尚市场均衡结构时基本上表现为失灵的尴尬,而且特定时尚企业据此寻求优势存身的“利润最大化与理性行为”,B99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据此,我们也就不得不从一个非经济学家的知识身份,向经济学知识域提出一个仍然很模糊的倒逼设问,那就是在价格杠杆原理不能完全甚至基本不能支撑时尚市场运行均衡规律或变化状况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从时尚设计师及其设计理念、设计方案等的意义变化和价值变量来考察时尚市场和时尚产业的特殊经济表现?如果这种或许极为幼稚的倒逼还存在哪怕很小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是否也就意味着产业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在进入时尚产业经济学研究之际,就可以而且应该给这一核心变量要素以新的给定函数代码,并由此建立完全吻合时尚市场运行的计算模型?形成此类倒逼的勇气在于,除了时尚市场、时尚生产、时尚消费乃至时尚产品价格等往往遁形于规律、惯例、范式、常态和通约等市场存有和社会存在之外,还在于一些学者在特定文化产业经济研究中所采取的知识行动,恰恰是在产业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知识谱系之外获得了某些文化产业事态的解读能力,例如奥拉维·瓦尔索依斯(Olav Velthuis)面对当代艺术市场艺术品价格的非成本性与反稀缺性所作出的探讨,尤其是关于“价格的符号意义”命题及其所指涉的“价格被悬置于意义网,一张没有人情味的网,效率高的意义具有唯一性。这张意义网依赖于由认知关联组成的精神评价体系,而且将价格与质量、声誉和身份联系到一起。反过来精神评价体系通过符号社会化得以建构”,B100对我们认识时尚产业中时尚设计师的核心变量要素地位,以及在时尚市场运行测值或时尚产业经济分析中放弃价格杠杆原理,无疑具有平移类推的巨大参照意义。按照这一思路,则通过经济学知识谱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形,当然也随着产业经济学、市场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知识范式对时尚产业和时尚市场经济的愈来愈关注和愈来愈具有针对性的特殊把握能力,一定会有非常规分析方式和反价格杠杆原理的计量数学模型,完整而有效地对时尚产业、时尚市场和时尚经济等给予反常规性真相解读。但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首先基于一个语用前提,那就是我们此时的时尚设计师所指,乃是一个总体概念而非具体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广义概念而非狭义概念。不过,虽然这个语用前提与时尚产业的边际延伸、内置谱系、产业链长度以及创意主体的能动构成等诸多方面密切钩连,但由于它在更深层面与诸如身份形态史或主体间性的未来社会走向等议题,有更多社会本体论及个体存在论的重大知识链接,所以只能留待“时尚设计师”或“时尚创意”这一类专议去给予义项谱系完形的整体阐释。endprint
六
时尚产业作为现代文化产业的先锋产业形态,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尽管如此,时尚产业仍然是产业形态不断升级、产业边际不断延展、产业规模不断扩张、产业效益不断拓值的朝阳产业。尤其对后发时尚产业国家而言,其竞争与发展的空间更大。全球化进程提速、消费社会全面深化、后现代性文化建构愈来愈显示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正能量价值,所有这一切,都在叠加意义上形成对时尚产业飞速发展的内驱合力。巨大的资本正源源不断地向时尚产业转移,它在魔力般地策划时尚符号生产的同时,以其无形的手实施其对时尚消费市场的强制性布控,与此同时,还时时诱惑着越来越多的时尚创意主题进入现场,并参与对时尚生产和时尚消费的无孔不入的全面诱惑。其结果是,日常生活现场在“被时尚化”的时尚浪潮中形成一种维度性的生活方式转型,而非个案性或单向度的生活意义事件。而我们在对时尚产业与时尚生活方式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等知识链接中不难发现,时尚产业与时尚生活方式的意义互动与价值博弈过程中,其利益空间之所以能以几何级数增长方式不断扩张,不过就是持续不断而且屡屡升级地演绎着资本神话、消费神话和创意神话,这些神话美丽地诱引着一切有能力进入时尚生活现场者以种种不同的进入姿态绵绵不断地涌入,而且这三方面的神话在时尚产业和实际演绎过程中,总是那么互文性恰到好处地共同支撑其利益累增功能,其利益累增强度与内在秘密,令既往的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叹而难释其全部事态真相。这就是我们渴望着、惊叹着、呼唤着、争议着、神秘着同时也正在热拥着的时尚产业! (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Eric Wilson, Fashion Industry, in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2005, Farminton Hills, P.51.
② Gilles Lipovetsky, A Century of Fashion, in Malcolm Barnard(ed), Fashion Theory: A Reader, Routledge 2007, London, P.76.
③ Patrik Aspers, Orderly Fashion: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ey, P.32.
④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Thom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Hills, P.373.
⑤ Elizaba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s And Modernity, I.B.Touris& Co Ltd 2003,London, P.135.
⑥ Roland Barthes,The Fashion System, Translated by Matthew Ward and Richard How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Berkeley, P.161.亦可参阅该书第三章中论及的“In order to analyse the general system of Fashio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deal with each of the system that comprise it separately; it is thu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to which these systems are autonomous”(P.39).
⑦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45.她甚至明确提出“My empirical study (Kawamira 2004) of French fashion indicates that fashion as a system first emerged in Paris in 1868 with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xclusive custom-made clothes known as Haute Couture”. (ibid.)
⑧ 迈克·费瑟斯通著,刘精明译《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时尚消费者身份常被一些学者指涉为能对“物恋”和“物用”进行条件性超越的消费个体,对此,可参阅Tim Dant的一段话: “They shift focus to the context in which an object is to be located and describe comsumption in terms of the use of the thing in that context. Commodities do not have a predefined use-value, and even the sign value of an object is not determined by the discourse of advertising. Its use is variable and negotiable (for example in terms of ostentation,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leisure practices) and its precious form varies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text".(Tim Dant, Consuming Or Living With Things, in Malcolm Barnard(ed), Fashion Theory: A Reader, Routledge 2007, New York, P.376)。
⑨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Thomsom Gale 2005, Farmington Hills, P.47.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时尚偶像如Coco Channel, Freda Dudley Ward, Joan Crawford, Marlon Brando, Jackie kennedy等,于所在时域具有极大的文化影响力,与其他文化精英人物的社会价值编序完全处于平行序列之中,所以我们才能读到诸如“我与个性很强的人总是能够相处融洽。和大艺术家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十分尊重他们,同时也非常自由。我是他们的道德心”。(保罗·莫朗著,段慧敏译《香奈儿的态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⑩ 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B11 Don Slater and Fran Tonkiss, Market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1, Cambridge, P.92.
B12 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B13 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B14 Carla Jones and Ann Marie Leshkowish,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Re-Orienting Fashion or Re-Orientalizing Asia, in Sandra Niessen, Ann Marie Leshkowich and Carla Jones(eds), Re-Orienting Fash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Berg 2003, New York, P.1.
B15 时尚产业全球化重新洗牌,正在生产和消费的后现代境遇中现实建构着学者们理论憧憬的“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regligion based on the full humanity of the Savior, the created world can be lauded for its beauty; the originality and charms of appearance can gain legitimacy; costume can outline and amplifythe beautied of the body".(C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rn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54.)事实上,在从“时尚帝国”走向“时尚世界”的递变过程中,时尚产业就其价值存在方式而言,具有本体论层面的革命性进展。正是时尚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现场化,不仅大范围地解放了时尚的生产关系,也极大地提高了时尚的生产力,从而也就意味着革命性进展本身为时尚产业确立起文化拓殖、经济拓殖的普世价值。
B16 Lise Skov, Fashion-Nation: A Japanese Globalization Experience and a Hong Kong Dilemma, in Sandra Niessen, Ann Marie Leshkowich and Carla Jones(eds), Re-Orienting Fash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Berg 2003, New York, P.227.很显然,这种变化使时尚的不确定性及非垄断性大大加剧,人们事实上已经很难在当代时尚生活中再以超级崇拜的集合心态,集体性长时间体验可可·香奈儿天后时代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创造着时尚……我不出门应酬是因为我需要创造时尚,而我创造时尚只是因为我要出门,只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享受到这个世纪的生活的女人”(保罗·莫朗著,段慧敏译《香奈儿的态度》,第190页)。
B17 Don Slater and Fran Tonkiss,Market Society, Polity Press 2001, Cambridge, P.55.
B18 Kevin V. Mulcahy, Colonility,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J.P. Sign(e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Policies and Power,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New York, P.161。实际上,这些“它者”已经使他们极不情愿地消融到他们的生活境域之中,与他们共同建构着“非它者性”的在场,亦如他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时尚伦敦”,如今也出现诸如“在这些经济领域中,英国的亚洲妇女是充满文化自信与商业自信的代理商(经理人)。她们是同等杰出的全球联系纽带,通过跨国时装经济,她们将自己的愿望和文化专业知识转移至全球”。(Parminder Bhachu, Designing Diasporic Markets:Asian Fashion Entrepreneurs in London, In Sandra Niessen, Ann Marie Leshkowich and Carla Jones(eds), Re-Orienting Fash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Berg 2003, New York, P.139)。
B19 Eva Tsai, Existing in theAge of Innocence:Pop Stars, Publics and Politics in Asia, in Chua Beng Huat and Koichi Iwabuchi(eds), East Asian Pop Culture: Analysing the Korean Wav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Hong Kong, P.217.
B20 Elizabeth Ewing, His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Fashion, B.T.Batsford Ltd 1992, London, P.288.
B21 T.L.Short, Peirce's Theory of Sig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New York, P.164.对此,亦可比较性参阅莫里斯·梅洛——庞蒂的“如果单独考察符号,那么每一个符号都是模棱两可的或无新意的,只有符号的结合才能产生意义……随着我们投入语言中,语言超越‘符号走向意义”(莫里斯·梅洛——庞蒂著,姜志辉译《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0页)。
B22 同⑩,第124页。
B23 Louise J.Kaplan, Cultures of Fetishism,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New York, P.5.对于一个产业经济学家而言,时尚产品不过就是“Material identity means that the item of clothing produced for example, in Dhaka-is displayed twelve weeks later in an store in Manchester. Phenomenologically, it may well be that the object produced is different from what is sold in the consumer market.”(Patrik Aspers, Orderly Fashion: 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y, P.117.)
B24 齐奥尔格·西美尔著,费勇译《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B25 Elizabeth Wilson, A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I.B. Touris &Co Ltd 2003,London, P. 208.另外的极端案例有如“Dress reform therefore easily came to be linked with feminism”(ibid)或者“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Dr Gustav Jaegar, Professor of Zoology and physi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successfully promoted the idea that human beings should were wool next to skin (and sleep between woollen sheets) because animal fibres alone could prevent the retention of the noxious exhalation'of the body"(ibid).
B26 C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rn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204.
B27 John Howkins,The Mayors Commission On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John Hartley(ed), 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Malden, P.122。Stuart Cunningham在讨论创意企业时更断言“Creating enterprise should increasingly be seen as an integral element of high-value-added, knowledge-based emergant industries. This is the least developed of the triad of positions outlined here, but it is the one most likely to advance new positioning of the high-growth cutting edg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to the future".(Stuart Cunningham, Creative Enterprise, in John Hartley(ed),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Malden, P.292。)此类情况,表现在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兴高采烈的中国,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文化产业条件命题之所以转换为中国事态的非条件性命题,就在于讨论和宣传的主要涉身者几乎都是文史哲或者门类艺术知识背景等的瞬间身份转型(我本人亦在其中),产业经济学知识谱系缺位,直接导致有知识投机之嫌的我们,总是行走在没有参照物和评价标杆的荒原上,狂奔得很过瘾,但往往找不着北。
B28 Jennifer Graik,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17
B29 Patrik Aspers, Drderly Fashion: 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ey, P.139.
B30 Brad Haseman, Creative Practices, in John Hartley(ed),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5, Malden, P.170.
B31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50.
B32 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3页。
B33 参阅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一个简单的技巧可以帮助你计算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直线(需求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弹性等于位于该点之下的线段长度与位于该点之上的线段长度的比较”、“更准确地说,供给的价格弹性(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是供给量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动的百分比”(见其所著,萧琛主译《微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7页。),进一步还可参阅“价格指数”所描述的“When newspapers tell us ‘Inflation is rising', they are really reporting the movement of a price index. A price index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price of a number of goods and serves. In constructing price indexs, economists weight individual prices by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each goods. The most importance price indexs are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the GDP deflator, and the produce price index".(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D.Nordhaus, Economics,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1998, P.407.)
B34 这种“新装”被时尚史家描述为“In 1947 the nipped-in waist of christian Diors New Look called for a new type of corset to set it off. Generally known as ‘waspies, such corsets ranged from 6 to 18in.(15.2 to 48.6cm) deep, were made of rigid material, and often laced at the back.The smaller waspies were on top of the usual roll-on. Both types were very uncomfortable, even if they did produce the required hour-glass look. However, at this date they were calssified as luxury garments"(C.Willett and Phillis Cunnington, The History of underclothes,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81, London, P.167.)
B35 Patrik Aspers, Orderly Fashion: 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ey, P.104.
B36 时尚学界通常习惯于把19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一个世纪成为时尚世纪,或者说是一个现代时尚的世纪,其叙事基点在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时尚涌起于19世纪后半叶。当然,并非一切都是全新的,实际离此要久远得多。然而清晰之处在于,空前的时尚生产和扩散制度出现在这一时期,而且维持了一个世纪的惯性”(G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rn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55),依此延伸,则我们似乎已进入或正在迎接一个新的时尚世纪,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个后现代背景下的时尚世纪。
B37 在时尚的“身份追逐”时代,即使在西方也与奢侈每多叠合空间,所以才有诸如“因此接下来便是鞋匠、发型师、天文学者、烹饪书作者、大厨、钻石商人、服装师和时装女王们,折叠伞的发明者……还有香槟的发明者,他们一起创造了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关于优雅、时尚以及奢侈观念的格调”(若昂·德让著,扬冀译《时尚的精髓: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优雅品味及奢侈生活》,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7页)。但是,进入“身体生产”时代的所谓“时尚世纪”以后,主流知识界便已将二者的语义边界和价值取向作清晰的分离,只是这种分离并未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途有效实现,至少是缺乏社会性的观念清理,其观念终结将取决于何时抵达中国现场的“在‘消费时尚取代等级时尚中,存在着更多的风格多样性,同时在特定时代更少关于‘时尚中的共识”(Diana Crane, 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 Class, Gender And Identity In Clothing,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hicago, P.134)。
B38 作为“涵化”(acculturation)对应概念的“文化阻抗”(cultural resistance),一般强调的是民族对于某些外来信仰、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本能排斥,而时尚生活方式恰恰被普遍认定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舶来品。
B39 Stephanie M. Stolz, Bank Capital And Risk-Taking: The Impact Of Capital Regulation, Charter Value And The Business Cycle, Springer 2007, New York, P.133.
B40 同B32,第230页。
B41 Philip Cooke and Dafna Schwartz(eds),Creative Regions: Technology, Culture And Knowledge Entrepreneuship, Routledge 2007, New York, P.7.
B42 斯坦利·杰文斯著,郭大力译《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88页。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斯坦利·杰文斯在用导数表述边际效用概念过程中,他接受了边沁学说对于快乐与痛苦以及欲望预期之间的情感计量描述方法,对诸如“强度”(intensity)、“历时”(duration)、“确实性”(certainty or uncertainty)、“远近性”(propinguity or remoteness)、“多产性”(fecundity)、“纯洁性”(purity)、“范围”(extent)等关联要素等给予相对定量考察,无论对人与时尚的发生论关系研究还是存在论关系研究,都具有建设性的知识导向价值。
B43 约·雷·麦克库洛赫著,郭家麟译《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5页。
B44 Thijs Ten Rea, The Economic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New York, P.22.作者将不等式注解为“The wedge in the inequality, x-Ax, is the net output of the economy, also called final demand. It comprises the quantities of commodities that are not consumed by industry and may be used by the household".(ibid).
B45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Berlin, P.115.
B46 Valerie Steele,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3, Thomo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 P.19.
B47 Philippe Perrot, Fashioning the Bourgeoisie: A History Of Cloth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Richard Bienvenu,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47.
B48 转引自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85.举证Charles Frederich Worth(1825-1895)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因为“通常他被确信为时尚公司的奠基人,开创了最高水平的时尚创意:高级时装”(Valerie Steele,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3, Thomo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 P.447.)
B49 Rita Gersten,Fashion Art For The Fashion Industry,Fairchild Rublications 1989,New York,
B50 约翰·柯廷顿、佩-奥洛夫·约翰逊、卡尔-古斯塔夫·劳夫格伦著,林谦译《开放经济中的非均衡宏观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在给定的计算模型中,必须满足约束条件
B53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o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Hills, P.214.Hip-Hop时尚不仅以时尚文化形态超越于通常的流行音乐,而且也超越了其他音乐导向的青年文化,其市场化事态和消费性巨额利润空间,同样既非贫困的纽约布朗克斯地区(the Bronx in New York)的诸如D.T.s Kool Herc, Grandmaster Flash and DJ starski等始料未及,更是大规模扩散的诸如新西兰、日本、非洲、法国、英国乃至世界各地至今未解其中真相的利益生成规律,至于由音乐活动形态引申出的所谓Hip-Hop时尚,以及这种时尚跟进性行为拼贴的诸如“宽松的服装”(baggy apparel)、“炫耀的棒球帽”(baseball caps emblazoned)、“羊毛阿飞帽和围巾”(woolen beanie hats and bandannas)、“低价傻瓜夹克衫”(goose down jackets)、“带罩帽的宽松长袖运动衫”(hooded sweatshirts)、“肥大的白体恤”(oversized white T-shirt)、“篮球马甲”(basketball vests)、“曲棍球衣”(hockey shirts)、“歌莉亚温德尔牛仔裤” (Gloria Vanderbilt jeans)、“从制手提购物袋”(bamboo carrings)、“名牌项链”(name chains)、“露腹上装”(midriff tops)、“文胸上衣”(bra tops)、“短裙”(short skirts)、“紧身牛仔裤”(tight jeans)、“高筒靴”(high boots)、“镶边的毕挺发浪”(straight hair weaves and braids)、“纹身”(tattoos)、“假指甲”(false fingernails)、“大号金手饰”(oversized gold jewelry)等,更是超过数亿美金音乐产品收益的百倍千倍,且绝非经济学家边际计量或曲线标值方法所能精确于万一。
B54 John Ryan,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the Music Industr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Inc.1985, Lanham, P.101.
B55 Dominique Veillon, Fashion under the Occupation, Translated by Miriam Kochan, Berg 2002, New York, P.111.
B56 理查德·弗罗里达著,方海萍等译《创意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9页。其实这类梦呓叙事乃是人类命运相终始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从来都是人类命运挣扎的反弹物,所存在的叙事缺陷不过在于,叙事人在相同语境或同一文本中不自觉地往往将大创意概念与小创意概念交叉混淆使用,从而也就不过是一种语用乱伦游戏。就大创意概念而言,人类社会相对于对象世界从一开始就可以看作创意社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社会本体论无论在中国先秦还是在古代希腊,皆无不把人类生存史看作创意社会史,所以就要先秦中国的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或者古希腊的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普罗泰戈拉《著作残篇》,引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8页)。就小创意概念而起,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重大社会进步时域,都可以看作是比较视野内的“创意时代”或“创意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即将到来的时代进行完全没有时间刻度限制的无限性命题指涉,就只能当作梦想情怀来给予抒情性亢奋体验。
B57 Terry Flew, Creative Economy, in John Hartly(ed), 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Malden, P.344.
B58 Mclcolm Barnard, Fashion As Communication, Routledge 1996, London, P.33.
B59 乔纳森·弗里德曼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0页。在我看来,“认同构造”命题作为文化全球事态的解释向度,之所以优越于直观思维或者线性思维的诸如“同质化”、“普通化”、“资本化”、“全球性与本土性冲突化”以及完全质疑的“中心霸权化”等拟题方式,就在于它是复合思维中既强调参与身份独立性又强调参与现场扩大化和可通约性迅速拓值,当然在总体事态框架建构中,必然包含类的同质性增长及其类别的异质性冲突同步走强,所以也就对人类各民族提出了更加严峻的在场协调性和在场文化价值共建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那些以维护政治利益为目的政客们(尤其是美国政客),总是假借国家软实力或民族文化传统坚守的伪正义托词,故意误读戴维·赫尔德的“全球大变革”重大知识行动及其中描述到的“当代文化全球化中最明显的要素就是服务于各种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和接受以及各种文化交流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页)。
B60 Scott Lash and Celia Lury,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The Mediation of Things, Polity Press 2007, Malden, P.181.
B61 雅克·阿达著,何竟等译《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B62 Parminder Bhachu, Designing Diasporic Markets: Asian Fashion Entrepreneurs in London, in Sandra Niessen, Ann Marie Leshkowich and Carla Jones(eds), Re-Orienting Fash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Berg 2003, New York, P.154.
B63 亚洲时尚产业发展进程中,日本的某些经验对我们或许具有参照意义。
B64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43.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更深层次地阐述这一命题,认为“A system will be(relatively)independent if, after subtracting to deal with the rest of the utterance without in any way altering the respective meaning of the residual systems. Thus, it is by opposing a system to the remains'of the inferior systems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judge its autonomy”(Roland Barthes, The Fashion System, Translated by Matthew Ward and Richard How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California, P.39)。
B65 Sandr Niessen, Three Scenarios From Batak Clothing History: Design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Fashion Trajectory, in Sandra Niessen, Ann Marie Leshkowich and Carla Jones(eds), Re-Orienting Fashion: The Globalization of Asian Dress, Berg 2003, New York, P.49.
B66 G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m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88.
B67 Valerie Steele,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Hills, P.51.
B68 譬如能助推时尚销售的所谓“5Rs”叠合进程,即所谓“Merchandising is the planning involved in marketing the right merchandise at the right price at the right time in the right place and in the right quantities”(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 2005, Farmington Hills, P.57.)
B69 Patrik Aspers, Orderly Fashion: 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ey, P.113.
B70 Patrik Aspers, Orderly Fashion: A Sociology Of Marke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New Jersey, P.156.
B71 对此,可以比较性地阅读诸如“现在无论是私人公司还是公共调控者的国内政策,通常都必须考虑影响自己业务范围的主要的国际性决定因素。随着系统的相互依存程度的提高,国家这一层为国际层所渗透和改变。在这种全球化经济中,这一点给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提出的难题是:怎样构建使它们的调控努力协调一致和一体化的政策框架,以适应它们的经济角色之间系统的相互依存的局面”(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著,张文成等译《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或者所谓“如果一个参与国在争取提高生产率的竞争中不能跟上,那么它的经济就会立即陷入危机。在此之前,有些货币发行银行,还可以靠贬低自己货币的币值来组织这类发展,至少可以以此支持其出口业。但是,随着货币联盟的成立,现在这一缓冲器不起作用了”(汉斯——彼得·马丁、哈马尔特·舒曼著,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4页)。
B72 参阅让·波德里亚的“纯粹的形式就是这种模糊的、没有美丽的、没有赌注的诱惑的形式,就是这种诱惑幽灵的形式,这个幽灵萦绕着我们无秘密的回路、无情感的幻觉、无往来的接触的网络”(让·波德里亚著,张新木译《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B73 Jeanifer Craik, 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13.
B74 Jeanifer Craik, 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17.
B75 Steven T. 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o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berg, P.231.
B76 让·鲍德里亚所谓“需要最好被界定为一种通过个人的内在逻辑推理得出的功能:更为确切地说,并不是作为被丰盛社会所解放了的消费的力量,而是作为体系自身的功能运演,即幸存以及再生产的过程所必须得生产力。换言之,需要的存在只是因为体系本身必需他们的存在”(让·鲍德里亚著,夏莹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或者苏珊·B.卡塞尔(Susan B. Kaiser)、霍华德·G.舍兹(Howard G. Schatz)、约翰·L.坎德勒(John L. Chandler)以及赖斯·M.利雅得(Lisa M.Lieder)等所谓“鞋体现了创造性的时尚符号,也许对零售商和消费者而言抓住的是不同的意义。零售商面对着理解流行趣味的任务,而且要评估全神贯注公众的趣味预期”(Susan B. Kaiser, Howard G. Schutz, John L. Chandle and Lisa M. Lieder, Shoes as Sociocultural Symbols: Retailersversus ConsumersPerceptions, in Michael R. Solomon(ed), The Psychology of Fashion, Lexington Books 1985, Massachusetts, P.127.),都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逻辑关系的理解。
B77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58.
B78 Gilles Lipovetsky, The Empire Of Fashion: Dressing Modem Democrac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New Jersey, P.30.
B79 “服装设计师”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使用,通常人们把查尔斯·弗里德里奇·沃尔斯(Charles Frederich Worth)看作巴黎的第一位时装设计师,而时尚指涉的时装设计师,在英语里直到1948年才开始使用。
B80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 2—5, Farminton Hills, P.36.
B81 必须注意的是,在迪奥企业发展史上,很多设计师会因各种原因离开并自立门户,例如皮尔·贝尔梅因就在1945年开了自己的时装屋,其中程度不同地隐藏着身份解放甚至身份反抗的社会内涵。当然,这将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时尚社会学议题。
B82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71.
B83 同⑩,第128页。
B84 参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过往的神权了”(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实际上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写于1895年的这本才子式著作,不仅对后来发生的20世纪诸多社会事态有不俗的指涉力,而且对这些社会事态中的时尚生活事态尤其具有解读张力,只不过“乌合之众”的命题和命名,并非时尚产业知识谱系内的参照物而已)
B85 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不同,更多的西方学者在研判“大众文化”思潮时,一方面将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提升为普适性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将消费文化与大众社会进行交互链接,于是作为消费共同体和消费社会基本力量的“消费大众”,就在对“乌合之众”的价值超越中实现了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和新的共同体价值目标。伯明翰学派的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其所断言的“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多样化的,而这一多样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同质化策略,是靠大众与文化的力量维系下来的”(王晓钰等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无非就立足于消费社会、消费公共性以及消费大众等一系列相关逻辑条件。
B86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lberg, P.273.
B87 Ibid, P.274.
B88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6.
B89 参阅让·鲍得里亚所谓:“诱惑比权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是一个可逆而致命的过程,而权力则希望自己像价值那样具有不可逆性,能够积累,像价值那样永恒不朽……诱惑实际上并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它从来就不属于力量的范畴,也不属于力量对比的范畴。然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只有诱惑才能涵盖权力的现实过程,就像涵盖生产的现实范畴那样,还有可逆性和不断减少积累的现实范畴——否则将不会有权利,也不会有生产”(让·鲍得里亚著,张新木译《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B90 Jennifer Craik, 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3.
B91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7.
B92 朱丽叶·朔尔《消费社会到底怎么了——竞争性消费和“新消费主义”》,引自比尔·麦吉本编著,朱琳译《消费的欲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B93 同⑩,第63页。
B94 Rita Gersten, Fashion Art for Fashion Industry, Fairchild Publication 1989, New York, P.1
B95 Elizabeth Wilson, An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I.B. Tauris & Co Ltd 2003, London, P.67.
B96 Angela McRobbie, Fashion As A Culture Industry, in Stella Bruzzi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eds), Fashion Cultures:Theories, 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 Routledge 2000,London,P.261.
B9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美国经济学家C.E.林德布姆所特别称道的“市场体制拥有最长的手臂和最灵巧的手指,对此,我们应该把它看成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不论是承认市场体制是人类的大施主,还是怀疑市场体制的长臂和灵巧的手指是令人生厌的怪物,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作为合作的非凡组织者的地位都牢不可撼”(C.E.林德布姆著,耿修林译《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其最大的秘密无非就是资本的布控魔力与价格的调节动力,而价格调节动力作为市场运作的边际效应和核心变量要素,说到底就是现代经济学描述的“相对需求来说供给情形的变化,和相对供给来说需求情形的变化,都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92页),同时也还是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效用和保有量是确定价格的根本原因和条件,由此可以推定,这两者也是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和条件”(莱昂·瓦尔拉斯著,蔡受百译《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5页)。
B98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berg, P.227.
B99 Harold Demsetz,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mbridge, P.61.
B100 Olav Velthuis , Talking Prices:Symbolic Meanings of Price on the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New Jeasey, P.159.在这里,除了所谓声誉(reputation)和身份(status)因素具有反经济客观性尺度,其他非客观性尺度(例如炒作、资金操控、人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在艺术品质量定性中所起的实际影响更大,艺术品质量据此与客观性尺度以及进一步的价格合理性之间就变得尤其缺乏必然联系。
B79 “服装设计师”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使用,通常人们把查尔斯·弗里德里奇·沃尔斯(Charles Frederich Worth)看作巴黎的第一位时装设计师,而时尚指涉的时装设计师,在英语里直到1948年才开始使用。
B80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 2—5, Farminton Hills, P.36.
B81 必须注意的是,在迪奥企业发展史上,很多设计师会因各种原因离开并自立门户,例如皮尔·贝尔梅因就在1945年开了自己的时装屋,其中程度不同地隐藏着身份解放甚至身份反抗的社会内涵。当然,这将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时尚社会学议题。
B82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71.
B83 同⑩,第128页。
B84 参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过往的神权了”(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实际上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写于1895年的这本才子式著作,不仅对后来发生的20世纪诸多社会事态有不俗的指涉力,而且对这些社会事态中的时尚生活事态尤其具有解读张力,只不过“乌合之众”的命题和命名,并非时尚产业知识谱系内的参照物而已)
B85 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不同,更多的西方学者在研判“大众文化”思潮时,一方面将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提升为普适性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将消费文化与大众社会进行交互链接,于是作为消费共同体和消费社会基本力量的“消费大众”,就在对“乌合之众”的价值超越中实现了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和新的共同体价值目标。伯明翰学派的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其所断言的“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多样化的,而这一多样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同质化策略,是靠大众与文化的力量维系下来的”(王晓钰等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无非就立足于消费社会、消费公共性以及消费大众等一系列相关逻辑条件。
B86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lberg, P.273.
B87 Ibid, P.274.
B88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6.
B89 参阅让·鲍得里亚所谓:“诱惑比权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是一个可逆而致命的过程,而权力则希望自己像价值那样具有不可逆性,能够积累,像价值那样永恒不朽……诱惑实际上并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它从来就不属于力量的范畴,也不属于力量对比的范畴。然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只有诱惑才能涵盖权力的现实过程,就像涵盖生产的现实范畴那样,还有可逆性和不断减少积累的现实范畴——否则将不会有权利,也不会有生产”(让·鲍得里亚著,张新木译《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B90 Jennifer Craik, 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3.
B91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7.
B92 朱丽叶·朔尔《消费社会到底怎么了——竞争性消费和“新消费主义”》,引自比尔·麦吉本编著,朱琳译《消费的欲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B93 同⑩,第63页。
B94 Rita Gersten, Fashion Art for Fashion Industry, Fairchild Publication 1989, New York, P.1
B95 Elizabeth Wilson, An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I.B. Tauris & Co Ltd 2003, London, P.67.
B96 Angela McRobbie, Fashion As A Culture Industry, in Stella Bruzzi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eds), Fashion Cultures:Theories, 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 Routledge 2000,London,P.261.
B9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美国经济学家C.E.林德布姆所特别称道的“市场体制拥有最长的手臂和最灵巧的手指,对此,我们应该把它看成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不论是承认市场体制是人类的大施主,还是怀疑市场体制的长臂和灵巧的手指是令人生厌的怪物,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作为合作的非凡组织者的地位都牢不可撼”(C.E.林德布姆著,耿修林译《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其最大的秘密无非就是资本的布控魔力与价格的调节动力,而价格调节动力作为市场运作的边际效应和核心变量要素,说到底就是现代经济学描述的“相对需求来说供给情形的变化,和相对供给来说需求情形的变化,都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92页),同时也还是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效用和保有量是确定价格的根本原因和条件,由此可以推定,这两者也是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和条件”(莱昂·瓦尔拉斯著,蔡受百译《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5页)。
B98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berg, P.227.
B99 Harold Demsetz,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mbridge, P.61.
B100 Olav Velthuis , Talking Prices:Symbolic Meanings of Price on the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New Jeasey, P.159.在这里,除了所谓声誉(reputation)和身份(status)因素具有反经济客观性尺度,其他非客观性尺度(例如炒作、资金操控、人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在艺术品质量定性中所起的实际影响更大,艺术品质量据此与客观性尺度以及进一步的价格合理性之间就变得尤其缺乏必然联系。
B79 “服装设计师”直到19世纪末期才开始使用,通常人们把查尔斯·弗里德里奇·沃尔斯(Charles Frederich Worth)看作巴黎的第一位时装设计师,而时尚指涉的时装设计师,在英语里直到1948年才开始使用。
B80 Valerie Steele(ed), Encyclopedia of Clothing And Fashion, Volume 2, Thomson Gale 2—5, Farminton Hills, P.36.
B81 必须注意的是,在迪奥企业发展史上,很多设计师会因各种原因离开并自立门户,例如皮尔·贝尔梅因就在1945年开了自己的时装屋,其中程度不同地隐藏着身份解放甚至身份反抗的社会内涵。当然,这将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时尚社会学议题。
B82 Yuniya Kawamura, Fashi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Fashion Studies, Berg 2005, New York, P.71.
B83 同⑩,第128页。
B84 参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群体不善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群众的神权就要取代过往的神权了”(冯克利译《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实际上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写于1895年的这本才子式著作,不仅对后来发生的20世纪诸多社会事态有不俗的指涉力,而且对这些社会事态中的时尚生活事态尤其具有解读张力,只不过“乌合之众”的命题和命名,并非时尚产业知识谱系内的参照物而已)
B85 与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不同,更多的西方学者在研判“大众文化”思潮时,一方面将大众文化的消费性提升为普适性时代特征,另一方面将消费文化与大众社会进行交互链接,于是作为消费共同体和消费社会基本力量的“消费大众”,就在对“乌合之众”的价值超越中实现了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和新的共同体价值目标。伯明翰学派的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其所断言的“我们的社会不折不扣是多样化的,而这一多样性,面对形形色色的同质化策略,是靠大众与文化的力量维系下来的”(王晓钰等译《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无非就立足于消费社会、消费公共性以及消费大众等一系列相关逻辑条件。
B86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lberg, P.273.
B87 Ibid, P.274.
B88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6.
B89 参阅让·鲍得里亚所谓:“诱惑比权力更为强大,因为它是一个可逆而致命的过程,而权力则希望自己像价值那样具有不可逆性,能够积累,像价值那样永恒不朽……诱惑实际上并不属于现实的范畴,它从来就不属于力量的范畴,也不属于力量对比的范畴。然而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只有诱惑才能涵盖权力的现实过程,就像涵盖生产的现实范畴那样,还有可逆性和不断减少积累的现实范畴——否则将不会有权利,也不会有生产”(让·鲍得里亚著,张新木译《论诱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B90 Jennifer Craik, The Face of Fashion: Cultural Studies in Fashion, Routledge 1993, London, P.3.
B91 Ben Fine, The World of Consumption: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visited, Routledge 2002, New York, P.27.
B92 朱丽叶·朔尔《消费社会到底怎么了——竞争性消费和“新消费主义”》,引自比尔·麦吉本编著,朱琳译《消费的欲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B93 同⑩,第63页。
B94 Rita Gersten, Fashion Art for Fashion Industry, Fairchild Publication 1989, New York, P.1
B95 Elizabeth Wilson, Andorned in Dreams: Fashion and Modernity, I.B. Tauris & Co Ltd 2003, London, P.67.
B96 Angela McRobbie, Fashion As A Culture Industry, in Stella Bruzzi and Pamela Church Gibson(eds), Fashion Cultures:Theories, 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 Routledge 2000,London,P.261.
B97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微观经济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美国经济学家C.E.林德布姆所特别称道的“市场体制拥有最长的手臂和最灵巧的手指,对此,我们应该把它看成首屈一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不论是承认市场体制是人类的大施主,还是怀疑市场体制的长臂和灵巧的手指是令人生厌的怪物,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作为合作的非凡组织者的地位都牢不可撼”(C.E.林德布姆著,耿修林译《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其最大的秘密无非就是资本的布控魔力与价格的调节动力,而价格调节动力作为市场运作的边际效应和核心变量要素,说到底就是现代经济学描述的“相对需求来说供给情形的变化,和相对供给来说需求情形的变化,都造成价格的剧烈波动”(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第192页),同时也还是古典经济学描述的“效用和保有量是确定价格的根本原因和条件,由此可以推定,这两者也是价格变动的根本原因和条件”(莱昂·瓦尔拉斯著,蔡受百译《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75页)。
B98 Steven T.Hackman, Production Economics: Integrating the Microeconomic and Engineering Perspectives, Springer 2008, Heideberg, P.227.
B99 Harold Demsetz, Th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mbridge, P.61.
B100 Olav Velthuis , Talking Prices:Symbolic Meanings of Price on the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New Jeasey, P.159.在这里,除了所谓声誉(reputation)和身份(status)因素具有反经济客观性尺度,其他非客观性尺度(例如炒作、资金操控、人际关系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在艺术品质量定性中所起的实际影响更大,艺术品质量据此与客观性尺度以及进一步的价格合理性之间就变得尤其缺乏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