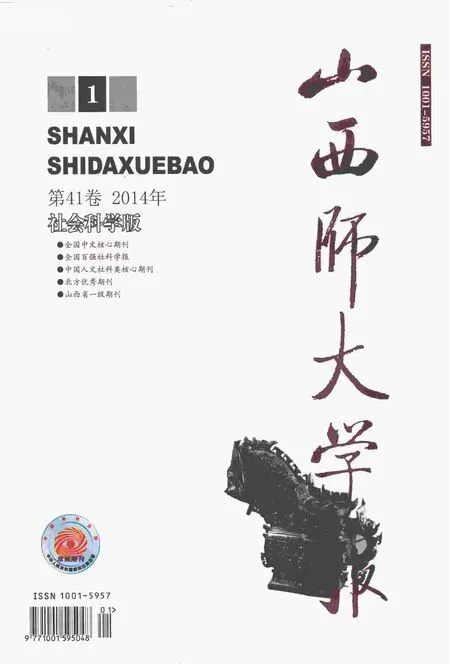被规驯与自我规驯
——中国文学场域中的妻性表征及其阙如
2014-04-10汪贻菡石梅芳
汪贻菡,石梅芳
(1.天津师范大学津沽学院文学系,天津300381;2.河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300387)
在一些以妻性为切入点分析女性形象的论文中,“无妻性”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祥林嫂的奴性被部分地阐释为无妻性,曹七巧的非母性成因是其妻性的缺失,以此视角观之,中国文学文本中妻性缺失的女子占绝大多数,正印证了鲁迅在《小杂感》中关于中国女子“无妻性”的论断。①1927年鲁迅在《小杂感》一文中提道:“女性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与女儿性的混合。”见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0页。然而,究竟什么是妻性?曹七巧缺失了宽容,祥林嫂缺失了独立,如果没有缺失,那么这些品质的相加即谓妻性吗?闻一多说中国女子的妻性即是奴性,又作何解?自鲁迅论断迄今,八十余年已过去,当代女子基本可以自由选择婚姻与职业,奴性不再具有身份意义却未尝不具备精神滞留性,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女子的妻性有无及其主要症候。而当我们进入中国文学场域中时,首先注意到的便是“贞节烈妇”和“荡妇淫妇”两种极端形象,这种遮蔽了女子真实性格的表述无疑拜男权文化所赐,而妻性同样意味着丈夫身份的在场,循此轨迹,或许可为中国式妻性特征的探讨找到一条可行之径。
一、所谓“烈女”:作为私有财产的妻性角色
(一)从“列女”到“烈女”
两千多年前,为向恃宠成娇淫乱宫闱的赵飞燕进谏,光禄大夫刘向编纂了一部《列女传》,内陈昔时贤明仁智之女仪、贞顺节义之妇德,纵未能引起朝廷警戒,却因此成为两千多年里女性修身养性的教科书。“列女”本意是多位女性的意思,经由程朱理学敷衍推陈,渐被谬为“烈女”,然忠贞二意,作为女性的基本要求却是一致的。这忠贞不仅体现为肉体的绝对忠实,而且完全忽略了女性灵魂需求与人格上的独立。体现在文学文本中,便是“思妇”形象的反复出现,每当男子外出徭役、打仗或是求学、游宦,女子便只能独守空门,即便荡子行不归,也需守死空床;若是夫死,便只能守寡终身。“望夫石”的多个版本与其说颂扬了爱情,不如说是体现了男性对女子灵魂与肉体双重忠贞的道德化规驯。诚如风流天子乾隆所题:“千古无心夸节义,一身有死为纲常”。而纲常借由民间传说融入集体无意识,便由规驯演变为自我规驯:楚汉相争,虞姬之死不输霸王光彩;西晋年间,宠妾绿珠为解石崇之困坠楼而亡;明末战乱,李香君为贰臣侯方域血溅桃花扇;民国之后,寡妇祥林嫂因被迫再嫁而寻死觅活。或真实或虚构,爱情在这些案例中是一点点退场的,夫妻之纲常则长驱阔步。
然而,如祥林嫂这样,对一个没有产生过爱情的死魂灵从一而终,是不符合人的天性的,更绝非女子本性。所以鲁迅说这种妻性是被逼迫而成的,是经由父母耳提面命、文化伦理长期灌输警策,及他人言传身教、相互示范等途径养成的,是对女子妻性的一种深久而残酷的想象与遮蔽。在文化与经济权完全由男性把持的年代,生理弱势的女性生存的唯一途径便是嫁作人妻,并为其繁衍后代、侍养父母、操持家务,不妨碍丈夫一切纳妾、宿妓行为,夫死后永生不得改嫁——惟有完成这诸项责任,才有可能换取相对稳定的生存。[1]婚姻在这里并不意味爱情而是一桩交易,彩礼便是定金。《说文解字》中说:“婦,服也”;“娶,取婦也”,是原始抢婚风俗的遗留,多发生在黄昏时分,故有“婚”字;又言“妻,妇与夫齐也。从女从屮从又”,“屮”是用手抓住的意思,似仍有抢婚之意。[2]256凡此种种,女性都是以客体的被动姿态出现的,经济的不平等造成人身的不平等,“妇与夫齐”的人格平等便只能是妄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则更是男权时代的婚姻童话,惟其理想化,才会如灰姑娘的故事般流传千年。
(二)从芸娘、宝钗看完美妻子的无我性
考究中国古典文本,《浮生六记》里的芸娘和《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堪称中国男人理想妻子的代表,也因此有可能最接近传统中的妻性概念。首先来看芸娘,她美丽聪颖而又温顺,闲时夫妻把酒夜谈、落魄时为夫君拔钗沽酒,在内操持家务、在外为夫纳妾,为承欢膝下可替公爹买小、受了婆婆委屈却自叹服侍不周,此等泯灭全部个性、脾气、人格与灵魂的妻子当能博得所有男性喝彩,也就无怪乎林语堂赞其为“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3]了,更是大张旗鼓地将其引入英语世界留此存照。拜沈三白清美文字所赐,芸娘像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一样流传百年,而当我们凝视完美圣殿上的芸娘时,却无法知晓这位女性内心深处的渴望与所思。即便拥有完美妻子,沈三白亦可在芸娘缠绵病榻时在某个曼妙女子的怀中流连。而在充斥了偏见与篡改的男性书写史中,一位完美妻子内心的孤寂与苦楚,将是永远晦暗的。
再来看宝钗,“识大体”是对其最重要的评价,亦是在贾府重孙的婚姻之战中完胜林黛玉的根本法宝。这就意味着她需要将自己不输于林妹妹的见解、才情与脾气一齐收敛,察眼意识眉语,尊重长辈善待下人,劝诫未来的夫君博取功名。《蘅芜君兰言解疑癖》一回,宝钗告诫黛玉勿以西厢词行酒令的说教极具代表性,闲书杂文不是不可读,却万万不可在人前表露,让人以为坏了女儿家心性。一番话说得孤傲的林妹妹也只有垂头暗服、道个“是”字。[4]1760客观来说,条件许可的家庭里,女子读书是被鼓励的,沈三白念念不忘与芸娘秉烛夜谈,宝玉钦佩宝姐姐懂的书多,而孟光之所以接了梁鸿案,也是对其超乎庸常的聪颖与智慧的尊重。
这就很有意思,柔顺怯弱虽被视为女子之美,然而男子往往既要求为妻者温服,亦要求其聪颖坚强。于是每当男子仕途不顺、内心脆弱时,便可以躲到温柔乡里寻求避慰。这种要求原是苛责的,却仍有不少女子外柔内刚,焕发出独特的女性魅力。《白鹿原》里面,布衣大儒朱先生拒绝了四五门亲事最终择定白家大姑娘,就是因为她有一双刚柔相济的眼睛,因此断定:“即使自已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而柔媚刚强的白碧玉也的确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朱先生驾鹤西游、两个儿子哭吼之时挺身而出:“这阵还能哭?快去搭灵堂。”[5]554然而,这种丈夫死后的自立,仍是为男性世界服务的,而远远谈不上同丈夫平等的独立。《列女传》盛赞女子应贤明仁智,从而可以规劝夫君、助其赢取功名与天下。可见女子聪颖是要得的,却只能以为男性服务为前提。综观四大古典美女,无论是貂蝉、西施还是王昭君,其美丽与智慧均作了男子政治斗争的砝码,唯有杨玉环为爱光彩照人、为爱葬身马嵬坡,但既然她不能为男人赢取功名,便只能成为男人失去功名的替死鬼。归根结底,在男性面前,女性永远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没有人身与人格平等的妻子,只能是丈夫的私有财产,其温顺美丽的肉身、聪颖坚定的灵魂,都是隶属于作为主人的夫君的,也因此无论是战国历史中的吴起还是三国文本中的刘安,均敢于毫无愧色地杀妻求禄。而在一些部落里,男子可以大方地将妻子送去给尊贵的客人过夜,而赠妾妓与友人更是士大夫间心心相印的一种佳话。
如果说,“红颜祸水”是女子依附性的必然演绎,那么从芸娘和宝钗这两个完美妻子的身上,则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式妻性的无自我症候。闻一多说话比较直接,干脆名之为“奴性”[6]164,即对平等和独立权力的完全漠视,从人身的被迫依附发展到精神上的主动依附,对经济权无能为力,对感情和性爱权利一无所知,从被规驯到自我规驯,“妻子”逐渐成为一个灵魂不在场的称号而已。两千多年前,《古诗十九首》里的女子还敢于咏叹“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一千多年后,王宝钏却只能苦守寒窑十八载,祥林嫂更是要为一个未成年的小丈夫寻死觅活,爱情在漫长而孤独的厮守中已然石化,唆使那无数年轻女子将活寡守下去的,是内心深处自我规驯的恐惧,是弥漫在中国式夫妻关系中的妻性要求:无我的忠贞。
二、所谓“娼妇”:缺失的恋人性
在中国文学文本的暗语里,“娼妇”是一个颇为暧昧的词。通常,该词是对女性性工作者的一种蔑称。纯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女子在最初的娼妓团体中,地位比拥有技艺之“妓”的身份还要低微。为揽得生意,娼妓们往往会有意识地表露自己的容貌、身段等女性生理特征向男性撒娇、邀宠,乃至进行性暗示和性诱惑并借以降伏男人,这与传统女子尽力收束心性以示端庄大方是完全迥异的,只能属于娼妓等特殊职业,故而赋予这种行为以“娼妇性”的蔑称,与此相似的还有“狐狸精”、“淫妇”等词汇。
然而,也正是从这暧昧不清的指称中,我们发现,所谓“娼妇性”毋宁说是一种恋人性的主张,是产生性吸引的男女之间正常的恩爱举动,也即一种天性。《聊斋志异》的卓越贡献之一便是塑造了诸多美貌天然的女子形象,如天真爱笑的狐女婴宁,与夫君日日游戏的狐仙小翠,主动索爱的牡丹精葛巾等,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对书生的诱惑往往是一击即中的,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恋人的天性隐藏在花妖狐媚的身份之下,使人们忘却了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里,便有怀春女子为吉士“舒尔脱脱”(《召南·野有死麕》),有顽皮的静女故意约会来迟(《邶风·静女》),有小夫妻在清晨起床前卿卿我我(《郑风·女曰鸡鸣》),有婉如清扬的女子在蔓草如烟中与男子邂逅眉目传情(《郑风·野有蔓草》)。纵然这大抵是女儿身份,却都是男欢女爱的真实情感勃发,却缘何做了妻子就应将其收敛至无呢?既然爱情像咳嗽一样难以掩饰,那么夫妻间因爱而生的恋人性便也是不可回避的。本质上,表露自己的女性生理特征和精神气质,传达一种恋人性来使感情融洽,并将彼此间的感情确立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女子在夫妻关系中唯一可以自我主宰的行为。也只有透过这种感情唯一性的确立,才可以实现所谓的忠贞。《离婚》里面的爱姑,是鲁迅笔下最具光彩与局限性的女性之一,因为死活不跟看上小寡妇的丈夫离婚,她理直气壮地闹了三年,最后闹到县里的七大人那里去评理,她申述的理由有两点,其一她是“三茶六礼定来、花轿抬来”的,其二她为人妻时“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她践行了忠贞守礼的义务,因此不能接受被抛弃的命运。[7]257然而如前所述,在中国式传统夫妻关系当中,忠贞只是妻子的义务,却无法作为享受丈夫忠贞的理由。爱姑是不懂得所谓爱情的,她宁愿维持没有感情的婚姻,更不会用感情的唯一性来指斥丈夫的背叛。我们通常将爱姑的失败解释为不彻底的反抗精神和封建婚姻观念的残留,事实上,这种忍辱负重的婚姻观正意味着一种传统的妻性认知,她根本无意识主张情感的唯一性,她甚至不曾拥有过恋人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恋人性当中,性意识的自觉始终是一道禁区,迄今也未能完全跨越:纵然上个世纪20年代即有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90年代有陈染、林白的身体写作,可是为人妻者在这场关于身体的欲望书写中都意味深长地沉默着。一个无声的盟约在女性作家群中结成:个性解放是做女孩时候的事,妻子们若言说欲望,则是淫荡的娼妇行为。在不多的出轨故事中(如王安忆《锦绣谷之恋》),作家们总是将笔触更多地放在夫妻生活的精神枯槁和灵魂需求方面。该点与当代男性作家自《沉沦》以来持之以恒、大张旗鼓的性描写形成鲜明对照。甚至,男孩对女性世界的摸索和体验已然成为成长类小说的经典母题,并以此作为男孩认识世界的必经轨迹。而作为引渡者的女子,却仍旧沿袭了圣母和荡妇两种极端形象。然而,欲望是生而有之的,生命既存在于道德以前,则无论怎样与传统道德相背离,妻性中对性爱和谐的要求理应与恋爱中的精神需求站在同一层面。
然而也正是如此,恋人性在妻性中被彻底压抑直至成为一种禁忌。于男子而言,恋人性的主张意味着男女情感上的平等,甚至有女性凌驾男性情感之上的可能,比如女子可以因此要求男性同样坚守忠贞,这无疑是不符合作为私有财产的妻性特征的。因此男子总是会娶一个端庄贤淑的妻子,而后去娼妓处寻求放肆与媚惑。于女子而言,恋人性也是被自觉排斥的,她们总喜欢用娼妇、狐狸精等词语来彼此攻击,日久天长的妇德规驯使她们不能表露天性,而第三方则会以媚惑性让男子沉溺温柔乡,从而威胁到其千辛万苦用子嗣和泯灭天性的妻性换取的妻子身份。对于没有独立生存能力的女性而言,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为自己攫取更多的生存资源,由此引发了女性间亘久而自发的斗争——与其说是情感嫉妒,毋宁说是一场生存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并不仅存于妻妾之间,刘兰芝莫名被婆婆不喜,唐婉儿被婆婆迁怒,连完美妻子芸娘也被逐出家门,究其因,当是夫妻琴瑟和鸣之时,恋人性的流露遭到了扼杀——这里的扼杀者往往是婆婆。在烈女和思妇们日复一日的自我规驯中,以男女情感平等为基础的恋人性便是大逆不道,而正是通过妻妾与婆媳间无休止的自我争斗,女人们以相互规驯的方式,实现了男性对女性数千年的规驯与奴化,从而成为自我规驯。
三、出轨与嫉妒:妻性的缺失与补偿
作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雷雨》当中两个家庭、七个主要人物、三十年的恩怨在一场大雷雨中终结性的爆发,究竟谁是这场爆发的导火索?似乎也只有周繁漪。既然从周朴园那里既无法获得爱情更无法获得自由,她未曾泯灭的恋人的心便只有从继子周萍那里获得补偿,她甚至不顾一切地让周萍带她走;而当周萍因厌恶、恐惧而移情别恋后,其对恋人唯一性的要求使得她无法自控地跟踪、偷听并不计后果地揭发。面对这个被欲望和嫉妒之火燃烧的妻子、母亲和情妇,作者只有引来一场大雷雨才可以终止这场燃烧的蔓延。事实总是如此,爱与自由既然是天性,被压抑和苛刻剥夺处便总会有反抗,而以一己私情之迸发来反抗数千年的妇德礼教无疑是以卵击石。于是,便总有不甘心的女子,从为妻者晦暗无天日的生活中凿一个小孔,以欲望出轨的方式,或以转嫁嫉妒的方式,为自己失去的平等和缺失的恋人性进行补偿。
(一)关于出轨
阅读文学史时,吸引人们的永远是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打破命运常规的英雄,而在不多的女性书写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往往并非思妇或烈女,而是那些为博取一日欢愉、拼却一生休的“坏女人”们,例如周繁漪、花金子、梅珊或田小娥。这当中,唐传奇中步飞烟的命运悲剧当属典型。身为临淮武公业之妾,步飞烟善秦声、好文笔,容止纤丽,武公业却只一介莽夫,整日忙于公务。偏这女子有颗不安分的心,端秀有文才通晓风月的赵公子在墙头惊魂一瞥,便不要命地前来调情,便只能如此了。正如步飞烟自叙:“勿谓妾无玉洁松贞之志,放荡如斯,自以郎之风调,不能自顾。”[8114]然而正如所有偷香窃玉的男子一样,这有风调的公子事实上给不了步飞烟任何保证:事发之时,跳墙而去;步飞烟被鞭挞致死后,遂变服更名、远窜江浙之间。他所需求和所能给予的不过是肉体的欢愉和精神的慰藉——步飞烟不会不知,因为这正是她想要而从夫君那里无法获得的。在为妻者压抑的恋人性中,性意识作为永久禁区是无法言说的,曹七巧之恋上小叔子(张爱玲《金锁记》),菊豆之与本家侄子偷情(刘恒《伏羲伏羲》),“我奶奶”心甘情愿地被土匪掠走(莫言《红高粱》),都是无法压抑的情和欲在燃烧。而在女子所有的罪孽中,肉体出轨是最不能被容忍的,因为它公然蔑视了忠贞,张扬了女子天生亦有的平等的肉体和灵魂需求,是对男女依附性关系不可饶恕的僭越。无论是在文本还是生活中,其所招致的惩罚都会格外残酷。
值得关注的是:也许并非巧合,在出轨的女子中,为妾者多过为妻者。或许,身为正妻,其被规驯和自我规驯的程度比起那些无法成为正妻的妾妓们来说,总要更深广一些。只要不成为弃妇,妻子们守着婚姻的空壳也可如此这般地过下去,而妾妓们作为性、生育和劳动力的提供者,是享受不到“妇与夫齐也”的地位的,其所承受的妻性角色的压抑自然也少得多。然而,偏偏是在这些女子身上,绽放了女子们为不可压抑的爱而迸发出的夺目的灵魂之美。纵被鞭打得鲜血淋漓,步飞烟那句荡气回肠的“生既相爱,死亦何恨”当可作为所有为爱出轨而死之女性的墓志铭。然而,同为女性,这种差异往往会带来的另一重结局便是嫉妒。
(二)关于嫉妒
某种意义上,最应该被原谅的女子便是妒妇,因为她无非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情感独占欲。然而作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反过来对妻子的拥有者表现出独占欲,这是不符合拥有者的情感逻辑的。因此妒妇往往是被抨击的对象,民间表述中的“悍妇”之悍,大抵也以嫉妒为主要特征。除却文本中的步飞烟之外,唐朝历史上另一位真实存在的奇女子是鱼玄机。她三番两次被男子辜负,无非是因其过于强烈的恋人性和对自身才情的完全张扬,虽然吸引男子的也正是这些,然而亦是这本自天性却背离传统妻性的个性要求,使鱼玄机最终走上出家为尼、放浪形骸之路。若干年后,她又因一桩莫须有的偷情而与婢女争风吃醋直至被打死,再次证实了这个女子对情感独占性的强烈渴求——纵然是可以理解的,却毕竟造成了自己和另一个无辜女子的双重毁灭。独自奔赴刑场之际,鱼玄机或许不曾想到,正是在夫君李亿那里始终不曾获得的妻性权利,使得她以极端的方式渴望对日后的男人实现情感上的彻底占有;而她对年轻婢女的莫名嫉妒,与当初被李亿正妻的排斥又是如出一辙的。为妻者无权享受恋人性,便会本能地对利用这种恋人性来谋取男性情感的女性深感恐惧。于是妒妇就产生了。所不同的是,李亿之妻对鱼玄机的嫉妒不仅有感情威胁,还有财产威胁。因此这样的嫉妒在妻与妾之间是亘久存在的。而中国历史上,最浩大而持久的妻妾之争无疑来自皇室宫闱。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妒妇之一,多年未育的陈皇后无法容忍其他女人来分占她注定要被分占的夫君,因此争风吃醋。这里她不仅未能以生养完成妻性角色的首要任务,还以张扬的恋人性挑战夫君的绝对支配地位,其被冷弃于长门之内便是必然。即便呈上幽怨深婉、情味隽永的《长门赋》,也无法唤回昔日的君恩了。回想金屋藏娇时的两小无猜,感慨之余我们更能从这个典型故事中,从古中国拥有最多女人为私有财产的皇帝身上,领略到何谓典型的中国式夫妻关系。很多年后,《妻妾成群》里的四位太太为了瘦弱阳痿的陈佐千老爷把陈家后花园里稀薄的空气搅得水花四溅时,我们嗅到的是数千年来,失去经济权无法享有和张扬爱情的妻妾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只是这恐惧被缺失的恋人性放大,以嫉妒的方式畸形地张扬出来,使得本源自男权压迫的恐惧演变为同性间浩大的生存斗争。
同属于这一斗争的还有婆媳之争。在只有为人母才可以坐稳妻子身份的女性生涯中,妻子往往被认为是从女孩过渡到母亲角色的、极其短暂可以被忽略的中间存在。不过因恪守缺失的妻性角色而终于熬成婆婆的女子,其对妻性的认知多半已是自我规驯的了。然而缺失的妻性终究需要弥补,往往便是对子女的过分情感依赖。曹七巧无情地摧毁一双儿女的幸福,是因为她既不能从病榻上的丈夫那里获得妻性之爱,亦无法从觊觎其财产的小叔子那里获得出轨情爱的弥补,其对儿女的情感控制,便不可避免地走入歧途。如果说母爱是一种完全给予的、无条件的包容之爱,那么妻爱则是一种付出之后索取平等回报的排他之爱。兼具母亲和妻子双重身份的女子,往往会将这种排他性放大,坚决抵制来自妾侍和儿媳对其丈夫与儿子的侵占,因为这两个男子都是她要抓住作为稳定自身根基的存在。很多时候,如果丈夫的心难以抓住,那么儿子则成为母亲唯一的同盟,会迸发出更强大的独占欲。《妻妾成群》里面,二太太卓云没有儿子,于是老爷便是她必须抓住的唯一砝码,因此便乐此不疲地与三太太、四太太斗,以控制和扼杀一切可能夺走老爷的女人;拥有儿子的大太太毓如,本对老爷另娶了三房姨太太置若罔闻,然而一俟四姨太企图与儿子走近,她便奋起怒叱。无论如何,多数中国父母老来是靠儿子养活的,儿媳作为一个入侵者,却要理所当然地分占儿子的爱心和财产,成为敌人便是理所当然的。该点在寡母身上,往往体现得更为突出。
巴金的《寒夜》里,一对在五四思潮中自由恋爱而共同生活的夫妇汪文宣和曾树生,却在无休止的婆媳矛盾和战争生活的重压之下走向了妻离子散的结局。在淡化战争背景后考察整个文本,曾树生离开汪文宣绝不只是因为汪的肺病、孩子的冷漠、生活的艰辛,抑或另一个男人的追求,而是永不可解的婆媳矛盾。来自婆婆的无止境的仇恨使得为了爱而容忍的这一切病痛与贫穷都失去了意义,而妻性意识始终未曾泯灭的曾树生最终选择了在寒夜里独自出走。意味深长的是,汪母对儿媳厌弃的最大理由仅仅是:她不是儿子明媒正娶过来的,因此便是个“娼妇”。在这种不可解释的仇恨中,隐藏着汪母对自己明媒正娶身份的骄傲,而这骄傲的底气则源于深久的为其所认同的男权文化——就像嘲笑祥林嫂再嫁的柳妈,其嘲笑中传达的正是对自己从一而终的骄傲。作为一个被规驯和自我规驯的传统女性,汪母以男权代言人的姿态,鄙夷儿媳以恋人的方式成为儿子的伴侣,恐惧儿媳可以抛头露面地工作挣钱从而与儿子平起平坐,在一辈子的压抑与自我压抑之后,汪母缺失的妻性以对儿子情感的过度占有方式进行自我弥补。在逼得儿媳出走的同时,也一并损伤了自己的母性。在母性的宽容中,可以容忍夫君不忠、儿子不孝,但绝不包括对儿媳的妻性主张的宽容。林妹妹动辄闹小性子,大抵是对处处留情的宝玉的一种警醒,然而也正是这种绝无包容、排他的恋人性的张扬,早早地在贾母、王夫人乃至袭人那里种下了眼中钉。如前所言,芸娘只因男扮女装与沈复出游便被公婆逐出家门,刘兰芝和唐婉儿则因莫名的“不喜”便被休掉,想来也无非是无法明说的对儿媳未曾压抑的恋人性的厌弃。之所以杜绝儿媳的恋人性,亦是从根本上杜绝其在情感上与儿子平起平坐的可能。从规驯到自我规驯,男权始终是稳定的,而稳定的男权使得妻性的缺失亦是恒久的,这就使得为情感与财产占有而起的婆媳之争卷入反复循环、不可自解的漩涡。
四、结语
对于男性来说,其生活目标是延伸到家庭以外的世界里,家庭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世界的一个停泊处,但对于多数女性来讲,家就是其成长的归宿、世俗的命运和生活的现实。如果说男人首先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者,那么女人则首先被看作是一个养育者。[9]而生养的痛苦是不被视作与生产者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生物的本能,从而永远地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尊严。也因此在妻性生活中,平等成为一种想象中的奢望。换句话说,女性得以被命名和确认身份,往往是通过其家庭角色即妻性和母性角色的实现而被指认的。而既然家庭只是世界中的小小客体,作为家庭附属分子的女性便只能是主持世界之男性的微末依附者。
从规驯到自我规驯,中国式妻子们走的是一条漫长而鲜血淋漓的道路。这当中,有欲望出轨者为缺失的恋人性而斗争,有妻性自觉者为可能的平等权而努力。无论是烈女还是娼妇、妒妇或是出轨者,她们所渴求和所缺失的,无非是一种天性释放的、与夫性平等的妻性角色。这里我们并非为出轨偷情者寻找借口,或是为不可解的婆媳矛盾找到解决之径,现代社会金钱权力的上升和人类欲望无底限的释放,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益发扑朔迷离,然从妻性缺失的角度切入,或许可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和谐夫妻情感的营造,缓解出轨的几率;亦可通过女性独立生存能力和情感处理能力的提升,缓解婆媳间剑拔弩张的整体氛围。从经济独立到情感独立,婚姻当中一场真正的女性解放,当是将女性从规驯和自我规驯中释放出来,让每一个妻子,成为真正的妻子。
[1]隋清娥.论鲁迅与钱钟书小说对中国女人“无妻性”问题的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4,(2).
[2]许慎.说文解字-女部[M].上海:中华书局,1985.
[3]浮生六记英译自序,林语堂文选(下)[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
[4]曹雪芹.石头记(列宁格勒本,全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十月出版社,2011.
[6]闻一多对“联大女同学会”所作题为《妇女解放问题》的演讲[A].自由之歌——闻一多精选集[C].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7]鲁迅.离婚[A].鲁迅选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8]皇甫枚.飞烟传[A].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7.
[9]高小弘.“家”神话坍塌下的女性成长[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