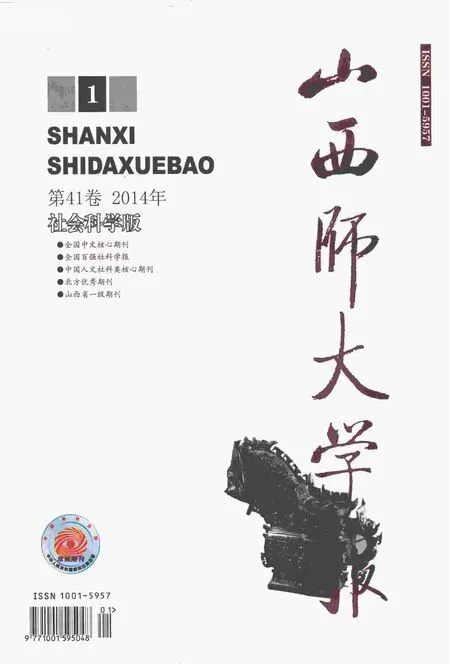夏庭芝《青楼集》之戏曲美学思想
2014-04-10梁晓萍
梁 晓 萍
(山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4)
夏庭芝(约1300—1375年),字伯和,一作百和,号雪蓑,又作雪蓑钓隐、雪蓑渔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原为云间望族,藏书极富,曾名其书斋“自怡悦斋”。元末变乱,隐居泗泾,改书斋名为“疑梦轩”。从其友人张择所作的《青楼集叙》[1]6可知:夏庭芝出生于富贵之书香门第,二十来岁时,相信术士之预言,广散家产。夏家藏书甚多,然大半毁于战乱。松江之变后,夏庭芝举家迁居至松江城北的泗泾,过起了隐居生活。与夏庭芝结交的有当时有名的戏曲家张鸣善、朱凯、邾经、钟嗣成等。夏氏有文才,能词曲,然大多散失,仅有《青楼集》存世。
《青楼集》是夏庭芝“追忆曩时诸伶姓氏而集”的一本著作,该书记载了元代一些歌妓的艺海生涯,记录了其时大都、杭州、平阳等几个大城市一百余位女演员和三十余位男演员的生活片断,以及戏曲作家、散曲作家、诗人和“名公士夫”等五十余人的事绩。《青楼集》的主要价值在戏曲史方面,这方面的论析不乏其文,本文则欲探讨其在戏曲美学方面的几点价值。
一、关注演员的生存境遇
《青楼集》的美学价值首先体现在对于戏曲演出主体——演员生存境遇的深切观照上。美学不是抽离了人的形而上思索,它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特质,它关注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关注人的生命际遇以及与之相关的幸福指数,强调人是美学真正的出发点和归宿;演员是戏曲活动的关键环节,作家只为戏曲接近观众提供了一个文本,要使这一文本变成真正的作品,实现其审美价值,必须经过演员的二度创作。因此,关注身处弱势的戏曲演员的生存境遇,同情其生命遭际的《青楼集》便折射出夏庭芝一定的审美意识与美学思想。
元代戏曲演员地位低下,身份卑微,其婚配、服饰、应试以及行动空间等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元典章》规定,“乐人只娶乐人”,其他人不准与乐人结婚,为官者倘若娶卑贱之戏子为妻,便会遭到来自统治者内部的讥刺与攻击:如邓州王同知娶了王金带,“有谮之于伯颜太师,欲取入教坊承应”;除为西台御史的贾伯坚因同山东名姝金莺儿“甚昵”而“被劾而去”[2]24,36。即使嫁入官宦人家的这些演员格外忠贞,甚至在丈夫死后依然坚守贞节,也不能驱除周围人鄙视的眼光。这就将乐人圈缩在一个狭窄的活动范围,不让他们与外界有更多的联系,轻视意味不可谓不浓。《元史·顺帝纪》还记载了当时对乐人穿戴打扮作的明确规定:“禁倡优盛服,许男子裹青巾,妇女服紫衣,不许戴笠乘马”,不准佩带“金面钗钏”,元律令甚至规定不准艺人在路中间行走,只许在路边走路。这样的规定,与在犯人脸上刺字何异?《元史·选举志》则明文规定:“倡优之家,及患废疾,若犯十恶、奸盗之人,不许应试。”[2]6将优人与恶、盗之人同视,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剥夺了优人进阶的机会,使其低下的地位永远难以改变。
戏曲演员身心常遭统治者欺压与束缚,夏庭芝却不顾世俗之偏见,以充满关怀的目光关注其生存命运。《青楼集》多处记录了杂剧演员的悲惨境遇,集中体现为对女演员常常不尽如人意的婚姻生活的同情。女演员们生活飘泊不定,辗转奔波,她们常常要离开自己的家乡,在流浪中谋生,流浪使她们具有了强烈的家园意识,因此,与心仪的男子结婚,过上稳定的生活便成为她们的梦想。然而如此简单的渴求对于她们来说却常常是一种奢望。女演员有时也会被元蒙统治者纳为侍妾,过着看似稳定的生活,如喜春景、金兽头、张玉莲等分别被张子友平章、贯只歌平章、爱林经历置为侧室,王巧儿、汪怜怜、李真童分别做了陈云峤、涅古伯经历、达天山检校的小妾。不过,这些嫁与元蒙官僚贵族家的女演员,因其自身卑下的身份、世俗鄙夷的目光,以及小妾尴尬的家庭地位,她们“必遭凌辱”的结局在一开始便已注定:她们只能或守寡如王巧儿,或为尼如汪怜怜,或为道如李真童,或者重操旧业,流荡江湖,如金兽头、张玉莲、顾山山等。有时候,女演员会与男演员进行内部婚配,较之被纳为侍妾,她们的幸福指数也许会因在家庭中地位的相对平等而上升,然而也有诸多不幸的存在。如小玉梅的女儿匾匾“资格娇冶,资性聪明”,嫁与末泥安太平后,“常郁郁而卒”;杨买奴“美姿容,善讴唱”,嫁给乐人查查鬼后,“憔悴而死”;乐人李四之妻刘婆惜三番五次地私奔官人。[1]30,38另外,《青楼集》还记载了一些优秀女演员薄命的事实,如金陵名姝樊香歌,“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可谓色艺俱佳,又颇具智慧,然“寿不永”,二十三岁便离开人世;赵梅哥,“美姿色,善歌舞”,名气很高,然而寿亦不永,她们的遭遇都如白居易所言:“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销歇,塞北花,江南雪”。
可见,夏庭芝没有如其他文人一般,仅乐道于文人们的艳遇和女演员的姿容,而是真实地记录了这些杂剧女演员的不幸经历,将同情的目光投向这群以往少有人关注的伶人身上。夏庭芝这种对于戏曲女演员薄命身世的慨叹,对于美好生命却深陷泥淖的不公命运的愤懑,正是建立在对于她们同情、理解基础之上的一种赞美,体现出一种积极的人文关怀和非中和的审美价值取向,对此,蓝凡的话颇有见地:“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不去赞扬当时的达官贵人,‘硕氏巨贤’,反而‘记其贱者末者’,称赏这些不入经、史、子、集的梨园女伶,在当时来说是很有些胆识的,《青楼集》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史料价值,其从中反映出来的戏剧审美见解,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元代末期的戏剧审美倾向和风神。”[3]
二、比较自觉的舞台表演意识
《青楼集》的美学思想还体现为较强的戏曲舞台表演意识,这是从戏曲接受主体角度着眼而生发的一种美学思想。有元一代,舞台表演意识已于胡祗遹的“九美说”中初露端倪,与之相较,夏庭芝《青楼集》中的舞台意识则更为深刻,这首先表现在对演员表演才能的重视方面。“天下歌舞之妓,何啻亿万,而色艺表表在人耳目者,固不多也。”能录入《青楼集》中的演员,挑选标准首先是演员的表演才能,看其在舞台上能否具有引人的本领,要求其或者扮演某一种角色无人能继,或者擅长某一剧种独步当行,或者歌声绝伦,或者弹奏超人,或者步线行针。
杂剧人物的脚色化,是中国古代戏曲舞台表演体制的核心,也是戏曲成熟的一个标志。《青楼集》很重视这一点,记录了元代戏曲舞台上不少女演员的扮演专长,表达了对她们技术特长的由衷欣赏,如擅长闺怨杂剧的天然秀,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的珠帘秀,长于驾头的南春宴,旦末双全的赵偏惜,颇擅花旦的李娇儿、张奔儿等,都为夏庭芝所激赏。还有一些演员在杂剧或某一剧种的演唱中表表于当时,《青楼集》精心记录并给予了热情的褒奖,如赞扬司燕奴精于杂剧,声名与宋郭相颉颃;称赞国玉乘长于绿林杂剧,尤善谈谑,于京师有名;赞扬天锡秀擅长绿林杂剧,尽管足很小,步开却甚壮等。
不仅角色表演优秀和擅长某一剧种的演员受到青睐,对于歌声无与伦比的女演员,《青楼集》亦不吝其辞,予以赞赏,如赞扬赛帘秀“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刘燕歌“善歌舞”,小娥秀“善小唱,能曼词”[1]26,20,21,31。观众赏戏,常被表述为“听戏”,可见,“听”在戏曲接受中的重要作用,好的声音常常使观众留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重视演唱便是重视接受主体的感受,也是重视戏曲舞台特性的重要表征。《青楼集》对于声音能遏住行云的赛帘秀、善于歌唱的刘燕歌和小娥秀、能依循旧腔古韵而演唱旧曲的张玉莲等的赞扬,都为这方面的具体体现。
善于弹奏乐器或擅长步线行针亦为《青楼集》记载的重要标尺,它同样是其重视戏曲舞台特性的具体体现。演员倘能弹奏一段动人的乐曲,或者“步线行针,不差毫发”,都可以使观众锁定戏场,不肯轻易离去。如擅长弹奏琵琶的于四姐,“搊筝合唱、鲜有其比”的金莺儿,中年双目失明、然比有目者更能流畅娴熟地移步换形、一招一式均引人入胜的赛帘秀等,均是因其胜于旁人的表演技能,以及所具有的非凡舞台效果,才引起了夏庭芝浓厚的兴趣。
夏庭芝对演员舞台表演才能的重视,更突出地表现在对一些“色中或差”、而“艺却超绝”演员的赞美上。“姿色不逾中人”而艺却超绝一时的喜春景,身体有些佝偻而长于杂剧的王奔儿,“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的王玉梅,貌稍显丑陋,却声遏行云、能在舞台上谈笑风生的陈婆惜等,若是以貌取人,她们尽管可以站在舞台上,却不一定进入《青楼集》被载入史册,然而夏庭芝却违反世俗之“常规”,以才论人。夏庭芝的言语兴奋点显然落在女伶擅长的技艺方面,对她们独特的表演才能和炉火纯青的技艺发自内心地加以赞赏,甚至忽略其“色”的不足,这显然是建立在对戏曲舞台表演特性认识基础之上且具有人文情怀的一种独特观照。
夏庭芝《青楼集》不仅重视演员的表演才能,还欣赏演员其他方面的才艺,如超群的记忆力、广博的见识力、过人的理解力、敏捷的反应力和不凡的作诗能力,等等。赋性聪慧的李芝秀能记杂剧三百余段;记忆力超群的小春宴则在演出前任看官选拣曲目;反应机敏的樊香歌颇多涉猎书史;还有刘婆惜、张怡云、刘燕歌等,思维敏捷,七步成诗,才华横溢,光彩照人,正是凭借这些舞台之外的功夫与能力,女演员们才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赞许。进一步追问,夏庭芝何以记录其高妙的记忆力?原来,记忆力是观众对演员的一种期望,或者说,对演员记性的高要求正是基于对观众多样性需求的一种满足,夏庭芝充分认识到这些有益于舞台表演的更深层次才华的重要性,重视能够为演员表演增光添彩的其他才艺,这又一次体现了他在戏曲审美方面比较自觉的舞台意识。
三、戏曲关涉风化
前面两点是立足于戏曲表演与接受主体而形成的戏曲美学思想,这一点则关涉戏曲的功能。戏曲艺术的生命与舞台息息相关,亦与执政者的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戏曲在其成长初期,常常需要承载较之后来更多的风化功能,文人们也正是基于“诗言志”的认识以及治世的长远目标,从而一次又一次强调戏曲的教化作用。元初胡祗遹曾强调戏曲的审美教化作用,夏庭芝也主张戏曲要能够有益风化,《青楼集》曰:“唐时有传奇,皆文人所编,犹野史也,但资谈笑耳;宋之戏文乃有唱念,有诨;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又非唐之传奇、宋之戏文、金之院本所可同日语矣。”[1]7唐传奇“但资谈笑耳”,宋之戏文、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这些都只为观众提供了一些解乏的笑料。元杂剧则不然,它有着丰富的教化内容和自觉的教化目标,或教臣子忠于国君,或教儿子孝敬父母,或教女子辅佐丈夫,或教兄弟、朋友互相礼让。总之,元杂剧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符合儒家“诗”之为诗的核心价值,也正是以此为标准,夏庭芝将元杂剧与唐传奇、宋戏文、金院本区别了开来。
以此为据,在记录女伶时,夏庭芝对那些色艺之外的、可能影响演员表演和演出效果的德性也格外关注,如樊事真“京师名妓也。周仲宏参议嬖之,周归江南,樊饮饯于齐化门外,周曰:‘别后善自保持,毋贻他人之诮。’樊以酒酹地而誓曰:‘妾若负君,当刳一目以谢君子。’亡何有权豪子来,其母既迫於势,又利其财,樊则始毅然,终不获已。后周来京师,樊相语曰:‘别后非不欲保持,卒为豪势所逼,昔日之誓,岂徒设哉?’乃抽金篦刺左目,血流遍地。”又如:“陈卒,王(巧儿)与正室铁,皆能守其家业,人多所称述云。”[1]25,27不违当初誓言而自刺左目的樊事真、与正室相安无事并一起守卫家业的王巧儿,都受到时人的称赞,并为夏庭芝《青楼集》所载。这种单向度地歌颂女伶忠心而不论对方表现如何的观念,确有其狭隘的一面,以今天女性主义的观点看,它从正面引导的角度为女性套上了死守贞节的枷锁,使其遵守规约,不得自寻自由。不过,若还原历史语境,从表演者乃施教主体之一的角度讲,则这种记载确实具有一定的审美教化功能。
《青楼集》之于戏曲教化功能的提倡是基于提升戏曲社会地位的一种理解。与在高雅殿堂里占据着显赫地位的诗文相比,无论是孕育与诞生戏曲的宋金时代,还是戏曲之光开始耀眼的元代,戏曲的地位都不容乐观,我们可以从元曲作家大都出入勾栏、瓦舍的经历中约略见出。夏庭芝生活的元代,以帝王为首的统治者对戏曲的禁毁远远大于提倡,而正统文人则往往把戏曲当作诗文之外的“小道末技”加以鄙夷,出于对戏曲社会功能的基本认识,他们形成了轻视戏曲的顽固态度,并制定了禁止、销毁的政策。那么,缘于对戏曲别样的理解,记录优人生活、让无名之人成为永恒存在的《青楼集》,恰好以一种别具一格的选择和违背正统文化的践行,以及贴近传统审美的文学功能观,就具有了先驱者和叛逆者的意味,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意味。
曾为夏庭芝老师的杨维桢写有《题夏伯和自怡悦手卷》一诗云:“道人家住在云间,日日赖云相破颜。晓风不做巫峡雨,玉气浑似蓝田山。中岳外史见图画,三茅山人应往还。我亦挂冠神武去,超堂归扣物云关。”这首诗展现了一个超然物外、纵情山水、自得其乐的夏庭芝形象。也正是有此种淡泊名利的精神气质,夏氏《青楼集》能为“贱者末者”立传,称赞她们精湛的技艺、出众的才华及其身为下贱却不断奋进的精神,其所记之事,与经史无关,体现出一种非中和的美学思想。夏庭芝视戏曲为一种关涉三种主体的活动,认识到接受主体之于戏曲的重要作用,表现出较为明晰的舞台表演意识。他对演员演唱能力、扮演角色能力、舞蹈能力、记忆能力、领悟能力、应辨能力等的推崇,都与此审美思想有关。徐大军认为,夏庭芝称“杂剧”而不是如周德清、杨维桢等一样称“传奇”,本身就表明了夏庭芝将之视作一种伎艺,而非文本。[4]舞台表演,是戏曲得以生存的关键所在,尽管夏庭芝还未从理论上明确提出,但他的讨论对后人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意义。直到今天,学人们依然会不断提及夏氏在舞台表演方面的审美先见。夏庭芝《青楼集》之于元代杂剧,一方面突破以往人格审美只限个别圣贤、少数英雄和士大夫的范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出身低贱,功业难以论及而才华却别具一格的女伶,表现出不以儒者是非为标准的新型美学思想;另一方面囿于传统诗教,强调戏曲要关涉风化,遵守礼义,能够对于统治秩序的巩固起到一定作用,表现出承继中国美学思想史上基于政治而形成的“德”与“和”的认识观念,成为这一思想链条上重要的一环。
[1] 中央戏曲研究院编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2] 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蓝凡.简论夏庭芝的戏曲论著《青楼集》[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
[4] 徐大军.明人“传奇”称名的观念基础及其渊源[EB/OL] .http://www.xiju.net/view_con.asp?id=2641.html,2008- 09-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