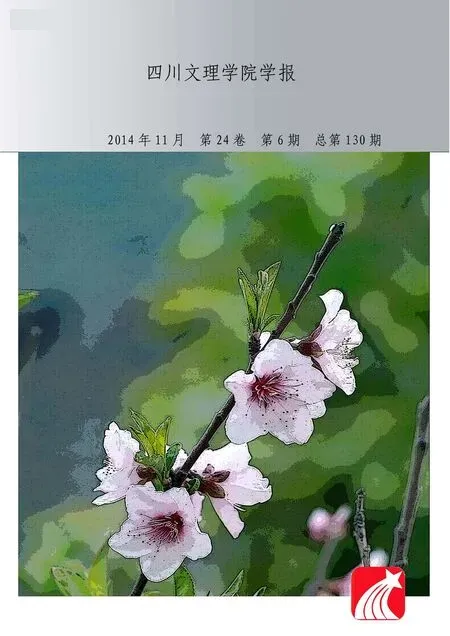胥健在《岁月浅吟》中呈现出的生命境界略论
2014-04-10范潇兮
范潇兮
(武警警官学院 人文社科系,四川 成都610213)
自从捧读胥健先生的词集《岁月浅吟》后,有两个悬疑长久萦绕于心。一是,时与空的意义。当年,孔夫子面对滔滔大江发出了“逝者如斯夫”的感慨,时间的无情化成了哲人的千古浩叹;后来,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发出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追问,空间的无尽凝聚为诗人的硕大问号;而《岁月浅吟》的作者将在时间与空间的张力中,如何抒写他的巴渠怀想和人生感悟呢?二是,诗与词的意义。作为具有抒情传统的中华文化,韵文源远流长而绵延至今,在诗词歌赋里,其中诗与词是韵文的主流,而“诗”无疑又是抒情文学的正宗,当今写“诗”普遍成为文人雅士和商人官员的爱好,而作者为何醉心于填“词”?进而言之,胥健先生的生花妙笔,将如何拉开生活与艺术的张力之弓弦,穿越时事的纷扰喧嚣、时代的缤纷色彩和时间的幽邈烟云,带领读者去触摸生活的真相、感受生存的真实和聆听生命的真谛,从而和我们一道感受充实而丰富、和谐而美妙的诗意人生。
一、在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张力中,彰显诗意的和谐
《岁月浅吟》既然为“词集”,那一定是沿袭宋词的套路和格式,旧瓶装新酒,推陈而出新。果真如此吗?但见开篇《自序》道“吾闲品古调新韵,宋词却犹鉴瑰宝。”以宋词为瑰宝借鉴,师法古典,得其精神,声调与格调的形式虽为古体,然意韵与神韵的内容却是新声。诗词的语言是最具艺术魅力的,它既具有一般语言的本质属性,又有着诗词这种特殊体裁所决定的特殊功能。[1]那么,词人又将如何在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张力中,给我们生长出一簇盛开的艳丽奇葩,并演绎出一段从古到今的“穿越”传奇呢?
诗歌和其他文学体裁相比,在本质意义上是内容融注于形式的艺术,既表现为分行排列的体裁形式,也表现为遣词造句的语言形式。一是,就体裁而言,如果说,近体诗或五言、或七言因太拘谨而呆板,白话诗如沫若、如艾青则太放纵而直白,似乎惟有“长短句”的宋词却兼具二者之长而摒弃二者之短,即它在体裁上既讲求字句规则和声律要求,又在语言上句式参差,平仄起伏。我想这就是作为诗歌艺术的宋词的形式魅力之所在吧。二是,就语言而言,与其说诗歌是形式艺术的典范,不如说是语言艺术的形式典范,因此,讲究语言美的锤炼词语、变幻结构、注重音韵、营造意境和运用象征的修辞艺术,就不能不说是诗歌与散文的最大区别;而宋词本自于勾栏瓦肆的唱和,与超乎文人雅士的唐诗和歌榭舞台的元曲的最大特点,正是它在语言上下里巴人风格的通俗易懂和词曲上便于传习演唱旋律的朗朗上口。
要在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张力中,彰显诗意的和谐,就得体裁上的于法度中富有变化,在变化中寻求规律,语言上的于通俗中蕴含高雅,在高雅中体现率真,这种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张力,既是“词体诗”由整句到散句的美学魅力的华丽现身,也是“长短句”从古代到现代的艺术风采的粲然绽放。我国古代有“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之说。诗的语言应该是形象鲜明的,但单纯形象还不等于就是画意,而是指画意的背后还隐藏着深远的境界。可以说意境美就是神韵之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又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2]想必胥健先生是颇得个中滋味和深领其中精髓的。敢于在格式的固定和语言的灵动中,于对立中求得内在的统一,在张力处寻觅诗意的和谐。《岁月浅吟》中的所有词牌多合体式,所写语言既古典雅致,又现代通畅。如《蝶恋花·大巴山上诗相会》中的 “巴山夜雨骚人泪”,《满江红·龙潭怀古》中的“伐纣助周歌与舞”,《清平乐·北湖观雪》中的“玉树琼花风曳曳”,《蝶恋花·悼恩师》中的“花繁今日恩何报”,《虞美人·罗马访古》中的 “西风残照凯旋门”,《醉花间·铁山美》中的“岚风催蓓蕾”。尤其是颇有词人品格和品位的《渔家傲·秋荷》:
雅丽常遭寒雨苦,清香却引群芳妒,玉洁曾同污浊住,前缘误,绿减红衰伤自顾。
为有品高多痛楚,宁枯不肯随流俗,冷月秋风犹自舞,虽迟暮,凌波摇曳香如故。
传统的宋词格式,古典的词牌韵律,高雅的遣词造句,优美的行文用语,经典的体裁与灵活的语言,固定的词牌与灵动的词句,表现崭新的时代精神和高洁的人生品位,水乳交融,相得益彰,超乎诗境而又蕴含诗情的诗意和谐,体现得圆融无碍而生机盎然,彰显得淋漓尽致而生趣怡然。
二、在豪放与婉约的情感张力中,感受艺术的和谐
众所周知,豪放与婉约是宋词的两大情感类型而形成的艺术风格,也是后人评说艺术类型的重要参照。尽管《岁月浅吟》不能简单地划入哪一流派,但在抒发情感方面,以彰显时代特色、反映重大事件的豪放为主,辅之以叙写人生感怀、记录生活旅痕的婉约。在这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的艺术表现上,我们不难窥见词人进取有为的人生姿态、多愁善感的生活情味,更领略到了艺术创造臻于和谐境界的无穷魅力。
文学和文章相比,其本质意义或根本特性在于它的审美性,而作为文学宝塔上明珠的诗歌其审美性的精髓就是抒情性,可以说抒情性是诗歌之于其他艺术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文心雕龙》说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3]“喜怒哀惧爱恶欲”之七情固然丰富,然情感的美学结构不外是阳刚与阴柔的二元互补,情感的艺术原理也大概是豪放与婉约两种类型。这典型体现在宋词的美学风貌和艺术风格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泾渭分明而又特色鲜明的风格,我们才记住了诸如豪放派苏东坡的恢弘、辛弃疾的豪迈和陆游的悲壮,还有婉约派李清照的委婉、温庭筠的绮丽和柳永的柔靡。由于词牌对于诗歌情感风格的规定性存在,因此古今的词作者几乎都难逃脱更不能超越这“潜在”的规定,要么显示豪放派的阳刚之美,要么展示婉约派的阴柔之情。
古代的孔夫子有“兴观群怨”的规范,近代的黄遵宪有“诗界革命”的倡导,诗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的宏大抒情已经承载着过多的使命了。那么词呢?当胥健先生一旦走进这座缤纷的花园,徜徉在这种似乎游离于韵文传统之外“诗之余”的小径上,他激情如火,柔情似水。他的豪放之情倾泻在了达州天然气开发的“气喷涌,正横空出世,中国气都”的豪迈;表现在了汶川的抗震救灾的“三军奋勇,同胞团结,亿众血犹热”的豪壮。他的婉约之情倾诉在了寄同窗的“桃花应红,枫叶应红”的意象,流露在了贺生日的“似水柔情,把酒人先醉”的深情。这类豪放和婉约的词章不论是前贤还是今儒都屡见不鲜,而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词作者,同在一首词中不但能拉开豪放与婉约的张力,而且能寻求二者的诗意和谐,将水火不相容的两类情感熔铸于一体。试看《浪淘沙·“九三”抗洪感赋》:
天漏史空前,雨撼巴山,汪洋一片浪滔天,地陷岩崩城灭顶,岭断湖悬。
众志挽狂澜,后禹新篇,塔沱璀璨舞翩跹,漫步洲河洪虐处,花好月圆。
上阙描摹洪水景况,十万火急,忧心如焚;下阙既有“众志挽狂澜”的豪情万丈,又有“璀璨舞翩跹”的娇媚几许,尤其是“花好月圆”将喷涌的激情融为一泓深情、千种风情和万般柔情。
三、在从政与为文的角色张力中,体验生命的和谐
在达州,乃至川东,说到胥健,人们的第一印象是“五品芝麻”,近年来,文人胥健的形象逐渐呈现文坛。就在人们纳闷官员与文人是否兼容的时候,回溯历史,我们欣喜的发现,从政与为文并非水火不相容,集官员与文人于一体的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屈原、曹操、杜甫、韩愈、苏轼,被贬通州的元稹更是达州历史上官位与诗名皆登峰造极的人物。
古代中国的官员们一生浓浓地浸染着诗礼文化,从战国时代外交的“不学诗无以言”到以后民间教育的声律启蒙,诗意渗透了几乎每一个官员的骨髓,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张爱萍等老一代革命家,以后则鲜有所闻了。在这其中写“诗”与填“词”在彰显他们人格结构和生命意识。所谓生命意识,即是人类对自我存在价值的反思与认识。一方面受时代感发,让作品充分发挥出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人类生命本身往往也构成为创作意识的内省对象,从自然、生命、人生等方面,展现出个体的探求与悲欢。[4]胥健的诗词,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出此两类审美意识的创作典范。就本文探讨的词的创作而言,这里存在着一个文学体裁与创作主体“二位一体”的对应结构。众所周知,成就于宋代的词既有体式和声律的规定性,也有选材和表达的灵活性,当一个文人式的官员选择了词的表现方式,也许看起来是偶然性的个人行为,但是背后蕴含着创作主体二元化的人格结构,即作为规定性格式的“词牌”与他的官员身份所要求的秩序与守常不谋而合,作为灵活性创作的“诗性”又与他的文人气质所具有的率性与洒脱天然相通。
“吾虽是五品芝麻,诗梦却情结少小。吾宦海卅年浮游,雅趣却寻觅到老。”这首《自序》的开篇四句生动地道出了他的官员身份和文人情趣。诚然,前者是组织培养和人民信任的结果;当然,后者是自我修炼和创作凝练的成果,他从学生时代起钟情诗词,入仕后依然笔耕不辍,每每公务之余、游览之后,他便神游诗境,抒情言志。也许,在常人眼中官员舞文弄墨要么附庸风雅,要么消遣时光,然而,于胥健先生而言,不管他的职级如何迁升,职位如何变化,正如他在《自序》中反复自述的“吾”:“闲品古调新韵”、“咏叹激情所致”、“崇尚诗词格律”、“吐真直白明快”。他写词与其说是要表达一种情志,不如说是要流露一腔情怀,更剀切地说是要为从政者提倡一种艺术风尚和美学情怀。正是如此,就是政务活动,他也能写出《沁园春·天然气开发之歌》、《一剪梅·天地人间正气弘》的词章,即使学习考察,他还能发出《画堂春·走进中央党校》、《采桑子·重走朱毛挑粮小道》的歌吟,哪怕邪恶阴暗,他也竟能抒发《如梦令·[清]东陵叹》、《虞美人·美国赌城印象》的感慨,更何况春花秋月的景色、良辰美景的际遇和丝竹管弦的美妙、悲欢离合的经历了。可以说,在从政与为文的角色张力中,他两相无碍,甚至珠联璧合,于此体验生命的和谐。这首《鹧鸪天·归闲吟》将这种和谐推向了天衣无缝的境界:
半世繁忙渐转闲,放飞心性步田园,是非功过烟云淡,进退去留任自然。
风不恼,雨无烦,人生少欲必心宽,寻诗问道踏歌处,山外青山天外天。
不必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更不必说人生最美夕阳红,是的,官员维系于一张纸,文人缘起于一支笔,当这二者都可以忽略之时,一段平凡的岁月、一个真实的生命、一种自然的人生顿时活灵活现而又鸢飞鱼跃般的呈现。
总之,不论是体裁与语言的形式张力,还是豪放与婉约的情感张力,也还是官员与文人的角色张力,作者似乎都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千斤重力四两拨动。他借助韵文非主流的“词”,与其说是在“戴着镣铐的舞蹈中”把玩文人的雅好和雅洁、抒写诗人的情志和情态,不如说是在表白真人的情趣和情味、哲人的天真和天然,质言之,是要开启通常意义上的“党政干部”如何使从政生涯充实而丰富、业余生活高雅而纯正,从而在生活与艺术的张力中实现和谐的生命意义。正如《岁月浅吟》扉页上著名诗人杨牧所言的:他在“生命历程中,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一次次诗意驻足,世俗约定形象下,以诗性自信赢得的另一种自我实现方式。”
芸芸众生之我们终日泛舟于岁月的河流中,常年行走在苍茫的原野上,即或如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5]又能怎样呢?古波斯王克谢尔克谢斯面对即将出征的大军,感叹道“一百年后我们都还活在世上吗?”言毕潸然泪下。《古诗十九首》叹息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让无数来者抚膺长叹。只有苏轼背靠时间、面向苍穹引出的“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追问,完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伟大对话,也成就了诗意与词章的千古姻缘。我们还不敢说《岁月浅吟》填平了时间与空间的永恒矛盾,调和了诗意与词章的难解纠纷,但可以肯定的是,词人以哲人的深邃、文人的情怀和凡人的恬淡,穿越并超越时事的纷扰喧嚣、时代的缤纷色彩和时间的幽邈烟云,引领我们在感受生活的真相、生存的真实基础上,感悟诗意生命的真谛。《岁月浅吟》推陈出新而翻唱古典,旧瓶新酒而品味人生,用宋词的体式抒发当今的见闻,借人生的旅程书写文人的感怀,这是一种弥漫在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氤氲诗意、缠绵诗情和高妙诗境;一言以蔽之,这是在生活与艺术张力中达到的美学和谐状态,更是在努力企及生命的和谐境界。
那就让我们如同十八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哲荷尔德林所言的那样——“诗意的栖居大地”!
[1]吴思敬.诗歌基本原理[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34.
[2](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3.
[3](梁)刘 勰.文心雕龙[M].南京:广陵书社,2010:88.
[4]童盛强.宋词中的生命意识[J].学术论坛,1997(5):86-91.
[5](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G]//唐诗三百首.北京:中华书局,1981:173-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