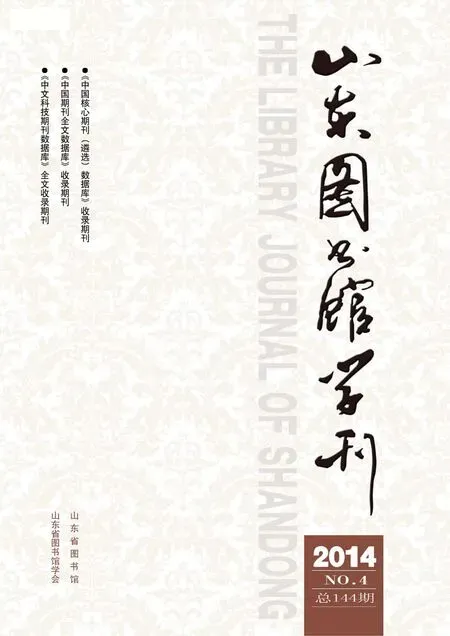花落春仍在
2014-04-10张建智
张建智
(浙江湖州文化研究所,浙江湖州313000)
接到来老噩耗,是三月三十一日深晚二十三点三十二分,短信响起接读后,简直太难相信这是从天津发来的事实:“来新夏先生于三月三十一日十五时十分仙逝。遵遗嘱‘丧礼从简,不举办任何告别仪式及追思会等悼念活动’。未亡人焦静宜泣告。”那一刻,我不知所措,取消了原想上床读书的习惯,独熄了灯,兀自在书桌前静坐,沉浸于一片暗光之中。我只是呆呆地想着:此刻,如若来老还在,他还会在做什么,灯下读书?还在为书稿打腹笥?乃或在梦中遨游书的世界。
记得初春时分,我还与他通话,问他今年还来江南吗?来老还是那种不慢不紧的话语,答道:“今年可能来不了,主要是腿有点走不动,其他尚可。”我听了很高兴,正如冯其庸先生一样,每次通话,他总说腿走不动,但还能写文、参会、访谈。于是,想来老还会来江南一走。放下电话时,一个满头白发、身躯魁梧、面色红润,带有儒雅风采的老人,又呈现在我的眼前。
此刻,不禁想起,2012年夏秋之际,与书友们一起参加在萧山举行的《来新夏九十寿辰暨学术研讨会》情景。那是一个难得的聚会,远在海南的伍立杨来了,上海的刘绪源,南京的薛冰、董宁文,苏州的王稼句、上海的韦泱等,还有几位台湾亲友也赶来萧山为来老庆贺、祝寿、论学。
“谁道人生无再少,休将白发唱黄鸡。”那两天,来老一脸喜采,兴致勃发,话语连珠,盎趣妙然,丝毫没有耄耋之年的状态,更没有一点感叹时光流逝,自伤衰老之情。他容光焕发、激情满怀地对大家说:“任何时候,我不会放下这支笔,百岁时再和在坐的朋友,相聚在这里!”听了这样的话,大家心里喜滋滋的。
一天下午,参观来老在萧山捐书馆时,他端坐在馆门入口处一把椅子上,让小友们紧靠着他合影留念。真的,如此“风来蒿艾气如薰”之气场,真让每个参会者欣钦不已。我私想,如此能招引一批年青学人赴会祝寿者,当今除来老外又有谁人?
来老曾说:“我虽称不上学有成就,但知识回归民众的行为,却给我很大启示。所以我就从专为少数人写学术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来,选择写随笔的方式,贡献知识于社会。”于是,短短数年,来老为读者奉献了《冷眼热心》《枫林唱晚》《学不厌集》《一苇争流》《谈史说戏》《来新夏书话》《且去填词》,以及《交融集》《不辍集》等十多种随笔集。当然,还有以他的书房“邃谷”为名的《师友》《书缘》《谈往》《文录》等书。
但我总感觉,来老“衰年变法”的精神,不仅自已每天在践行着,而且还常常不断地勉励后辈多读多写,看到他的许多书评,就是为他的后辈而写。与来老交往,全在一种平等、平和、平静、平心的境界中进行。在来老身上,你丝毫看不到他“以大家自居”的作风,也没有“好为人师”教诲,更看不到“一阔脸就变”的势利。记得我第一次与他面交,是因为细听了一个讲座,他便视你为友。每次我奉上拙著,不论多忙,他总细细披阅,札记后,还抽出点滴时间,为你撰写书评,如此的费心费力,对一位上了年纪的学术大家,实为难得。
今晚,我翻阅由来新夏支持发起编辑的《天津记忆》,在一大堆《记忆》文中,正好翻到为来老米寿庆祝的《专号之六》第一篇《邃谷书香》,王振良先生说“先生藏书、读书、用书,但绝不私之。”还说“先生藏籍丰富,每日坐拥书城,而且先生出版印行的各类成果,已逾百种,是名副其实的著作等身……”
我和来老神交与面聆多年,书架上插了来老赐赠之书,列着一排,除《北洋军阀史》,大都有了。而来老赠书,可谓在所不惜,两大册《书目答问汇编》、一大册《近三百年人物年谱见知录》,让我随时查阅。可谓“播书不止,遗人书香。”如若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新夏”这三个字,在中国学界有着丰富的涵义。他在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三个不同领域,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但他曾感慨:“人到退休之年,我方起用之时。”六十多岁的他,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南开大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创建图书情报学系并任首任主任。有说他是“巨擘”,是“大师”,但来老一律回绝这类空泛的美誉,说他只是笔耕不辍的“读书人”,所以,他有《不辍集》问世,以明己志。
八十岁时,他说:“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来老如此“变法”而写出的随笔,既带学术性,又具知识性,更有真情实感。如在“文革”中,他眼看家中的一部五洲同文版《二十四史》线装本,在“破四旧”中被火点着浓烟滾滾厄而起时,他写道:“我祗能在旁垂手而立,不敢乱说乱动。看书箱和书多少年来,像亲兄弟那样相依为命,从未分离。我呆呆地看着火势,目送这些朝夕相处的亲兄弟同归于尽。……但仍能隐约地听到‘豆在釜中泣’那种书的呻吟。”
这样一位把读书视为“淑世”和“润身”的学者,在经历了“囚居牛棚、轧地打场、掏高粱、掰棒子、出河工”等历史遭遇;可晚上,仍回归书卷,在一盏孤灯下“盘腿而坐,阅读和整理从火堆中被抢救出来的残稿断章”。试想,一个经历了如此大悲大喜,上高山下地狱的他,年至八十,呼出“难得人生老更忙,新翁八十不寻常”诗句的学者,能不使人读出“斜阳不语,晚景宜珍,穷坚益壮,相许莫辜负”之志?
正因有这般的大起大落,2013年春,当张梦阳先生发表《谒无名思想家墓》诗集后,早已把人间沧桑视为浮云的来老,终说出了不寻常的读后感,他说:“你拨动了我的心弦,终于让感情的死灰复燃。我感动了,哭了,流下了久已枯涸的泪水。”还说,“我早已不哭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折磨,太久的不公,但是我懦弱没有反抗,只有‘引颈就戮’,人家说我什么,我都会笑脸相迎,把泪水倒流进肚里,但你的诗掘开了我心灵的缺口……因为,它让一位已经淡定、漫步在走向百岁的老者,在行程中感动了,停下脚步,回头再审视。……”
读此,我似读出了来老一如巴金《随想录》中的语言,更读出了俄国诗人们常见的主题诗:“没有痛苦成甚么诗人的生活,没有风暴成甚么海洋?”我想,中国的史家,一如来老,他不就是诗人吗,因他心中有无限的诗可唱,他的心胸就是无垠的海洋。二千年前的史家司马迁,以及二千年后的鲁迅,无不如此。“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话,足证了这一切。
如今,来老已远去,但他心中深藏的诗,他的大爱与大悲,他的懦弱与坚强,他留下的千万文字,他最后的绝唱与深邃的思考,都将成为人们的珍宝,长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