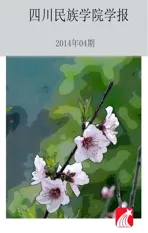白族本主崇拜与民族性特质的辩证关系探析
2014-04-10孙侨兵
孙侨兵
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研究。其中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该书中,米德根据自己在萨摩亚社会为期9个月的田野调查,通过与美国文明的对比,米德认为青春期并非必然是一个危机四伏的紧张时期,任何心理紧张都来自于文化条件,从而得出结论:“以往我们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自己的各种限制的一种反应。”[1]尽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争议,米德的文化决定人格论在解释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上,有合理和值得借鉴的地方。笔者通过在云南大理白族古生村寨关于本主崇拜文化的学习研究,亲身感受到其民族性格与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白族的本主崇拜
本主崇拜起源于原始崇拜,南诏大理国时逐渐形成,元明清时期尤为盛行,一直沿袭到现在,是白族人民特有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白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由原始的图腾和自然崇拜产生、发展至祖先英雄崇拜,自成体系。本主往往被当做一村或数村的最高主宰,至今在白族聚居区,几乎村村有本主。各地白族群众常封予每个本主天神、圣母、龙王、皇帝、帝母、太子、夫人和老爷等尊称,其中有男有女,有本主本人,也有本主的侍从和子孙,用泥塑或木雕成偶像供奉于本主庙内本主庙成为白族村落的象征和民族特有文化的标志。
迎接本主和本主庙会通常在每年的本主寿诞之日举行,这是白族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届时人们穿上盛装,宴请亲朋好友,置备丰盛的食物,演奏洞经古乐,唱大本曲,跳舞唱歌,耍龙,耍狮子,更换对联等,以表示与本主同乐,歌颂本主功绩。白族人通常认为本主就是掌管他们居住境地之主,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本主。各村平时凡是大灾小病,都要祈求本主,能够解救自己,除此之外,他们每年都有一定的日期进行祭祀本村本主。传说有一年,天因为大旱而无法栽秧,当地人民将这一带九个本主集中在一处求雨,而最后形成九坛神庙。诸如此类关于九坛神庙起源的传说,充分的说明了喜洲白族供奉本主的意义。白族本主崇拜具有将英雄人物和封建统治者神化、将自然力人格化的特点。
作为白族人民精神支柱和意识载体,本主帮助凡人追求现世的幸福和真善美、战胜假丑恶。所以,本主一般都会有神话故事相随,这些神话故事长期在白族人的社会生活中起到规范、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通过世代相传形成了牢固而有力的白族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
二、白族的民族性格
本主崇拜对白族社会的影响极其巨大,白族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熔铸其中,它是白族诸多传统的折射,凝聚着丰富的思想内容,白族的民族性格亦蕴含其间。可以说,本主崇拜是白族性格的一个投影,从本主崇拜中不难寻觅出白族鲜明的民族性格。
(一)开朗乐观,热爱生活
本主崇拜呈现的并不是一神教通常具有的威严与神秘,而是轻松愉快的风格,具有极浓的生活情趣,也并没有玄而又玄让人们感觉离其生活相差甚远,充满了幽默与诙谐的人文主义色彩。很多白族本主传说的婚姻情爱故事体现了这点。相传,上阳村苦于本主段宗磅与马久邑村一位卖酒妇女相爱而长期不在本主庙而责难马久邑村,段宗磅出面调解,以每年五月初五让马久邑村接其住一个月,六月初六又由上阳村迎回自己村子而圆满解决。这样,段宗磅就得以如愿以偿,上阳村和马久邑村的误会也烟消云散。这些世代传送的充满世俗气息和浪漫情调的本主故事比比皆是,影响了白族人民的性格,使其开朗乐观,热爱生活。
白族本主节期间,氛围通常畅快热闹,人们可以无拘无束的活动,这种氛围也对白族人民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云南大理,每年一度举办“绕三灵”活动,白族群众在朝拜的路途中会载歌载舞,尽情欢乐,游戏嬉笑,欢声笑语穿梭在苍洱之间。有文献记载大理三塔寺下的三文笔村本主节“游人如蚁……有卖春酒、烧猪肉、生螺黄、生螺师、凉米线、供人吠,醉饱与薄片葛根者。”①《大理县志稿》。白族的孩童从小生活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和活动里面,性格受其影响,多数乐观开朗,热爱生活。
(二)豁达宽容,热情开放
本主崇拜具有开放性。在树立本主神的时候,不以出身、功过、成败来取舍,也不受民族族别的限制。在众多本主中不乏有这样一些人物:唐将李必统兵征讨南诏时战败,在洱海地区自尽,后来不只是李必,连同他的亲属、下属都一起被大理白族列为本主。甚至是洱海金梭岛上因为偷香窃玉被姑娘父亲打死的灵猴,也受到了白族人民的信奉。类似情形数不胜数。总之,白族人民对那些有愧于白族的人物并没有永无止境的仇视,而是以德报怨。
本主崇拜的信仰使得白族人民心中宽容豁达,人们内心深处秉持着“毋以一言不合而忘人雅谊,毋以一行有疵而弃人生平”②(明)《二艾遗书·圣希录》。的思想,白族积极友善地与别人交往,而不是闭门造车拒人于千里之外。白族在待客上遵循“居家宜俭,待客宜丰,但不可如小人斗胜,遇知己即一羹一疏有无穷况味,”③(明)《二艾遗书·教家录》。对客人真诚相待,倾心相处。白族本主崇拜所确定的内容和信仰与民族性格是相通相连的。
(三)兼容并包,追求和谐
在白族本主信仰形成的过程中,在原始宗教、巫教或“鬼教”的基础上,又逐步融入了儒、佛、道的成分,“演化成一个兼容各种形态之神祇,令学术界在宗教类别划分之时大伤脑筋的宗教形态。”[2]白族与汉族相邻而居,白族地区收到汉族文化很大影响,在长期交往过程中,不少汉人也融入了白族,白族把儒家学说及代表人物吸纳入本主崇拜的系统里,丰富了其文化内涵;佛教在唐初传入云南,其具有完备的宗教文化形态,曾一度成为南诏、大理国的国教。本主信仰有选择地吸收了佛教的相关成分,以提升自己的表现形式,如佛教的祭祀仪式、神像雕塑、寺庙建筑;一些曾为白族民众做过好事或为地方发展做出过贡献的佛教祇或高僧,则被吸纳成为本主神;道教与本主信仰具有更多的相通性,在其传入白族地区后,其所崇奉的许多神祇,先后为本主信仰体系所吸收,其一些宗教仪式如画符念咒、祈福消灾,也被纳入本主信仰体系。白族群众也制定了一整套道德规范和清规戒律来分辩善恶,规范信徒的言行,它实际上是儒、道、佛三教善恶观念与古代白族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相融合的产物。
在本主崇拜的影响下,白族人民非常注重和谐,追求安宁祥和,人际关系也总是很融洽。在这样的信仰下,白族人养成了孝顺父母、关爱子女的传统美德,不仅家庭和睦,而且善待邻里。除此之外,白族人还善于同汉族、回族、彝族、蒙古族、傈僳族、藏族各民族和睦相处。据历史记载,大理境内多次发生过民族的迁徙和交流,但最终都还是交融到一起,形成了以白族为主体、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多元一体格局。综上所述,本主崇拜显现了白族文化兼容并包的整合功能,使得白族人民具有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美好品德。
(四)求真务实,守成稳重
在庞大的本主体系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定本主可以被奉为神抵的原因。在确立本主时,人们都希望它能带来切实的利益。因此在本主碑铭中称本主能“掌握一方,安生民之保泰”[3]并且“驱邪辅正,珍恶天灾,赐福格祥,为斯方土主也”。[3]本主能够保境安民,替人消灾免难,给人幸福,对信徒“逢善则驾之祥,有求皆应,遇凶则化为吉,无愿不从。”[4]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达到“为士者,程高万里;为农者,栗积千钟;为工者,巧著百般;为商者,交通四海。”[4]由此可以看出,白族信奉本主带有明确的功利性,是为了一种实实在在的需要。
本主崇拜是在白族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具有持续稳定、自主独立发展的特点,其在历史上曾不断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和冲击,比如佛教、道教的传人等。但本主信仰能平稳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本主崇拜在吸收外来因素为己所用的同时,能稳固地保留本主崇拜的核心内容,吸收但不全盘异化,变体而不离其根本。本主信仰能延续至今,也反映了白族守成稳重的民族性格。
三、本主崇拜与民族性格的辩证关系
以米德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人类学家认为文化造就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命运。“基本人格”不同,文化便呈不同的形式,民族的命运也就不相同。白族的本主崇拜在白族人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起来,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它在白族社会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白族本主崇拜的主导功能,已经从宗教方面扩展到文化、社会方面,它建构了白族群众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相信其能帮助战胜现实中的困难,实现人生福祉,同时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在本主崇拜的信仰和仪式活动中,白族的孩童从小对这种开朗乐观、热爱生活的氛围耳濡目染;对豁达宽容、热情开放的白族风俗有所教化;对兼容并包、追求和谐的生活态度有所感受;对求真务实、守成稳重的民族性格有所熏陶,反之,也正是这种影响下的民族性格使得白族人民的本主信仰更加坚定和不可撼动。这种文化环境自然会影响从中长大的白族人民的性格,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性格。白族在长期的本主崇拜文化中,创造了各种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用人民的智慧将各种外来文化吸收整合,并且创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仪式活动,这充分显现出白族人民的创造力和创新力,进而证明了人民对民族文化的反作用能力。
米德为了证明其文化决定人格论的正确性,于20世纪20年代出版了《萨摩亚人的成年》,距今已有九十余年,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今天看来仍然对我们有所裨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不完全是一种学术问题,归根结底,实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发掘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可以让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得到传承和弘扬,良好的性格得到鼓励和发展,进而丰富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为提高文化竞争力和国民素质,使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做出贡献。
[1]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p2
[2]杨仕.试论白族本主崇拜的性质 [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p58-63
[3]田怀清.大理州白族本主信仰调查之二[A].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 [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4]杨政业.白族社会历史调查 (四)[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p184、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