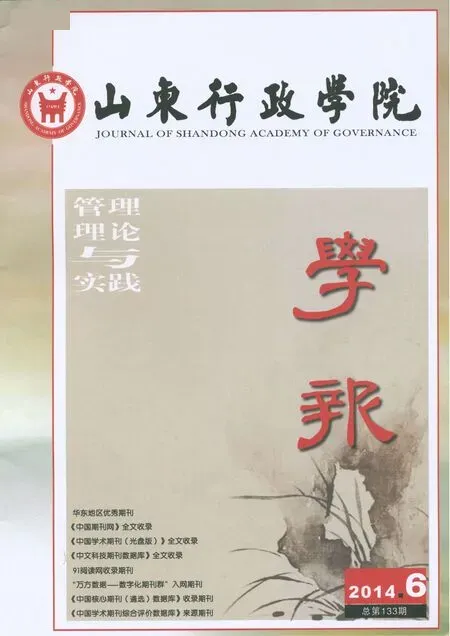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及协调
——以中国近现代婚姻立法史为视角
2014-04-10杜晓彤
杜晓彤
(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100)
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及协调
——以中国近现代婚姻立法史为视角
杜晓彤
(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100)
通过梳理近现代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历史嬗变,探究了习惯的类型,试图探寻适合当代中国国情的婚姻立法进路和婚俗改革,进而协调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问题。
婚姻习惯;婚姻立法;彩礼;冲突与协调
婚姻制度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国情民风联系最为直接、密切;另一方面在社会变革中也承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在长期历史中发生渐进性的变革与发展。然而自近代起,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思想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促使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在婚姻领域则体现为婚姻法制观念和婚俗文化的碰撞,促进了中国对西方婚姻法律制度的学习、移植和借鉴,实现了中国婚姻立法自传统型向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飞跃。
本文试图探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婚姻制度在立法方面的法律变革,尝试以动态的角度来揭示婚姻立法与婚姻习俗在社会变革、制度转型期的历史变迁,获悉婚姻立法对传统婚姻习俗的态度。
一、中国近现代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的历史嬗变
(一)近现代结婚制度的历史嬗变
1.婚约制度。清末并未将婚约明确地纳入法律并对定婚加以具体条文规定。而北洋政府时期,修订法律馆制定草案第一节第一款为定婚,其规定“定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1],由此产生了婚约制度。在民国初期,仍将定婚作为成婚要件,不经定婚而缔结婚姻的,为可撤销婚。可见民国初期的立法尊重了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聘娶婚原则。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0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较北洋政府时期的婚姻法草案,该法律确定了尊重当事人意志、无条件解除婚约、确立婚约自由原则,使婚约制度在近代化演变过程中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个时期的婚约改变了先前强制履行的规定,鼓励缔结婚约,却不强迫必须履行。
解放后的法律对婚约持既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在后来的《婚姻法》及其修正案中,并未提及关于婚约的规定。但有关部门对婚约所作的解释,被视为代表了国家法律对待婚约的原则。
2.彩礼制度。彩礼,作为婚约的附带性礼节习俗,通常依附于婚约制度的变化而改变,同时,返还彩礼也是解除婚约后附随的一种后果。
彩礼作为国家法,始自西周,至清末,仍将彩礼作为国家法。民国初年的彩礼制度仍旧沿袭前清时的规定。彩礼已经作为定婚的形式要件,因而法律对彩礼返还做出了严格限制。首先规定了若男女双方订立婚约,未至结婚而有一方亡故,不追彩礼;其次,对于有悔婚另嫁者,就因毁约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要求对方赔偿;最后,如果聘财逾期未至,女方得请求解除婚约。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村妇女问题草案》提出:“婚姻须得女子之同意,反对买卖婚姻,取消聘金制。”[2]自此,几千年居于国家法之列的彩礼被废除,演变为民间习俗。
然而,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4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其中第十条对返还彩礼条件进行了规定,表明彩礼这一自革命根据地时期便被废止的民间习俗,又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重回国家法之列。[3]
3.结婚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人们形成了以举行结婚仪式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习俗认知。然而该习俗在近代法律变革中受到了挑战。北洋政府时期,婚姻生效方式效仿日本民法典,采法律婚主义。婚姻形式要件采取登记婚主义,婚姻呈报户籍吏起方生效。不承认事实婚,即有事实上的同居也不是婚姻成立的要件。这样的改革显然颠覆了以仪式婚为婚姻成立标志的传统。
1931年12月1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正式废除了国民政府时期的仪式婚制度,采单一登记婚主义。该条例第八条规定:“男女结婚需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4]该规定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并为各根据地婚姻立法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婚姻法所沿用。
尽管登记婚主义的沿用在中国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结婚仪式却是经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洗礼而内化的民间传统,为社会民众所信赖。法律上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出现男女举行了婚姻仪式且符合登记结婚的实质要件,但未登记的事实婚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格外普遍。1994年2月民政部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者按非法同居对待,否定了事实婚姻的效力。2001年《婚姻法》颁布,规定了事实婚姻的当事人补证才有效。同年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第五条以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为节点,在此之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该解释出台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4.禁婚制度。传统中国的禁婚制度包括同姓不婚和亲属不婚两种基本制度。但对男系亲属的限制范围远大于对女系的限制[5]。清末修订《大清民律案·亲属编》仍然坚持了该立法精神,沿袭了前朝禁止中表婚的做法,此后北洋政府沿用了该草案的规定。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禁婚制度才发生了质的变化。立法者借鉴了西方法律划分亲属的方法,摒弃了原先的以男系血亲为中心划分宗亲、外亲和妻亲,而是按照婚姻与血缘关系,将亲属划分为配偶、血亲、姻亲三类,改变了长期存在的重男系轻女系的情况,对男女系采用平等的限制。该法律颠覆了传统的立法精神,完成了禁婚制度的近代转型。
解放后有关禁婚制度的法律规定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的规定大致相同。1950年《婚姻法》第5条规定:“男女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2]1980年《婚姻法》进一步缩小了禁婚范围,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其改变了原先“从习惯”的禁婚规定,明令禁止近亲婚。其原因在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数量减少,需提升人口质量。
(二)近现代离婚制度的历史嬗变
1.离婚制度。在中国古代,男方一纸休书即可宣告夫妻关系解除,这体现了在离婚制度上,男女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清末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离婚制度上赋予夫妻双方平等的主体地位,废除了传统离婚中存在的“七出”等制度,改采用两愿离婚和呈诉离婚。对于两愿离婚,法律采取的离婚标准是夫妻不相和谐,形式要件采登记离婚主义。对于呈诉婚姻,法律采有责主义,即夫或妻一方若发生重婚、虐待等过错,则准予离婚。[5]
北洋政府时期,基本沿用了《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但对两愿离婚的标准作了修改,以夫妻双方愿意离婚作为两愿离婚的标准,较先前的“夫妻不相和谐”更具客观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对于离婚制度,大致沿袭了先前的规定。但对两愿离婚的形式要件作出修改,排除登记离婚主义,要求两愿离婚采书面形式和两人以上的证人即可。此外,对于呈诉离婚中的法定事由,该法增加了一方患有不治之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等法定离婚事由,标志着离婚立法开始从有责主义向无责主义转变。
1950年《婚姻法》明确了男女婚姻自由原则,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较先前几部法律,该法偏重维护女性权利,做出了在女性怀孕、分娩的特殊时期,限制男方的离婚诉权等规定。
197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则明确将“夫妻关系事实上是否恢复和好”作为准予离婚的原则。1980年,受世界上无过错离婚主义的影响,感情破裂说成为了准予离婚的标准。此后2001年《婚姻法》沿袭了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
2.离婚救济制度。离婚救济制度贯穿于近代至今的多部法律立法中。《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规定了呈诉离婚中男方为过错一方,则男方应当给付女方能够维持生活的赔偿。1950年《婚姻法》较前者又做出了调整,不再将有无过失作为衡量标准。即如果一方未再婚且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给予帮助。可见,确立经济帮助的要件仅在于一方生活困难。1980年《婚姻法》除将确认生活困难的时间限定在“离婚时”外,基本沿袭了该规定。2001年《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完善了离婚救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诸多突破。
二、中国近现代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
中国近现代的婚姻立法史,亦是从“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缩影。随着法制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国家法不断向乡土社会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外部规则与乡土社会的内部规则发生互动、冲突与融合。
对习惯的司法适用主要采用分类处理的办法,民间习惯可分为与法律规定相容的习惯、中性的习惯和与法律规定冲突的习惯。
(一)与法律相容的习惯
所谓与法律相容的习惯,即该习惯与法律规定是相互符合、相互融合的。甚至在我国的某些法律中,法律还赋予习惯以适用地位。对于该习惯的适用问题,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纳入法律框架内加以解决,在婚姻领域有颇多体现之处。譬如1950年《婚姻法》第5条规定:“男女为直系血亲,或为同胞的兄弟姐妹者,禁止结婚;其他五代内的旁系血亲间禁止结婚的问题,从习惯”[2]等规定。
(二)中性的习惯
所谓中性的习惯,是指那些既不与法律相悖,但又不符合国家政策提倡或者现代文明社会要求的习惯。[6]如现在普遍存在的订婚收受彩礼。这一类习惯在司法适用中面临着尴尬的境地,也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力。考虑到该习俗在乡土社会中由来已久,普遍适用,如果简单地不予适用,当地的人民将难以接受该结果。因此,如果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该习惯,法官多会基于公平和司法效果的考虑,适用该习惯。
(三)与法律冲突的习惯
所谓与法律冲突的习惯,即该习惯的内容与现行法律的具体条文具有违背的地方。由古及今,这一类习惯都因违反法律或社会公众利益而不被法官所适用。譬如依照婚姻习俗,男方给付彩礼后又悔婚,则男方不能追回彩礼。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男方在符合法律的条件下得以要求返还彩礼。法官不予适用的做法在实体法的意义上无可厚非。然而在法律适用中,某些制定法条文的规定难以发挥立法时所预设的作用,出现了立法之初所难以预料的情况。如果法律规定本质上不能调整它所欲调整和规范的社会事实,但习惯能够更加妥当地表达、调整、规范相关社会事实时,那么显然习惯就具有了正当性。
习惯与制定法的矛盾在司法适用中得到体现,简单地依据制定法做出的判决难以得到广泛地司法认同,协调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矛盾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中国近现代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协调
(一)立法进路的协调
很多地方法院通过考察当地民间习俗,出台了特色的裁判规范。江苏姜堰市法院就曾制定了《婚约返还彩礼纠纷案件裁判规范指导意见》,尝试在不与现行法律冲突的前提下引民间习俗入司法审判过程。对于婚约彩礼,其规定了女方提出解除婚约的,彩礼价值在2000元以上至10000元以下的,按照80%返还;价值在10000元至20000元以下的,按照90%返还。男方提出解除婚约并要求彩礼返还的比例,低于女方提出的20%。彩礼少于2000元的可不予返还,20000元以上则全额返还。[7]通过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察当地的婚约民俗,制定符合民情的折中的指导性意见,不失为协调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冲突的良策。
(二)司法进路的协调
1.利益衡量的法律方法。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新的社会规范体制尚未建立,而旧的社会规范体制在法律制度的移植下受到冲击,需要经历重构的过程。在这种新旧规范共存的社会现状下,极易导致规范之间的矛盾,出现了多种利益主张与权利诉求。而婚姻领域中的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实质亦是发生在此种背景之下的利益冲突。法官可通过对个案中的各种秩序价值做出层次上的区分,将利益进行权衡比较,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
2.法官的裁判策略。当习惯与制定法相互冲突时,基于现有的裁判规则,在有明确制定法规定下只能适用制定法,仅在社会纠纷涉及无法律明确规定的领域,方可考虑适用习惯法。然而,简单地适用这一规则,对习惯不加考虑,做出的判决很难说是符合公平正义理念的判决,也难以为乡土社会的群体所接受。这就对法官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高标准,即既要符合该共同体所秉承的正义理念,又要符合现有法律。处理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时,想要达成这样的标准,法官必须要灵活处理:首先,法官要对习惯进行考察。即该习惯是经长期历史过程形成的、确定的、为该共同体所遵守的。只有具备以上条件,习惯方可进入司法裁判程序。其次,法官应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依照法官经验和前见,预先对案件作出判断。然后,根据预设判断,法官开始找法的过程,寻找到与案件相关的可适用的法律条文。最后,法官需根据预设判断和法律条文,构建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概念框架。
[1]王新宇.民国时期婚姻法近代化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2]张希坡.中国婚姻立法史[M].人民出版社,2004.
[3]李霞.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J].民俗研究,2008(3).
[4]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金眉.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从《大清民律草案·亲属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M].法律出版社,2010.
[6]姜世波,王彬.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及其查明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7]汤建国,高其才.习惯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的实践[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编辑:崔维)
D923.9
A
2095-7238(2014)06-0083-04
10.3969/J.ISSN.2095-7238.2014.06.018
201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