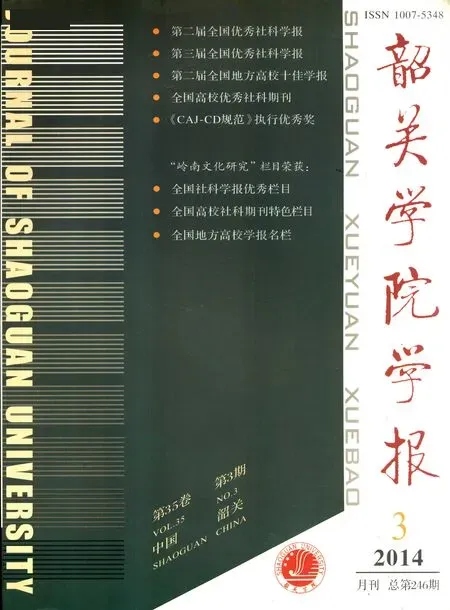论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
2014-04-10刘昊
刘昊
论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
刘昊
(贺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贺州542899)
广东土地革命时期的“秘书专政”现象耐人寻味。革命知识分子因“原罪”而受排挤,因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专政”,其能否发挥作用对革命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
广东;土地革命;“秘书专政”;知识分子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先后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即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其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1931-1934年),在理论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备,影响最深,危害最大。在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受三次“左”倾错误的影响尤为明显,其境遇通过革命队伍中较普遍、颇耐人寻味的“秘书专政”现象可见一斑。笔者拟通过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境内革命队伍中的“秘书专政”现象,探讨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事业的关系。
一、因“原罪”而受排挤
近代以降,中国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剧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家命运和时代变迁,以致反思现实并百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许多知识分子纷纷了解、研究乃至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即是由知识分子创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建立的最初几年内,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一直是党组织尤其是党员干部的主体和中坚的力量。
在那个年代,能成为知识分子者往往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商人买办或有人在外国做工的家庭。若将这些家庭按照中共引进的前苏联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区分,那他们大多数无疑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是应予被工农革命阶级消灭的。因此,知识分子便有了如基督教所宣称的“原罪”,尽管其中参加革命者绝对多数忠诚于共产主义信仰和党组织,而且在事实上既是革命理论的传播者,又是革命行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参与者,却难以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很多时候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
1928年元月份,中共广东省委通过的二个决议竟然均无视敌强我弱之客观现实,把广州暴动失败归咎于革命知识分子。如,中共广东省委在1928年元旦通过《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断定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此次暴动最高的指导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恐怖、动摇起来”[1]4。而1928年元月下旬,广东省委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对参加广州暴动决议案》(1928年1月23日)再次指出,广州暴动失败的主观原因就是“当时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不很坚决与缺乏指导的能力,始终倚重军事而轻视群众工作”[1]146。
广东省委决议案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偏见,与当时事实上受前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方针不谋而合;这为当时的中共临时政治局分析广州暴动失败的原因时开罪于革命知识分子提供了政策根据。在1928年初,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受失败情绪的影响以至支配,便低估广州暴动的意义,处分暴动领导者以泄愤;甚至得出“知识分子始终是动摇的”之类的结论,还要求用排斥知识分子的办法来改造党。从1928年起,中共广东省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命令所辖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设法将知识分子党员排挤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岗位。
在苏维埃革命曾开展得如火如荼的东江地区,尽管工农出身的干部多无能,也难以让知识分子摆脱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当时广东省委曾批评五华县委,指出:“县委工农同志没有实际参加工作,县委组织仍然是旧的办法,以三人分任书记、组织、宣传,这三个人又完全是智识分子”,以致工农同志当县委常委在事实上只是挂名而已。省委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应将7个县委常委轮流到各个区去指导工作,“不能只把所有工农同志都调出去,而留清一色的智识分子在县委机关”[1]132。也就是说,不能将工农出身者都调到基层,而把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常委留在县委机关做决策。因此,省委要求,“党的发展在成份上应多增加工人及贫苦农民”[1]134。这种指示的本质在于唯成份观念作怪。后来的事实表明,仅仅增加党员中工农分子的数量,是绝对难以增强党的无产阶级性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与欧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相比,具有其更多的劣根性(以小农特点为尤)。个人的政治思想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出身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人生阅历中形成的,与国家民族的处境和时代的使命、个人理想息息相关。
1928年,中共北江特委严格按照中共广东省委的决定对待知识分子革命者。在党的方面,尽量剥夺知识分子党员的领导权。如,中共北江特委在《中共北江特委关于各县暴动工作纲领》(1928年1月15日)中命令其所辖各县县委:“除各县工委由特委加派得力同志(各支部改组后再开代表大会改选县委负责人)负责外,各支部应立即改组,以最勇敢忠实农民同志担任书记及干事(知识分子能负责的也要减至最少限度)”[1]1。这样做,无异于视知识分子为党的事业的天然隐患。例如,中共北江特委在暴动一度取胜的地方,对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干部人选及其不同成份出身者所占比例予以明确指示:“苏维埃人选最好不加入知识分子。否则,应减到绝对少数(不能多过五分之一)”[1]6。如此指示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甚至厌恶,简直就是让人把革命知识分子当做革命的潜在异己力量进行提防。这种情况在广东和全国各地都是较普遍的存在。
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尤其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工农出身的党员不断增加。这在客观上为党组织排挤革命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左”倾政策的贯彻执行,为排挤革命知识分子提供了主观的、必要条件。主客观条件均具备了,革命知识分子被排挤的可能便成为现实。
据史料记载,1928年初,在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海丰县,知识分子党员占党员总数的3%。当时,在组织方面,“组织状况全县[原]有党员2,500人,增加7,570人,开除党籍者83人。成份农民占85%,工人占10%,知识分子占2.5%,其他占2.5%”[1]4。“农民王”彭湃曾留学日本,在当时不管怎样,在常人眼中必定是大知识分子了。他领导下的革命队伍为何知识分子党员所占比例那么小呢?原因有二,即,海丰县委在给上级的报告所指出的:“海丰是文化低落的地方,知识分子的数量甚少。而我党自政变后,对于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戒严,很少去介绍他们入党”[1]5。第二个原因无疑是主要原因!也正如《北江巡视员李一鸣的报告——政治经济形势、党的组织情况、宣传工作、群众运动、军事工作》(1930年1月14日)所言:“我党自政变后,对于一般知识分子特别戒严,很少去介绍他们入党”[1]179。另外,严格限制知识分子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关于县委与特支的组织工作,省委和特委往往以硬性比例限制知识分子在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如《中共北江特委关于各县暴动工作纲领》(1928年1月15日)记载,在北江地区,“曲江、英德、乐昌各县委是以七人组织之,采用中间分子会议选举。县委成份十分之七是贫农,十分之二是工人,十分之一是智识分子”[1]179。组织规则名义上规定知识分子在县委成员中占十分之一的比例,但是,由于县委成员总数才七人,知识分子党员能进入县委者最多一人。如此做,策略上是用选举规则剥夺知识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决策权、领导权,让知识分子只能处于屈从地位而做驯服的工具。
《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东委组织系统与组织工作状况》(1929年8月2日)告诉后人,“当反机会主义又厉害时,一般同志以为机会主义是知识分子而变成,知识分子是机会主义,故反机会主义就反对知识分子出来了,所以变成一种反‘知’运动。当海丰政权在握时,党曾一次召集开会,彭湃同志说‘工农分子前坐,知识分子后坐’。这竟表现党内一种界限观念”[1]186。有“农民王”美誉的彭湃自己是留学过日本的知识分子竟然如此鄙视知识分子,何况其他人呢?
究其原因,在于革命知识分子总是讲究人道,有主见而不盲从,尤其对“左”倾错误能予以抵制。例如,革命知识分子对土地革命早期的红色恐怖进行消极反抗,其“原罪”因而暴露无遗。据《滚舞〈海丰农民暴动与地主政府高压的概况〉》(1928年)记载:在各阶级成分的人当中,“尤其是雇农更趋向于革命,杀地主分土地为最热烈。他们往日听学生之演说,受智识分子的领导”,但是,“到了斗争的营垒分明而趋剧烈之斗争,多数贫农起来领导学生了!尤是拿反动派的时候,智识分子对革命更不忠实,他们对之反动派,私做人情,放他逃走”[1]108。
二、因对革命事业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专政”
在那个特殊时期,出于工作之必需,党组织在总体上排挤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同时,又必须用他们。1928年4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4月13日通过)指出:“贫苦的知识分子党亦应注意吸收其中有阶级觉悟的分子,以便利于城市运动”[1]216。可见,党组织要用知识分子,仅仅是出于“以便利于城市运动”这个意图,鉴于较多工作是工农分子完全无法取代的罢了。
在党内过分重视工农出身,片面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左”倾背景下,中共揭阳县委被改组,以致县委领导均由农民出身者担任,而秘书则由革命知识分子充任。针对这种情况,1928年6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发出指示信,告诫揭阳县委:“如果是机械的执行‘工农化’,那末,实际上反有很大的毛病。你们应懂得要工人、农民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绝不是一种形式,必须真能实际增强指导机关的力量”[1]155。也就是说,工农分子尚无领导能力,县委机关的知识分子不宜完全排挤。对于揭阳县委的人选,省委顾虑出现海丰县委的闹剧,就在指示信中建议:“知识分子亦不应机械的排除,如果是好的,有参加的必要,仍可以加入”[1]156。据当时的有关文件记载,海丰县委委员绝对多数是农民出身者,工人出身者仅一人,知识分子出身者仅仅任秘书长。因工农同志目不识丁且无知,而事实上形成某个知识分子出身者大权独揽的“秘书专政”局面。
知识分子因有文化知识而形成的“秘书专政”现象在广东各地苏维埃运动中普遍存在。例如,《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潮、普、惠三县党组织状况与整顿计划》(1928年6月24日)指出:惠来县县委辖五个区委,“区委委员多是农民同志和工人同志,知识分子则为区委的秘书。但是实际上差不多秘书专权包办党务,区委会很少开,不能指导支部,工作上不能按期向县委报告或简直不报告”。惠来县县委如何呢?“虽然是民主选举出来,而且工农同志占多数,但实际上又是黄*、德*同志包办,县委全体会到今未曾开过一次会”[1]160。工农干部自己不会布置工作,只是上级的文件转发下去而已,每次给东江特委的工作报告均为百把字篇幅。这种情况表明,工农干部总体上对党的工作既无能又无应有的责任感。至于普宁县所辖八个区委的情况,该报告指出:各区委“大多数仍是旧的工作同志,他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多是国共合作时候工作到现在的”。“县委从前是陈魁亚同志一人包办,并无所谓县委。后经东委派人改组,则变是彭奕同志个人包办,常委会不能开,全体会议更没有了”[1]165。可见,革命知识分子党员既有能力又很忠诚。
另一重要原因是,在较多地方,知识分子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实在太高甚至全部。例如,据《中共北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朱德部队和各县情况》(1928年1月21日)记载,中共北江特委完全没办法在南雄县执行省委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因为南雄县“有四十余个党员,尽知识分子”[1]35。另外,据邓凤翔1930年7月17日向党中央汇报东江情况的报告透露,各个地方党部的人数通常为七至十一人,而汕头党部人数最少——仅三人,而“职业最多仍是知识分子,其次是农民,最少数是工人(如东江特委五个常委中全是知识分子)”[1]183。知识分子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但加入共产党的竟然有那么多人,由此足见其革命觉悟之高。
省委巡视员蒲凤鸣在《蒲凤鸣关于东江党务及军事情况的报告》(1928年7月19日)中明言:“至于各级党部负责的人(据我完全知道的便是海丰和普宁),都是为少数知识分子所把持”。非知识分子的,负责组织、宣传工作的甚至书记竟然不知各自的职责和工作情况。“因为什么事情都是为少数的知识分子执行一切”[1]237。蒲凤鸣甚至认为,农民入党纯为私利而不知党的纲领等[1]238。据《中共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过去执行富农路线的危害及今后的总任务》(1933年1月10日)记载,“各级苏维埃尤其区苏维埃工农分子变成挂名委员,形成秘书长专政,工农群众视苏维埃委员为苦差”[1]357。针对这种状况,东江特委颁布《中共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过去执行富农路线的危害及今后的总任务》(1933年1月10日),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刻苦的有系统的训练工农干部培养他们的能力,提拔他们到党的领导机关来”[1]371。然而,初通文墨尚且绝非举手之劳,更毋庸说短期内提升文化素养了。不用因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而主动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却计划在战斗间隙“刻苦的有系统的训练工农干部”,无异于缘木求鱼。
据《中共琼崖特委最近总的工作大纲》(1928)记载,琼崖特委论及组织问题时指出,尽管党员人数激增,但是,“各级指导机关,虽有过半数的工农参加,然多未能起作用,事实上是知识分子把持”[1]110。1932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巡视员定川在汇报两广党的领导及各地工作情况时也指出:“琼崖特委共有十一个人,主要负责同志都是知识分子”[1]140。
可见,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能够造成“秘书专政”的局面,仅仅是革命事业的成功须臾离不开他们,因为他们有文化知识且总体上能干,是出于信仰共产主义而参加革命且矢志忠诚革命事业;也因为知识分子在土地革命早期在党员总数中所占比例很高,是革命事业最初的发起者、领导者和参加者。
三、对革命事业的影响巨大
对革命知识分子政策的错误,各地特委曾有所警觉。例如,《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东委组织系统与组织工作状况》(1929年8月2日)表明,特委认为反机会主义运动“变成一种反‘知’运动”和彭湃鄙视知识分子革命者“这是很不好的现象”[1]186。痛心的是,省委未予重视,更未采取纠正措施。
“秘书专政”现象,是知识分子革命者因有“原罪”而受到排挤以致只能做无决策权的“秘书”——俗话所言的笔墨匠之奇特现象,对我党的事业负面影响很大。名义上是“秘书专政”,实际上知识分子革命者往往被剥夺了决策权,受到“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种种制肘,其才能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对知识分子革命者的“左”倾错误政策在广东各地执行后危害很大,不仅损害了党的形象,而且使党失去了可靠的智力支持。例如,海丰县的党员以农民出身者居多,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本性在分配土地时原形毕露。据《关于海陆丰的失陷与当前形势的报告》(1928年3月26日、29日)记载,“海丰分配土地,同志得多些。农民叫我们同志是‘双料’的,他们是‘单料’的,因为同志分配土地得多一半”[1]103。如此分配土地,共产党员的形象怎能不差?
1930年7月,邓凤翔在向党中央汇报东江党组织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东江地区党员从职业方面分析,“农民占最多数,产业工人同志数量是极少数的”[1]175。在斗争中,工农出身的党员勇敢且团体观念较强,但是政治水平普遍偏低,很多人对党无最起码的常识,斗争一旦受挫则剧增失败、报复情绪。各支部纪律约束松弛,斗争中常常各自为战,“故平时支部倒能开会,而斗争起来,如同解体一样,这是东江的支部最大弱点”[1]178。可见,缺乏知识分子党员领导的党组织是没有战斗力的。
知识分子革命者被剥夺决策权且受到制肘,其作用必定难以发挥。《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潮、普、惠三县党组织状况与整顿计划》(1928年6月24日)指出,东江特委改组潮阳县县委后,使县委由林姓某同志个人包办,变为“现在的常委是两个知识分子、三个农民同志”[1]170。试想想,三个农民进入县委,除了起制肘作用外,如何指导工作呢?又如《中共东江特委扩大会议决议——过去执行富农路线的危害及今后的总任务》(1933年1月10日)指出,到了1933年,东江“各级苏维埃尤其区苏维埃工农分子变成挂名委员,形成秘书长专政,工农群众视苏维埃委员为苦差”[1]357。可见,农民党员多为眼前利益而不顾党的形象,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入党最主要是出于真诚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占据领导职位的工农分子只能起到牵制知识分子的消极作用,而任秘书的知识分子专职维持政令的上传下达。
“秘书专政”更恶劣的后果是,革命队伍的领导集体渐渐离心离德。1933年3月7日,东江特委要求潮普惠工作委员会,对苏维埃工作“尤要纠正秘书长包办一切及过去文教部代替秘书长以及对主席团的工农分子看不起的严重错误”[1]452。这说明被拉入主席团的工农分子常因为自己的无知而自卑,而知识分子可能也有意无意地看不起这帮主席们。
为何如此?党的文件给读者提供了答案。《中共惠阳县委给省委的报告——县委会议讨论省委第五号指示信的结果》(1929年4月)指出:“惠阳党员*员农民只有七个工人,但这些工人都与农民意识无异,不像大工业里产业工人,因他不为工人时亦是一个农民”[1]305。《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东委组织系统与组织工作状况》(1929年8月2日)指出:“改造党的形式主义。这是换汤不换药的改组,不是改造。如五华县委虽有一部分工人同志参加,但仍然是古大存同志包办。各地亦如此,前由少数知识分子包办,现在都变为知识分子少数同志,这是更糟的现象”[1]187。这些话反映了东江特委对改造党的领导机构的无奈:按照上级指示设法让工人出身者进县委,以尽量减少知识分子在领导机构的人数;但是,党的工作一刻也离不开知识分子,以致各县委从总体上由少数充当秘书的知识分子“包办”变为知识分子数人“包办”。可见,建设工人阶级的党并非就是安排工人出身者当领导。笔者以为,为工农群众谋福利的党和政权就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没有大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领导或参加,就没有工农群众自己的党和政权。
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论述土地革命时曾指出:“土地革命虽然轰轰烈烈,但主要是在南方的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影响”[2]23。事实的确如此,进步知识分子往往如彭湃、邓祝三等烈士,均出身于富裕家庭,却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献身革命事业,常常是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的骨干成员,对革命事业起了中坚作用;不但为革命献出了万贯家财而且矢志不渝直至献出了生命。即使在工农出身受到极端重视的岁月里,知识分子革命者也起了工农分子无法替代的作用。“秘书专政”这种怪异现象是“左”倾错误造成的,对革命事业危害很大,折射了知识分子革命者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尴尬处境,在本质上表现了党的事业的兴衰与能否重用知识分子息息相关。
“学习研究历史是为了向前看,要学会在学习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此来启发思想”[3]2。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行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关于知识分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广大党员必须时刻警醒“左”倾错误,应该牢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教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375。
[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中共两广省委文件[M].[出版地不详].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
[2]金冲及.谈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五十年变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3.
[3]王炳林,方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贡献[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5.
Study on 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under“the Secretary Dictatorship”Phenomenon in the Period of the Guangdong Agrarian Revolution
LIU Hao
(School of Marxism of Hezhou University,Hezhou 542899,Guangxi,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Guangdong land revolution“the secretary dictatorship”phenomena was very interesting.Intellectuals revolutionaries because of“original sin”were to be excluded,they could play a role of“dictatorship”because of their irreplaceable role,and then,if they can play a role in the cause of revolution is crucial to the success of revolution.
Guangdong;agrarian revolution;the dictatorship of intellectuals;intellectuals
K263
A
1007-5348(2014)03-0010-05
(责任编辑:宁原)
2014-01-13
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项目“为了共产主义信仰:抗战前岭南地区革命知识分子群体之心路历程研究”(KF2012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昊(1965-),男,湖南衡南人,贺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