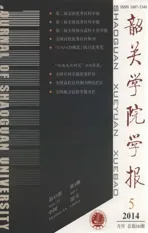论电影《美食、祈祷和爱》的空间叙事策略
2014-04-10甘细梅
甘细梅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论电影《美食、祈祷和爱》的空间叙事策略
甘细梅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电影《美食、祈祷和爱》(Eat,Pray&Love)是一部关于美国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在婚姻和情感遭遇挫折后,通过在意大利享受美食,在印度祈祷冥想,在印度尼西亚施予爱、获得爱而最终明白生活真谛的作品,其心灵的成长在充满衰落、冲突、贫困和异域风情的空间中得以实现。因此,影片旅行空间的表征模式具有政治的策略性,伊丽莎白的在场是一个能指,是获取认同、传播美国文化价值的符号。
表征;旅行;认同;他者
电影《美食、祈祷和爱》(Eat,Pray&Love)是瑞恩·墨菲自编自导的电影,改编自美国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于2006年写作的同名回忆录。该书因女性自我寻找的主题备受推崇,被誉为“治愈系的圣经”(Oprah,American Queen of Talk Show),曾连续187周位于《纽约时报》最畅销书名列。而影片也因女主人公伊丽莎白寻找自我和生活真谛的主题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
伊丽莎白自我成长的主题是影片的主要视点。然而,随着伊丽莎白旅行路线的展开,影片展现给观众的是一场景观的盛宴:时尚现代的纽约都市、历史悠久却已衰落的罗马古都、贫民窟式混乱的印度、充满异域田园风情的印度尼西亚。影片旅行时空的表征模式不禁让人怀疑影片的意图是为新女性的成长树立典范,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伊丽莎白是跨越边界的旅行者,也是旅行叙事的叙述者。她在旅行空间内生产了自己,同时也生产并叙述了旅行的空间,并赋予了空间以身份和叙事性。伊丽莎白如何在空间中生产自己并生产旅行空间?她采取了什么叙事策略表征旅行空间?目的何在?本文将利用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对电影中四个编码的空间进行分析,探讨影片空间表征的特点,进而挖掘空间表征模式背后隐藏的动机。
一、出发点:谁动了“我”的奶酪?
旅行是寻常生活的寻常之事。此处的旅行,指跨越分割不同人群和不同文化状态边界的行为[1]。在本质上,旅行即旅行者所处空间的变化。旅行者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一个空间,离开某个地方,经过某些地方,主动或被迫直接体验他者的文化,性格、心智发生改变,然后以崭新的姿态返回出发点或到达预设的某处。这是旅行最具普遍性的隐喻。从影片的故事情节上看,伊丽莎白为期一年的旅行即是为了心智的成长。然而,“空间并非剥离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科学客体,空间总是政治的、策略性的。”[2]10空间并非纯粹的中性容器,而是主体意识形态活动的产物。主体在空间的活动“赋予一系列的事件和空间以叙事身份”[3]。伊丽莎白的旅行从表面看来是为获得个人心灵成长,然而从深层次看,它是具有政治性、策略性的权力活动。这一点从旅行的出行点就可以看出端倪。
旅行包括出发、旅途和返回三个阶段。旅行的起点定义了旅行的动机以及旅行的最初意义[4]25。纽约是伊丽莎白旅行的起点,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在经济、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处于世界顶级的高度。摄影师采用大量的全景式和仰视角度的镜头呈现纽约的现代性、经济的发达以及文明的进步和强大:雄伟挺拔的高楼大厦、时尚优雅的生活、雄心勃勃的人们。然而,大量使用全景和仰视角的镜头也通过厚实、高大的墙体渲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距离感和疏离感。摄影师转而通过细腻的特写镜头描写微妙的情感关系。宴会结束后,在伊丽莎白和史蒂芬开车回家的路上的一幕,摄影师巧妙地运用了狭小昏暗的车内空间与全景式光亮的纽约空间形成光、色和空间维度的对比,暗示伊丽莎白和史蒂芬的情感陷入了困境。从车窗上可以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路灯昏暗模糊,伊丽莎白和史蒂芬话不投机,一个想出行,一个想深造,气氛尴尬,伊丽莎白面露失望、失落的表情。在表征伊丽莎白家的室内空间时,摄影师通过灯光效果进一步渲染伊丽莎白的情绪。他关掉所有室内灯光,让室外的微弱灯光射进房间,鲜亮的家具因此蒙上了阴暗的色调,伊丽莎白在曾经苦心营造的一切里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影子,这加重了她失落的情绪。情感的不能沟通成为伊丽莎白出行的导火线。人与人情感的隔阂和疏离是大都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副产品,是人们生活缺乏幸福感的根源。纽约的大都市孕育了繁荣也因此而生成了情感交流的障碍。
纽约作为旅行的起点,是伊丽莎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土壤,也是培育伊丽莎白身份特质的母体,因为“空间化身体的物质特征源于空间,源于那些在空间里布展和运用的能量”[5]28。主体从空间获得特殊的能量而获得身份。和她的丈夫一样,伊丽莎白也是典型的纽约人:事业成功,生活富足,时尚高雅,来往有鸿儒,却存在亲密沟通的问题。摄影师同样采用了仰视角的镜头来凸显一位遭遇感情挫折仍不失理性、文明、优雅、幽默的铁娘子形象。在伊丽莎白与好友迪莉娅去看戏剧的路上,摄影师首先采用了俯视角度的镜头,顺着高大建筑往下摇镜头,俯瞰街道,紧接着采用仰视角的镜头后推。仰视的镜头中,建筑物巨大,而伊丽莎白一点不显渺小,反而显得高大、强大,继续前行。即便处在婚姻和情感困境之中,失去家庭,身无分文,她依然听从内心的召唤,坚持年少时周游世界的梦想,依靠预支的稿费踏上了自我寻找之旅,重建自我、再创辉煌——又一个美国白手起家的现代版本。创业者不再是强壮的硬汉,而是铁血柔情的白人女性。伊丽莎白是自由女神的活雕塑。她高举燃烧着的美国梦之火炬,崇尚自由,拒绝僵化,敢于挑战新的困境,变革自我,更新自我,建构自我。
因此,伊丽莎白的在场是一个能指,指向美国的文化价值观。《独立宣言》中规定幸福的生活是美国人民的权利。伊丽莎白婚姻的不幸福和情感危机是对《独立宣言》的背离。离婚和离开即是割弃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恶性肿瘤,将自我置于陌生的空间中,磨砺心智,寻找接近上帝的契机,获取心灵的平衡。旅行在向内的维度上是抛弃隔阂,修复伤痛,重获沟通,获得幸福;在向外的维度上是美国社会在发展的困境中,向内审查自己,剔除病变,以便在世界发展潮流中重新扬帆起航——即是出行的最初意义。为了掩盖血淋淋的伤口,影片为伊丽莎白的旅行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巴厘岛的九代巫医传人凯图·莱耶的预言。
二、旅途:“我”的地盘“我”做主
旅行的出发是“离开”或“脱离”的体验,是旅途的起点。而旅途则是旅行者“跨越边界和空间的体验”[4]56,是对旅行目的的实现。根据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法则,生命体“在空间里生产自己,同时也生产那一空间”[5]5。主体在空间中形成自我的身份,同时,因为其姿态和能量的布展状态,也赋予了空间以身份。伊丽莎白是旅行者,也是旅行空间和旅行事件的叙述者。她存在于空间之中,是空间的一部分,同时也生产了空间。她的主体性决定了空间能量布展的状态。旅行的空间是她凝视的客体,具有强烈的伊丽莎白式的价值观色彩。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每个有生命的身体,在它们对物质领域(工具和对象)产生影响之前,在它们通过从那一领域吸取营养来生产自己之前,在它们通过生产其他的身体来繁殖自身之前,它既作为空间存在,同时又拥有它的空间”[5]5。空间生产的前提是生命体的存在。而生命体需要能量才得以维持生命活动,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进而生产空间。因此,伊丽莎白首先解决的是作为个体的生存问题。因为婚姻和感情的不幸福,伊丽莎白感觉自己失去了食欲、活力,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她需要重新获得对食物的欲望和对生活的热情。在旅途中,她依赖空间而存在,是“空间的被构成者”,也是“空间的产物”[5]28,依赖旅行空间给她供给物质和精神的养料,以愈合她身体和精神的伤口,获得再生产的能量。意大利的美食激活了她的味蕾,强壮了她的体质,也重新激活了她的热情、激情和信仰,使其重获生命力和活力。同时,她又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罗马古城获得文化精神力量的支持。摄影师用了大量的全景镜头和俯视镜头表现罗马历史的辉煌岁月和奥古斯丁陵墓的宏伟壮观。在巨大的古建筑群中,伊丽莎白没有了在纽约的高大形象,她显得非常渺小。摄影师通过伊丽莎白的眼光特写了支撑巨型房顶的架子,尤其是奥古斯丁陵墓经历了洗劫、烧毁、衰败的沧桑之后依然屹立不倒。虽然辉煌已经不再,毁灭却带来变化和发展。厚重的体验给了伊丽莎白迈出变化、面对变化的勇气。通过回忆,纽约的空间嵌入意大利的空间,并从中获得了冰释前嫌、宽恕理解、在毁灭中重生的力量。伊丽莎白所代表的美国缺乏历史底蕴。回归古都,熏陶意大利的人文气息,在历史文化的源流中感悟人生哲理,重新找回通往幸福的途径,也丰富了美国关于幸福的含义。伊丽莎白选择意大利作为旅行的第一站,目的即在于通过罗马城的空间补充历史文化的正能量,培养身体和精神健康的文化载体。
然而,通常情况下,生物体所捕获的能量并非刚好等于其自身所需要的能量,过剩的能量会储存起来或消耗掉。但能量在本质上是“生产性的扩张”[5]11,它的布展和扩张以生物体为中心,将“我”的主体置于中心位置,并需要“他者”的存在作为能量扩张的前提。影片将伊丽莎白的主体地位置于空间的中心,一切活动皆以她为轴心开展。她是旅行路线的策划者,她主导故事,推动故事进程。她劝说瑞典的朋友苏菲享受美食,她在意大利的家庭主持感恩节晚餐仪式,向意大利人民传播上帝之爱以及真正的美国感恩文化;她在印度指点困惑的印度女孩图尔西,并祈祷她婚姻幸福;她与巴厘岛的单身母亲韦恩是“姐妹”关系,并以自己的生日为名凑款为她建造了房屋。伊丽莎白并非是一个需要别人拯救的受难者,相反,她是边缘文化的救赎者,是落后地区的光明使者,是先进文明和上帝福音的传播者。伊丽莎白在意大利、印度和巴厘岛的主要出场场景暗示了她的天使身份。第一幕,伊丽莎白进入凯图家门的镜头,镜头微微向上,伊丽莎白从光环中走进来,走下台阶,伊丽莎白仿佛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天使。第二幕,在意大利,伊丽莎白登上高大的建筑,摄影师以俯视角度的全景镜头鸟瞰罗马古城,并以幽默引出她此行是上帝给的彩票,暗示伊丽莎白的旅行是上帝的旨意。第三幕,虽然在印度的路上,镜头展现的是贫困、喧闹、肮脏、混乱、冲突的景象,但伊丽莎白抵达印度静修处的时候,静谧的黎明曙光出现在天空,伊丽莎白的到来给混乱带来了秩序、安静、平和。第四幕,伊丽莎白踏着早晨的阳光以愉快的心情骑车到凯图的住处。她自由跨越定义空间的边界,作为天使的化身,以上帝的名义观察、检查和批判现实生活。上帝,即伊丽莎白的出发点,在哪里呢?纽约。伊丽莎白在纽约进入进场时,走的是向下的楼梯,进入的是“底部”的世界。而纽约所代表的美国文化则是上帝的文化。
“空间——我的空间……首先是我的身体,然后是我的身体的副本或‘他者’”[5]17。空间不仅仅是一部能量的供给机,赋予主体身份和能量,同时它也是一面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的是颠倒的自己。“‘他者’是为映照‘自我’而出场。”[5]8“他者”的存在是为了说明“我”的身份,也是自我能量扩张的对象。“我”站在镜子前的姿态,决定了“他者”的身体和“我”看“他者”的角度。伊丽莎白呈现的旅行空间取决于她的观看姿态和角度。作为处于美国上层社会的白人女性,她体验的是已毁的文明,边缘化和落后的异域文化,建构的是与纽约的空间特质不同的文化空间。异质的空间、群体和文化强化了中心/边缘,东方/西方,文明/落后,现代/破败的二元对立机制。“社会空间关系其实表征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2]11二元对立的空间体现了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也为伊丽莎白传播美国文化价值观,获取其他国度包括受众的认同做了背景铺垫。
“‘他者’除非是‘自我’通过暴力,或者通过爱而成为能量扩张的对象……否则这个‘他者’是不可渗透的。”[5]8自我通过暴力或者爱的力量使“他者”成为能量扩张的对象,以此将主体的意识形态渗透“他者”,获得“他者”的认同。影片通过确立伊丽莎白的中心位置,通过建构差异空间,通过大爱将美国文化价值观渗透到意大利、印度和巴厘岛的空间,从而实现了空间的扩张。
三、抵达:联姻——新的出发
“空间在一种意义上,是作为千篇一律的旅途而供人选择使用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提供各种具有特殊价值的路径。”[5]25空间为旅行服务,也通过旅行得以体验。抵达是旅行的终点,是旅行目的的实现。影片以全景式的镜头从巴厘岛旖旎的风光开始,以巴厘岛海景的长镜头结束。巴厘岛是故事的起点,也是伊丽莎白为期一年旅程的终点。经历了意大利和印度的心灵之旅后,伊丽莎白在巴厘岛的身份从旅行者变为观光客,由苦行变为享受生活。“仅仅是方位的变化,或者是环境的变化,就足以使物体的构成片段被展现。”[5]17主体所处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事物的不同构成片段也被呈献出来。观光客追求的是视觉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景观满足观光者的休闲、放松和放纵,以迎合观光者的消费需求[6]。伊丽莎白在巴厘岛的住处是田野中一个隐蔽别墅,幽静、私密的浪漫之地,预设了浪漫爱情故事的上演。通过旅行者的凝视,伊丽莎白把巴厘岛让人畏惧的“险山恶水”、荒芜之地变成了牧歌式的友好之地,将处于边缘状态的土地逐渐趋向中心,成为都市人的梦想之地。
作为观光者,伊丽莎白在空间进一步扩张能量的基础上,缔结“姐妹同盟”和“联姻同盟”。结盟对象是具有经济实力的经济体或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国家。韦恩所代表的印度尼西亚地跨亚洲和大洋洲,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创始国之一和东南亚最主要的经济体。伊丽莎白对韦恩的捐助,映射了多年来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所发生自然灾害以及民主化进程中的诸多捐助,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重建家园。而伊丽莎白与费利佩在巴西的偶遇实际上是美巴“成熟伙伴关系”的拼贴。巴西和美国长期保持着传统、密切的政治和经贸关系,而美国是巴西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最大债权国。根据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2011年12月26日公布的最新年度全球经济体排名,巴西的经济规模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费利佩所代表的巴西富有且忠诚,与伊丽莎白一样有周游世界的经历和梦想,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好丈夫”。结盟反映了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和巴西之间微妙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表明了美国希望与强国结成稳固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浪漫主义想法。
四、结语
伊丽莎白是一位兼具才智、个性、美貌、魅力和梦想于一身的完美现代女性。她拥有世界上大多数现代女性所渴望拥有的一切:成功的事业、体面的生活、深爱自己的丈夫。然而,因为看起来有些无病呻吟的痛楚,她自愿放弃现有的一切,周密计划旅行路线,生产并叙述旅行空间。旅行的空间“改变旅行者与地点的关系,调节旅行者对世界、自我和他者的感知”[4]56。旅行的空间与主体相互作用,使得主体获得成长,获得对世界、自我和他者的认知。伊丽莎白英雄之旅的目的是让世界了解自己,获取“他者”对“自我”的认同,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影片的空间表征方式正是通过建构差异性,并通过温暖的“爱”的力量来拓展美国的意识形态疆域并维护与其他国家友好关系。
[1]唐宏峰.旅行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旅行叙事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6.
[2]赵莉华.空间政治:托尼·莫里森小说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
[3][芬兰]凯·米科隆.“叙事即旅行”的隐喻:在空间序列和开放的结果之间[J].甘细梅,译.江西社会科学,2010(1):35-42.
[4]Eric J.Leed.The Mind of the Traveler:from Gilgamesh to Global Tourism[M].Basic Books,1991.
[5]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建筑学”[M]//文化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John Urry.The‘Consuming’of Place[J].Discourse,Communication and Tourism.Adam Jaworskiand Annette Pritchard(ed.).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2005:20-21.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ravel Spaces in the Film Eat,Pray&Love
GAN Xi-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 China)
The film Eat,Pray&Love is on a famous American female writer Elizabeth Gilbert,who quests for the true self by eating in Italy,praying in India and falling in love in Indonesia after her tough divorce. However,her self-discovery is placed in the spaces full of decadence,poverty and exotic landscapes,which are thus represented to encode Elizabeth’s travel,and Elizabeth is a signifier to the American culture and values.
Representation;Travel;Identity;Other
I207
A
1007-5348(2014)05-0028-04
(责任编辑:王焰安)
2014-01-10
甘细梅(1980-),女,广东韶关人,韶关学院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