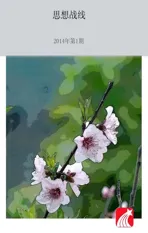认同与冲突:民国时期云南华永宁地区的“夷患”问题和民族关系
2014-04-09谷跃娟
谷跃娟
华永宁地区,孤悬金沙江之北,地理范围概指今云南西北的华坪、永胜及宁蒗彝族自治县及毗连地区。民国时期,这一地区分布着汉、彝、傈僳、摩梭、普米、藏、回等几个民族,其中,宁蒗所属之地,鸟道崎岖,交通不利,彝族诺苏支系聚族而居,势力炽盛,云南省政府政令未能行之有效,局部军事冲突多有发生,又屡有封闭道路、内部械斗、外掠他族之事端,致地方不安,族际关系失和。对此问题,时人惊叹:“长此以往势将演变至于不可收拾之境,是不独三属汉民之大患,实亦西南无穷之隐忧!”[注]马 钫(时任云南省保安第五团第三营营长):《华永宁彝区治理彝务问题意见书》,载永胜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98年10月,第169页。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边疆危机出现,云南省政府视边政建设为要务。事实上,云南省政府亦把对华永宁地区的经营视为巩固省防的内容之一,鉴于当地混乱失序的社会局面,经营设治,驻军不断,然而,民国政府的管理始终没有延及彝族内部,华永宁地区的“夷务”[注]民国时期的彝族,在政府文书、学术文献与民间口述中,有倮倮、猡猡、猓猓、倮夷、夷人、蛮子等族称。为体现当时的语言意识,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本文的一些论述援用彝族旧有称谓不做更改。“彝”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民族识别出现的族称,宁蒗彝族民主改革后有小凉山彝族之称。问题,直到民国末期未获解决。对于这一地区彝人“不服王化”的历史解读,传统的研究往往归结为政府治策的失误。显然,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并没有完全给出这一问题的所有答案。
民族认同是理解民族关系的一个基础,人类学家认为,族群指“一个民族中的各次族群单位”,族群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族群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注]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0页。族群认同在族群的互动关系中产生,认同不仅是心理层面的,而且还是行为层面的。“工具论者”认为,族群认同是基于对利益与资源的竞争。科恩(Abner Cohen)更指出:族群是和权利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认同都可以看做是与一定的权利争取有关。为了争取权利与资源,在实践过程中不同族群会利用相应的层次概念来表达。[注]转引自巫 达《传统宗教与凉山彝族文化认同》,载谭伟伦,王 刚《宗教、社会与区域文化——华南与西南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5~154页。
毫无疑问,民族认同与民族关系的生成息息相关,如果把问题再深拓的话,在民族国家认同体系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还应该存在着递进的逻辑关系。因此,在对民国时期华永宁地区“夷患”问题和民族关系的解读中,有关彝人“本族意识”和“他族意识”,以及他们的民族认同是怎样整合制约着民族内部、民族与政府、与周边各族之间关系的发展,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民国时期华永宁地区是云南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矛盾冲突最为严重的典型地区。华永宁地区的彝族,与地处中国西南腹心、人口众多、有“独立倮倮”之称的大凉山彝族,有着共同的地缘和族源关系,对这一地区民族问题的研究,可以为理解民国时期西南彝区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学术样本。
一、民族竞争中的“家支”与“诺苏”
有关华永宁地区彝族诺苏支系的来源,史籍鲜于记载,据最早迁入宁蒗的黑彝补余家支系谱及当地的口述传说,约在清乾隆、嘉庆年间,补余大小家支因冤家械斗陆续从大凉山迁入,迄今已有250余年的历史。黑彝瓦渣、倮姆、罗洪、热柯家支迁入略晚。民国时期,华永宁地区上述五大黑彝家支势力较大。
作为华永宁地区的非原驻居民,彝族开发华永宁地区的历史非常短暂,这就使他们在资源的占有上,先天性地失去了某些话语权。因为后来者的身份,他们租种土司林地,开荒放牧,向土司缴纳地租和草场税,为土司守哨,这一时期的彝人在周边各族眼中,是“服管又服调的”。[注]杜玉亭:《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载《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页。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民国前期。
移民是个渐进的过程,彝人陆陆续续从大凉山不同地方辗转迁徙到华永宁地区,越来越多的彝人进入到宁蒗山区,形成了曲诺家支依附诺伙家支聚族而居的情况。
家支在当地彝语中称“搓佳”,指人的血缘集团,“搓佳”的分支叫“搓涅”,“涅”原意为“根藤”,指同一个血缘集团中由血缘近亲构成的支系。学术上把家支理解为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个体家庭的联合体,是诺苏社会的基本组织。诺苏的家支社会由诺伙家支及曲诺家支两个层面组成,每个层面又由若干没有隶属关系的家支群体组成。每个诺伙家支下面,有世属的曲诺家支,发展到民国时期,补余家支世属的曲诺家支有金古、吉伙、佳日、阿鲁,瓦渣家支有阿的、阿西、阿库,罗洪家支有布散、吉伍,倮姆家支有阿克、阿略,热柯家支有阿苏、结海等。家支具有维护等级制度、保护家支成员生命财产、处理家支内外关系以及经济互助的作用,家支内部严禁通婚,实行等级内婚、世代联姻,如补余与瓦札家支、罗洪与倮姆家支、瓦札与罗洪家支,都是数世的婚姻世家。
血统是彝人构建自我的核心要素。在这里,民族构建的原生论得到强烈映证。清咸同年间,白彝阿鲁几祖帮助清军击败滇西回民起义军,得到地方政府和蒗蕖土司信任,被委为“千长”,并且得到当地富裕地主的资产,一跃成为地方巨富。阿鲁几祖是黑彝余家的曲诺,他的主子补余阿呷及其子孙,在阿鲁几祖的帮助,成为闻名小凉山的富有的大黑彝。关于这一现象,用“阶级”的观点显然解释不通。但是,如果以诺伙阶层所承载的血统与族性来看,这种对“骨根”的认同,并不难理解。
在彝人社会,每一个人生而有之地具备了某种血统和族性,而识别的工具,就是家谱。家谱是家支的物化形式,家支名称后面,对应着血统与等级。每一个成年的诺苏男子基本都能背诵自己的家谱,家支谱系在诺苏社会是一种通晓性的地方知识。个体的人通过家谱找到家支,从而找到他的社会归属,同样,人们通过一个诺苏男子的姓,首先判断的也是“他是哪家(支)的”,然后再决定交往的态度与方式。任何认同都可以看做是与一定的权利争取有关,家支是个体成员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是个人身份识别的旗帜(事实上,凉山彝族历史上就是以旗帜来区别家支)。在诺苏社会内部,尽管个体的认同具有多种层次性,但与其他成员发生关系时,首先呈现是对自己家支的认同。比如,民主改革前的宁蒗彝族,在婚姻上奉行的是家支通婚和等级内婚,个人意义上的婚姻关系是不存在的,婚姻关系的缔结,实质就是家支关系的缔结。此外,家支认同随着家支血缘关系的远近具有层次性,不同家支之间会产生不同的认同,在认同难于统一时,彼此就成了“冤家”。民国时期宁蒗彝族的冤家械斗非常频繁,如黑彝补余与瓦札,倮姆、瓦札与热柯就常有械斗。有些械斗甚至长达数十年,规模最大的有1943年补余和瓦札由争地引起的械斗,万余人参加,死伤数百人。
家支已经起到了政权的实际作用,成为利益博弈的载体,家支利益取向,则成为影响族群内部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个以血缘和血缘纯净度来构建“族”与“族的纯粹性”的共同体,在自我的认同方面所具有的层次性,或许是对彝族历史难以产生超越家支之上政权力量现象的一个解读。
20世纪20年代,彝人势力开始崛起,部分黑彝开始不照例缴纳官租和草场钱,停止给土司看哨,势力较大的补余、罗洪、瓦札等黑彝,则将土地直接据为己有,成为了土地的实际所有者。[注]《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历史调查》,1977年,铅印本,第30页,第31页。在土地所有权的流失过程中,土司势力逐渐走向了衰落,以新营盘为统治中心的蒗蕖土司,对其辖境内的黑彝已近不能制,远处泸沽湖畔的永宁土司,也不得不联合和利用大黑彝米撒瓦的力量来保境平安,抵制东南部黑彝补余、瓦札、热柯家支的劫掠。[注]《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云南小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历史调查》,1977年,铅印本,第1~7页。
家支的作用愈显突出,家支势力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力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彝区社会秩序的构建之中。依仗家支合力,彝人对其他民族展开了对土地的争夺,居住在宁蒗河谷坝区的汉、回等族频遭劫掠,凡衣食用度,尽其所取,大批汉、回不得不离家弃土,逃到四川、永胜、华坪,土司辖区的傈僳、摩梭和普米等族亦不得其保,如蒗蕖土司所辖的十余村普米族,有一半以上村子被迫迁徙并寨,有的汉族、普米等民族为了生活,不得不向黑彝和富裕曲诺投保。据统计,到1949年,这一地区不到总人口4%的黑彝,占了总耕地面积的70%,[注]杜玉亭:《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载《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其中大约20户黑彝,占了彝族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
华永宁彝人自称“诺苏”,意即“黑色的人”。在彝语里,“诺伙”、“曲诺”、“诺苏”里的“诺”,同音、同字、同义。“诺苏”是一个涵盖性极强的词,强调的是“根骨”。它不仅消弭了诺伙与曲诺之间的血缘差距,还消弭了家支之间的分歧和界限,即便是冤家,也能凝聚起来一致对外。诚然,没有“他族意识”就没有“本族意识”,民族认同是在与周边族群的交往和矛盾中,不断得到强化的。在“诺苏”这一概念层次,彝人是整体的、同质性极强的,在血缘与文化方面与其他民族存在明显边界的人群。比如,在整个民国时期,宁蒗的诺伙和曲诺,没有发生任何和外族通婚的案例,首先,强烈的“本族意识”,已经密闭和阻断了所有的可能。
二、“夷患”问题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民国,是在新旧体制更替和抵御外族侵略中成长起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高涨,在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就华永宁地区而言,微观的历史呈现,往往与宏观的历史叙事相去甚远。近代民主运动的兴起、王朝统治的覆灭,并没有推动这一地区社会的进步。与激荡的时局相契合的,是这一地区愈演愈烈的民族竞争,特别是在鸦片大面积种植后,彝族发展了蓄奴经济,致对外掠夺升级,政府管理失控,酿成所谓“夷患”问题。
据乾隆《永北府志》及光绪《永北直隶厅志》的记载,清朝时期华永宁地区就开始了种植鸦片的历史,至民国三十年鸦片种植进入到了高峰区。对于鸦片,云南省政府时禁时种,政策不坚定,1937年云南省政府曾将宁蒗设治区划为鸦片“展种区”,据统计,当年宁蒗种植鸦片七千亩,收取烟土十四万两。[注]陶 广:《宁蒗县三十四年代查禁烟毒情况》,载宁蒗彝族自治县政协委员会《宁蒗文史资料》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鸦片经济是在汉族与彝族畸形的经济互补关系下发展起来的,受其影响,彝区经济结构改变颇大。宁蒗红桥区石福山乡,民国时期,“特别是汉区禁种以后,石福山鸦片的种运量就大大地增加起来。据调查,该乡大烟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3%,而农业收入才占总收入的42.3%。”[注]王叔五:《宁蒗彝族自治县红桥区石佛山乡彝族社会调查》,载《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9页。鸦片让彝人有利可获,并成为彝人最有价值交换商品,彝汉之间的贸易范围也随之扩大,汉族商人用大量的白银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大烟,彝族对汉族日用商品的需要量也相应获得满足。
枪支也在这时候大量流入。中华人民共国成立前,宁蒗彝人已拥有枪支近2 000支。[注]杜玉亭:《云南小凉山彝族的奴隶制度》,载《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武装使彝人对外劫掠随之升级,掠夺范围从宁蒗发展到了永胜、华坪等地,为补充鸦片种植的劳动力,20世纪20年代以来,彝族对周边民族人口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掠夺。1944年至1945年在任宁蒗设治局局长的易忠孝,在向省府的情况报告中曾说:“一日数抢,一年不下百余起”。[注]陶 广:《小凉山奴隶社会》,载宁蒗彝族自治县政协委员会《宁蒗文史资料》第2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政府视角中,“夷患”对当地社会经济的破坏是极大的:
民国38年,永胜县北胜乡第5保遭到了黑彝的劫掠,杀伤5人,杀死2人,被掠成年男女及儿童28人,牲畜1 825头(只)、农产品及财物若干,“人民逃散四方流离道途,哭声震地,罕古未闻。其占据村闾肆意抢劫,凡民家财物日常用具概行搜掘,门窗墙壁任其毁坏,牛马牲畜鸡犬不留,农产粮食掠夺尽磬。最可痛者衣服被剥,时值寒冬,日则以棕衣被体,夜无铺盖,唯烧蒿棘愁待天明。入厨难觅糟糠而炊煮之器全失,形同乞丐不如。更可恨者圣贤书籍蹧踏泥塗,家堂神位任意毁坏,所到皆然,目不忍暏。”[注][民国]北胜乡公所《永胜胰北胜乡第五保被匪抢劫灾况表》,永胜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案卷号10,序号33。
彝族的劫掠行为还造成当地社会经济的倒退。例如,宁蒗有“木里金洞,凹里金厂,龙达金厂,铜厂河之铜厂,黑盐塘之盐厂、二平厂之银矿,金子沟之铁厂,白牛山之白牛银厂等,于民国前十八省人土,集资大批开采,曾设有十八省会馆,规模宏大,至民初因彝患猖獗,遂渐歇业”。[注]马 钫:《华永宁彝区治理彝务问题意见书》,载永胜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永胜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98年10月,第169页。
民国时期处理“夷务”的原则,“或择取羁縻政策,或用怀柔方略,或主剿抚兼施,或用以夷制夷的方法,然都视夷人为化外,从没有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积极地抚助他们,领导他们,使他们成为国家的一种良好的民族。”[注]毅 夫:《宁属的政治指导区》,载《康导月刊》第2卷,第6期,1930年。
国民党政府在华永宁地区虽多有设治,但能力所及,仅限于汉族居住的坝区和部分土司辖区,对宁蒗的管理近于失控,如宁蒗设治局为政13年,局长更迭就高达10人次。设治局主查禁鸦片、征收田赋、解决民事案件、整顿社会治安,但收效甚微,[注]宁蒗县志编纂委员会:《宁蒗彝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65页。鸦片屡禁不止,边政不藏,律令废弛,社会十分混乱。1937年,龙云的嫡系、国民党华永独立营营长安纯山曾坐镇永胜,利用黑彝补约家支刻意经营,但收效不大。事实上,家支取代了地方官署的管理职能,“到政府那里去讲理,靠国民党,脑子里一点点这种想法都没有”。[注]2011年2月14日笔者在宁蒗天宝酒店对彝族金古五斤访谈记录。金古五斤,83岁,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人大原副主任。显然,在民族自我认同强于国家认同的情况下,民国政府既没有找到破坏彝区政治权力的方法,也没有找到加强认同、构建一个新体系的途径。
针对当时藏区和摆夷地区出现的领土危机,这些认识并非危言耸听。所谓“不知国家为物何”、“视汉人竟如仇敌”,正道出了当时西南各数民族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普遍现象。
比如,在华永宁地区,彝族对于汉族,大多也有蔑视心理,和大凉山彝族一样,在彝汉冲突中,“夷常胜而汉常败,遂作成倮倮轻视汉人之心理。夜郎自大,自命高贵。使俘虏之汉人为奴隶,严定阶级,不通婚媾,而同化之希望以绝,汉夷相疾之思想,乃更养成”。[注]常隆庆,施怀仁,俞德浚:《雷马峨屏调查记》,中国西部科学院发行,1935年。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的军事组织与彝族曾发生了数次武装冲突,其中较大的有“马鞍山” 战役(1931年),伤亡高达100余人。[注]宁蒗县志编纂委员会:《宁蒗彝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页。这是厉行禁烟引发的彝人的抵抗。在彝族口述史中,这次战役又被表述为彝族多个家支与“汉兵”的交锋,“把彝族家刚刚长点的大烟给砍了,当时这是彝族的生存来源,比较恶劣的人把鸡啊、牛啊抢起走,抢啊、杀啊。但是彝族要报复,不知道是国民党的兵抢的,就是说汉兵抢的”。[注]2011年2月14日笔者在宁蒗天宝酒店对彝族金古五斤访谈记录。在那一时期,宁蒗彝人的认识里,无论川军、滇军,都是“很坏”的汉人,他们没有政党或国家的象征意义,只是异族的代表。彝语云:“石头做不得枕头,汉人做不得朋友”。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内涵,在于国家内部各多元民族和族群是否认同新的民族共同体。在对主流民族——汉族的认同没有建立之前,对政权、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还有很长的距离。
政府对宁蒗经营的失败,是治策和民族合力的结果。其实,民族隔阂历代有之,彝汉对立并非天生存在,这应当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对彝区军事围剿和文化歧视的积累。对于彝族“不服王化”的人类学解释,必须从彝族对历代政治主体的认同来寻找答案。
三、结 语
民国时期云南华永宁地区的夷务问题和民族关系,对民族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彝族某些历史发展的痕迹,至今仍然可见,如近几年来悄然复苏的家支制度问题,又比如,彝族的民族认同及新的民族关系的构建,以及对彝族社会非“非彝根”彝人的认同问题,在今天看来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