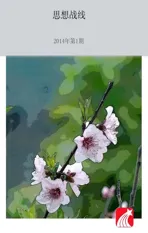从地方一族到国家公民
——“白族模式”在中国民族建构中的意义
2014-04-09李东红
李东红①
一、乡土根基的确立:白族本土起源论的进一步深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昆明羊甫头》,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剑川县文物管理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澄江县文物管理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 2011年第1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使沉寂多年的云南青铜文化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云南青铜文化从何而来?洱海、滇池两大区域青铜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云南青铜文化为什么在汉代开始转型?谁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白族起源甚至是云南历史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2003年至2006年,考古工作者对洱海银梭岛古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结果证明,这一遗址开始于距今5 000年前,到商末至战国时期结束,经历了新石器、青铜器、铁器三个考古学时代3 000年的连续发展。该遗址中期文化层中出土青铜鱼钩、青铜残片、青铜炼渣与铜矿石,还有用于铸造青铜器的石范。从地层关系、器物证据两个层面,证明新石器文化直接过渡到青铜文化。[注]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大理市文物管理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
2008年,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有三大成果:一是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二是证明了洱海区域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三是用确切的地层关系说明,当地新石器文化与青铜文化之间,具有直接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注]剑川海门口遗址的年代:起于距今约4 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经铜器时代初期至中期,到铁器时代。遗址是目前云南已发掘的最早的铜器时代遗址之一,为云南青铜文化的发源地。
以上两个遗址都是跨度长、内涵丰富的居住遗址:前者是云南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后者则开启了云南的金属时代。这两个遗址从器物、地层、时代三个方面,证明云南青铜文化并不是从域外传来,而是起源于当地的新石器文化。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洱海区域,并经历了自西而东的传播过程。青铜时代早期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明显地受到来自洱海区域青铜文化的影响。[注]彭长林:《云贵高原的青铜时代》,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发端于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由剑川海门口向南到洱海周边,经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后到达滇池地区,以石寨山为代表形成了“滇文化”。甚至向东、向南,影响了黔、桂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化。[注]马 曜:《从海门口到石寨山——云南洱海和滇池地区原始社会的解体与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载《马曜学术论著自选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1~290 页;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更重要的是,它说明洱海区域、滇池区域的青铜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类型。这种青铜文化的基本面貌是:当时的人们多数生活在山间平坝地区,梳着“椎髻”发式,居住“干栏式”住屋,他们使用锄、斧、铲、镰等青铜农业生产工具,从事稻作生产,过着“耕田,有邑聚”的定居生活。社会形态上,已然是“君长以十数”的方国时代。“君长”们有权杖、铜鼓、贮贝器、编钟、葫芦笙等象征权力、财富与地位的礼乐器。剑、矛、戈、钺、箭簇、刀等大量的青铜兵器,说明那时战争不断。海贝、绿松石、黄金、玉器、青铜装饰品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流行,说明社会财富的集聚,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汉时期“西南夷”大致分为“椎髻、耕田、有邑聚”及“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两大族群。前者以“僰”人群体为主,居住在洱海、滇池为代表的山间平坝中,从事农业生产。后者统称为“昆明”,大多居住在同区域的半山区和山区。[注]尤 中:《从滇国到南诏》,载纳张元主编《大理民族文化研究丛书》第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年。从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来分析,我们认为,创造云南青铜文化的古代族群,应该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耕田,有邑聚”的“椎髻”民族。[注]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童恩正:《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通过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相关性比较,只有“僰人”在活动时间与空间、文化面貌等方面,与云南青铜文化区、系表现出一致性。因此,“僰人”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
“僰”字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说文解字》称“僰”是“夷中最仁”。《逸周书·王会解》说:“成周之会,白人贡乘黄。”《注》说“白民亦南夷”。“僰”与“白”同声通假。可见在中国早期有关族群的文献之中,就有了“僰”(白)活动的记载。秦汉时期,记载更为明确。《史记·货殖列传》说:“南御滇僰、僰童。”尤中先生认为“僰”即“僰族”,是先秦至秦汉时期居住在滇池、洱海等坝区的古老族群,他们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注]尤 中:《中华民族发展史》第1卷,昆明:晨光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在后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僰人”发展成为“上下方夷”、“白蛮”、“白人”、“民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为白族。
近10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使白族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的观点,得到进一步深化。从云南青铜文化起源于当地新石器文化这个意义上说,白族文化植根于云南乡土文化的沃野之中。
二、地方传统的形成:从白蛮文化到南诏大理国文化
考古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进入西汉以来,云南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汉文化色彩浓厚的文化类型。进一步的观点认为,云南古代文化出现了断裂。事实上,并不存在云南文化突然消失的问题。由汉至唐,云南文化经历了两次文化接触,进行了两次文化建构和转型:一是两汉以来与汉文化的接触,导致云南青铜文化转型为“白蛮文化”;二是初唐以来佛教的传入,使“白蛮文化”转型为“南诏大理国文化”。
(一)汉晋移民与“白蛮文化”的建构
云南青铜文化,上起距今4 000年左右的夏代初中期,下迄两汉,历时2 000余年。《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征服“滇国”之后,于元封二年(前109年)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长其民”。由于设治、驻军、移民等举措,中原地区的军人、官吏、商人、平民开始进入云南,并集中分布在从蜀川通往云南的交通沿线。设治是行使国家主权最重要的体现,国家政治的深入,使滇池、洱海两大区域为代表的云南“腹里地区”进入了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这一过程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云南青铜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之后,迅速转型;特色突出、个性鲜明的云南青铜文化开始向具有汉文化取向的铁器时代过渡。
考古发现表明,洱海区域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墓葬中,常出土铜柄铁剑等铜铁合成器和大量的西汉五珠、半两等“汉式器物”。[注]张增棋:《滇西青铜文化初探》,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92页;大理县文化馆:《云南大理收集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4期。滇池区域的西汉墓葬之中,汉式器物更加明显。晋宁石寨山9号墓,不仅出土汉式器物,墓内的器物组合也具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注]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文物》1978年10期。昆明羊甫头云南青铜文化墓葬,出土器物早期以“滇式器物”为主,中期“滇式器物”与“汉式器物”并存,晚期墓葬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滇式”葬法,但随葬品已经不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滇式器物”,而是以“汉式器物”为主了。 羊甫头墓地直观地展示了西汉中期至东汉初年,在汉文化影响下,云南青铜文化转型的过程。[注]1998~1999年羊甫头“滇文化”墓葬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滇文化”晚期墓葬中,尽管出现了不少“汉式器物”,但“滇式器物”仍然十分明显。东汉中期的墓葬之中,已难觅“滇式器物”的踪影,汉文化色彩浓厚。墓葬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葬法,但随葬品已经不是云南青铜文化的“滇式器物”,而是以“汉式器物”为主了。说明自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对云南本土文化的影响日益深入。参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4期。
云南的土著族群,特别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僰人”,与汉人移民接触频繁,经过两百多年的接触与融合,“僰人”接纳了大量汉族移民人口及其文化后,出现了“汉化”现象,[注]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政局动荡,王朝更替不断,大多无力顾及云南。由于王朝政治力量的缺失,汉人移民中的“大姓”与土著族群中的“夷帅”纷纷据地自雄,云南进入了“大姓”和“夷帅”统治时期。两汉以来迁入云南的大量汉族移民,与内地汉族失去了联系,他们与原著族群交错杂居,互通婚姻,逐渐由客籍变为土著,出现“夷化”倾向。西汉晚期以来,在洱海、滇池为代表的云南“腹里地区”反复上演的“夷人汉化”和“汉人夷化”过程,以“入夷则夷,入夏则夏”的方式,体现了文化的力量,最终导致了云南古代族群的重大变迁和文化转型。演变为“白蛮”或“西爨僰蛮”。“僰人”文化——云南青铜文化,完成了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演变成为汉文化色彩浓厚的“白蛮文化”。[注]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说:“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在文化上,有所谓“语言虽小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农业方面,除种植水稻之外,还种植麦、豆、粟等粮食作物。有葱、韭、蒜,桃、李、梅等蔬菜和水果。纺织业已发展起来,养蚕、纺丝绢和织麻布已成为妇女的家庭副业。家庭饲养的禽畜有鸡、猪、牛、马、狗等。其丧葬之俗“哭泣棺椁袭敛,无不毕备”。还“自云其先本汉人”。“僰子国”就是今天祥云、弥渡一带白蛮族群建立的国家。
“白蛮”及其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与汉文化接触与建构的产物。“白蛮”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具有明晰的族际边界、认同意识的族群。“白蛮”是“僰人”的后裔,是南诏统一后的主体居民。因此,“白蛮”及其文化,是云南青铜文化与南诏大理国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是“从滇国到南诏”的桥梁。[注]冯汉骥认为:滇族是当时南中文化最高的民族,“西爨白蛮”是滇族的后裔。唐天宝年间,爨氏内讧,遂为蒙氏所灭,并徙西爨20万户于滇西地区,成为南诏的主体民族白族。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试探》,《考古》1961年第9期。
(二)佛教与南诏大理国传统的形成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南诏统一洱海区域。南诏采用“拓东、开南、镇西、宁北”的战略,[注]南诏的众多城镇之中,在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分别设置“拓东城”(今昆明)、“开南城”(今普洱)、“镇西城”(今盈江)、“宁北城”(今剑川)。这些城镇的设置,体现了当时的战略。统一了整个云南地区。南诏是以洱海、滇池两大区域为中心的政治实体。南诏境内有众多的部族,但白蛮是它的主体民族。
大约在7世纪初的隋末唐初,即云南历史上的六诏时代,佛教就从古印度直接传入洱海地区,在白蛮社会中传播开来。[注]参见李东红《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经过100年左右的发展,到南诏中期,佛教被广泛信奉,对南诏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大理国时期,佛教成为国教,社会生活全面佛教化。南诏大理国文化,是以佛教信仰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它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室成员都皈依佛法,主体居民全体信仰佛教。南诏第七代国王丰祐“喻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每户供佛一堂,诵念佛经,手拈佛珠,口念佛号,每岁正、五、九月持斋,禁宰牲畜”。[注]尤 中:《僰古通纪浅述校正》,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页。大理国时期,段氏国王传22世,其中有10位皇帝先后出家为僧。豪门权贵高氏家族,为僧者更是不胜枚举。[注]大理国段氏传22代,其中第2、8、9、11、13、14、15、16、17、20代共10位国王,先后从国王的宝座上走向神坛,避位为僧。参见李东红,杨利美《苍洱五百年》之“国王避位为僧之谜与高氏专权”,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当时许多重要的佛教寺院、石窟寺、佛教造像、佛塔、画卷的建造与绘制,都与皇室和王公贵族有关。[注]具体的例子是:a.《南诏图传》是南诏王舜化贞向“儒释耆老之辈,通古辨今之流”,征询“圣教入邦国之源”令王奉宗等官员所作的佛教画卷。b.《大理国张胜温绘梵像卷》的内容,包括“利贞皇帝段智兴礼佛图”、“诸佛菩萨像”、“天竺十六国王众”等部分。此画卷完成于大理国圣德五年(1180年),是大理国宫廷画师张胜温专门为利贞皇帝段智兴“捏诸圣容”,以“利苍生”,并祈盼“家用国兴,身安富有”。c.现藏美国圣地亚哥美术馆的观音铜像,是“皇帝骠信段政兴,资为太子段易长生、段易长兴等造”。d.中国公高贞寿、高明清、高量诚是崇圣寺三塔的修塔大施主。e.楚雄兴宝寺为“大理国上公高踰城光”捐建。f.昆明地藏寺经幢为“大理国佛弟子议事布燮袁豆光敬造”。
其次,南诏形成了“用僧为相”、“以僧为官”的官员选拔制度。南诏大理国的人才制度,与唐、宋科举制有较大的差别。中原王朝的科举应试者是儒生;南诏大理国的科举,参加考试的都是僧人——释儒。“以僧、道读儒书者应举”、“用僧为官”、“用僧为相”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实现“以佛治国”统治方略的制度保障。[注]李东红:《白族文化史上的“释儒”》,《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第三,南诏大理国形成了仕宦出家的社会风尚。国王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让出王位,出家为僧;蒙氏、董氏、段氏、高氏、杨氏等名家大姓中的高官,往往舍弃高官厚禄,出家为僧;王室、大姓子弟之中,出家为僧者众多,大德高僧云集。[注]参见张锡禄《大理白族密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李东红《佛教密宗阿吧力教派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不恋红尘爱佛门,是当时的社会风尚。
第四,南诏大理国具有独特的教育制度与人才培养方式。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僧人被称为“释儒”,他们是传播文化与知识的“师僧”。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读书识字的目标,是要读懂、理解以汉字为载体的“佛书”。这种教育体制,推动了知识阶层社会生活的佛教化。[注]杨德聪主编:《图说云南历史文化》,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00~145 页。
佛教加速了南诏统治区内多元族群的一体化进程,促成了南诏主体族群“白蛮”与其他族群的整合,在南诏中心区域“十赕”形成了新的人们共同体——“白人”,更促成了“白蛮文化”的转型:具有较强汉文化取向的“白蛮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以敬佛礼佛为取向的“南诏大理国文化”。
南诏的建立、佛教的传入与流行、白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唐代中国西南边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三件大事。白人是云南历史上最早形成的、具有现代民族意义的族群,它是特色鲜明、辉煌灿烂的南诏文化的承传者。正如林超民先生所说,南诏国的建立、巩固、扩大、发展的过程,就是白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注]林超民说:洱海地区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釐城为中心的十睑(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河蛮、汉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河蛮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乌蛮”、“白蛮”的界限也不复存在,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参见林超民《白族形成问题新探》,载《林超民文集》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南诏大理国地方传统的形成、繁荣与发展,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开拓与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繁荣产生了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三、国家公民身份的确立:从白人到民家的转变
(一)元代儒学与地方传统的博弈
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征服大理国。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立云南行省,并确立了行省、宗王和段氏总管共同掌控云南的制度。终元之世,三大势力之间关系微妙。国家政治与地方传统、儒学与佛教的关系,成为矛盾的焦点。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传统与帝国政治之间发生了“佛道设教”与“儒道设教”之争。以“释”为主,还是以“儒”为主,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理念,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人才培养和选拔体制,服务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前者实行的是由佛教徒“师僧”为教授,培养“通释习儒”的“释儒”型人才,实践“以佛治国”的方略,它是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地方传统。后者以庙学为载体,以“师儒”为教授,讲授儒家经典,培养科举人才,实践的是“以儒治国”的政策,这是唐、宋以来儒学教育及科举制度的标准范式。因此,建立庙学,改革学制,是南诏大理国地方传统融入元朝国家政治的关键所在,它成了地方传统与王朝政治的争端。[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273页。
在“佛道设教”与“儒道设教”之争中,段氏地方势力做出了妥协。云南行省在洱海、滇池两大区域建立了11所学宫。[注]主要在云南府、邓川州、石屏州、河西县、大理府、嵩明州、澄江府、鹤庆州、永昌府、临安府等。“至元十九年(1281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注]《元史·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60页。庙学的普遍建立,使云南主流的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自南诏大理国形成的“释儒文化”开始转型。大理路儒学教授赵傅弼就说:“当今大理创修学庙,使旧染之俗咸与维新。”所谓“旧染之俗”,指的就是“重佛不重儒”的传统,“咸与维新”,当然是说地方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整体性的变迁。说明白人丧失了云南主体民族的地位,云南自南诏大理国以来的“白族化”趋向被中断了,白族历史文化的发展方向由此改变。[注]林超民:《白族形成问题新探》,载《林超民文集》第2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话题:历来论云南社会文化变迁的学者,都把明代作为观测点,把变迁的原因归于明代强力推行的汉化政策。事实上,如果没有元代渐进式的文化转型所奠定的基础,明代急风暴雨式的汉化政策,是不可能推行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元代云南行省的建立,不仅重建了中央王朝在云南的政治基础、健全了行政管理体系,而且在文化建设方面,开启了云南各民族国家公民文化建设的进程,引领了此后云南文化发展的方向。
(二)明代白人国家公民文化身份的建构
明代的云南,是国家政治、儒学、汉族民间文化与云南地方传统强烈接触、急剧碰撞的时代;是王朝体系彻底消灭了地方势力,“土人”建构国家公民身份,从地方传统转入国家政治的时代。
明代的白人,被视为南诏大理国及元代段氏总管时期的“遗民”。明王朝在云南推行的政策,就是在洱海、滇池两大区域,实行大规模的汉化举措。明代白人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是白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接触事件。它使地方传统中的白人文化,转型为王朝政治下的国家公民文化,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发展模式。
明代汉文化与白人文化的接触,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
战争。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派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经“白石江之战”、“昆明之战”与“大理之战”3次主要战役,打败了元朝梁王和大理段氏总管两大势力之后,平定云南,将云南纳入了明朝的直接统治。
屯兵。“我圣祖既平滇宇,卫、御、所东西星列,此不惟开疆辟土,垂示远略,其镇压周密,殆雄视百蛮也。”“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注]《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179《云南都指挥史司碑记》。在交通沿线及主要城镇形成了卫、所、营、屯、堡等驻军点,留戍士兵近10万人,建立了完备的卫所制度。[注]明代云南都司卫所有: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等处。
移民。把土著大姓有计划地迁出核心地区。根据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担心世族繁多的段氏滋生事端,就把居住在大理喜洲的7支段氏宗亲,强制迁往外地。[注]长支段世迁云龙,次支段宝迁昆明,三支段绂迁安宁州,四支段义迁陕西雁门关,五支段顺迁剑川州,六支段仁迁邓川州,七支段明迁腾越州。参见大理州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抄本《云龙石门段氏族谱》。与此同时,明朝在云南各地,特别是在原大理段氏总管管辖的洱海、滇池两大区域和重要城镇采取了移民屯守政策,把大量汉族人口,通过军屯、民屯等方式,迁到南诏大理国以来白人居住的地区。[注]按明制,卫领5 600人,千户所领1 200人,百户所领120人。仅就设卫的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10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的人数。明代屯兵,军士都是拖家带口而来,据有关资料考证,明代到云南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人口,估计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军屯就有30万人。形成与白人共同杂居的格局。
兴学。根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的考证,明代在云南设立的72所学宫、65座书院,大多分布在大理府、云南府、澄江府、永昌府等白人主要聚居区。建学校,兴儒学,图教化。大批学宫、书院的建立,成为白人聚居区儒学繁荣与发展的标志。明代中后期,儒学俨然成为白人社会中的正统文化。
科举。学宫、书院的普遍建立,儒学教育的发展与繁荣,为云南的科举考试储备了人才。有明一代,云南共有进士223名,以白人为主要居民的大理府、蒙化府、鹤庆府、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永昌府就有97人。[注]以卫学和府州县学来分,前者92名,后者130名;其中,以白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有:洱海地区(大理、蒙化、鹤庆)51名,云南府、澄江府24名,临安府16名,永昌府6人。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4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2~508页;木 芹,木霁弘《儒学与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及文化转型》,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李元阳《云南通志·大理府风俗》说:“郡中汉僰人,少工商而多士类,悦其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乡。”白人学习儒学,参加科举蔚然成风。南诏大理国以来以“释儒”出仕的传统路径,已经完全被明经取士所替代。
移风易俗。即以汉人移民文化习俗改造白人文化传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云南、曲靖、澄江、临安、楚雄、姚安、澜沧、大理、鹤庆、蒙化、永昌诸府及所属州县,渐被华风,尚诗书、登科第,接受汉文化。这些地区的白人,服饰言语都接受汉人的习惯。岁时风俗、宗族和宗法制度、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习俗、土葬和祭祀祖先方式等汉人的礼俗逐渐为白人所吸纳,变成白人文化的重要因素,形成“汉僰同风”。[注]2001~2002年,考古工作者对蒙自县城区西南部的古代墓葬进行了发掘,揭示了明清两代在汉族移民葬俗的影响下,白族由火葬向土葬的变迁过程。参见《瓦渣地明清火葬墓地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第159~192页。
“行教化以淳风俗”,达到“用夏变夷”的濡化效果,是明代治理云南的政策根本。在上述行政举措的共同作用下,白人开始了“去释崇儒”的新文化建构,其结果是白人逐渐摈弃了南诏大理国以来的地方文化传统,努力走近明王朝国家文化,建构国家公民身份。
“汉僰同风”成为明代以来云南文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关键词”之一。两百多年以后,滇东地区的曲靖府、云南府、澄江府、晋宁州、寻甸府、广西府,滇西地区的楚雄府、姚安府、永昌府等地区,由“土著者多,寄籍者少”,变为“寄籍者多,土著者少”。“土著者”从明朝中期的“汉僰同风”,逐渐融入到汉人移民之中,变为汉人。而在洱海区域,一方面白人外迁,一方面汉人移民进入。汉人“夷化”与白人“汉化”同时发生,导致白人文化发生很多变迁,汉人祖源说开始在白人社会中出现。
明代,“白人”称谓演变为“民家”。[注]有的学者认为“民家”是与“军家”相对应的称谓;有的学者认为“民家”是“名家”之演绎;有的学者认为“民家”是白(僰)人从统治族类变为少数族类后,为维护族类集体记忆、唤起族类共同意识、显示族类自尊自信的新称谓。这是汉、白文化接触的结果。范义田说,“民家”其实就是“明家”。通俗地讲,就是大明王朝的子民。“民家”成为白人的通称,说明白人已经完成了由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南诏大理国以来形成的“青山蒙氏赕,绿树僰人家”的地方传统,发生彻底改变:云南成为大明王朝管辖的13省之一,“白人”从云南的主体民族,转变为具有大明王朝国家公民身份的“少数民族”。
(三)清代至民国初期白人国家公民身份的强化
清代主政云南的官员,一直把地方传统纳入内地的文化体系之中作为执政的首要目标。[注]〔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中华帝国在西南的教育:陈宏谋在云南(1733~1738)》,载陆 韧主编《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7~137页。在云南土著族群的乡民社会中建立、推行儒学礼仪,通过“化导”土著民众,最终达到“化民成俗”的目标,就成为官员的首要使命,是那个时代的“一把手工程”。国家政治不仅通过儒学教育,同时还利用道教组织“同善堂”、宣扬帝王思想的“圣谕堂”等“坛”与“社”,对乡民社会进行政治控制。清代初年任云南巡抚的尹继善就说过:“夷人慕学,则夷可进而为汉;汉人失学,则汉亦将变而为夷。”[注]尹继善:《义学汇记序》,载王 昶编《湖海文传》,清道光丁酉经训堂刻本。儒学成为区分“华”“夷”的边际,是国家公民文化身份的象征,是国家认同的根本。
民国建立之后,通过设立保甲制度,彻底改变了“国权不下县”的传统,使国家政治深入到白族乡间。20世纪前半叶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使白族文化的国家公民身份更加明显。白族民间流传的“汉人祖源”说,与其说是血缘上、体质上,不如说是文化上的,即从“汉僰同风”到“汉僰一家”,认同以儒学为主流的国家公民文化。
四、“白族模式”在中国民族建构中的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都为云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历史进程中,洱海、滇池两大区域,还有滇东北地区,与内地联系密切。学术界把这一区域称为“腹里地区”。云南本土文化起源、汉代益州郡的建立与云南青铜文化转型、南诏大理国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元明清王朝政治等对云南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接触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区域。我们看到,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云南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汉文化接触与建构这样一个主题。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云南“腹里地区”的文化始终与“僰人”有关联。“僰人”与今天的白族不能画等号,但是“僰人”与南北朝至隋唐的“白蛮”、南诏大理国至元代的“白子”、“白人”、明清时期“民家”、现代白族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白族的历史与文化经历了乡土起源、地方传统形成与发展、国家公民身份建构三个阶段,该族也由地方一族发展成为国家公民,实现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对接,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发展。这一“白族模式”在中国民族建构模式中具有典型意义: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决定了各民族、各地域不同的根基历史;复杂的历史过程造就了以地域文化与族群文化相叠加的地方传统。地方传统融入国家体系,实际上是具有乡土文化习惯的地方族群,建构国家公民身份,成为国家公民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包括“华夏”与“四夷”在内的多样性地方传统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与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共同成就了中国的国家公民文化——中华文化。
秦汉以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表象上看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过程,实际上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从乡土根基与地方传统等“地方性”,逐渐建构国家公民文化身份,融入国家政治的必然路径。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既要保留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个性,又要实现民族文化与国家公民文化的对接。建构“国家公民文化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对于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