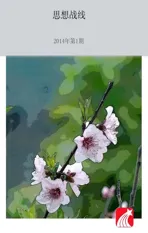青姑娘符号:明清汉白文化融合中的一个特例
2014-04-09王本朝
熊 娟,王本朝①
白族作为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形成于南诏国时期,成熟于大理国时代。从明代开始,白族在真正意义上被纳入中原政权的统治,从此走上与汉族文化的全面融合过程。与云南其他民族相比,白族的汉化过程较为成功,未出现激烈的暴力冲突,至清代,大理地区“僰(白)人”[注]从唐至民国,汉族对白族的称谓有“白蛮”、“白人”、“僰人”、“民家”等,本文为清晰起见,除引文外皆用“白族”称谓。明后,大理为白族的主要和核心地区,本文的白族主要指大理地区的白族。呈现“科甲繁盛”, 人才辈出,“渐被华风”[注]黄元治:《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 严镇圭重印。和“彬彬文献, 与中州埒矣”[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第696页。的景象。由此,白族汉化过程历来被正史称赞为“以夏化夷”的成功例证。
按照文化交流的理论逻辑,汉白文化作为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在交流的过程中既有融合,也会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特别是在外部政治压力之下,以儒教为代表的汉文化大规模介入白族地区时,两种文化的冲突必然有所显现。而精英历史记录的是中原政权的“以夏化夷”政策的成功和汉白两种文化交融的“和合”景象,然而,作为发展并不均衡且社会呈现二元状况的白族,对汉文化是否都表现出同样的艳羡和接纳心理,颇值得怀疑。
事实上,至今还流传在大理剑川白族地区具有重大影响的青姑娘故事和青姑娘节(节日在“文革”时被迫中止),以其独特的方式表征了明清汉白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痕迹。青姑娘传说为剑川海虹村底层家庭的一位姑娘, 因父母早亡而成为童养媳,聪明、勤劳和能干的她,受尽婆婆辱骂、小姑挑唆和丈夫殴打。那年的正月十五晚上,她不顾“夜不出门”的特殊家规出去与青年男女游玩,回家后遭受打骂,以示反抗于当晚跳河自尽。当地女性为纪念她,将正月十五日定为青姑娘节。青姑娘民间叙事以口传和仪式的形式,保存和表达了当地白族对汉族儒教礼仪文化的反抗,体现了白汉民族文化融合中的复杂状况。
一、明清白族“汉化”中的性别差异
明清被称为白族“汉化”时期,也即白族文化的转折和变迁阶段。从洪武十九年(1386年)在“白蛮”[注]“白蛮”为唐元明清汉族对白族的歧视性称谓,此引用为方便起见,无歧视意。地区开始的大规模军、商、民屯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伊始的大兴文教,“白蛮”走上了较为迅速的“汉化”过程。而在明清之前,早在汉武帝时就有大理人盛览、张叔前往若水向司马相如求学的记载,这是汉白之间最早的文化交流案例。从汉代至元代,汉白文化交流更甚。明清之前,虽然汉白之间文明程度有一定差距,两者之间往往体现为后进的“白蛮”文化向较之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作为文化输出方的汉文化在交流中占据主动地位,但由于汉白文化从属两个独立的政权,汉白两者的关系往往体现为平等的以单向为主兼具双向的交流。因此,“白蛮”在长期的与汉文化的交流和学习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致在唐就有“言语音白蛮最正”和元“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略本于汉”[注]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页。的记录,成为云南各民族中文化最为发达的民族。
明清之后,白族地区被纳入中央集权统治,丧失了原有的作为地方政权的独立地位。明代统治者通过屯田和兴办儒学,使得以儒教思想为主的汉文化大规模介入, 白族文化在外部压力下被迫全面接受汉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汉白文化之间的交流已不再是之前的传播关系,代之的是涵化与被涵化的关系。所谓涵化,即“不同社会处于支配—从属关系环境中的广泛的文化借取”,[注]〔美〕卡·恩伯,梅·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杜杉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6页。也即被迫接受强势文化而改变原来的文化。由于白族有着较深厚的汉文化基础,汉白文化本身不存在较悬殊的差异,所以,白族文化被涵化的过程较为顺利,没有出现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白族上层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积极学习和吸收汉文化,而且践行和传播汉儒教文化。[注]张丽剑:《明代汉文化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影响——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但白族社会的发展并不均衡,存在着地区、阶级和性别差异,按照美国人类学家芮斐德在《乡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观点来看,这种二元现象明显存在于明清时期的白族社会中。明清白族上层和知识分子在中央王朝恩威并施的儒化政策下,特别是开科取士制度,直接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权力体系。他们习汉书、汉文,参加科举考试,涌现了一大批文人和政府官员。正德《云南志》谓:“僰(白)人,少工商而多士类……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仅是剑川地区,明清两代中举者125人,其中进士16人。[注]剑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剑川县民族宗教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0页。白族上层浓郁的汉文化氛围影响着下层文化,使得白族底层家庭也非常重视男性的汉文化教育。特别是有“文献之邦”声誉的剑川地区,清末95%以上的村寨置学田或公产,作为民间办学的基金。不论家境如何,男孩六七岁后均要读书,至十四五岁或继续升学或转学手艺。因此,当地白族80%以上的男性粗通文墨,能写联语、书信和记账等。[注]剑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剑川县民族宗教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0页。由于剑川地处茶马古道上,是藏入滇的“咽喉”,又加上“地近雪山,土地饶瘠”,“间终岁勤动,往往衣食不给。故横经者不免负耒轭,而业农者必兼习工艺”,[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故剑川底层社会的男性出走他乡求学、做手艺、做工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张泓《滇南新语》真切地描写了剑川白族底层社会男性的生活:“(剑川)食众生寡,民俱世业木工,滇之七十余州县及邻滇之黔川等省,善规矩斧凿者,随地皆剑民。近则仲夏孟冬栽获两归,远则亦收获为期必一返,获毕仍往。”[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9页。白族底层社会的男性由于普遍接受了汉文化教育和周期性的向外流动,对汉文化出现了与白族上层一样的倾慕倾向,认同白族上层的 “耕读有人”和“宁可作汉朝之臣,莫作夷狄之君师”观念。而白族底层社会女性则与白族男性形成鲜明对比,她们既未能接受汉文化教育,又被隔离在外界之外,被捆绑在田地、家庭和村寨中。当男性游走他乡寻求发展机会时,女性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是以剑之耘蓐樵牧尽属村妆,男既远游,女当门户,催粮编甲,亦多妇代夫役,皆能练事无误”。[注]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1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0页。当地白族女性由于活动范围较窄,生活较为固定,成为白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真正传承者。她们不像白族男性那样,在对汉文化的比附和认同中日渐疏离其传统文化,逐渐失去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文化特性。
白族二元社会在面对外来文化介入时,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对于“完全适应变革”的“大传统”的白族上层、知识分子和大部分白族男性能成功“转型”,[注]〔德〕哈拉尔德·米勒:《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郦 红,那 滨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9页。而对于较为保守的“小传统”的以女性为代表的下层民众,往往坚守传统,更多是从民族文化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依据。于是,在白族的“小传统”中,产生了对外来汉族儒教文化的不适应和反抗,衍生于民间底层的青姑娘的故事和青姑娘节,便是这种文化“小传统”对汉文化反抗的集中体现和代表。
二、青姑娘:汉白文化冲突的证据
在大理剑川地区,至今仍流传有青姑娘的民间叙事,包含青姑娘故事、青姑娘甲马纸,青姑娘节(“文革”被迫停止),青姑娘歌和青姑娘舞等。白族历史上是否有青姑娘其人,因缺乏证据难以确证,但其祭祀仪式据专家推断至少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应产生于明清。青姑娘故事长期以来被解读为“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婚姻”,但许多细节显示着这种解读遮蔽了很多“意味”。
首先,故事中反抗婚姻的只有青姑娘,青姑娘的情郎却未出现。青姑娘歌中虽提及情郎,但只是在歌的“序歌”部分和结尾的“祝祷”部分,分别以第三人称口吻说,青姑娘盼望元宵节与情郎见面和众人祝福青姑娘魂归南海后与情哥同聚的情景。在整个故事中,情郎一直都是缺场者,既未与青姑娘有海誓山盟,也未与青姑娘一起抗争婚姻。因此,“青年男女反抗封建婚姻”只是青姑娘故事的部分意义。其次,青姑娘丈夫在故事中被塑造为 “唯母是从”、“心狠手辣”的形象。他对漂亮能干的妻子似乎没有感情,既不同于汉族相似主题的民间故事《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焦仲卿虽懦弱、孝顺,但有情有义;也不同于白族另一则同类主题的著名民间故事《火烧磨房》中的丈夫和小叔子,该故事情节为王氏与丈夫感情甚笃,丈夫外出服徭役后,王氏遭受婆婆乔氏折磨,险些被婆婆烧死在磨房中,小叔子则站在正义的立场极力营救王氏并痛骂母亲乔氏。青姑娘故事的如此设计应有一种寓意,相当于原型理论中的“置换变形”,即将婆婆、丈夫和小姑一家塑造为恶而无情的化身,他们合谋暴虐青姑娘,可看做故事中“凶恶”的反面人物,他们不仅违背了白族社会“一夫一妻较为牢固的婚恋习俗”,[注]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白族文化大观》,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而且制定“夜不出门”的特殊家规,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汉族礼教制度,可看做是汉儒教文化代表的隐喻。而故事中的其他主要人物:村东大妈、村西姑娘和全村人,皆被塑造为善良形象。青姑娘上山干活受伤后被伙伴送回家,在村东大妈和村西小妹照顾下痊愈,跳水自尽后全村人出去寻找,体现了跟前一方的凶恶完全不同的善良和温情。这两方形成的鲜明对比已不是同一群体内部的性格冲突,而应从属于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
此外,青姑娘节的仪式展演空间格局也强化了这一冲突。青姑娘为死于非命之“女鬼”, 按照汉儒教文化的观点来看,她是一个不遵守“三从四德”妇道的女鬼,是邪恶的化身,应被驱逐和绝对隔离在人居之外。然而,在儒教思想浸淫的剑川,青姑娘却被当地白族妇女当做神灵接入村寨祭祀和游玩,祭祀空间囊括了村外鬼魂的住所(桥下)、村内的私人和公共空间,这种有悖于汉儒教文化的行为不仅没有被普遍接受汉文化的白族男性制止,而且还以禁忌(节日里女性不能劳动)的形式得到鼓励。
青姑娘作为白族的一个民间故事,它以节庆仪式的方式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以人类学的眼光看,“仪式无不是自然和真实的一个社会媒介机构,它将自然的事件以转换的形态和面目出现”。[注]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所以,青姑娘祭祀仪式讲述的不只是故事陈述的表面内容,而有着更多的文化隐喻。即使历史上未曾有青姑娘其人,但“人们‘造神’具有一个历史的需要和必要”,[注]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3。也就是说,即使青姑娘是人们创造的人物和故事,但其创造的心理过程与象征也具有真实意义,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历史记忆”的事实,凝聚着这个群体的心理和命运的因素。青姑娘故事被重复讲述和青姑娘节被重复展演,它们皆为“重复出现的象征性交际活动”,[注]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深含着这个群体对青姑娘事件的思考和追忆,表达了群体强烈的愿望和情感体验,已成为传递文化信息的载体符号。因此,青姑娘俨然成为明清汉白文化冲突在底层显现的符号,但却与正史所记载的文化融合情形有所抵牾。
三、青姑娘符号生成的内在文化情景
文化冲突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作为文化冲突符号的青姑娘,其生成的内在原因也即为汉白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明代中央政府企图通过实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政策来达到“以夏化夷”,并彻底实现加强中央集权目的,但“华”、“夷”其实只是汉族统治阶层“想象的共同体”,是当时拥有文化优势心理的汉文化统治者以儒家礼教为衡量标准的产物。事实上,正如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言,每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它产生于并服务于其社会,是很难被外来文化强行替代的。因此,中央政府将中原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儒家礼制推行至白族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与白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汉白婚姻伦理价值观的不同导致了青姑娘符号的出现。明清之前的婚姻状况,我们从唐代樊绰《蛮书》和元代李京《云南行记》的记载,解放初期尚存于怒江白族勒墨人中的“南毫制”以及白族早期几则婚姻主题的民间故事中皆可看出。《蛮书·蛮夷风俗第八》云:“俗法处子孀妇,出入不禁,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闾巷,吹壶芦笙,或吹树叶,声韵之中,皆寄情言,用相呼召。嫁娶之夕,私夫悉来相送,既嫁有犯,男子格杀无罪,妇人亦死。”[注]木 芹校注:《云南志补注》卷8《蛮夷风俗第八》,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6页。婚前女子和寡妇与男子通过歌声自由交往,但出嫁后不得与男子私通,否则处死。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条》记“白人”风俗曰:“处子孀妇出入无禁。少年子弟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注]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 云南志略辑校》,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87页。后者与前者所记大致相同。明初从丽江移至怒江的白族勒墨人解放初尚存“南毫制”——青年男女十二三岁以后,单独与年轻伙伴在父母给他们盖好的“南毫”里一起休息、娱乐、睡觉,男女分别居住,但可以互相往来、唱歌对调、谈情说爱,此应是明清以前白族婚俗的遗留。反映白族早期婚姻主题的民间故事以《白王与金姑》最具代表性,故事说的是倔强的三公主金姑与父白王赌气离家出走,在野外遇险被善良、勇敢却丑陋的猎人细奴罗相救,金姑爱上猎人并与之成亲。白王得知后并没阻止,后来白王与金姑和好并将王位传给有才干的细奴罗。从以上资料可看出,明清之前白族婚姻相对较为自由,白族婚姻的缔结与当时汉族婚姻须符合等级性的“礼”制不同,多是出于自由人性的相互吸引。
明清白族地区在汉族移民大量移入和大兴文教之后,普遍实行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白族地区因此有俗语曰:“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包办婚姻成为社会的一个现象,也因此导致明清民间故事和歌谣中很大一部分为反抗包办婚姻主题。青姑娘勤劳、善良和聪慧,在白族传统观念中,她应得到两情相悦的爱情,但童养媳婚让她失去了获得自由爱情的机会。当她正月十五晚上和同伴出去游玩时,却被婆家以“败坏门风”为由遭受丈夫毒打。青姑娘没有将其遭遇归因于命运安排,而是对疼爱她却给她订立这门婚事的父母以控诉——“亲生娘啊亲生娘,接他多少钱和粮?”[注]杨亮才,李瓒绪选编:《白族民间叙事诗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6页。同时,她对自我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并且有掌控自我命运的主动性——“叫我一生当牛马,叫你枉费心机 ”,“你有铁链千百丈,难锁我的心”[注]杨亮才,李瓒绪选编:《白族民间叙事诗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95页。——以自杀来对抗婆家的虐待和压迫。这些在儒教文化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出自白族传统民族精神和基本价值理念。
其次,汉白人际伦理价值观的不同导致青姑娘符号的产生。在汉文化中,个体从属与整体,社会通过一套严格的以血缘共同体为原生点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礼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底层女性处在整个社会体系的最下层,她们在封建“三从四德”的规训中对自己的生存和命运几乎没有权利可言,被丈夫和婆婆毒打是常有的事。因此,中原有歌谣曰:“乐乐乐,你是弟弟我是哥,买些酒儿咱两个喝,喝得醉醉的,回家打老婆。打死老婆怎么过?你打鼓,我敲锣,滴滴答答再娶一个。”[注]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67页。此外,还“能够听到大量有关婆婆专横与残酷的事例”,婆婆“虐待儿媳妇的事非常普遍,除非罪恶昭彰,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注]转引自罗雪松《婆婆——男性世界的同谋》,《社会科学家》2000年第7期。而白族传统文化则不然,众物平等的人际伦理观已积淀在白族文化心理的深层。青姑娘因家贫和父母早亡而成为童养媳的可怜身世被当地人同情,同时并不因其身为女性、穷人而遭受歧视和丧失生存及获得幸福的权利。当青姑娘受伤后,同村女性悉心照顾,当其投水自尽后,全村人出动寻找,包括男人在内的全村人的寻找行为体现了白族底层社会对青姑娘婆家剥夺青姑娘生存权利的愤怒和对抗。同时,青姑娘的亲人和族人自始至终未出现,血缘关系在此被地缘关系代替,而这也是白族文化的一个特点,正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对民家(白族)来说,村子,而非家族,是位居家庭之上的基本社会单位。”[注]〔澳〕菲茨杰拉德:《五华楼》,刘晓峰,汪 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6页。从此可知,以血缘关系为原点的汉儒教文化并未将其根基植入白族文化。此外,青姑娘极具白族特色的终结方式——“投水”体现了白族文化赋予青姑娘以死亡与复活的深层内涵。水是白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意象”,许多本主神的功能跟水有关,或为管水、降水之神,或为除水中妖魔之人,或本身就是水神,既为英雄又为本主神的柏洁夫人最后亦投水自尽。水与白族的这种情结,一方面跟白族为农耕、渔猎民族有关,水和洱海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条件;另一方面,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因此,水这一意象凝聚着白族人的一些心理和命运的因素,渗透着白族人在历史上以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青姑娘以投水方式自尽隐含着其生命的终结,但水又让她以精神的意义和价值“重生”和“复活”,这种复活不仅是白族人的强烈愿望,更是对青姑娘维护正义的反抗行为的认可和赞美。由此,可以解释普遍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当地白族男性为何允许女性将青姑娘偶像抬入村内走街串巷祭祀。
四、民族文化融合与文化生态平衡
两个族群的文化融合一般经历双方对各自文化要素的接触、认识、选择和融合的过程。当一方以权力强迫对方接受自身的文化要素时,文化冲突或“融而未合”(费孝通语)便出现。明初中央政府通过实施军事、政治和文化一体化政策来加强对白族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大兴文教之前收缴南诏、大理国及元代的图书文献,将“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注]师 范:《书<沐英传>后》,选自《古籍中的大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企图在“白蛮”“夷地”新建汉儒教文化,彻底实现“以夏化夷”的目的。清承明制,进一步推进此策略,至清代大理呈现“渐被华风”的成功景象。但拥有自身历史和传统的白族文化在元明之际的剧烈社会变更中也会有一种警觉和危机感,从而形成一种为保存民族文化而进行的抵抗。明清汉白文化的融合因为伴随始终的强迫性导致抵抗心理的存在,广泛流传在大理地区的“白子国”和白王等传说便是这种社会心理的体现。[注]明清出现的《白古通记》(已佚)、《南诏野史》、《滇载记》、万历《云南通志》等方志和民间传说,叙述说大理很久以前有一个“白子国”,白王英明和爱民,后将王位传给细奴罗建立南诏国,或说观音开创了大理坝子并显化指点细奴罗建立南诏国。这种抵抗实际上是社群与社群之间出了问题,是原有的社会秩序、道德并未被白族底层民众所摒弃,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并未被认同和实行,也即文化生态失衡。[注]高丙中:《关于文化生态失衡与文化建设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我们从大理地区无等级秩序的村落格局,并未形成等级森严的本主神灵体系和青姑娘故事便可看出,以血缘体为原生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森严的儒家礼教并未被以女性为代表的白族底层民众所接受。在社会底层,因为其本主信仰和切实的生活体验与传统的承续,他们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念,保存了其民族性。当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遭受到来自上层的文化规制的时候,他们以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的形式,隐晦曲折地表达着底层民众的价值和生活诉求。我们说,当优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未被弱势文化接受和优势文化未改变接受者的核心文化时,优势文化的传播往往局限在权力的影响范围内,而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从根本上说就并非如正史所言的“以夏化夷”的成功,就更为广泛的民间而言,其文化变易的程度,是大可质疑的。所以,在青姑娘的身上,我们即可看到白汉民族文化在融合过程中的冲突,以及民族文化融合的有限性和复杂性。
然而文化有自身的规律,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与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于明清汉文化在发展水平上所具有的相对先进性,白族文化主体出于社会、经济或政治的需要,主动学习和融合汉文化便成为一种主流和绝对趋势。明清白族社会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文而得到发展,出现了一大批文人、士人、汉文诗和诗论,从而呈现文化兴盛景象。但这些文化成果除了部分颇有影响外,大部分都只是中原文化在边疆的余响或“滞后性”的发展,与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的灿烂文化艺术相比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实为白族传统文化和个性的消逝,使白族文化失去了生命力。因此,在民族间文化融合和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文化的多元性与保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和文化本身的活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在大理剑川延续的青姑娘民间叙事,不仅教育了当地一代又一代白族人,顽强地传递其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而且使后人从中了解到人类理想和智慧的一种向度和可能性。青姑娘故事在当时文化失衡的情况下,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一体化”势不可挡。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加快中华民族内部的“一体化”进程。青姑娘故事启示我们,中华民族内部势不可挡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是“汉化”过程,而应是在保持56个民族共同利益一致和文化生态平衡基础上增强文化认同的过程。要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必须认识到文化融合的层次性和复杂性,主流文化应尊重少数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以主流文化为引导,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互补互促的融合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