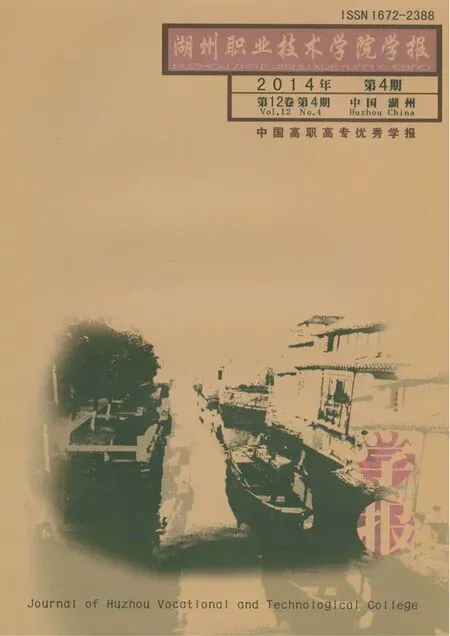游走在“乐群”与“乐道”之间从“交游酬唱”诗看中唐湖州文人茶友的文化心态*
2014-04-09丁国强
丁国强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旅游分院,浙江 湖州 313000)
所谓文化心态,是指一种将分散的社会普通成员的心理要素加以整合、汇集,使之以整体面目存在和流行于广大成员之间的集体性的文化精神状态。文化心态的精神内核为群体性的社会态度。中国是诗的国度,又是茶的国度。茶文化的主体从来就是文人。饮茶活动中蕴含的深厚的文化特质,始终与文人士大夫处世及自我修养的精神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经过雅化与诗化后的文人茶聚活动,孕育了浓厚的诗性文化氛围,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文人特有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
从唐代宗大历到唐德宗贞元年间的唐代中叶,在江南环太湖地区的重要州郡浙江湖州,以颜真卿、皎然、陆羽为中心,以修订《韵海镜源》为主要任务,聚集了大批文人雅士,诞生了一个较为固定的文人茶友集团。其成员包括湖州刺史颜真卿及其族人、湖州当地地方官与幕僚、外来游历文士、隐士与僧道等。据清人黄本骥考证,颜真卿任湖州刺史的近五年间(772777年),与其交往的文士多达85人,[1](P75-77)著名人物有诗僧皎然、灵澈,隐士张志和、茶圣陆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湋,以及朱放、秦系、严维等人。除了颜真卿,“茶道”的提出者诗僧皎然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最为特殊,皎然事实上是这个文人茶友集团的第二号人物。颜真卿到任湖州刺史时,他正和陆羽隐居在湖州杼山妙喜寺中。作为本土文人,皎然俨然有领袖之风。他交游的范围十分广泛,颜真卿刺湖前和离湖后,以皎然为中心的文人唱和十分活跃,与其交游的可考人物,大约有200余人。当时在江南地区著名的文人士大夫、隐士及僧人都与皎然有过交往,如韦应物、刘禹锡、刘长卿、顾况、孟郊、李端、灵澈、吴筠等。茶圣陆羽作为颜真卿和皎然的好友,是湖州文人茶友集团的又一重要人物。在《全唐诗》中,我们能发现陆羽友人有五、六十人之多。而且《全唐诗》载及的陆羽友人,大多有诗赠陆羽。中唐湖州文人茶友集团成员,由于散居湖州城及周边乌程、武康、德清、长城、安吉各县,加上当时大批外来文士游历或客居湖州,文人们将茶会活动融合在诗会中。他们诗酒唱和、雅集茶饮,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迎来送往之间,写了大量送别、赠答、酬和诗作,形成了当时除首都长安之外的又一文化活动中心。文人唱和活动既满足了文人茶友作为世俗生活中社会人的情感需要,又使他们获得了精神上的归属感。
一、中唐湖州文人茶友集团成员交游情况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诗歌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交流的产物,是人的社会属性并相互影响的产物。中唐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又是一个诗歌流派和诗人层出不穷的时代。大历、贞元年间的湖州成为人文荟萃之地,许多著名诗人来此寓居、任职,文坛十分活跃,所以不仅人际交往极其频繁,而且在交往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诗篇。这些诗歌既体现在集团成员群体性的活动中,又体现在成员个体之间的日常交游中。
颜真卿作为这一文人茶友集团的盟主,与皎然、陆羽、张志和、耿湋、皇甫曾等都有赠答往来。颜真卿传世的诗歌不多,与联句加在一起,约为30首。赠给皎然的诗歌,现存《赠僧皎然》1首,写给陆羽的有《谢陆处士杼山折青桂花见寄之什》1首,但存目的亡逸诗歌较多,有:《遇皎然郭中山寺》《同王员外圆宿皎然寺》《同袁侍御高皎然上人登杼山上峰》《同李侍御萼皎然上人游法华寺》《晦日同皎然集白蘋洲》《修韵海毕会诸文士东堂重校》《同袁侍御高骆驼桥玩月》《修韵海毕州中重宴》《同皇甫曾西亭重会韵海诸生》《登岘山送张侍御严归台》《岘山送李法曹阳冰西上献书》《清明日同皎然游因送萧主存》《修韵海毕东溪泛舟饯诸文士》《泛舟送皇甫侍郎曾》《送李侍御萼》《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落玄真子舴艋舟歌》《和玄真子渔父词》《清风楼送吴炼师筠归林屋洞》等(本文所引颜真卿诗作均出自清黄本骥《颜鲁公全集》,上海仿古书局1936年版)。我们从这些诗歌中大抵可以看出颜真卿在湖州的交游情况。
皎然作品《杼山集》中,与颜真卿唱酬的诗也最多,达22首。颜真卿的宴集、游赏活动,皎然大多参与了。皎然在湖州与士大夫、文人、方外诗人的交游十分广泛。除颜真卿外,与袁高有《遥酬袁使君高春暮行县过报德寺见怀》《奉酬袁使君高寺院新亭对雨(其亭即使君所创)》;与卢幼平有《冬日遥和卢使君幼平綦毋居士游法华寺高顶临湖亭》《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敡上人房论涅盘经义》;与秦系有《酬秦山人系题赠》;与乌程令杨华有《酬乌程杨明府华雨后小亭对月见呈》《酬乌程杨明府华将赴渭北对月见怀》《和杨明府早秋游法华寺》;与陆羽有《寻陆鸿渐不遇》《访陆处士羽》《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羽青塘别业》《同李侍御萼李判官集陆处士羽新宅》《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与李纵有《酬李司直纵诸公冬日游妙喜寺题照昱二上人房寄长城潘丞述》《春日杼山寄赠李员外纵》;与李伯宜、沈仲昌有《赠乌程李明府伯宜沈兵曹仲昌》《感兴赠乌程李明府伯宜兼简诸秀才》;与灵澈有《宿法华寺简灵澈上人》;与裴济有《答裴济从事》;与崔子向有《白云上人精舍寻杼山禅师兼示崔子向何山道上人》;与吴均有《奉同颜使君真卿清风楼赋得洞庭歌送吴炼师归林屋洞》;与吴冯、李洪有《奉酬李中丞洪湖州西亭即事见寄兼呈吴冯处士时中丞量移湖州长史》《劳劳山居寄呈吴处士》《秋宵书事寄吴冯处士》《戏呈吴冯》《戏赠吴冯》;与韩章有《招韩武康章》;与陆长源有《奉陪陆使君长源裴端公枢春游东西武丘寺》《奉和陆使君长源夏月游太湖(此时公权领湖州)》《奉和陆使君长源水堂纳凉效曹刘体》;与康造有《夜过康录事造会兄弟》;与李萼有《七言遥和康录事李侍御萼小寒食夜重集康氏园林》《五言酬李侍御萼题看心道场赋以眉毛肠心牙等五字(得牙字)》《五言采实心竹杖寄李侍御萼》等(本文所引皎然诗作均出自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杼山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皎然65岁时,与孟郊相识。孟郊是晚辈,但两人很快就成为忘年之交。皎然与灵澈等诗僧的交往和提携也特别值得关注。
茶圣陆羽本人的诗作虽大都散佚,但在《全唐诗》中载及的陆羽友人有五六十人,他们大多有诗歌赠送陆羽。除颜真卿、皎然之外,还有皇甫曾、皇甫冉、李冶、刘长卿、权德舆、戴叔伦、孟郊和耿湋等著名诗人。可以肯定,当时与陆羽相互酬赠的诗人茶友一定还有很多,但在现存资料中能够查见的,就这10人(加上与陆羽一起参与联句活动的诗人共有五六十人)。这些人不但赠陆羽以诗,而且从诗文和其它记载来看,他们多数和陆羽还是莫逆之交。其中颜真卿、皎然与陆羽结为方外之友,相善终身,皎然有著名的《寻陆鸿渐不遇》诗;权德舆与陆羽,大致在江南时便有交往,及其仕江西时,与陆羽再度相会;戴叔伦由诗文来看,与陆羽主要交往于江西任上;孟郊与陆羽曾会诗江西,是陆羽晚年挚友之一;李冶有《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昔去繁霜月,今来苦雾时。相逢仍卧病,欲语泪先垂。强劝陶家酒,还吟谢客诗。偶然成一醉,此外更何之。”(《全唐诗》卷八百○五)诗意缠绵,说明她与陆羽情非一般。
隐士张志和在湖州也游历甚广,留下许多佳话。其中之一就是颜真卿慨然赠舟于张志和。颜公为张志和造成新舟,还为此举行了“下水仪式”,召集好友聚会。当时与会各人均有诗作歌咏此事,可惜大都亡佚,不知其内容了。张志和游历湖州的其他事迹,除创作著名的《渔父》词外,还有为颜真卿画湖州洞庭三山图,在乌程县水堂书武城赞等。这些,我们可以从颜真卿的碑文和皎然的诗中见到。
酬寄唱和之作,自曹魏邺下文人集团以来,一直是士大夫文人的天地,而女性是无权涉足的。女性在文学史上即便有一些寄赠之作,也大多是“寄外”之类。除此,异性间很少有和谐融洽的社交酬答。湖州文人茶友集团的女冠诗人李冶(李季兰),由于与文士名流交游广泛,思想自由,常参与宴饮、集会活动,自然也就参与到酬唱之中。这种寄赠、送别的作品在李冶传世约16首诗中就有10首。《寄校书七兄》《寄朱放》《道意寄崔侍郎》《恩命追入留别广陵故人》《结素鱼贻友人》《明月夜留别》《湖上卧病喜陆鸿渐至》《送阎二十六赴剡县》《送阎伯钧往江州》《得阎伯均书》等均是这类作品。仔细看看这些诗歌,它们记录了李冶广泛交友的情况。可想而知,如果没有了相互的交往,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作品。
湖州文人茶友集团是一个开放型的文人群体。松散、活跃、自由的组织形式是这一集团结构上较为明显的特点。文人往往不受严格固定的活动宗旨的限制,缘兴而起,随聚随合,不受拘束,开展随意洒脱的文化活动。在集团成员的身份构成上,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他们中间山人布衣之类的平民身份者占有相当的比例。除了集团内部相互间的交游唱和外,还有成员个体各自独立的交游圈子。集团成员唱和的题材内容也十分宽泛,四时节令、春花秋月、夏雨冬雪等等都可以使他们文思泉涌,往来酬答、朋友赠别、观光赏玩等等更是他们彼此交游唱和的缘由。而宴席、茶聚、游览之际,更是他们唱和频繁之时。诗人们通过诗歌创作和讨论,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以增进合作,加深友谊,起到了文学协和群体的社会功能。
二、“乐群”——文人茶友交游酬唱之社交需要
孔子论诗,首倡“兴观群怨”之说,着重强调了中国古代诗歌的教化、认识、交际、怨刺四大功能。“诗可以群”是儒家关于文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看法。闻一多先生曾说:“诗似乎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2](P202)诗是全面的社会生活,不仅表现在上层社会重大的政治生活中,也体现在世俗生活的言谈举止中。同时,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所以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必然要与其他人发生关系。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有远近亲疏之分,便有亲朋好友。与亲朋好友的聚会使人兴奋,与亲朋好友的离别令人感伤。钟嵘《诗品序》把“嘉会寄诗以亲”作为“诗可以群”的表现之一。在官府或私人的宴会上,主宾赋诗酬唱,培育并增进了感情。在湖州编纂《韵海镜源》的过程中,颜真卿多次举行了宴请、茶聚、饯行等活动,既有盛大的公宴,也有诗朋词客间会聚品茗的小型集会,皎然《五言奉和颜使君修韵海毕州中重宴》等诗可以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其它宴请、聚会活动也不在少数,与颜真卿关系十分友好的皇甫曾就有一首饯行送别诗《乌程水楼留别》。诗云:
悠悠千里去,惜此一尊同。
客散高楼上,帆飞细雨中。
山程随远水,楚思在青枫。
共说前期易,沧波处处同。(《全唐诗》卷二百十)
我们从“惜此一尊同”和“客散高楼上”两句诗中可见,这是一次集合了众多文人的送别酒会和茶聚,此种酒会和茶聚往往会衍生出诗歌。
联句是文人雅集活动的又一种形式。颜真卿在湖州任上和皎然、陆羽、李萼等人作的联句诗共22首,参与联句唱和的人数达到140多人次。以颜真卿为首的湖州联句,《登岘山观李左相石樽联句》有29人参与,共成29联,58句,每句五言,计290字,是《全唐诗》所录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联句活动。其余较大规模的还有:《与耿湋水亭咏风联句》12人,《又溪馆听蝉联句》10人,《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6人,共涉及诗人茶友44人。44人中,参与编纂《韵海镜源》的有20人,他们是陆羽、李萼、陆士修、刘全白、魏理、左辅元、权器、裴循、潘述、刘茂、张荐、颜浑、殷佐明、蒋志、杨德元、颜岘、韦介、崔弘、崔万、房夔;其他诗友及子侄22人,他们是耿湋、李益、吴筠、袁高、皇甫曾、强蒙、范缙、王纯、王修甫、史仲宣、柳淡、裴幼清、释尘外、杨凭、杨凝、李观、乔(失姓)、陆涓、伯成(失姓)、颜颛、颜须、颜顼、颜粲(四颜系真卿族侄)。
以皎然为首的联句有31次。其中,与汤衡、潘述联句9次,与长城(今浙江长兴)崔子向等联句6次,与吴兴守卢幼平、陆羽、潘述联句3次,与安吉令崔达等联句5次,与武康令韩章等联句3次等。联句地点有湖州项王古祠、建安寺、长城东溪、宗光寺、箬里天居寺、顾渚山、荻塘、安吉崔明甫山院、武康后亭等。
诗歌的社交功能,既体现在群体的活动里,又存在于个体的交往中。皎然居湖州时,与陆羽、吴冯、皇甫曾、李端、崔子向、李萼、秦系、朱放等交游酬唱。历任湖州刺史卢幼平、颜真卿、陆长源等,均与皎然有交游唱和。颜真卿与皎然之间的交游更为频繁。他们常常相互酬唱、共赏山水,有时也游览寺庙,谈禅说佛,一起感受“忘机”的乐趣。皎然还陪同颜真卿游赏了湖州境内许多名胜。这样的诗歌有《奉酬颜使君真卿王员外圆宿寺兼送员外使回》《杼山上峰和颜使君真卿袁侍御五韵赋得印字仍期明日登开元寺楼之会》《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同颜使君真卿李侍御萼游法华寺登凤翅山望太湖》《奉同颜使君真卿袁侍御骆驼桥玩月》《九日陪颜使君真卿登水楼》《晦日陪颜使君白蘋洲集》等。皎然诗云:“山中常见月,不及共游时。”(《奉同颜使君真卿袁侍御骆驼桥玩月》)身在佛门的他,内心并未平静如水,在湖州秀美的山水中,皎然找到了俗世温情下共游的乐趣。
身为僧徒的皎然似乎更喜欢在交游诗中表达世俗的情绪,在一些送别朋友的诗篇中,如《七言同颜鲁公泛舟送皇甫侍御曾》《五言奉同颜使君真卿送李侍御萼赋得荻塘路》《五言奉陪颜使君真卿登岘山送张侍御严归台》《同颜使君清明日游因送萧主簿》等,皎然极力要将别离的伤感传达出来。
文人茶友的社交活动,其交际主体是文人。文人是文化的掌握者、传播者,又是文化的实践者、创造者。魏晋以后,文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交往更为广泛而频繁,社会交际变得越来越重要。诗歌创作在注重个人“吟咏情性”的抒情功能的同时,其社会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诗坛出现了大量表达亲情、友情、同僚之情的诗篇。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人们交往频繁。唐代又是一个诗的时代,诗歌的功能得到了全面发挥。文人茶友们在交际中创作,在创作中交际。《韵海镜源》的编撰和成员间的诗酒茶会产生了大量文学作品,反过来,这种交游酬唱又满足了文人作为世俗生活中社会人的情感需要。
三、“乐道”——文人茶友交游酬唱之精神指向
“道”是君子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文化精神,是他们的人文理想、道德追求和价值目标。权德舆《唐使君盛山唱和集序》说:“士君子以文会友,缘情放言……同其声气,则有唱和。”[3](P5001)文人集会具有高雅文化品格、快乐感情基调与群体活动方式的特征。“雅”的特质正是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根本差异。不管是在庙堂还是在民间,文人茶友间的群居切磋既是“乐群”,也是“乐道”。
从根本上说,文人的这种“乐道”观念和行为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它以人伦友情为其学说的一大支柱。首先,儒家注重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学大师在重视人伦友情的同时,进一步规定了友情的精神指向——合志同方,同气相求。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故选择朋友时以同志者为友。孔子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公冶长》),曾子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荀子进一步指出:“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荀子·大略》)这种以道义为守的朋友观,在中国古代社会有广泛的共鸣者。蔡邕《正交论》说:“朋友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欧阳修《朋党论》也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通过文学艺术而达到上下和悦、互相仁爱、协作团结的特殊作用,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仁者爱人”,即真诚互爱的仁爱精神在文学上的反映和要求。可以这样认为,文学这一社会功能的确立正是有赖于“乐道”这一文人间共同的价值目标和精神基础。
联系到湖州文人茶友集团,其成员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处于闲人地位或闲居状态。他们或闲居读书、或弃官学道、或出任闲散的幕职,他们追求的是闲适宁静,淡泊平和的生活,恬退独善是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他们游赏风景,品茶赋诗,在湖州杼山妙喜寺、岘山石樽、竹山草堂、府衙清风楼、东亭西亭、骆驼桥、洞庭三山、苕霅二溪、顾渚山等地留下了许多诗篇,以此获得了精神上的自慰和自足。如《竹山连句题潘氏书堂》,有18人参与联句,颜真卿开头吟道:“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陆羽续道:“万卷皆成秩,千竿不作行。”李萼的联句:“练容餐沆瀣,濯足咏沧浪。”裴修是:“守道心自乐,下帷名益彰。”皎然的联语是:“水田聊学稼,野圃试条桑。”房夔是:“解衣垂蕙带,拂席坐黎床。”柳淡是:“昼歠山僧茗,宵传野客觞。”潘述收煞:“偶得幽栖地,无心学郑乡。”郑乡即郑公乡。史载后汉北海相孔融深敬郑玄(12700年),认为他是仁德之人,下令高密县特设一乡,名之“郑公乡”,以资褒扬。郑玄是东汉著名的著作家和教育家,四方就学的弟子达数千人。潘述表白自己得一隐居的好地方已心满意足了,不图富贵闻达,亦不学习郑乡授徒扬名,只想在此安居乐业,做一个淡泊的隐者。全诗充满了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又如《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颜真卿首倡:“居人未可散,上客须留著。莫唱阿亸回,应云夜半乐。”潘述继之以:“诗教刻烛赋,酒任连盘酌。从他白眼看,终恋青山郭。”《七言重联句》:“诗书宛似陪康乐,少长还同宴永和”(颜真卿),“独赏谢吟山照耀,共知殷叹树婆娑。”(皎然)《还丹可成诗联句》中汤衡结语:“与君弃成市,携手游蓬瀛。”《泛长城东溪暝宿崇光寺寄处士陆羽联句》:“野鹤翔又飞,世人羁且跼。”(崔子向)《安吉崔明甫山院联句》:“人不扰,政已和。世虑寡,山情多。”(皎然)“禅客至,墨卿过。兴既洽,情如何。”(崔逵)《春日会韩武康章后亭联句》:“坐看青嶂远,心与白云同”(韩章)“松竹宜禅客,山泉入谢公。”(皎然)“便寄柴桑隐,何劳访剡东。”(皎然)
这些诗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集团成员推崇的是诗意化的隐士幽人生活和闲适心情,文人茶友们仰慕的是纵情山水的谢灵运,神往的是兰亭会。他们陶醉于悠闲自适的闲居生活,表现的是平和、萧散的心境和超然高蹈的共同生活情趣。
此类联句诗歌还有颜真卿《与耿湋水亭咏风联句》《又溪馆听蝉联句》《五言月夜啜茶联句》等。文人茶友们散漫渔樵、流连酒茗、咏风吟月、无忧无虑、陶然忘机。他们将日常生活进行了诗意化的浓缩,在对生活的品赏和把玩中虚化了与现实社会的冲突,获得了一种精神上自我救赎后的喜悦。
湖州文人茶友集团的成员还大都喜欢交接僧人,其中主要人物皎然本身就是一位诗僧。据元和年间沙门福琳所著《唐湖州杼山皎然传》:“释皎然,名昼,姓谢氏,长城人。康乐候十世孙也。幼年异才,性与道合……,昼清静其志。高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3](P9573-9574)皎然的《戏作》,就是这种任放精神的写照:“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另一重要人物张志和是个隐士。他“居江湖,性迈不束,自称烟波钓徒。”[4](P210)陆羽常问他:“‘孰为往来者?’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5](P5069)再看与皎然同居湖州妙喜寺,为莫逆之交的陆羽。“上元初,结庐苕溪上,闭门读书。名僧高士,读宴终曰。……闻人善,若在己。与人期,虽阻虎狼不避也。”“扁舟往来山寺,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击林木,弄流水。或行旷野中,诵古诗,裴回至月黑,兴尽恸哭而返。”[4](P211)盟主颜真卿亦好佛,皎然《唐湖州佛川寺故大师塔铭》:“刺史卢公幼平、颜公真卿、独孤公问俗、杜公位、裴公清,唯彼数公,深于禅者矣。”[3](P9559)另外,尚有嵩山道士吴筠、处士强蒙、释尘外以及深受马祖禅风影响的临川令沈咸和抚州人左辅元等人。湖州文人茶友集团重要的雅集活动透露出来的,正是纯粹的恬淡和怡然。诗人茶友们置身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读书、醉酒、饮茶、垂钓,人生充满了乐趣。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不是俗世间的琐事,更多的是默言之中的禅趣。爱好和信仰的相同使他们建立起了彼此的信任与友谊。
四、结 语
我们可以说,湖州文人茶友集团是一个禅僧和士绅结合的文学社团,它以禅学和诗文交流的形式存在,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以士大夫为主具有深厚佛教色彩的禅诗茶客集团。恬退独善,萧散闲静的心境正是这个文人茶友集团形成的精神基础,而这种心境与茶道的美学要求正好是完全契合的。
[1][清]黄本骥.颜鲁公全集(下)[O].上海:上海仿古书局,1936.
[2]闻一多.神话与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
[3][清]董 诰.全唐文[O].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元]辛文房.唐才子传[O].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5][宋]欧阳修,宋 祁.新唐书[O].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