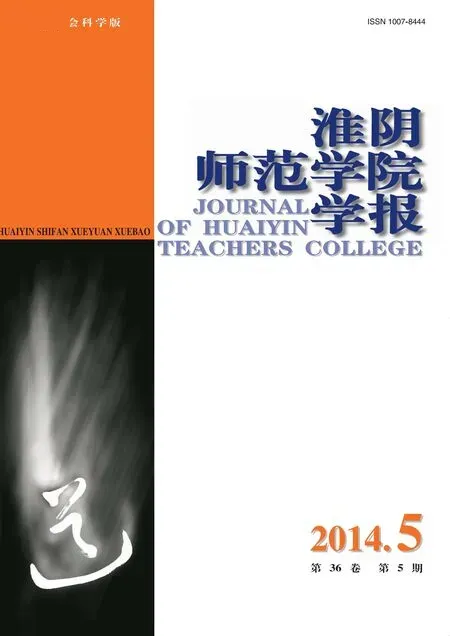论严歌苓中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
2014-04-09李惠
李 惠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223300)
在海外华文女作家当中,严歌苓是一个“了不得的异数”(旅美作家陈燕妮语)。她用英语为好莱坞编剧,用中文写小说。双重身份使得她的文学视野格外开阔。单就小说创作来说,她也是一个多面手,既有荡气回肠枝繁叶茂的长篇巨制,又有玲珑剔透短小精致的中短篇小说。其作品屡屡在国内外获奖,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学成就。近年来,她的很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金陵十三钗》等,都曾经引起过收视(观影)狂潮。严歌苓成了最受影视剧导演青睐的作家之一。然而,与影视界的热烈反响不同,批评界对严歌苓作品的反应相对要冷淡得多。相较于严歌苓丰硕的创作量来说,对严歌苓创作的研究显得过于冷清了。大概是由于严歌苓近几年致力于长篇的创作,批评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大多集中于她的长篇小说。而实际上,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无论在叙事艺术还是整体文学格调上都不逊色于她的长篇。
严歌苓熟谙小说的虚构技巧,可称作小说叙事上的能工巧匠。她将灵活多变的叙事技巧运用到炉火纯青,小说因而显得轻倩灵活,而又细腻丰腴。尤其是她的中短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可以作为写作课的“范本”。
一、场面叙事
著名评论家陈思和先生说:“如果我们把一部作品中的情节自然发展看作是游走的气脉,那么,那些被称作最难以描述的场面往往就是作品中气脉所结的气穴,只是充分写出了情节发展而刻意回避关键性的场面,等于是畅通了气脉却封闭了气穴,作品往往精巧而缺乏大气;而不仅写了情节的自然发展又独出心裁地展现难以描述的场面,即既畅通了气脉又打开了气穴,气韵才能弥漫于作品之中,显现出浑然大气的艺术风格……”[1]严歌苓的小说无疑在“浑然大气”之列。不管是长篇还是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严歌苓都难以舍弃对场面叙事的偏好。她擅用场面描写来渲染气氛、生成意境、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将场面描写的叙事功能发挥到极致。读罢她的作品,往往脑海中翻腾不已的是小说中一个个精彩的场面。
要在体积和容量都不大的中短篇小说中描写好众多的场面,如果作家没有删繁就简、缩龙成寸的驾驭叙述节奏的艺术功力,那作品难免漏洞百出,流于平庸。中短篇小说受篇幅的限制,对场面描写的要求甚至比长篇小说更高。它无法像长篇小说那样对任一场面作铺枝散叶式的酣畅淋漓的挥洒,也没办法任何时候都可以随意从容地娓娓道来,它要求既要写得穷形尽相,活色生香,又要干净利落、不蔓不枝;既要写得精彩,增加小说的神韵,又要简洁明了,不影响情节的发展。因此,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布置必要的场面并写“出彩”,这是文学创作交给小说家的艺术难题。严歌苓丝毫都不回避对一些关键性的、难以描述的场面的正面描述,总是迎难而上,用有限的文字去探索和实现无限的艺术可能。
在小说创作中,每个场面所起的艺术作用是不同的,它们有主次之分、轻重之别,因而可分为重点场面、一般场面、过渡场面。重点场面对人物性格的开掘、情节的发展、矛盾冲突的展示,起着重要的乃至关键性的作用。一般场面、过渡场面,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占有突出位置,但它们是使文气贯通、作品生色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它们,作品同样黯淡无光。有经验的小说家,在描写场面时决不平均用力,而是重点场面,花大力气写,写细写深写透;一般场面和过渡场面,则大笔勾勒,淡描粗绘。严歌苓显然精通这一艺术法则,她的中短篇小说的场面叙事,对重点场面浓墨重彩、细描细绘,而对一般性、过渡性场面则是着墨不多,轻描淡写。
以她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为例。这篇不足5万字的作品,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场面环环相扣连缀而成。小说中,“妓女夜闯教堂”“神父收留伤兵”“妓女伤兵教堂狂欢”“日本兵教堂搜查”“金陵十三钗慷慨赴义”是重点场面,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作者对这些场面作了精心铺排,而对“红菱骂阵”“豆蔻舀汤”“书娟复仇”“教堂葬礼”等一般性、过渡性场面则是点到为止,见好就收。“妓女夜闯教堂”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个重点场面。写好这个场面至为关键。它就像音乐的起调一样,奠定了小说的叙事语调,也决定着情节的走向。作家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将一个人物众多的场面写得极为生动。就像打开一面折扇,人物场景依次进入读者的视野。这个场面通过线索人物书娟(她不是主要人物,却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关键人物。她就像一条丝线,把众多人物和场面串连成一个艺术整体。因此笔者称其为线索人物)的眼睛展开。她先是“看见两个年轻女人骑坐在墙头上”,然后“墙上已坐着五个女人了”,继而“一个黑皮粗壮,伸手到墙那边,又拽上来五六个形色各异,神色相仿的年轻窑姐”[2]。作家写14个妓女对教堂的“入侵”并没有让她们一拥而入,而是先出现两个,再是五个,然后再拖五拽六地全部出场。这样写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而在具体描绘这一场面时,作家则用了点面结合的方法。既写了整个场面的“不可收拾”——“女人们哭嚎谩骂,抱树的抱树,装死的装死”[2],又通过描写红菱、豆蔻与阿多那多、陈乔治的死缠来增加场面的具体性、生动性。整个场面像一场小型戏剧,一下子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而这样一个场面发生在大屠杀前夜的南京城,就更加激起读者的阅读期待。严歌苓高明的地方在于,写这样“逃难”的场面,她没有像传统作家那样用黑夜一般凝重的笔调描绘一幅生灵涂炭的血腥画面,进而悲愤交加地予以控诉,而是用活泼甚至幽默的笔墨描画了一幅香艳的“妓女夜奔图”。这当然是和作家无意于揭露和控诉,而是敏感于“人性挖掘”的创作意念有关。
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创造、生成意境,从而把读者引入充分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是严歌苓场面叙事的另一个特点。“金陵十三钗慷慨赴义”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最难描写的一个场面。女学生会不会惨遭荼毒?13个妓女命运如何?作者把读者早已被激起的满心疑窦全盘交付给这一场面来作解答。情节发展到最后,故事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13个妓女舍身相救,代替女学生以身饲虎。这恰恰与第一个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小说一开篇的荒唐、香艳到这里一变为“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
严歌苓惯于以这样“出人意料”的场面叙事作为小说的结尾。如《拖鞋大队》以“众女孩围猎耿狄”作结,触目惊心的背叛刺痛了读者的眼睛。《爱犬颗韧》以“枪杀颗韧”的场面描写作结,鲜血淋漓的惨状让人不忍卒读。而《奇才》以“老吴阅读毕奇家信”的场面作结,骤然而至的人性虚伪与丑陋让读者猝不及防。这样的叙事模式,耐人寻味,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意蕴。
二、历史叙事
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还呈现出历史叙事的特点。她喜欢把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希望通过“历史”通道还原人的本相,阐释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她的历史叙事无意于历史真相的探究,或对宏大的历史事件的概说、把握,而是着眼于个人记忆、个体经验的叙述。罗素认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3]严歌苓进行的就是这种“有关人性的知识”的“小历史”书写。
我们将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从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一下分类,就会发现严歌苓特别关注的“历史”主要有这样几块:“文革史”“移民史”“战争史”以及“后文革时期”。而前两块又是涉及篇目最多的。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严歌苓这一代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有着特别的文革经验与记忆。对于任何一个有着“文革”成长背景的作家来说,这段历史都具有某种神秘莫测的魅惑,吸引着他们去回望与反思。80年代中期,严歌苓远赴美国,在那里求学、打工,饱尝异己文化语境中的冲突与迷惑,作为“第五代移民”,她对长达150年的“华人移民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缘自这样的生存经历,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在历史背景上主要有这两大类:“文革小说”和“移民小说”。前者,有著名的“穗子系列”。后者,有《少女小渔》《海那边》《女房东》等。除了这两大类以外,严歌苓的文学目光也偶尔会游移到“战争年代”或“后文革时期”。她写了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金陵十三钗》和以20世纪80、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为背景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所有这些作品,都是把人物张贴在历史的幕布上,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书写他们的性格史与心灵史。
严歌苓说:“我总在寻找这个‘特定环境’,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4]“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在非极致的环境中人性的某些东西可能会永远隐藏。我没有写任何‘运动’,我只是关注人性本质的东西,所有的民族都可以理解,容易产生共鸣。”[6]因此,在严歌苓那里,历史不过是“特定环境”,她对历史的兴趣也仅仅在于它能够激活她笔下的人物,赋予他(她)们展现隐秘性格的能量。探索人性的真相与极致,绘制波澜壮阔的人性风景,是严歌苓一以贯之的文学追求。她的“穗子系列”,以少女“穗子”的视角写文革中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境遇。通过“伤痕”小说,我们已经熟知这场运动造成的种种灾难。对于读者来说,不管什么样的“创伤”“疼痛”都已经是习以为常。而严歌苓开启的是“后伤痕”时代的写作。她没有挖空心思去正面写“运动”“批斗”,或者“血渍”“伤痕”,而是竭尽全力去索探人物心灵的幽微,去想象在极致环境中人性的种种可能。严歌苓经常会引用维吉尼亚·沃尔芙(Virginia Woolf)的一句话:“走向人内心的路,永远比走向外部世界要漫长得多。”[4]确实,表现内心世界的真实远远比表现外部世界的真实要悠远、艰涩的多。而严歌苓毅然舍弃了文学表现的捷径,踏上了另一条漫长、艰难却更美丽、丰盈的文学之路。
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主人公多是女性,多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展开历史叙事。她的小说从未停止过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凝注,其擅长在历史的大框架中展现女性生理、心理、情感的成长历程。在文学的疆域里,也许没有什么比历史漩涡中的女性更迷人的了。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就塑造了这样一个处于历史中心的女性群体。这中间,有移民美国的妓女、留学生,有文革时期的女知青、文艺女兵,也有战争年代的女学生、妓女,20世纪80、9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打工妹。她们在历史浪花的席卷、裹挟之下,绽放出迷人的人性之花。对于此类书写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用《浮出历史地表》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总结:“女性的真理发露,揭示着那些潜抑在统治秩序深处的、被排斥在已有历史阐释之外的历史无意识。揭示着重大时间的线性系列下的屋里是,发露着民族自我记忆的空白、边缘、缝隙、潜台词和自我欺瞒。它具有反神话的、颠覆已有意识形态大厦的潜能。”[6]
三、意象叙事
“意象”作为诗学的闪光点介入到叙事作品后,除了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也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杨义认为“意象作为叙事作品中闪光的质点,使之在文章机制中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功能”[7],充分肯定了意象的叙事功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利用意象来开展叙事的作品并不少见。《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药》中的“人血馒头”,《金锁记》中的“黄金枷锁”,以及汪曾祺笔下的“大淖”,莫言笔下的“红高粱”,苏童笔下的“大红灯笼”……这些迷人的意象都深深刻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它们或是作为叙事线索推动、发展故事情节,并且凝聚、深化作品主题,或是作为抒情对象调整叙事节奏和视角,奠定叙事基调,是文本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元素。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也汲取前辈及同时代作家的叙事经验,充分发挥意象叙事的长处,利用意象点亮文本,同时,也让意象参与到叙事中来,形成了诗意盎然、含蓄隽永的意象化叙事风格。
以意象疏通叙事脉络,贯穿叙事结构,是严歌苓中短篇小说意象叙事最为鲜明的特点。如《灰舞鞋》中的“舞鞋”意象,《梨花疫》中的“梨花”意象,《橙血》中的“橙子”意象,《红罗裙》中的“红罗裙”意象,《风筝歌》里面“风筝”的意象等等,这些意象都是贯穿作品始终,发挥着疏通叙事脉络、构建叙事结构的叙事功能。我们以《拖鞋大队》这个短篇小说为例。这个作品以文革为背景,叙述了一群缺管少教的青春少女背叛友情的故事。这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她们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当中,纷纷被关押或者劳教,为求自保,女孩们纠结到一起,组成“拖鞋大队”,以团体力量对抗周围的歧视与欺侮。在严酷的环境下,她们逐渐变成喝了狼血的狼崽子,粗俗、野蛮、下作,并且集体背叛了她们最为可贵的朋友。被她们背叛的女孩叫“耿狄”,是将军的女儿,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为“拖鞋大队”的女孩们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资助。在“拖鞋大队”成员们眼中,耿狄是个谜一样的“女孩”。她有着与男孩绝无二致的气质、样貌、风度,却偏偏脑袋上扎着两只“不伦不类”不搭调的辫子。除了这两只辫子在“假惺惺地”宣示耿狄的女性身份以外,其他的任何信息都在毫不含糊地将其性别指向男性。随着交往的深入,耿狄的性别成了不可索解的谜,越来越重地压在女孩们的心头。最后,她们一起设计拽下了耿狄的裤子,揭开了谜底,却也让人性跌落到最低处。耿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意象化人物,以她来反衬出女孩们的“狼性”。她的性别之谜隐喻着那个时代的混乱、荒谬,以及对人的异化,也因此,这个人物不再是单纯的人物形象,而具备了某些意象化的特征。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她承担着叙事线索的作用,整个叙事围绕女孩们同她的关系逐步展开。
除了这类贯串作品始终,支撑叙事结构的中心意象,在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中还有一些个别意象,它们虽不影响叙事全局,却能够营造叙事氛围,形成独特的叙事语调,并且,对于凝聚、深化叙事主题,也起着非同寻常的作用。《白蛇》是严歌苓较受瞩目的一部中篇小说。这个作品写了文革中一段错乱的同性之爱。舞蹈家孙丽坤因塑造“白蛇”形象而闻名全国,在她落难之时,崇拜她的年轻军官徐群珊“女扮男装”闯进她的生活,由此上演了一段缠绵悱恻的畸恋。文本中作家引入了“白蛇”这个神话意象,来形成对文本故事的影射与同构。文本故事以独特的叙事格局完成了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演绎,而传统神话反过来奠定了文本凄美的叙事语调,也强化了文本故事迷人的意蕴。此类意象的运用几乎遍布严歌苓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如《名角朱依锦》中,用美丽而又凄怆的“白蝴蝶标本”意象来比喻备受摧残的女主人公。《老人鱼》中以“老人鱼”的意象来形容孤独、被抛弃的外公。《灰舞鞋》中以“离群之雁”的意象,来隐喻孤立无援的穗子。《天浴》中以“水”的意象来反衬肉体备受摧残的知青文秀。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审美意蕴,也营造出了浓郁的叙事氛围。
结语
严歌苓作为“学院派”作家,其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将叙事艺术的技巧发挥到极致,相伴而生的,是作品因过于“娴熟”的技巧而流露出的些许“匠气”。这也难怪,让一个“身怀绝技”的作家“收着写”绝非易事。难能可贵的是,严歌苓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在技巧上的使用过度,在她近些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这一缺点得到了很好的弥补。
[1] 陈思和.最时髦的富有是空空荡荡——严歌苓短篇小说艺术初探[J].上海文学.2003(9).
[2]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英]罗素.论历史[M].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4.
[4] 严歌苓.主流与边缘·代序[M]//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5] 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N].南方日报,2002-11-29.
[6]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4.
[7] 杨义.杨义文存·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