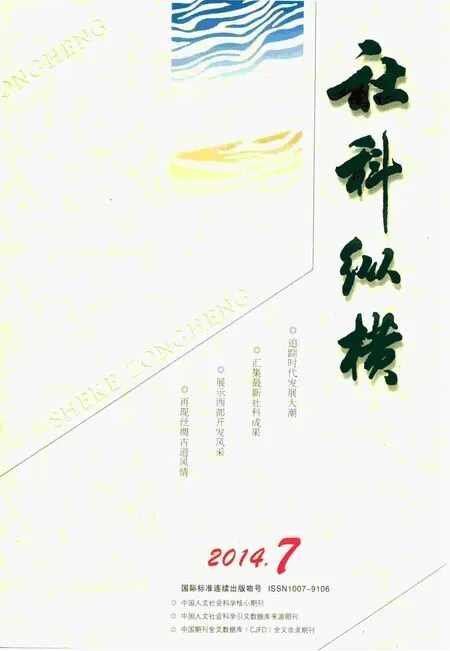论陆游论诗诗创作的多元情境
2014-04-09曹瑞娟
曹瑞娟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宋代是诗话兴盛的时期,在文人们喜好品评诗歌的文化大背景下,论诗诗也相应地繁荣起来。如果说诗话是从容不迫地以文论诗,那么论诗诗就是凝炼集中地以诗论诗。郭绍虞先生曾经这样分析论诗诗在宋代流行的原因:“盖以(1)宋诗风格近于赋而远于比兴,长于议论而短于韵致,故极适合于文学的批评;有时可以阐述诗学的原理,有时可以叙述诗学的经历,有时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2)宋诗风气,又偏于唱酬赠答,往返次韵,累叠不休,于是或题咏诗集,或标榜近作,或议论龂龂,或唱和霏霏,或志一时之胜事,或溯往日之游踪。有此二因,则论诗诗之较多于前代,固亦不足为奇了。”[1](P247)也就是说,宋诗偏于理致的特点以及宋代文人以诗酬赠的社会风气,是宋代论诗诗创作兴盛的两个主要原因。
正如陈伯海先生在《唐诗学史稿》中所言:“如果将以诗论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则广义的以诗论诗就是在诗中论到有关诗的问题,而这样的诗不一定专为论诗而作。……狭义的以诗论诗当是用诗的形式专论诗的问题,是专为论诗而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论诗诗。”[2](P130)这一分类是合理的。我们不妨借用来将论诗诗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论诗诗是较为集中的诗论,规模较大,常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同时在题目上有较为明显的标志,如“读某人诗”、“题某人诗集”、“论诗”等;其他偶然论及诗歌创作的诗歌,其中的论诗语句是只言片语式的,不够集中,可视之为广义的论诗诗。
陆游在其闲居生涯中将精力投注在诗歌创作方面,现存诗歌就达9200多首。其中包括了数量可观的论诗诗。据统计,辑录整理陆游现存诗稿中的论诗篇目,广义论诗诗有584首,狭义论诗诗有141首。[3](P7)那么,这么多的论诗诗陆游是在何种情境下创作的呢?综观这些诗歌,我们发现其创作情境、论诗缘起是丰富多样的,大致可分为读诗读诗、教诗论诗、酬赠论诗、触景论诗、感怀论诗等几种情况。前两种是专门论诗,后几种则是间或论及,但亦不乏诗学奥妙含蕴其中。本文以陆游诗歌为例,解析古代文人论诗诗创作的几种情境。
一、读诗论诗
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下,宋人热爱读书成为社会风气,而读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读前人诗集,学习诗歌创作。陆游作为一个喜好读书之人,在读前人诗歌时往往会抒发感慨,以诗论诗。有时在读自己的旧稿之后也会将自己学诗作诗的心得体会以诗歌的形式道出。
陆游认为《诗经》是后世诗歌的典范,但后人不知取法乎上,以至于古音莫传。这就是陆游在《读豳诗》后所感慨的:“我读豳风七月篇,圣贤事事在陈编。岂惟王业方兴日,要是淳风未散前。屈宋遗音今尚绝,咸韶古奏更谁传?吾曹所学非章句,白发青灯一泫然。”陆游屡屡在其诗歌中提到《七月》、《东山》、屈宋,以之为诗学宗尚,提倡后人向其学习。
追慕陶渊明成为宋代文人的一代文化风尚,陆游在品读陶集时也流露出对陶渊明的钦慕。如他的《读陶诗》:“我诗慕渊明,恨不造其微。退归亦已晚,饮酒或庶几。雨余鉏瓜垄,月下坐钓矶。千载无斯人,吾将谁与归?”将陶渊明引以为知己,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学习陶渊明的平淡清丽诗风,而且在生活上亦效仿其饮酒耕田的生活方式。另有一首七言绝句《读陶诗》:“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疏句,还许诗家更道不?”将陶谢并提,拈出陶渊明《读〈山海经〉》中的句子作为实例表现陶渊明的诗歌造诣,这就将论诗诗与摘句两种批评形式合而为一了。
唐诗作为宋人学习诗歌的典范,自然受到高度重视。陆游曾写过《读唐人愁诗戏作》五首,关注到自屈原以来“穷愁得诗”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并以七绝组诗的形式论之:
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
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九分头。此怀岂独骚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飞雪安能住酒中,闲愁见酒亦消融。山家有力参天地,不放清尊一日空。
少时唤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尽世间愁故在,和身忘却始应休。
清愁自是诗中料,向使无愁可得诗?不属僧窗孤宿夜,即还山驿旅游时。
陆游不仅在形式上借鉴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而且在思想上也继承了杜甫“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的诗学理论,认为好诗常出于仕途不得志人之手,困顿不遇、“清愁”皆为诗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很明显,这一主张与欧阳修“穷而后工”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岑参是陆游自年少时就非常喜爱的一位诗人,“尝以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跋岑嘉州诗集》)[4](P2229)。长大后的陆游渴望从戎报国,因而将岑参视为知己。他曾夜读岑参诗集并作诗曰:“汉嘉山水邦,岑公昔所寓。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至今蠹简传,多昔横槊赋。零落才百篇,崔嵬多杰句。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韶頀。我后四百年,清梦奉巾屦。晚途有奇事,随牒得补处。群胡自鱼肉,明主方北顾。诵公天山篇,流涕思一遇。”(《夜读岑嘉州诗集》)对于岑参的生平经历、英雄气概以及豪气纵横、刚健有力的诗风,陆游都是十分感佩的。
杜甫是宋代诗人普遍推崇和学习的对象,陆游亦曾写过多首读杜诗,对杜甫的诗歌艺术和人生风貌都给予高度评价。如《读杜诗》:“千载诗亡不复删,少陵谈笑即追还。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此盖论其诗艺;又《读杜诗》:“城南杜五少不羁,意轻造物呼作儿。一门酣法到子孙,熟视严武名挺之。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此论其胸次襟怀。
对于宋代诗人的诗歌,陆游在阅读中发现了某些作品议论雕琢的弊病并直斥之:“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气骨多。君看大羹玄酒味,蟹螯蛤柱岂同科?”(《读近人诗》)以“大羹玄酒”与“蟹螯蛤柱”作对比,倡导古朴雅淡的诗歌。陆游作有《读宛陵先生诗》二首,推崇梅尧臣雄浑的诗风。另外,陆游喜读林逋、魏野诗歌并赞赏之:“君复仲先真隐沦,笔端亦自斡千钧。闲中一句终难道,何况市朝名利人。”(《读林逋、魏野二处士诗》)陆游自己在闲居山阴时在作诗方面也效仿二人:“家居禹庙兰亭路,诗在林逋魏野间。”(《书喜》)
在阅读他人诗歌之外,陆游有时还会偶读自己的旧稿,而感慨自己的学诗经历,并析论诗学奥妙。如《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作者感慨自己从前学作诗只是逞弄技巧,并无生气,后来在从戎生涯中丰富的生活经历才使他悟出写诗的真谛,那就是诗歌创作应来源于生活。他十分重视自己从亲身经历中悟得的诗法,因此作诗道之以期流传。另一首偶读旧稿有感则十分重视自然外物对诗人的触动感发作用:“文字尘埃我自知,向来诸老误相期。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丏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江山之助”就是自然山水给诗人带来的诗情、诗兴、诗材,它对于诗歌创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这亦不失为一个精当之论。
二、教诗论诗
陆游喜欢作诗,也常借诗歌的形式教导子孙,而教导的内容之一就是教其作诗。在示子诗中,陆游常常以自我学诗经历为例说明作诗的道理,如《示子遹》:“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他指出少年初学作诗时往往喜欢雕琢藻绘,未能领略作诗的实质,等到中年阅历渐丰,才感悟到诗歌作为六艺之一,不需狡狯,作诗真正的功夫在于诗外,应该到诗外求诗,这样才能写出言之有物、内容充实的作品。
陆游又曾作诗向自己的后辈桑世昌传授诗歌创作心得:“好诗如灵丹,不杂膻荤肠。子诚欲得之,洁斋祓不祥。食饮屑白玉,沐浴春兰芳。蛟龙起久蛰,鸿鹄参高翔。纵横开武库,浩荡发太仓。大巧谢雕琢,至刚反摧藏。一技均道妙,佻心讵能当。结缨与易箦,至死犹自强。《东山》《七月》篇,万古真文章。天下有精识,吾言岂荒唐?”(《夜坐示桑甥十韵》)陆游以“灵丹”为喻,认为好诗不宜雕琢过甚。陆游还有一首专论文学创作的《文章》:“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瑕疵,岂复须人为?君看古彝器,巧拙两无施。汉最近先秦,固已殊淳漓。胡部何为者,豪竹杂哀丝?后夔不复作,千载谁与期。”可见即景即事而发,妙手偶得而非刻意为诗,是陆游一贯的诗论主张。
三、酬赠论诗
以诗唱酬是古代文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宋代文人所作寄赠诗、和韵诗、次韵诗尤多。这类诗虽然是为应酬而作,但亦不乏佳作。陆游在以诗酬赠过程中也常论及诗歌创作原理。如《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古诗三千篇,删取财十一。每读先再拜,若听清庙瑟。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乃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陆游在此诗中论及诗歌发展的历史,推崇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而对于晚唐诗歌持否定态度,认为后人作诗应当取法乎上。这些理论无疑会影响到酬赠对象的诗学观,从而渐渐对诗坛风气产生一定作用。
就宋朝诗人而言,陆游推崇曾几的诗歌,认为作诗应灵活,并应深入浅出,在看似平常的字句中寓有深意。如《赠应秀才》:“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以及《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
陆游还曾经在寄赠诗中论到诗歌的审美效果:“诗如古鼎篆,可爱不可摹。快读醒人意,垢痒逢爬梳。细读味益长,炙毂出膏腴。行吟坐卧看,废食至日晡。想见落笔时,万象听指呼。亦知题诗处,绿井石发粗。”(《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书云所寓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怀》)他认为真正的好诗是能够让人废寝忘食,品味不尽的。
与此同时,陆游推崇屈宋卓有笔力的作品,而非仅仅是“圆美流转如弹丸”。他在《答郑虞任检法见赠》中说:“卧龙山前秋雨晴,郑子过我如夙昔。照人眉宇寒巉巉,悬知笔有千钧力。镜湖岁暮霜叶空,乃闻载酒同诸公。归来湖山皆动色,新诗一纸吹清风。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评方误人。”寄赠诗多会涉及对对方作品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往往是宏观的、概括式的、形象化的,而在作者的评论用词中我们就能窥见其诗学主张。
四、触景论诗
在六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常出现论述诗歌创作契机的“感物论”。如《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5](P318)在后世诗歌作品中,自然意象成为其构成的基本元素。陆游在行旅途中,往往遇美景而作诗,但他除了吟咏山水自然本身,也常在此类自然景物诗中论及诗歌创作的发生问题。如:
沙路时晴雨,渔舟日往来。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
堤上淡黄柳,水中花白鹅。诗情随处有,此地得偏多。(《野步》)
澄潭集鱼艇,村路亚酒旗。欲归且复留,造物成吾诗。(《春晓东郊送客》)
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冬夜吟》)
年年最爱秋光好,病起逢秋合赋诗。(《秋光》)
我似骑驴孟浩然,帽边随意领山川。(《夜闻雨声》)
此处诗学思想与上文所提及的“挥毫当得江山助”(《偶读旧稿有感》)的思想是一致的。自然界的山川风物、生机盎然的动植物,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诗材。与此同时,描写自然风物的诗往往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并超越时代的界限而流传久远。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一首咏梅诗里却表达了似乎与以上理论相悖的思想:“梅花如高人,妙在一丘壑。林逋语虽工,竟未脱缠缚。乃知尤物侧,天下无杰作。老我怀不纾,樽前几开落。”(《开岁半月湖村梅开无余偶得五诗以“烟湿落梅村”为韵》其三)他认为梅花妙在其高深不言,诗人一旦吟咏就落入窠臼,不如让它自在自得。但在通常情况下,自然物象正是由于诗人的一再吟咏才附加上相应的文化内涵的,陆游这首“老我怀不纾”的作品本身即是一首咏梅之作,自然物象仍旧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写作素材。
陆游在外出游览过程中即兴赋诗,有时亦会专门自述学诗经历,如《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首识之以“野店山桥送马蹄”为韵》其一:“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宁知竟卤莽,所得才土苴。入海殊未深,珠玑不盈把。老来似少进,遇兴颇倾泻。犹能起后生,黄河吞钜野。”这首诗体现的仍然是陆游注重诗情诗兴的创作观。
五、感怀论诗
还有一种情况,是陆游在日常起居生活中有感而发,将诗歌创作与自身生活境况紧密联系起来。如《夜吟二首》:“似睡不睡客欹枕,欲落未落月挂檐。诗到此时当得句,羁愁病思恰相兼。”“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在深夜静思之际,月色清冷,尘嚣散尽,陆游认为羁旅之愁与多病之身相兼,感从中来,自然得句。这里讨论的仍然是诗歌创作发生的问题。
陆游在闲居生活当中还体悟到心境与诗歌格调的关系。“身闲诗简淡,心静梦和平”(《幽兴》);“身闲诗旷逸,心静梦和平”(《山中》);“身闲诗简淡,道胜梦轻安”(《秋夜》);“无意诗方近平淡,绝交梦亦觉清闲”(《幽兴》)。可见作者推崇的是平淡自然的风格,并认为心境闲淡、无意于作诗才能写出平淡之作。作诗的目的是抒怀,并非刻意求工:“作诗未必能传后,要是幽怀得小摅。”(《幽居遣怀》)因此,陆游一贯主张作诗不要雕琢苦吟:“亦莫雕肺肝,吟哦学郊岛。”(《晨起》)同时,他认为诗歌与作者的身世境遇密切相关:“易虽病里犹能读,诗到愁边始欲工”(《山园晚兴》);“诗情剩向穷途得,蹭蹬人间未必非”(《舟过樊江憩民家具食》)。这里明显继承了欧阳修“穷而后工”的思想,认为仕途不得志、生活不称意的人往往能写出好诗。但在另一首诗中陆游又反其意而用之:“面大如盘七尺身,珥貂自合上麒麟。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对镜》)欧阳修认为并非诗能穷人,乃穷而后工也,陆游却戏谑的口吻说诗能“穷人”、“瘦人”,这恐怕是诗人醉心于诗歌事业的结果。
除了以上五种情境之外,陆游还曾在题跋、伤悼、记梦时以诗论诗。如《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诗句雄豪易取名,尔来闲澹独萧卿。苏州死后风流绝,几许工夫学得成?”“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这是陆游题在友人萧彦毓诗卷后的两首诗,评价其诗为“闲澹”,是在山程水驿的生活经历中写出的,因而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在经过李白墓时,陆游写下了一首伤悼之作,自然离不开品评诗人:“饮似长鲸快吸川,思如渴骥勇奔泉。客从县令初何有,醉忤将军亦偶然。骏马名姬如昨日,断碑乔木不知年。浮生今古同归此,回首桓公亦故阡。”(《吊李翰林墓》)诗中以具体意象形容李白思如泉涌、浩荡奔腾的创作风格,恰如其分。陆游甚至在梦中也会梦到作诗,醒来后写诗记之:“夜梦有客短褐袍,示我文章杂诗骚。措辞磊落格力高,浩如怒风驾秋涛。起伏奔蹴何其豪,势尽东注浮千艘。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气死岂埋蓬蒿?晚唐诸人战虽鏖,眼暗头白真徒劳!何许老将拥弓刀,遇敌可使空壁逃。肃然起敬竖发毛,伏读百过声嘈嘈。惜未终卷鸡已号,追写尚足惊儿曹。”(《记梦》)即使在梦中,陆游所欣赏钦佩的仍然是“措辞磊落”的诗骚,认为后世罕及,应以之为学习的典范。
由上可见,诗人们不仅在读诗、学诗、教诗时会专论诗歌创作,而且在酬赠、触景、感怀、题跋等多种生活情境中都会言及诗歌,并且不乏精到之论。论诗诗不同于诗话、评点等其他批评形式的一个特色,即在于它短小精悍,运用起来灵活自如,并且凝练直截、形象可感,不失为诗性与理论二者得兼的论诗形式。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陈伯海主编.唐诗学史稿[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
[3]田多瑞.探赜索引,探骊得珠——陆游论诗诗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