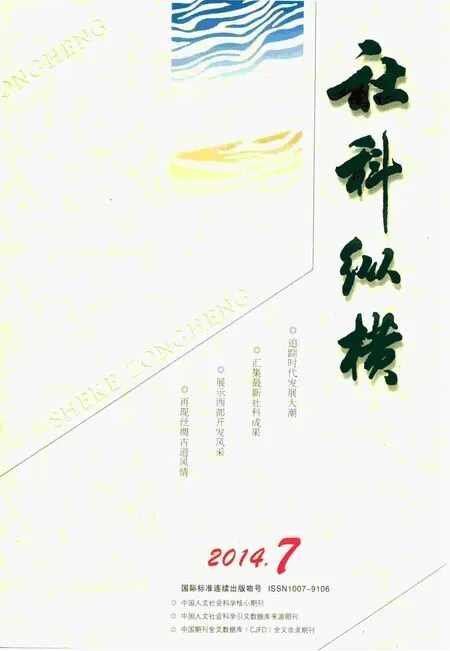论春秋时期的大都耦国
2014-04-09尉博博
尉博博
(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大都耦国是春秋时期各主要诸侯国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是指在一个诸侯国中,存在着与该国国君所在的国城势均力敌的一个或几个大型城邑。也就是说,一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势力相当的政治实体共存的政治局面。大都耦国一词系出《左传·闵公二年》:“大子(申生)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谂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与此相类似的说法还有《左传·桓公十八年》:“并后,匹敌,两政,耦国,乱之本也。”从《左传》记载来看,当时一些士大夫已隐约感觉到大都耦国对旧的政治格局的巨大冲击,所以认为是“乱之本也”。
春秋时期,首先出现大都耦国局面的国家是晋国。公元前745年,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其城邑的规模大于晋之国城,曲沃经过桓叔、庄伯、武公,祖孙三代的苦辛经营,历68年奋战,终于以庶支代替嫡宗,夺取了晋国政权。以旁支取代大宗而成功夺权的,在春秋时期仅此一例。这就在以宗法为基础的旧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自此之后,晋国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增强,公室力量逐渐削弱,最终形成赵、魏、韩三家鼎立。广义而言,三家并立也是大都耦国、尾大不掉。因此,可以说大都耦国几乎贯穿了晋国史的全过程。晋国后期也有一次比较典型的因大都耦国而造成的政治事件,公元前550年,晋大夫栾盈以曲沃之甲攻入晋都,但未成功而身死族灭。
郑国开始出现大都耦国局面的时间略晚于晋国。公元前743年,郑庄公封其弟共叔段于京,京大于郑的国城。共叔段在其母亲的引导下,于公元前722年攻郑,被郑庄公打败。《左传》记录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从“郑伯克段于鄢”开始的,足见大都耦国在当时已引起关注。公元前680年,郑厉公自栎攻郑,大夫傅瑕作为内应,复得君位。栎也是郑国的大邑。郑厉公以大都耦国之势夺取政权与曲沃并晋不同,郑厉公属于复辟,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远比不上晋国,因此对各自国家的影响也不可同日而语。
卫蒲、戚之大,与其国城有过之而无不及。蒲是卫大夫宁殖的采邑,戚是孙林父的采邑。公元前559年,由于卫献公故意侮辱孙林父和宁殖,孙林父自戚攻卫,卫献公出奔齐,孙、宁二人拥立新君殇公。十二年后,卫献公复位。卫国是在殷墟之上建立的,殷周文化相互融合,固守传统的色彩很浓。因此该事件对卫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不深,也与晋国不可比拟。
宋可敌国的大都则有萧和蒙。根据《国语》韦昭注,萧、蒙是宋公子鲍的采邑。当时宋昭公无道,公子鲍乐于施舍,施舍的经济后盾当来源于萧和蒙。施舍的结果大得国人之心,再加上其祖母的帮助,弑昭公而即君位,是为文公。此年为公元前611年。宋国还有一次因大都耦国而发生的严重政治事件,公元前682年,宋国的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闵公,而立子游。群公子逃奔到萧,公子御说,即后来的宋桓公逃到亳,亳为宋国又一大邑。该年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的后裔进攻南宫长万,杀子游,立桓公。宋国是殷遗民的封国,又地处中原,忠君观念向来较重。因此,大都耦国对宋国政局的影响较弱。
鲁国的大都耦国之局非常典型。公元前659年,僖公把汶阳之田和费赐给季友,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又取卞。成是孟孙氏的采邑,郈为叔孙氏的采邑。三家分别于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三分、四分公室,昭公、哀公出亡于外,大都耦国之势至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鲁国是周公的封国,是周文化的代表,宗法礼制势力最强,三桓虽专鲁,但终没有废君自立,未能彻底进行改革。孔子生当其时,看出大都耦国是鲁国政治矛盾的症结所在,遂利用仲由为季氏宰的时机,主张堕三都,鲁定公十二年,郈、费被堕,成未攻克。从深层次说,大都耦国只是症状,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体制、结构是病根。晋所以兴,鲁所以衰,与此不无关系。
齐足以耦国的大都则为渠丘和高唐。渠丘是齐大夫雍廪的采邑。由于齐公子无知虐待雍廪,当无知一度被拥立为君时,雍廪弑无知,该年为公元前685年。高唐是齐权臣陈氏的采邑。公元前532年,齐景公的母亲穆孟姬为陈桓子求得高唐作为采邑,势力不断壮大,终于在公元前391年田和代姜齐而为田齐,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命田和为诸侯。齐国地近东夷,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不深,很早便开始改革。陈氏利用大都耦国之势,因势利导,先后消灭各派守旧势力,使齐国从血缘为基础的早期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齐、晋均为春秋大国,大都耦国对两国的影响都很深远。
秦国的大都耦国形势最不明显。秦景公之弟公子鍼得征、衙为采邑,又承其父秦桓公之宠幸,与秦景公如两君并立,被迫于公元前541年奔晋,出奔时带了一千乘车子,其富之逼国,可见一斑。
楚国在春秋时,也出现了大都耦国的局面。公元前531年,楚灵王修筑了陈、蔡、不羹三座大城。不出三年,楚公子弃疾率领陈、蔡、不羹的军队攻楚,楚灵王自缢。之后,还有“白公之乱”,但很快被楚惠王平息。接着叶公子高、子国相继为令尹,楚国复兴。楚为南蛮,尚左,文化礼仪自成体系,不与华夏同,自“白公之乱”后走上振兴之路。所以,大都耦国对楚国有积极影响。
春秋时期之所以出现大都耦国的局面,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大都耦国是分封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封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实施初期确实起到了巩固公室本根的作用,列国存灭时间多至数百年以上,分封制功不可没。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显,愈益走向自己的反面。
首先,分封制随着人口的繁衍,必然越封越多,使封主的政治、经济势力相对被削弱。如:郑庄公封叔段于京,则京所属的土地、人口,财富,均脱离了公室的管辖,公室势力必然削弱无疑。郑国还有栎,卫国的蒲和戚,宋国的萧和蒙,鲁国的三都,齐国的高唐,晋国的曲沃等,这些都的分封,实为公室的巨大损失。分封的都越大,公室的损失也就越大。
其次,所封卿大夫之都是国之翻版,具有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等权力,不同于完全听命于中央的郡县。势必独立性、离心力越来越强。《左传·昭公十六年》:“立于朝而祀于家,有禄于国,有赋于军。”这是卿大夫权力的集中体现。
“立于朝”,杨伯峻认为是朝有官爵,实质上就是卿大夫的世官制。在春秋时期,世官制还很盛行,如晋国的郤氏、先氏、赵氏、中行氏、范氏、韩氏、知氏、魏氏等,齐国高氏、国氏、崔氏、庆氏、陈氏等,鲁国三桓,郑国七穆,周单、刘二氏等,除非灭族,皆世代为官于朝。
“祀于家”,杨伯峻认为是家有祖庙,至于祖庙所祀,服虔以为“祀其所自出之君,于家以为太祖”。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拥有独立祭祀权,在神权时代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祭祀祖先,可以从精神上控制全族上下,使之惟命是从。
“有禄于国”,杜预注为受禄邑。采邑可以说是卿大夫的生命线。卿大夫之所以能够在春秋历史舞台上叱诧风云,在各国飞扬跋扈,上弑君,下灭族,都是仰仗采邑这个后盾。
“有赋于军”,杨伯峻认为有采邑之卿大夫皆出军赋,在国家战争时,率领属邑军队作战。如襄二十五年传叙楚、吴之战,楚子强“请以其私卒诱之”,宣十二年传楚、晋邲之战,晋知庄子以其族反战,十七年传叙郤克请以其私属伐齐。“私卒”、“其族”、“私属”皆卿大夫之采邑之军赋。从“有赋于军”可以看出,卿大夫拥有私家军队,这是造成大都耦国局面的直接原因。郑国公叔段与郑庄公成二君,就是通过缮甲、兵,具卒、乘而实现的;晋国曲沃庄伯以其私家武装伐翼,弑孝侯;曲沃武公伐翼,韩万御戎,梁弘为右,将哀侯赶出翼;卫国孙林父率领私兵攻入帝丘,并大败公徒于河泽,足见其军队力量之强大。鲁国季孙意如联合孟孙、叔孙氏,以三家的武装打败鲁昭公的公徒,公徒释甲执冰而踞,昭公出奔;晋国栾盈帅曲沃私军攻入绛。可见,卿大夫手握重兵,直接促成了大都耦国的局面。
总之,卿大夫的都实质上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具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等权力。而这些权力都是封主赐予的,并非封主有意为之,实由分封的体制所决定。当都的实力膨胀到与国城相当或超过国城,大都耦国之局便形成了。郡县制就是惩大都耦国之弊而出现的,郡县唯中央之命是听,中央集权因得以实现。
第二,大都耦国是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改革的必然结果。考古发现证明,春秋早期开始出现生铁制品。生铁是在较高温度下,用木炭还原铁矿石得到的含碳量较高(超过2%)的液态铁可以直接铸造各种器物,并能批量生产,因而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春秋时可能已出现牛耕,《国语·晋语九》:“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山西浑源出土的春秋晋国的铜牛尊,其鼻穿环,从另一侧面证明牛已被牵引以从事劳动。根据赵世超教授《周代国野制度研究》,由于生产力不断提高,春秋时的农业劳动组合方式已由大集体过渡为小集体。而这种小集体劳动组合反过来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精耕细作。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旧的剥削方式必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各国纷纷进行社会改革,卿大夫乘机使社会财富向自己倾斜,这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卿大夫。如晋国“作爰田”、“作州兵”之改革,将军赋的征收扩大到野,从此卿大夫势力得到迅猛发展。郤氏,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军。《左传·昭公五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晋人若丧韩起、杨肸,五卿、八大夫辅韩须、杨石,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奋其武怒,以报其大耻。”鲁国则通过“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的改革,将鲁国公室架空。《左传·襄公十一年》:“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第。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左传·昭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尽征之,叔孙氏臣其子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由上可知,鲁国的人口、土地、财富被三家瓜分,鲁公只能靠贡度日。卿大夫势力到此,可谓达到巅峰。
第三,大都耦国是各诸侯国家族兼并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都的数量大增,但并不是凡都皆能耦国,只有少数大都才能耦国。少数大都的出现,家族兼并是一重要原因。如晋国的卿族大者有十一家,赵、魏、韩、狐、胥、先、栾、郤、知、中行、范氏等。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斗争,最后剩下赵、魏、韩三家,成大都耦国之势而分晋。晋国以军的将领为卿,而以中军之帅为正卿,这一军政体制对家族兴亡关系极大。董之蒐,以赵盾为中军帅,贾季不满,使人杀阳处父,己出奔狄,狐氏亡,而赵氏兴;胥童灭郤氏,瓜分其地,被命为卿,车辕之役中被栾、中行氏诛杀,胥氏亡;先且居为中军帅,先氏兴,后先毂因邲之败,召狄之故被诛,先氏亡;栾书为政,灭郤氏,分其地,栾氏兴,栾盈以曲沃叛,范、中行氏灭栾氏,栾氏亡;士会代荀林父为政,范氏兴,荀林父代郤缺为政,中行氏兴,知、赵、魏、韩灭范、中行氏,瓜分其地,范、中行氏亡;知罃代韩厥为政,知氏兴,赵、魏、韩灭知氏,尽并其地,知氏亡。晋国家族兼并的结果是赵、魏、韩三家强,大都耦国之势成。齐国大卿族有国、高、崔、庆、陈氏。陈氏将其逐一消灭,以一卿独大,成耦国之势而代姜齐。齐国原本只有国、高二卿族,齐灵公封崔杼为大夫,崔氏兴,后灵公以庆封为大夫,庆佐为司寇,庆氏兴,鲁襄公二十七年庆封灭崔氏,二十八年,陈、鲍灭庆氏,并瓜分其室。陈氏据高唐,始大。陈成子诛国、高二族,尽灭诸氏,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为采邑,占地超过齐平公,耦国之势成。
纵观春秋史,大都耦国在晋国和鲁国的表现最为典型。晋国通过大都耦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率先由血缘国家向领土国家转变,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思维模式都领先于各国。鲁国三桓专权,虽有初税亩、用田赋等改革措施,但整个社会体制没有根本变化,血缘纽带在鲁国根深蒂固,“周礼尽在鲁”,正是说明鲁国的传统保守力量特别强,改革的阻力相当大。
大都耦国对晋国和鲁国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具体表现是:
首先,大都耦国在晋国的旧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动摇了血缘关系作为整个社会基础的地位。曲沃并晋后,晋国君主认识到血缘关系并不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甚至对自己危害最大。《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晋桓庄之族逼,献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过了二年,遂“尽杀群公子”。这样血腥屠杀公族的事件,在春秋史上是空前的,对晋国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左传·宣公二年》:“初,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晋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公族的国家,后来设立的所谓“公族”是由异姓卿大夫的嫡子所组成,实属假公族。血缘关系第一次在晋国政治中丧失了重心地位,为异姓优秀人才的崛起开辟了道路,也为晋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鲁国的血缘关系纽带十分牢固,即使三桓也终未敢弑君而自立,始终保守君臣名分。鲁国的执政卿大夫都是公族,绝对排斥异姓掌握政权。鲁国一直秉持周礼。《左传·闵公元年》:“(桓)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左传·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可见,以周礼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笼罩着鲁国,改革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因三桓专权而形成的大都耦国局面没有触及鲁国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因此,社会的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孔子当时也看出大都耦国对鲁国公室的危害性。倡导堕三都,但是没能彻底解决三桓问题,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血缘关系这个基础。
其次,大都耦国催生了晋国的县制。晋自献公,鉴于大都耦国之患,始行军功赐县制度,逐渐地将灭国改为县,以有军功的异姓卿大夫为县大夫。县大夫早期主要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但是到了晋国后期,则不再世袭。在县大夫的任命上,也是以举贤为主。《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谓贾辛、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故举之;谓知徐吾、赵朝、韩国、魏戊,余子之不失职,能守业者也;其四人者,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以贤举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此时晋国有如此广大的举贤胸怀,何患晋国不能崛起。县大夫之下设有县师和舆尉,可见晋县已具有行政组织的雏形。
鲁国的三桓专权却导致了“陪臣执国命”的乱局。“陪臣执国命”是鲁国宗法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三家的家臣是世袭的,如南遗,南蒯世为季氏家宰;家臣或有大宗的背景,如阳虎是孟孙氏的庶支。家臣还拥有封邑。“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南遗曾拥有东鄙三十邑。阳虎将郓、阳关据为己有,《左传、定公七年》:“齐人归郓、阳关,阳虎居之以为政。”“陪臣执国命”实质上就是大都耦国在卿大夫家中的重演,其根源在于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体制。阳虎居鲁则乱,居晋事赵简子则善,即是有力的证明,不然,同是一人,难道变化如此神速。鲁国由于历史包袱沉重,没能出现县制新制度。
大都耦国贯穿了春秋史的全过程,是宗法分封制过渡到郡县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它既是分封制和宗法制的产物,又对分封制和宗法制起到了瓦解作用;既阻碍着中央集权,又催生了郡县制度。历史正是在这种二律背反中前进的。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990.
[2]徐元诰.国语集解[M].中华书局,2002.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4]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研究[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5]李孟存.晋国史[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6]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