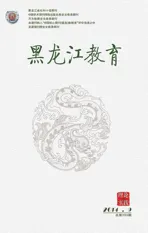论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深层原因
2014-04-09孙记
孙记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论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深层原因
孙记
(黑龙江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解决程序失灵问题的前提在于弄清原因。当下刑事诉讼制度可以通过立法实现现代化,但立法者、司法者、辩护人、当事人却不能按照现代刑事诉讼文化的内在要求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立法者即便适度迎合理论预期也必然会疏离实践部门利益诉求,使新法在运行中大打折扣;在法律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即便受过职业训练的办案者基于利益权衡,难免要在个案中为迎合特定需要而规避程序,久而久之,一些办案者在日常工作中规避程序便会常态化。
刑事程序失灵;刑事诉讼文化;刑事诉讼现代转型
一、问题的由来
陈瑞华教授认为,刑事程序的失灵是指“立法者所确立的法定程序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受到了规避和搁置,以致使刑事诉讼法的书面规定在不同程度上形同虚设”,实际上“无论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并不是不遵守任何程序任何程序规范的。只不过,它们所实际奉行的是一套并未得到正式法律确认的‘潜规则’或‘隐性制度’。这些‘潜规则’或‘隐性制度’,往往是公检法机关基于办案的方便而自行设计出来,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逐渐得到普遍认可的规范。……似乎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正式法律程序的权威地位”,[1]之后他便分析了失灵问题的原因,对于唤起法律各界重视程序失灵问题作出了积极贡献。学术界并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此也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程序失灵问题至今悬而未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在于弄清原因,为此本文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
二、诉讼文化与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着深度断裂
尽管学术界不乏对观念性诉讼文化与制度性诉讼文化现代化同时并举的主张,但是至今仍未有人将其与程序失灵问题进行直接勾连。诉讼文化并非学界所主张的那样,仅仅为制度性文化与观念性文化的简单两分,并强调观念性现代诉讼文化的主要表征,以此作为我国诉讼文化转型的目标。其实,诉讼文化说到底是作为群体性的人对诉讼的态度,现代刑事诉讼文化的内在要求只有成为立法者、司法者、辩护人、当事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才是刑事诉讼现代化的真正实现。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弥合立法与司法的距离,失灵问题才有望解决。我国通过借鉴域外刑事立法成就实现刑事诉讼的制度现代化相对容易,可是,与域外刑事诉讼制度契合的观念性文化内化于中国人人心,或以域外现代刑事诉讼之文“化”当下中国之人谈何容易,刑事诉讼观念的现代化因此任重道远。林语堂先生可谓一语中的:“在中国的城镇,总是有一个阳性的三位一体:官、绅、富,以及阴性的三位一体:面、命、恩。阳性的三位一体通常是在一起共事的”,阴阳互补,最终“社会等级观念与等级内平等导致了中国某些社会行为规范的产生。这就是3个不变的中国法则,比罗马天主教的教义还要永恒,比美国的宪法还要权威。它们是正在统治中国的三位女神,……它们的名字是面子、命运和恩惠。这三位姐妹过去统治着中国,现在也如此。唯一真值得一试的革命是反对阴性的三位一体的革命。问题是这三位女人是那样地斯文,那样的迷人。它们使……司法机构瘫痪,使宪法失效。它们讥笑民主,蔑视法律,拿人民的权利开玩笑……”,于是“一个中国人被捕了,或许是错捕,他的亲戚本能的反应不是去寻求法律的保护,在法庭上见个高低,而是去找长官的熟人,去求他的‘恩典’。由于中国人非常重视个人关系,重视‘情面’,这个去求恩典的人如果‘面子’足够‘大’,他的说情往往能够成功。这样,事情总是很容易,比那耽延时日的官司花钱要少得多”。[2]家国本位契合的等级观念等及其所决定的中国人行为规范——面子、命运、恩惠,因建国后的集体优位及其所要求的个体服从而在改头换面后延续,从法律领域外阻滞着现代刑事诉讼理念的传播,最终支配着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工作人员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刑事程序失灵问题发生因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立法者在理论预期与实践诉求间难作选择
尽管近几年刑事诉讼法学界更加侧重实证研究,但是包括这一研究在内的所有学术研究基本上自说自话,除了早些年间针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产生“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争鸣态势外,理论界自身停留在制度层面就事论事,很少针对某一论题产生真正的观点交锋,甚至连商榷性的文章也难得一见。
究其原因,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没有形成真正的学术流派,老一辈学者在拨乱反正中尚致力于海纳百川,新一代学人大多却在浑然不觉中坐享其成,不能在继承导师或前辈研究成就后推陈出新,新老学人的说理难以服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域外经验进行介绍与传播,但是在传播中亲疏不分,研究成果虽然在数量上蔚为大观,但在建言献策上却平分秋色,最终使看似丰富的立法资源在立法者看来无所适从,都重要就是都不重要。现实层面,我国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后,进一步对公检法等机关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作出明确定位,赋予它们各异而又多元的司法使命,但面对犯罪手段与时俱进,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预期众口难调,各机关在各自系统内逐渐形成自成一体的部门利益,面对理论预期与立法呼吁,最高专门机关基本上能达成利益共识,合力抵制因加强权利保障而对执法予以制约的立法步伐,面对社会责难,它们也差不多能做到异口同声地共同开脱。但是,在立法配置权力过程中,它们还是为了捍卫部门利益而寸权必争,立法后在司法解释中又出于本部门办案需要而有意扩权。同样,各系统的地方专门机关也会在司法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维护本部门利益。
这样,立法者便在理论预期与实践诉求间处于两难选择,即便适度迎合理论预期也必然会疏离实践诉求,注定使新法在运行中大打折扣,扩张本部门权力的各司法解释相互之间无法契合,这些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决定了刑事程序失灵的必然性。
四、诉讼转型中办案者存在轻法逐利的工作惯性
上述诉讼文化与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的断裂,立法因迁就理论与现实而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决定的,刑事诉讼现代转型最终是人在刑事诉讼方面的现代化,特别是办案者在刑事诉讼方面的现代化,即他们在诉讼中能恪守刑事诉讼法、信仰刑事诉讼法、切实保障人权、最终实现正义。但是,我国漫长的传统社会却存在着一种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为官之道”,如《笑林广记》里有这样一则笑话:“说的是京城附近,有个裁缝格外讨达官贵人的欢心,生意比别家的都要红火。于是,就有人问他发家的秘密,裁缝笑答,裁衣服不仅要量人的胖瘦高低,还要询问人家为官的年头,官职的大小。那些新任要职的官员,往往趾高气扬,突肚挺胸,衣服要做得后短前长;过了两年,他们吃了些耀武扬威的亏,不敢过于张扬,待人平和了,衣服就要做得前后一样长短;再过两年,他们渴望升迁,就不得不巴结高层,摧眉折腰,衣服就要做得前短后长了。这才叫‘量体裁衣’。”[3]这在古代司法中体现便是造就出诸多“判断葫芦案”的“葫芦僧”。
今天,随着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推进,前述现象早已被否定,但轻视程序的习惯做法却与此“剪不断、理还乱”,改头换面后依旧大行其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早期办案者职业素养整体不高,在打击犯罪作为首位乃至唯一任务的前提下必然会忽视程序,但在人权保障被重视后,即便受过职业训练的新一代办案者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间存在着冲突、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不能统一、业务素质与政治素质不能两全、恪守程序与追求绩效背道而驰时,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法律自身规定不具体的情况下,难免要在利益权衡后的个案中规避程序,以迎合社会、上级机关、单位领导乃至政治要人等的需要,“处断前请示、处断后汇报”“上下之间早沟通、平级部门之间勤协调”,力争使领导满意、让社会放心,最终为自己的升迁积攒资本,为绩效考核加码。此情此景,除了信仰程序,所有的因素都可能成为办案者工作中的上帝。久而久之,规避程序便会在一些办案者日程工作中常态化。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96~297.
[2]林语堂著,郝志东,沈益洪译.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46~150.
[3]李涛.龙之殇:中国文化的尴尬与嬗变[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17.
编辑∕岳凤
孙记(1972-),男,辽宁建昌人,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诉讼法学、法理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的刑事诉讼文化及其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3D26;2013年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我国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原因研究”,项目编号:12532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