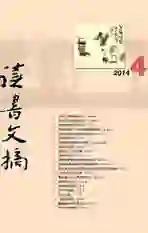看电影的记忆
2014-04-08王学泰
苏联电影风靡一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包括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到电影院看电影是个极普通的事。喜欢娱乐的北京人、特别是年轻人一年看四五十场电影不是特别稀罕的。那时单位一般是两个星期组织一次看电影,作为工会的福利;人们也常常以看电影度过假日或星期天。至于寒暑假有学生专场,节假日还有夜场。我想,从那个时期生活过来的人们一定都会保留着丰富的“看电影的记忆”。
建国那年我只有7岁,小学二年级。看的第一部新电影是个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在中央电影院(今北京音乐厅)看的。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当银幕前那张薄薄的浅色帘幕还没有打开的时候,“百万雄师下江南”七个大字已经打在了上面。看的第一个故事片是《天字第一号》,是讲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谍报人员打入一个汉奸大员家庭获取情报的故事的。谍报人员以“天字号”和“地字号”排序。详细的情节记不太清了,但“天字第一号”、“地字”某某号在小孩子游戏中流行了很长时间。这部电影大约是1949年初在国民电影院(即首都电影院)看的,建国后这类“歌颂国民党”的电影被禁,就不可能看到了。看的第一部外国电影是苏联的《喀朗仕塔德》,在大都市影院(这个影院现已没有,旧址在西绒线胡同,四川饭馆对面)看的。这部电影是写1920年黑海水兵暴动的。只记得一个情节是被捕的水兵,被绑上大石头,从山崖上推入海中,而水兵身上有小刀割断了绳索,又从别处游了上来。
十多年间看了多少片子?很难统计了,大约不下100部吧。但给我留的印象深的、现在还有清晰记忆的是外国影片。50年代初,中国对外交往很少,这时只有大量苏联电影和少量的东欧电影。最早的译制片是东北厂(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放映这类影片时都要在海报上郑重地写上“华语对白”四字,以招徕观众。不过当时的“华语”还不是现在的普通话,而是民国时期,糅合南北两京口语而成的“国语”。“文革”当中能够公开放映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都是东北厂译的,人们已经习惯听普通话了,听着列宁、瓦西里等讲的东北味儿的国语很好笑,所以许多年轻人喜欢拿腔作调学“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让列宁同志先走”等对白。这时翻译的、而且很火爆的电影还有《乡村女教师》(后来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听很多同学以“乡村男教师”自嘲)、《钦差大臣》《夏伯阳》,《保卫察里津》《日日夜夜》以及高尔基的“三部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
提到好莱坞一定要批判
我一接触电影看的就是黑白的有声片,但在五十年代也看过无声片。给我记忆最深的是上初中时看的卓别林的默片,大约是在1956年,我们在阶梯教室上完“动物课”后(当时生物分两门《植物学》、《动物学》),就着放映机给我们放了一段卓别林短片,卓别林的滑稽动作逗得大伙狂笑不止。那时谈论美国电影都是犯忌的,特别是好莱坞,就是西方腐朽反动文化的象征。有文化的人,只要提到“好莱坞”三个字都要加上几句批判的话,免得使人怀疑立场有问题。不知道老师出于什么想法,冒险放了一段美国片。好在这是在反右以前,大家的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没有后来那么紧。补充一句,一般中学不会有阶梯教室。我们是在老北京师范大学旧址(和平门外)上课,用的是师大的课室。
五十年代社会上还真是公开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这也是我看的第一部美国片《社会中坚》。不过这部片子不是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代表好莱坞的产品,而是美国共产党(不过后来反修斗争中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共产党时,美共是第三个被批判的)领导工人阶级制作的。是描写美国反动政府如何镇压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人搞罢工,结果被警察抓了起来,不分男女老幼都被关在铁笼子里。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些被抓起来的工人们一齐有节奏地高喊“我们要洗澡!”“我们要洗澡!”我觉得很奇怪,进监狱要洗澡干什么?这个问题直到九十年代我才有点理解。
彩色片与宽银幕
我看的一部彩色影片是什么记不清了。因为黑白片拍得好的,就像水墨画一样,也是墨分五彩的。他拍的是黑白片,可是进入头脑后,你把它翻译成彩色的,于是记忆中就成彩色的了。例如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英国影片《百万英镑》、西德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影片我对它们的电影海报的记忆是黑白片,而实际看影片时留给我的记忆是彩色的,真是奇怪。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也干扰了我的记忆:苏联影片中有一种“红白片”,平常电影的黑色部分,它是红褐色的。如五十年代初的《忠实的朋友》(写好朋友远游遇险的)、《茹尔宾一家》(描写造船工人生活的),这种红白片很像历时久远的褪色的彩色片。
我第一次看立体声宽银幕片是在1957年。先是首都电影院停业,大家很关注,后说要改造成专放宽银幕立体声的电影院,引起了民众的兴趣。报上和《大众电影》上做了很长一段宣传,说这类影片是普通银幕的电影无法比拟的,宽银幕立体声给观众的感觉是像进入影片似的。首都终于开张了,大家排队买票,尽管票价很贵。第一场是苏联电影《革命的前奏》,此片描写1905年俄国彼得堡工人星期日上街请愿,惨遭沙皇屠杀的故事。看电影时,我努力找进入影片的感觉,怎么也没找到。我感觉到的与普通银幕的唯一差别就是近卫军打着军鼓从银幕左边走到右边时,声音也从左边走到了右边。可是这个宽银幕的票价是5角钱啊,比普通银幕贵了一倍以上。真不值。
从此首都就成了北京第一个宽银幕电影院。在这里看的宽银幕影片还有法国的《塔曼果》,这是根据法国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描写白人贩卖黑人奴隶和黑人反抗的。苏联的《上尉的女儿》,这是根据普希金小说改编的。
第一次的感觉总是难以忘怀的。
大墙里面看电影
1976年7月26日,我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罪行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经历了7月28日的大地震,过了上诉期,8月初转入“北京第一监狱”,因为属于“重刑”(10年以上就算重刑),便留在一监监狱工厂劳动改造。endprint
这是个比较规范的监狱,始建于清朝末年推行新政之时,连鲁迅都参观过,他有个书桌,买的就是一监工厂产品。他称此地为“洋监狱”,其“构造坚固,不会倒塌”。鲁迅所言不虚,它经受住了这次大地震的考验,没有太大的伤损。它有百年历史,如在美国一定是文物了。
监狱与看守所不同,相对宽松一些了,在工厂劳动,每星期有一天的工休。两三个星期放一次电影。放电影的地点是狱中的一个露天广场,不大,但狱中千余人都能装下,时间一般是在休息日的头天夜晚。一监地处北京宣武区自新路,那时宣武区星期四停电,看电影的时间多在星期三的晚上。待天色黄昏时,犯人按照中队的编制在看守的带领下各自携带自己的小板凳来到小广场,端然静坐,天一擦黑,就开始放映了。
在“一监”呆了两年,大约看了一二十场电影罢,每场一般是两部影片,其中有三场至今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象。一是所谓“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片。转到一监不到一个月,毛泽东逝世,接着就是“四人帮”垮台。本来“反击右倾翻案风”该刹车了,不知是由于惯性,还是其他秘而不宣的原因,北京的运动并未停止。那时旧电影(1966年以前拍的)大多没有解禁,社会上放的电影也多是1975、1976年间拍摄的。经过“文革”,文艺政治化搞到极端,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因此这时的影片内容就是谎言的汇聚,是对观众智力的侮辱,也不妨说是一种测验。
有个片子的名字记不清了,但它的第一个镜头,过了32年仍然记忆如新:一个革命派的姑娘,风风火火,怒气冲天,从岸边跳上一只小船,一把抓住船上一男人的肩头,哧啦一声,撕下一大块布来,这是一个大特写。原来这位女革命派阻拦其男朋友进城做小买卖,“搞资本主义”。这位女士的形象就是当时极其时髦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角色。另一个就是《欢腾的小凉河》,这是个针对性很强的政治片,它的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影片中有个“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出场就是要“整顿”,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搞“四个现代化”等等一类大多数民众听着合理、却被主流舆论狠批的口号。这个副主任在外在造型上都模仿邓小平,留着小平头(“四五”之后,“小平头”就成为一种“反动”的政治意象),穿着藏蓝色的中山装,并在与无产阶级革命派争论时,引用“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句邓氏名言。虽然影片把这个副主任当作反面人物来塑造,但他颇具气势,言辞尖锐,与造反派辩论时侃侃而谈,影片想贬损这个人物,反而增加了普通观众对他的好感。
印象最深的影片是1975年中央新影拍摄的访问“民主柬埔寨”的纪录片。这个片子很长,分上下集,约三个小时。我很佩服拍摄者的毅力,这样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欢笑的空间,他们居然能够专心致志地审视那么长时间。当时柬埔寨国内,人们穿的一律是黑色(仿佛是秦始皇时代的“尚黑”),无论男女,女的只比男的多一条黑围巾。不过这让一监犯人(犯人服装都是黑色)感到亲切,看看银幕,再瞅瞅衣裤,真有“天下同此一色”之感。
歌舞团的演出也一律着黑装,其歌唱如诵佛经,不知是佛诵取法于柬地民歌,还是柬埔寨人由于深信释迦惯用佛音梵呗以表达情怀呢?舞蹈只是顿足扬臂,颇具古风。女舞者持镰刀,男扬斧头,两者携手,就是工农团结;举枪联臂,昂首扬眉,便是消灭敌人。一看就懂,非常大众化。
影片中的首都金边,更令人惊讶,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只有军用卡车往来疾驰,扬起阵阵沙尘。片子中给我印象最深的镜头是一位十来岁的小革命军人。这个孩子大约也就一米三四高,着一身工作服,面无表情、专心致志地在车床上加工机器零件。因为个子矮,只得站在一个肥皂箱上,车床旁边还竖着一支冲锋枪。旁白说,这个孩子六七岁时,父母被美帝国主义者杀死,为了报仇,他参加了红色高棉革命部队,用枪打击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为革命建立了功勋。现在革命胜利了,他放下武器、拿起工具为柬埔寨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工作,再立新功。当时还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人间浩劫,但我想这样小的孩子,如果在革命战火中没有条件上学的话,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不让他们读书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根本没有学校了,因为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统统被取缔了。
电影这种有刺激的娱乐往往会引起犯人的遐想,特别是1977年下半年,旧电影开放了,许多电影的放映都能带来点震撼。例如“政治犯”(当时不承认有政治犯,因为刑法中有“反革命罪”,“反革命”也是刑事犯罪)对影片的政治涵义很敏感。改革开放前,中国文艺、学术都是政治信号,开放旧电影简直就是发布政治信号。荧屏播放了关于海瑞的湘剧影片《生死牌》是一声春雷,大家议论,“文革”第一个倒霉者吴晗要平反了,“文革”有点站不住脚了,彭德怀也要重新评价了;《甲午风云》更是具有震撼性:“邓大人”可能快要出山了(“政治犯”中也有对“批邓”不满入狱的);放《林家铺子》知道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又快成为文艺红线了……政治是个谜,时时放出些微信息让大家“猜一猜,谁来吃晚餐”。这真是一种益智活动,连监狱的犯人也能半公开地参加。
“文革”中拍的“革命电影”特别适合监狱中放映,因为影片中一律孤男寡女,不食人间烟火,不会引起犯人的遐想,有利于思想改造。因此,我想,当时积极提倡的“为工农兵服务”,似乎也没忘了犯人,也是为犯人服务。可是“文革”前的影片中还是有点爱情内容的,尽管这已经是革命+爱情,或劳动+爱情了,最不济也是爱情不忘革命、爱情不忘劳动,与现在拍的爱情片根本不是一回事。但就是剂量甚微的爱情也有副作用,足以使一些定力不足者心动。
有一次放完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是一部歌颂“大跃进”农民改天换地的影片。其中女主人公孔淑贞,很是抢眼。第二天一早在三角院洗脸时,碰到大老黑,他拿着一块新的花毛巾擦他那张黑脸,因为对比鲜明,我不禁赞叹:“真花啊!”大老黑用手拍着毛巾说:“知道吗?孔淑贞给的!”我笑了说:“你真是至死不悟啊!”他的案子在北京很有名。大老黑本是某工厂的书记,当过兵,去过朝鲜,为人嘻嘻哈哈,很豪爽,很有人缘。家在河北农村,独居北京,平时与工人打成一片,没大没小,偶尔失足,与食堂女炊事员发生关系。1970年代的北京“备战备荒”,挖了许多地道,这位女炊事员常值夜班,卖完夜宵后,常常从地道溜进老黑的办公室,宵入晨出,“来非空言去绝踪”,很是秘密,真是“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后来,终于被女炊事员的电工男友知道了,气愤异常,要去捉奸。老黑在厂里的耳目多,马上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老黑把电灯的火线接到门把上,想电来人一下。没想到那天恰好下雨,电工怕穿胶鞋出声,光着脚板,提着鞋去捉奸,一拉门把,陡然中电,因无防备,猝然摔倒。老黑知道出事,抱着电工抢救,不治而死。最后老黑被判“死缓”。老黑劳动好,乐于助人,又由于当时判得有些重,缓刑期满直接改为18年(一般是改为无期),不久又减两年。是不是女炊事员就是他的孔淑贞呢?没有探究过。
(选自《王学泰自选集:岁月留声》/王学泰 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9月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