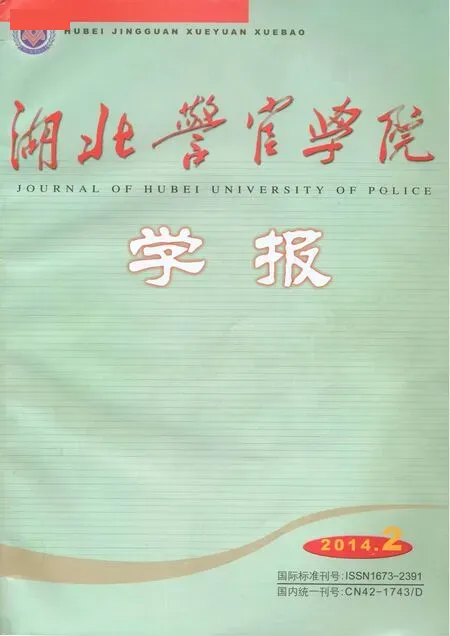中国普法教育走向何处
——“受众”视角下普法教育的内在路径
2014-04-07张昊骏
张昊骏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中国普法教育走向何处
——“受众”视角下普法教育的内在路径
张昊骏
(广西大学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我国28年来的普法运动成果显著,随着普法教育的不断推进,主体间的矛盾也不断凸显,普法教育的形式亟待丰富。受众视角下的普法教育路径应当从政府主导逐步过渡到公民主体,用法律信念支撑公民自觉参与法治社会的建设。
普法教育;内在路径;受众
一、引言:普法教育从何而来
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大项立法已经基本完成,而今后一段时期的主要任务便是对法律科学地适用。而法律素质作为法律适用中的关键因素,它的提高离不开法律知识的普及。法律素质是一种公民所具备的法律意识、法律知识和适用法律能力等综合性素质,是人们成为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
普法是中外法制发展领域中的一次壮举。自“一五”普法开始,我国的普法教育逐渐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实施、人大监督、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这种由国家主导的全民普法教育历经近三十年的积淀,使我国的法律制度得到了广泛宣传普及,广大受众的法律素质也得以提高,人们逐渐树立了“社会应依法管理”的意识,有效地提高了全民法律意识。通过普法,也为法治建设奠定了普遍的认识基础。不得不说,政府主导式的普法教育,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在短时间内覆盖目标区域并达到立竿见影、呼谷传响的效果。
2011年拉开的“六五”普法大幕标志着普法教育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从最初的“扫除法盲”到“用法维权”,从单纯的宣教到全方位的参与,这项系统工程正在改变亿万人民的生活。有学者认为,“立足于现实条件,着眼于现实需要,服务于法制建设发展,向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进行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是二十多年来普法工作的基本经验。”[1]这里所呈现的向上趋势肯定了普法教育带来的正面意义。但是,普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人们“知法”的目的,但却与公民“守法”的预期目的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二、普法教育中被忽略的问题
有学者将普法教育定义为一项“运动”,“是一种不期然间意在将当下中国整合为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动员,一种表现为法权主义努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构,也是一次民族心智的现代洗礼。”[2]早先,我国法制并不健全,公民法律素质亟需提升,这种政府发动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但随着普法的渐次推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一)“政府—受众”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政府主导的普法教育在角色设定时就有弊病,如客观层面的“双重身份”问题。在推动实施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作为普法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和推动者,广大的领导干部又成为“重点普法的对象”。想让普法教育健康的运作就要杜绝一身二任的情况,因为官员在角色认知中认为自己制定政策,是推动普法的主体,凭借这种天然的优势反而成为更好规避的借口。公众会认为,“法律对自己来说完全是一个外物或异己的东西,它不是自己的生活需要而是社会强加的,其目的是限制和束缚自己,自己对法律的遵守是被迫而不得已的行为。因此他时刻想到的便是远离、规避和拒斥法律”。[3]就现实情况而言,如果政府行政权力的具体执行者——行政工作人员,一旦因为自身行为问题而受到法律的追究,政府的威信便会打折。
“受众”一词源于传播学领域,是“传播过程或传播活动中信息的接受者或受传者,是读者、听众和观众的统称。”[4]我们习惯性地将普法教育的“受众”称之为“对象”。但笔者认为“普法对象”的说法有待商榷,因为这不利于普法受众自觉性主体地位的确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认为,主体之间是存在差异性的,而要弥合主体间的差异,理解、交往和对话则是基本的方式。普法教育是一种以宣传法律信息为主的传播活动,为了达成预期的传播效果,传播方与接受方必然是互构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传递者主宰的对象,不能将双方对立起来,故称接受方的参与者为受众更具合理性。如果区分重点群体与一般群体,则会使动用的公共资源不能得到平衡利用,为普法教育消极地创设了空白地带。
(二)普法教育推广形式之缺陷
普法教育的推广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普法教育能否落到实处,影响着普法受众的实际认知效果。有学者将普法教育的推广形式总结为六个字“编(编印法制宣传教育资料)、讲(法制讲座)、摆(摆摊搞法律咨询)、演(法制文艺演出)、考(法律知识考试)、评(优秀或先进评比)”[5]。而这些普法教育形式很少注重普法的群体需求,宣传手段比较单调枯燥,缺少灵活性和生动性。如“三五”普法,当时笔者所在地的学校组织的普法教育主要是通过建立“警—校”联系模式,即每所学校都由附近的公安局或派出所的负责人担任学校的“法制校长”,定期安排警务人员讲青少年犯罪问题,狱中的服刑人员也到学校为学生讲述自己惨痛的教训,让青少年引以为戒。这种模式虽然让学生知道了“杀人抢劫犯法”,但是并未教给他们如何去尊重生命和维护权利,而是对法律产生了深深的畏惧感。其实,这种方式在全国的中小学也不乏少数,青少年因其认知水平不足,现身说法式的教育方式悄然增加了青少年群体与法律的疏离感。无论是从法律知识获得的角度,还是从法律意识培养的角度,这样的形式都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
法律素质的教育不是形式化的走马观花,而应通过终身教育的方式来影响一个人。法国教育家保罗·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6]所以,我们不应把普法教育的时间仅限于青少年时代,而应该贯穿于一生;不应该将场所限于学校,而应该扩展到社会。
三、反思:普法教育该走向何处
古语云:“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对人类精神活动而言,没有反思就没有理性。随着“六五”普法大幕的拉开,我们的反思不仅可以为进一步提升公民法律素质提供理论支撑,也能为政府的后续决策提供参考。
(一)淡化政府主导的角色意识,扩大公民主体性参与方式
从“公民”概念的发展历史来看,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人的世俗性充分解放,重要性空前提高,个体性逐渐张扬,终于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完成了由“文字到目标”的基本转化,人们表现出的对参与国家事务的渴望,对法律的遵守使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本身就带有守法的意义。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只有强调这层含义,才能确立普法受众从“人民”到“公民”身份转变的意识。只有确立了主体性地位,才能提高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我们希望看到,公众对普法教育的参与不再仅仅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因此,只有受众角色发生转变,才能让普法教育走得更远。
通过法律来限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却又在最基础的普法教育层面上,把实现这种限制的希望寄托于国家权力的运作者。这成为一个国家权力运作的悖论。在理想状态下,权力与权利应该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具体而言,我们应逐渐弱化政府在普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完善非政府组织(NGO),使普法教育常态化。当前,公益性法律组织主要集中在维权领域,如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等,但是在普法教育行动中却鲜有相关机构的身影,主要是由高校的研究中心来承担。的确,现实情况不容乐观,国内或缺乏相应组织,或刚刚起步,尚不能承担全国范围内普法教育的重任。但是,举旗不定不如迈步前行,公益组织的尝试性举措能否为普法教育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值得期待。
(二)让法律信念成为从“知法”到“用法”的航标
当然,我们也可喜地看到,从“一五”到“六五”普法的纲要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政府层面越来越重视“法治”的意义,宣传教育的手段也越来越贴近人们的真实生活。“以人为本”已经被作为指导原则而适用,多渠道、全方位的普法教育新途径也将不断开拓。
当然,知法的程度越高,守法的可能性就越大。通过对法律的认同、内化和升华建立起法律信念,只有在支配了受众的日常行动选择,不去做违法的事,才达到了守法的目的。公民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并不是法律知识增加那样简单,普及到大多数人的还是法律法规之类的条文,这种法律认知水平的提高为集体认同提供了一个前提——只有社会成员对其了解到的法律产生了确信的信念,才有可能做到守法。核心的前提还在于对法律的理性认同,简单地说,就是法律信念。法治是规则之治,这要求人们应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意识。基于此,法律信念比法律信仰更加客观,保持了法律应有的本色。
如果将“六五”普法理解为一个单纯静态的宣传式教育,那么这种“应声式”的法律普及便是一具空有皮相,没有血肉和灵魂的躯壳,我们动用公共资源所做的努力或许也将变成“无用功”。而法律信念的树立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动态过程,不应仅仅推进知识量的增加,而更应注重法治意识的培养。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浸淫,让法律把公平正义的体验送达给全体公民,使法治成为公民的自觉选择。
[1]施英.为“法治”铺路——二十年普法回顾与瞻望[J].中国人大,20 06(9).
[2]许章润.普法运动[J].读书,2008(1).
[3]姚建宗.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 (2).
[4]刘燕南,史利.国际传播受众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8.
[5]梅义征.当前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历史方位及推进方式研究[J].中国司法,2009(9).
[6][法]保尔·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16.
D90
A
1673―2391(2014)02―0070―02
2013-08-26责任编校: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