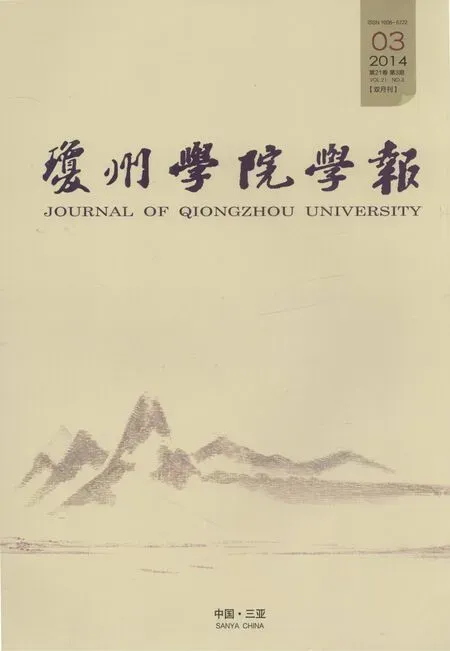胡应麟《四部正讹》的成书原因探析
2014-04-07赵玉萍
赵玉萍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胡应麟,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别号石羊生,兰溪县城北隅(即今浙江省金华县东北)人,明代中叶著名的文献学家和文学家。胡应麟终其一生以读书为业,除偶尔短暂的出游外,皆常年侍亲左右。其性情淡名薄利,唯嗜书如狂,在文学、史学、文献学方面皆有建树,尤以古籍文献辨伪成就突出。《四部正讹》正是其在辨伪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四部正讹》的成书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学术发展演变及胡应麟本人的治学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
一、社会背景所需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并成为学术主流,对明代学术影响至深。由于“心学”思想的泛滥,“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1]1063。终日空谈心性成了很多学者的为学之道,渐渐便形成了一种虚妄的学风。“心外无理”是心学的重要主张,他们注重反观己心,认为世间的万物都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故而多凭己意去注解古代典籍,甚至是篡改伪造古籍,使古代典籍文献的研究陷于主观决断。因而辨伪求实之学成为时代之必要。此外,印刷术发展到明代,技术水平已十分成熟,这为书籍的大量出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自然也使书籍的获得与聚集较之前代变得更为容易。私人著述大量出现,但其中真伪杂陈。如王世贞、杨慎等这样一些大学问者,为支持己见,竟也纷纷采取作伪书的方法以资证明。以致明朝到了万历年间,造作伪书已蔚然成风。“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之第一要义也”[2],清代学者姚际恒如是说。辨伪之于读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胡应麟生活在这样一个空谈心性、作伪成风的学术环境之中,本着求真求实做学问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他意识到从事古籍的去伪存真、抉诬摘伪是件亟待去做的治学之大事,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读书治学,而且也会影响到整个学术的发展。这是胡应麟著写《四部正讹》的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是其成书的客观原因。
二、辨伪学发展使然
中国自先秦开始,便有了疑古思想。为了求真求实,学者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疑古思想用于书籍的真伪辨别上。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所标出的“似依托”等零星辨伪之始,其后马融从文字、内容等方面考订论证《泰誓》之伪;之后由于战乱,朝代更替频繁,书籍的大量散佚与焚毁,新一朝代建立之始的悬赏搜集,形成了魏晋南北朝那个“造伪甚于辨伪”的时期,最为有名的莫过于这一时期王肃的古书伪造,于是到隋唐时一股辨伪风气盛行,如刘知几的疑古惑经,啖助、赵匡对春秋三传的考辨,柳宗元对诸子及其他古籍的考辨等等;至宋,学者以疑古思想审视先前典籍(突出表现在对经学的怀疑)。然而这些辨伪学者,只是在笔记或文集中出现少些零星的辨伪语句,并没有专著进行有系统的辨伪方法总结。朱熹曾有过专著这样一部书的想法,但很遗憾最后并没有著出。后来,元末明初的宋濂,著有《诸子辨》一卷,在此书中他对先秦至宋的四十多种子书真伪进行了考辨,不过宋濂在辨别伪书之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评判诸子思想的标准,是为了“卫道”之需,因而从他的目的性来看,这也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为辨伪而辨伪”的著作。至明代,胡应麟的辨伪工作开始有意识地在这些先贤们片段零星的方法基础上,进行辨伪经验的总结,既而结合自己平时的读书所见,提出了一整套相对系统严密的辨别伪书方法,为《四部正讹》的成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借鉴经验。它的成书,也是历代辨伪学术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不断积累而成的结果。
三、自身条件保证
《四部正讹》的成书,除了上述客观社会因素和学术发展因素所决定的必需性外,与胡应麟自身的学术积累、丰富藏书等自身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更有着莫大关系。
胡应麟藏书之富是其辨伪学取得如此成就而必不可少的坚实物质基础。胡应麟嗜书,在他的生活中,购书、藏书、读书是最大的爱好。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他曾自白道:“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诵之可以当韶頀,览之可以当夷施,忧藉以释,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3]33书籍在他这里成了无所不能的至宝,是自己此生安身于世的重要精神支柱。王世贞道:“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日俸不给,则脱妇簪珥而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宋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赀以治屋而藏焉。”[3]33由此可见其嗜书欲狂之状。由于胡应麟终其一生并未出仕,财物不免拮据,买书需求不能时时得愿,故而借书、抄书也是其藏书的重要来源。王世贞在《石羊生小传》中云:“元瑞自髫鬐厌薄荣利,余子女、玉帛、声色、狗马、服玩诸好,一切泊然,而独其嗜书籍自天性。身先后所购经、史、子、集四万余卷,手钞集录几十之三。”[4]序此外,因机缘低价购得义乌藏书大家虞守愚之藏书,对其存书量的扩充占了很大比例。关于胡氏藏书数量,在王世贞为他所作的《二酉山房记》中这样记载:“所藏之书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经……合之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5]其实,他的藏书应不止此数,在王世贞作此篇之后至胡应麟殁时的十多年里,以胡应麟嗜书之状,收藏之书必然会不断增多。如此丰富浩瀚的藏书,使胡应麟能够接触大量著作以及著作不同的版本,这是从事读书辨伪工作十分重要的先决物质条件。
胡应麟藏书不是为有附庸风雅的谈资,或是“为藏书而藏书”的装点门面,而是作为实际的读书治学之用,“书之为用,枕籍揽观”“夫书聚而弗读,犹亡聚也”[3]70,这是他对藏书的态度。胡应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在给王世贞的信中,他曾陈其心迹志向曰:“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4]卷一一一在《弇州四部续稿》中,王世贞也曾称赞他:“元瑞于书,聚而读之,几尽矣。”[3]35常日发奋读书沉浸于典籍之时,广博览读,勤思善疑,“有概于心,则书片楮投箧中”[3]166,笔耕不辍。在考辨伪书工作中严谨审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惟其是而已”的考证精神,是其从事辨伪工作及后来《四部正讹》成书所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从而做到“真其所真,伪其所伪,使真伪各得其用,此吾辈读书应有之态度,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6]张舜徽先生曾经对胡氏的治学精神做了高度评价,“一生博极群书,各有撰述。论皆有据,语无虚发,学者叹其精审!”[7]
再者,胡应麟自幼喜读杨慎之书,然而,杨慎喜爱造作伪书以证己之所持论述,从而从反面上为他在辨伪学方向发展提供了学术启蒙,也为之后《四部正讹》的完成提供了辨伪实践的经验总结基础。杨慎,明代中叶以博学闻名于世,胡应麟对他的学识钦慕之至。“余少癖用修书,求之未尽获,已稍稍获,又病未能悉获。其盛行于世而人尤诵习,无若《艺林伐山》等十数编,则不佞录丹铅外,以次卒业焉。”[3]258由此可见,杨慎著作对胡应麟的影响是颇大的。但是,正如《四库总目》中所评价的,杨慎的著作,“至于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1]1502杨慎不只是在考证方面不力行查实所引,更甚的是,故意伪造古籍以证明自己所持之说,在当时就被一些如陈耀文等学者所诟病,陈耀文所作《正杨》在纠正杨慎讹误之处的确功不可没,但是“其兢心独胜,意气用事,哄然纠驳,态度极不公正,虽不必‘不免为前人所笑’。”[1]1026鉴于陈《正杨》一书的尚不完备,加之对杨慎学识的仰慕及由此而产生的爱护之情,使得胡应麟决心以客观严正、严谨求实的态度来纠正杨慎之失,从而让后人对杨慎之学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在客观上也为胡应麟辨伪方法的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料,有利于著作《四部正讹》时辨伪方法理论性的概括。
小 结
《四部正讹》的成书是辨伪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是中国首次有系统、规律性的文献辨伪方法总结。在书中,胡应麟对伪书考辨的范围扩展到了四部。对历来伪书出现的原因做了具体详细的分类与总结。其后民国时期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古书真伪及年代》中所论,很多基本上是和胡应麟相同的,并无多少超出胡应麟归纳的地方。因此我们基本可以说胡氏对伪书各种情状的分类为后世的辨伪学树下了一个范本。他还结合自己辨伪的实践,提出著名的“辨伪八法”。这在中国文献辨伪学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此外,在对待伪书的态度上,并不是简单的一概否决,关于如何利用伪书的价值,他又根据具体的情况做了具体的讨论。这些提议都是十分宝贵的。
《四部正讹》作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辨伪学的专著,它的成书,是在前贤繁碎辨伪实践发展到一定成熟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加之杨慎治学的部分影响因素,然而群书的广博饱览与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是胡应麟能够完成这部辨伪著作的关键因素。
[1][清]永溶,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3][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O].续金华丛书民国十三年永康胡氏梦选楼刊本.
[5]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序[M].济南:齐鲁书社,1980.
[6]张舜徽.爱晚庐随笔[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