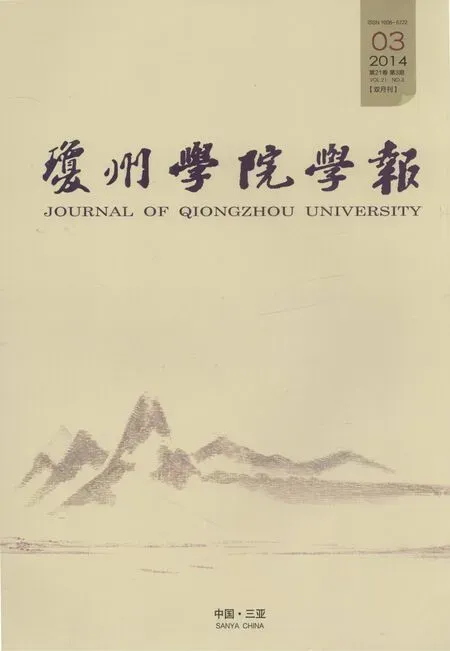宇文所安五言诗论——以《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蓝本
2014-04-07李明华胡良萍
李明华,胡良萍
(琼州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海南 三亚572022)
从古至今,对于五言诗的起源与成熟的论断由于学者对史料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见解。目前文学史上关于五言古诗来源最主流的说法是“东汉说”。五言诗歌是否真的起源于东汉,或是更早的时期,亦或是东汉之后的另一个时期。我们还不得而知,学术界的学者们还在探索中前行。
其中,宇文先生和木斋先生对古诗的起源及其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新的探讨,产生了对传统文学史约定俗成的对古诗起源及其形成和发展观点的质疑,并结合史料分析研究,从而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在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和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这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后,就像是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使得传统的五言诗起源于“东汉说”的观点面临重组或解构的挑战。与时代传统主流观点相悖的观点总会饱受争议,但同时新旧观点的碰撞、融合才会促进传统观点的发展。宇文所安关于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生成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研究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本文就以宇文所安先生的新作《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为蓝本,讨论宇文所安对五言诗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宇文所安所著《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并非简单的研究诗歌的体裁和作者的问题,而是深入的探究诗歌是借鉴哪些材料并通过何种方式创作而成的。此外,作者在书中还辨证的分析了这些出现在公元二世纪后半期的修辞等级低俗的古典诗歌是如何被保存下来的。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有关古诗的教材,教师们教授的有关古诗的知识,以及我们对古诗的论断和认识,似乎都是不变的真理,很少有人会对它们产生怀疑。就算有过一丝的怀疑,却也没有想要打破这一知识体系的想法。但宇文所安却对这稳定的知识体系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宇文所安对所谓“汉魏”诗歌的质疑
“我们通常认定我们所读的是“汉魏”诗歌,但我们实际上是无法直接接触到那些所谓‘汉魏’诗歌的。”[1]9“我们对于早期古典诗歌直到三世纪晚期的理解,是经由两个世纪之后一个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时代的中介而得到的。”[1]27这一中介便是五世纪末六世纪初那一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孜孜不倦地对早期的诗歌进行修订、保存、确定作者归属并以此来给诗歌进行排序,以及给诗歌编史。多亏了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才对“汉魏”诗歌有所了解。但是宇文所安抱着谨慎的态度对早期中古文学史进行反思后,对现存的所谓“汉魏”产生了质疑。因为,我们不知道的是,在三世纪晚期到五世纪末六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诗歌在流传的过程是否原封不变地被保存下来,或者是因为编者们的个人原因或受到了某一时代的成规的制约而产生变化。并且我们普通人在接触阅读“汉魏”诗歌时,也不会对其真实度进行怀疑,尽管有过怀疑,也不会对其进行过多地探讨研究。
(一)手抄文本
就“汉魏”诗歌真实度这一问题,宇文所安认为,现存的来自手抄文本的文学体系并非其最原始的形态。他首先把目光放在了早期抄写者和编者,以及他们所处的抄本文化时代。从遗留下来的文本可以看出,当时编者和抄手们对于文本的复制的精确度并不是很在意。“因为手抄文本具有随意性,抄手们在编辑和抄写文本的过程中,会依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地对文本进行修改。或者是在抄写的过程中依照其所处时代的审美情况来对诗歌进行抄写保存。由于是人为的操作,在抄写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错字、漏字、借字、衍文等情况。”[1]29此外,“还有问题太多、意义难通以至于根本无法标点的文本”[1]67。
“我们不知道那些手抄本的抄写质量究竟如何。梁代僧人僧佑曾经向我们证实了他阅读佛经写本是如何的凌乱不堪。”[1]5并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同一资料的来源越多,那么它遗留下来的异文也就越多。“我们看到无数异文,看到一个文本以多种不同的‘版本’存在。增减几个对句,或使用不同的诗行,似乎都是家常便饭,不仅后期的抄本如此,六世纪之前的文本传统也同样如此。”[1]65同一种诗歌出现了不同的版本。“我们浏览一下隋志即可发现,文集的卷数和题目都会经常发生变化;这种情况正如僧佑在整理佛经文本书所言,‘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1]31这时,我们也就不能确定哪一个才是“原本”。
“钟嵘在《诗品》中提到提到的五十九首‘古诗’显然大部分不符合六世纪初人们对于‘古诗’所持的观点和标准”[1]42,并且“在钟嵘的心里,对于古诗应该是何模样有了自己的见解和标准,所以他在选编作品时,会依据自己的爱好和当时社会对‘古诗’所持的观念和标准来对诗歌进行取舍和品级”[1]42。所以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诗歌被钟嵘淘汰掉了。“大概没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说明我们现有的‘早期诗歌’是按照某种特殊的标准从一大堆材料中挑选出来的,打上了从事挑选的时代所特有的文化观和历史观的烙印。”[1]42
此外,“萧统在处理有问题的作品时,总的来说还是很谨慎的,他没有收录那些质量低劣但是可以确信为东汉时期的五言作品”[1]60,然而,“徐陵在编纂《玉台新咏》时觉得并没有谨慎行事的必要。他编纂这部诗集是为了阅读的愉悦”[1]60。
“他们按照自己心目中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意识对其加以挑选,有时甚至是改写”[1]44,尽管现有的关于早期诗歌的文本是经过挑选的,但它们还是可以代表早期诗歌的,只是它们的文本形式和写作年代和作者还有待商讨。
此外,“编者和抄手们在抄录文本有时不是很细心,而且往往只是给出片段和节录,目的只是提供适合他们需要的范例。但同时,这些材料却没有像那些被编辑整理多中介过的文本那样,动辄收到‘校正’”[1]68-69,“我们知道当时的学者会订正写本中的错误,但是一个六世纪学者所认为的‘错误’对二十一世纪的学者来说有可能是价值连城的证据”[1]7。到了近代,“这类‘校正’通常会被编校者小心地标注出来,但我们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在印刷文化初期,编选者们对其认为错误的地方往往根据自己的想法加以改正,却不加注明”[1]69。所以我们不清楚,编者和抄手们在抄录文本的时候,对哪些地方做了改动和删减。
早期的诗歌除了通过手抄文本进行传播,有时也通过口头传播。同样的,这种传播方式同样具有随意性。
再者,“在西晋沦陷和北宋印刷文化兴起之间,皇家的藏书机构遭受过一次又一次的损毁”[1]32。书籍遭受了的损坏或遗失,使得我们必须从其他的渠道来重新收集文本。而这些渠道收集来的文本可信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二)编写者们是怎样来对诗歌进行排序
接下来,我们在来看看编者们是如何对诗歌进行排序的。书中,宇文所安用“恐白”一词来形容人们对于五言诗历史的态度。所谓的空白,是因为害怕空白,所以想法设法的去填补。由于五言诗的历史太过于单薄,而为了填补五言诗历史中的空白,出现了把诗歌安放在知名作者之下,然后并以作者的所处的年代来给诗歌进行排序的现象。而这种做法并没有事实作为有力的证据。“人们觉得某一特定的历史人物很适合于做某首诗中的主人公,以至于二者之间的转化不知不觉就完成了”。[1]51
“无论是《诗品》《文选》《文心雕龙》,还是《玉台新咏》都是按照作者的年代的先后顺序来给诗歌进行排序的。”[1]43
既然是以作者的先后顺序来个诗歌进行排序,那么首先就要为诗歌确定作者。但是这时编写者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对于无名的古诗文本,它们到底应该是放在有名的诗作之前还是之后呢?这时他们就会以常理来判断,无名“古诗”的写作年代会比有名有姓的作者的作品要早。
第一部完整的对五言诗史进行叙述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其中也包含了五言诗的起源。“刘勰认为五言诗起源于《诗经》。并且他对于系于班婕妤和李陵名下的诗作归属产生了质疑。他也提到了枚乘,我们看到了之前未有的一种说法,刘勰把“古诗”归于枚乘名下,并把他们排序在李陵之前。”[1]53刘勰做出这么个排序,似乎遵循的是:无名“古诗”产生的年代早于那些有作者归属的诗作。为了给无名“古诗”找到作者,他着眼于早期西汉著名文人。经过一番推测之后发现枚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文心雕龙》一书中,很多早期的作者都被提及到,但是刘勰本人并没有明确地说明这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以自己之口来陈诉他人的观点。刘勰也书中也明确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两汉之作也/乎”。但这一观点容易造成歧义。这句话既可以作为肯定的理解,也可以作为不确定的理解。也有一种可能是刘勰本人对于“古诗”早期断代的不确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继《文心雕龙》之后出现的又一对五言诗的起源做了重要叙述的作品——钟嵘《诗品》。与刘勰意见不同的是,“钟嵘对于署名班婕妤和李陵的诗作确信无疑。并且明确的指出无名‘古诗’是汉代的作品,而且大概是西汉之作,并且引述了这些来自汉代的‘古诗’作品出自曹氏父子和王粲之手”[1]57。由于五言诗的历史实在单薄。为了凑数,钟嵘把西汉末年的郦炎和赵壹的诗作也收录进来,尽管两人的诗作质朴而少文采,但为了填补五言诗史的大部分空白,对于钟嵘来说,作此决定也是别无选择的。此外,钟嵘也选取了班固的一首五言诗《咏史》取代了张衡的四言诗《怨诗》来代表东汉。
“刘勰和钟嵘在对于五言诗史的叙述产生了真正的分歧是在建安之后。在刘勰看来,建安是诗歌衰弱的时期,并且西晋的情况更为糟糕。而唯一能在这糟糕情境下使诗歌产生一丝亮色的是嵇康和阮籍的作品。与刘勰不同的是,钟嵘认为汉魏时期诗歌开始衰微,但是西晋却是诗歌兴盛的开始。”[1]58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五言诗的历史存在着大片的空白,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文人学者和批评家们便想尽办法来填补这一空白。空白消失了,但是把诗作和作者名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并没有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而是编者们心甘情愿做出的推测罢了。
(三)拟古诗作
“最早对古诗十九首进行模拟的人是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后期的陆机。对于‘古诗’表现出的赞赏和喜爱,使得陆机对其进行模拟。对‘古诗’的模拟在五世纪的时候发生了变化,诗人们有‘心机’的在模拟的过程中注意修辞的使用,并加入了典故,这使得模拟出的诗歌变得更加典雅。书中,宇文所安列举了谢灵运模拟王粲大概写于二世纪,题为“七哀诗”中一组作品的第一首来加以对比。”[1]38-39从谢灵运的拟作与王粲的原作对比,谢灵运在拟作中加入了典故,并且也更注重修辞的使用。
随着模拟早期诗歌进行创作这一文化风气的发展,“诗人对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之间的差异有了更清楚的认识”[1]39。正如“江淹指出:读者不应只根据自身所处时代的标准作出判断,而必须对于审美情趣的变化和差异抱有理解和同情”[1]46。“他要求读者应能够欣赏和理解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诗歌,而不要作出‘彼优此劣’这样缺乏历史精神的价值判断。”[1]46
“在不断发展和增多的拟作中,大部分是对特定作者的仿真。那么,编者们在给诗歌进行排序的时候是依照其模拟的特定的作者所处的时代来给诗歌排序。”[1]39正如钟嵘所说,“是拟作引起了人们对原作的注意,是原作变得更加引人瞩目”[1]41。
“虽然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作者们早于齐梁文人两个到三个世纪,可是这一诗歌在同样程度上也是起齐梁的创造。齐梁的文人在某些情况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比较近期的诗歌置于较早的时期,用以补充早期诗歌的总体数量。”[1]4“以前的五言诗作少得可怜,现在却一下子多出了许多——其中似乎不少是近代的拟作,是一个诗歌极大丰富的时代对一个诗歌短缺的时代做出的慷慨捐赠,……空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典’。”[1]60-61
手抄文本和口头传播的主观随意性,诗作保存的成规性,诗歌排序的不确定性,诗歌资料来源的多渠道,拟古诗的成熟发展等这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我们无法确定我们所接触的“汉魏”诗歌是否是真正的“汉魏”诗歌。
二、关于无名“古诗”写作年代的思考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纪的猜测之外——表明无名‘古诗’的年代早于建安的确凿证据。”[1]26
(一)“古诗”一词所指
“古诗”二字最早指的是《诗经》中的诗篇。但在陆云给其兄弟陆机的一封信中我们看到了对于“古诗”一词的另一种说法,“‘古诗’即‘古五言诗’”[2]135。但这种说法有可能是建立在与当前的诗作作比较的基础上而得来的,所以我们还不能很肯定地说,“古诗”就是“古五言诗”。
(二)五言“古诗”的来源
书中,宇文所安引述了《汉书》中戚夫人的歌,列举了《汉书》中街陌谣讴、关于“臭名昭著的赵飞燕姐妹”的诗还有一首“据说是语言王莽篡汉”的诗歌。从以上列举的诗歌我们唯一可知的是,“五言句式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已经被人使用,当时是和低微的社会低微联系在一起的”[1]73。
“在西汉晚期已经有了固定节奏的五言诗句,但是在可确信为西汉的作品中,并没有使用“古诗”的文体形式。”[3]175-176此外,约瑟夫·阿伦在《以他者的声音:乐府诗研究》中认为,将“古诗”归于汉代纯属假设。这只是编者们的推断,而这些推断并没有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撑,经受不住不是“古诗”不归属于汉代的考验。[1]26
那么,“古诗”一词是何时被大众所知晓的呢?《世说新语》中有这么一则轶闻: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最佳。”[4]276
我们不能确定这则轶闻叙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但我们可以由此推断出的是,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应该是发生在公元四世纪后期,并且这时“古诗”一词已经被大部分人所共知。尽管“古诗”被大部分人所了解并欣赏,但是它们在诗歌的历史上却没有一个特定的位置。它们不知道产生于什么年代,也不知道作者。它们并不引人瞩目。当“古诗”在五世纪被模拟时,由于修辞层次大大提高,并在诗歌中加入典故,这使得诗歌变得更加的典雅。有可能就像钟嵘所言:“是拟作引起了人们对原作的注意,使原作变得引人瞩目。”[1]41
(三)学者们对于五言古诗来源的探讨
对于五言古诗来源的说法大致有三种:东汉说、西汉说和建安说。较早提出“建安说”的学者是徐中舒。他认为“不论是归为西汉还是东汉的五言诗作,其真实度不能让人信服”。因此,“五言诗的成立,要在建安时代”[5]。此外,木斋也赞同“建安说”。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和这个时代的社会背景、风气是息息相关的。在建安时代,统治者对于诗歌写作的倡导与支持;社会风气的开放,大批的有才者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此外,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注重情景交融,也更注意辞藻的使用。“那些没有主名的所谓古诗,主要都应该是曹植之后的作品,包括《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传为班婕妤的《怨歌行》,也包括一向含混不明的所谓汉魏乐府诗歌中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那些优秀五言诗作品,例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都不是两汉之作。”[6]宇文所安也支持“建安说”。他认为“我们根本找不到任何——除了五世纪的猜测之外——表明无名‘古诗’早于建安的证据”[1]62。学者们对于“古诗”起源于建安之前的推断是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作为支撑的,经不起否定观点的推敲。
给无名“古诗”进行排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编者们所持有的一种信念“相信文学发展从简单到复杂,有质朴发展到典雅”[1]64,“用修辞层次较低的语言风格写成的作品,被认为早于那些修辞层次较高的作品”[1]64。但是“虽然在三世纪社会上层的诗歌创作实践中,诗歌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一个修辞越来越讲究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辞层次较低的诗歌完全被修辞程度较高的诗歌所取代”[1]64。因为“有证据表明,用修辞层次较低的语言写作的诗歌,一直贯穿于整个三世纪的文学写作之中”[1]64。
编者们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编写诗歌史:编写者们在给诗歌进行排序时,会综合分析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以及作者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来确定把诗歌和其可能的作者联系到一起,但是在假设的一切因素中看似完全符合的情况下,却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假借他人之口所做的诗,诗中说话者也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说话,但却不是诗的作者”[1]65。此外,“同一诗歌出现不同版本”这一问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玉台新咏》和郭茂倩《乐府诗集》所引用的材料中,某些文本进行加工,以适应当代的诗歌标准。”[1]65用这些人为主观意念加工过的文本来进行排序,就不可能接近真实。
三、宇文所安对汉魏诗作的具体解读
被收入班固《汉书》里的一首系于李延年名下的五言诗作[1]74-75:“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宇文所安认为,首先,“这首诗化用《诗经·瞻仰》的成句:‘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在《诗经》里,女性的摧残力量还没有成为美貌的同义词。因为这则故事明显在暗示汉武帝对歌曲中《诗经》典故的警告缺乏觉悟,完全有可能是在班固模仿他心中的一人风格编造了这首歌。”[1]73此外,“这首诗中只有第一行用了‘古诗’、乐府中熟悉的程序”[1]74,“并且混合和真正的五言句式(第1、3、4、6句)和加上一个虚词扩展成五言的四言句”[1]74。再者,“这首歌以及《汉书》收录的街陌谣讴里,五言诗中常见的词组和模式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词组和模式在后代五言诗中太习见了,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么这些诗产生在一个这些传统还并不存在的年代,要么它们就是出自一个社会阶层较高、因此不熟悉五言诗传统的作者之手(比如班固)。”[1]74
“大约在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在一篇碑文中看到了这些缺失的传统。”[1]74接下来我们在看看为名为费凤的人写的碑文。在碑文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日期:公元143年。“但是碑文本身可能写于公元二世纪后半叶”[7],诗中有一部分为叙事,文采质朴无华,却“为一些系于曹操名下的乐府提供了先例”[1]74。“但是这首诗既包括了长短多变的句子(这些句子常常是从《诗经》中的成句变形而来的),也包括了在乐府和‘古诗’中常见和经典的程序句。”[1]74比如,碑文中“丹阳有越寇”比较曹操《嵩里行》中“关东有义士”。
具体看下碑文中诗的中间部分,在写到费凤在临死时,我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句子:“不悟奄忽终,藏形而匿影。耕夫释耒耜,桑妇投钩莒。道阻而且长,起坐泪如下。”诗的结尾是这样的:“壹别会无期,相去三千里。绝翰永慷慨,泣下不可止。”在费凤碑诗中,我们看到了与著名乐府《陌上桑》中“耕者忘其犁”一模一样的描写,“表现了耕者对费凤的去世感到悲哀”[1]75。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是一个可以被不断重新表述并用不同语境的‘话题’,无论语境是一个重要人物之死还是一个采桑女的美丽”[1]75。
此外,我们再把这首诗与《古诗十九首》第一首的几句诗做一下对比:“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古诗十九首》中,“相去万余里”与碑文中“相去三千里”相比,“也许最好地显示了费凤碑诗是对五言诗传统的一种‘实现’方式,因为一句本来是描写‘生离’的诗现在用来描述‘死别’,但是非常精确地给出生者和死者之间的距离”[1]76。此外,“在费凤碑诗的结尾,诗人表现完全被悲哀情绪所征服,不能再写下去。这可以说是‘古诗’里面常见的结尾形式”[1]76。但是,在碑文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细节,“诗中的叙述者说他‘绝翰’停下手中的笔——这非常明确地指出向以书写形式进行创作。这是我们在传世的早期诗歌里面看不到的。”[1]76宇文所安把费凤碑诗与“古诗”、乐府作比较,“并非是想说‘古诗’、乐府以及现存的形式一定可以被追溯到公元一世纪或者二世纪,而是为了告诉我们:到二世纪中叶,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系列诗歌常用手法的存在,它们是许多‘古诗’的创作基础。并且同样的手法在整个公元三世纪都一直被人使用。”[1]77
有些作品在确定作者时是依据:“作者未知但似乎适合某个特定历史人物的诗歌”。就比如《古诗十九首》中[1]264-265:“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无乃’即恐怕是,想必一定是。这种论断是依靠直觉来把诗中的叙述者与作者联系到一块,把诗中的叙述者当作诗的作者。”[1]265接下来要分析的一首被系于班婕妤名下的《怨诗》(或怨歌行)同样属于这样一种情况。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首诗:“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恩情中道绝。”班婕妤是汉成帝在没有遇见赵飞燕姐妹之前的宠妃。可能是她对于最终会失宠的一种预见,使她作出了这首诗歌。这预见的时间可能是在失宠之前,也可能是在新宠的时候便开始了。“当皇帝感到‘炎热’时,妃子可以充一时之用,但她意识到他的热情终将冷却(‘秋节至’),她会被弃置一旁。”[1]265因为“这首诗与班婕妤的历史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即使当学者们不再相信班婕妤是这首诗的作者,他们仍然希望这首诗采取了班婕妤的声口,或至少采取了一位受宠妃子的声口。”[1]268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十分的合理。此外,“人们愿意将这首诗读作是宫人的声音,和其中隐含的权利落差很有关系”[1]268。但是,宇文所安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这首诗可能并没有把宫人比作团扇,而就是描写了一把扇子,而在最后一联中把它含蓄地比作宫人。至少从三世纪起,职业诗人就要被要求赋诗咏物”[1]270;并且“班婕妤的诗在早期文献材料中有时被引作《扇诗》或《咏扇》,似可支持这种假设”[1]268。
此外,从中文的语境中来研究这首诗,需要很谨慎的把“作者”和“权威”联系起来。因为在中文的语义里,二者并没有一点联系。“这首诗是以‘团扇’为中心意象展开描写”,“团扇不仅被比作女子,而且还装饰着‘合欢’的图案——合欢代表了情人的聚首,正如团栾的明月(诗中对团扇的一个比喻)也代表团圆和聚首一样。扇子会产生‘微风’,而‘风’也是一个用来指称诗歌与‘讽’——委婉的讽谏(对皇权的讽谏)——的语汇。”[1]269正是由于诗中对于“团扇”的巧妙运用,并且把感情的深度蕴藏在其中,使人们认为这首诗作极大的可能创作于三世纪。
现在我们来看看两首在叙述者上不存在争议的同名长诗——《悲愤诗》。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吗?这两首诗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但却以不同的体裁版本出现。一首是五言诗,另一首是“楚骚”诗。这两首诗都是在真实的历史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叙述者是东汉著名学者和作家蔡邕的女儿蔡琰。这两首诗表现的是在“蔡琰在汉末的战乱中被掠至匈奴,后来被曹操赎回中原,但她不得不将所生的二儿子留在匈奴。在她返回中原之后,发现所有的佳人亲属都已经过世。曹操将她改嫁他人”[1]278的这一时期的故事。对于蔡琰是这两首诗的叙述者的身份,学者们是肯定的。但却在蔡琰是否是这两首诗的作者产生激烈的争议。傅汉思相信这两首《悲愤诗》都不是蔡琰所作,宇文所安也同意这一观点,但这个问题却一直都没有得到确证。
“虽然《悲愤诗》现在已经成为早期诗歌中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而且被所有的选集记录”[1]280,但是在此之前,它却没有得到学者和编者们的欣赏。“两首《悲愤诗》都没有被《文选》或《玉台新咏》收录,《文心雕龙》或《诗品》也没有提到蔡琰。考虑到《后汉书》在当时的易得,和齐梁学者在搜集和评论早期诗歌方面的勤勉,这一缺席意义重大。”[1]279究其原因,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也许这只是出于对长篇叙事诗的偏见,而长篇叙事诗似乎是一个持续不断的通俗传统。”[1]291我们就其中的一首五言《悲愤诗》来进行分析比较。对于这首诗创作时间的上限,我们可以从五言《悲愤诗》的第一句中开头的“汉季”来进行推测。“‘汉季’意味着汉朝已经灭亡,因此也就是在曹操死后。”[1]286五言《悲愤诗》有一段对董卓之乱的描述,我们可以在曹操的《露》中找到相似的诗句:“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悲愤诗》中“汉季失权柄”与“惟汉二十世”相比较,我们可知,诗人们对于在汉代即将灭亡和没灭亡之前的称呼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诗中直捷的叙述风格与其他诗作的比较:“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曹操的《嵩里行》也可以读到类似的句子:“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同样的,我们在费凤碑和《古文苑》中系于孔融名下的一首六言诗中也出现直捷的叙述风格。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五言《悲愤诗》的开头和石崇的一首描写王昭君远嫁匈奴所经历的遭遇的代言诗:“我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诗中,“流畅的风格和‘同情’的意象标志着五言诗发展史上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1]288这首五言《悲愤诗》把五言诗具有的叙事能力这一优点很好的表现出来。诗中,孩子直接与母亲进行对话:“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此外,诗中还叙述了蔡琰与一起被掠去的同伴们的告别;叙述了被赎回后回到家中得知家中亲人都已经去世的消息和如废墟一般的家;同时也叙述了她的再婚以及对于婚后害怕由于自己被掠至匈奴的这一经历而遭遇丈夫的嫌弃。“这首诗用‘古诗’的传统方式结尾,发出‘人生几何时’的感叹,最后以表达悲伤收束全诗。”[1]289
诗中也出现了对诗句的变体的句子:“回路险而阻”和《古诗十九首》中的第一首“道路阻且长”;“悠悠三千里”与费凤碑“想去三千里”(也可以对比《古诗十九首》第一首中“相去万余里”);“何时复交会?”与《古诗十九首》第一首中“会面安可知?”[1]290。
在五世纪早期,一组关于离别的诗作被系于李陵名下。而把李陵和这组诗作联系在一起的依据是《汉书》中记载了李陵与苏武相见与离别的场景。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可信的证据表明,这组诗作与作者的联系。
“在《隋书·经籍志》记录了一部两卷本的《李陵集》。”[1]292对于李陵是这组诗作的作者这一说法当时大家并不是很认同。并且刘宋最早对这本集子的真伪提出质疑,“他称其‘总杂’而且怀疑它是‘假托’,但他并未全盘否定每一首诗(‘非尽陵制’)。”[1]292“李陵的作者身份被大家普遍接受是在五世纪末和六世纪头四十年这一关键的时期。”[1]292
宇文所安显然也不赞同李陵诗作的归属,他认为,按照常理进行判断,一个人在同一个场景创作了两卷诗是荒谬的,并且,就算李陵真的就在同一个场景一首诗歌接一首诗歌的创作,那么作为收件人和写信人的苏武对于这一不断重复的现状不会感到厌烦吗?
接下来我们看看在《玉台新咏》中收录了秦嘉和他妻子徐淑之间的赠答诗。宇文所安认为,这三首赠诗和一首答诗“产生的时间不早于五世纪下半期,而秦嘉的诗可能不会早于梁初。”[1]300
宇文所安之所以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第一,通过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离别的场景。但是,这三首赠诗和一首答诗中所描绘的故事在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后汉书》没有提到秦嘉,如果他们的往来信件和诗歌在五世纪中期已经广为流传,很难想象范晔会遗忘他和叙述,因为范晔特别喜欢这种能够激发读者情感的场合和事件。”[1]300第二,“江淹在五世纪晚期模拟的诗作组诗中没有模拟秦嘉和叙述的诗,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拟徐淑的诗,因为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五言诗;但是他如果见过秦嘉的诗,应该一定会有模拟之作。”[1]300此外,钟嵘在《诗品》中也曾经提到过徐淑的这首答诗,宇文所安据此推测:“在六世纪早期,人们已经知道秦嘉任‘郡上计’之职,他的妻子在娘家病重,无法送他离开。这些情况可以从徐淑的书信和诗中得知。徐淑的诗是一首答诗,因此需要与之对应的‘赠诗’,这些‘赠诗’显然在六世纪前半期被发现或被提供——从而大大增加了东汉五言诗的数量。”[1]300
我们可以从秦嘉的第一首赠诗中得出,“至少有一封徐淑的信在这首诗写作的时候已经存在”[1]303。宇文所安认为,是先有徐淑的答诗,之后为了填补与徐淑答诗的空白,对应的赠诗才出现。而我们也不能确定的是,系于秦嘉名下的这三首赠诗是以秦嘉之名的代作还是齐梁的学者们依据诗歌史的叙事而把它们系于秦嘉名下。并且,齐梁学者在对早期诗歌进行编排整理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对早期诗歌中,他们认为不满意的地方进行修改。
班固《咏史》这首诗讲述的是缇萦为救父上书皇上,自愿为父亲甘受刑罚的举动感动了皇上,并释放了她的父亲的故事。(原诗略)这首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确定在班固名下,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梁代的选集和隋唐类书并没有把这首诗收录其中。钟嵘对这首诗的描述是“有感叹之词”。宇文所安假定,如果这首诗是后来才被确定在班固名下的,那么这首诗是为什么被按上班固的名字的呢?结合钟嵘对这首诗的描述,我们可以找到答案,这首诗之所以被系于班固名下是因为班固对于历史上所发生的相似的事件与自己所遭遇的事情之间的撞击有感而发。“班固死于狱中,而他有一个入宫为妃的妹妹。”[1]306他是在借着这一事件来哀叹自己的命运。
结 语
当今这个时代,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是需要勇气的,并且这一见解是与主流思想相异的有价值的独特见解更值得鼓励。在新思想与传统的主流思想碰撞的瞬间,或许一时之间让大家难以接受,但是,这对于我们学术的研究是有推动作用的。宇文多按所提出了有关五言诗的新观点对于诗歌的研究史是具有很大意义的。他不仅为诗歌史的研究注入了一股新泉,给予的学者们反思,同时,也给读者们带来了新的看点。
[1][美]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北京:三联书店,2012.
[2][晋]陆云.陆云集[M].黄葵,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35.
[3]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75-176.
[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76.
[5]徐中舒.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J].东方杂志,1988,24(1):18.
[6]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反思[J].社会科学研究,2012(2):54-66.
[7][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逯钦立,编.北京:世界书局,1963:1120-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