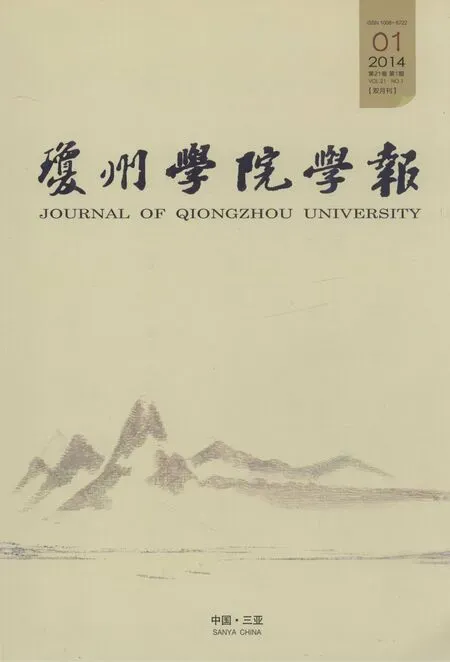骑在马背上的黑奴——浅析“陌生化”理论在电影《被解救的姜戈》中的运用
2014-04-07陈梦
陈 梦
(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一、导言
《被解救的姜戈》(以下简称《姜戈》)是“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继《低俗小说》、《无耻混蛋》等的又一力作。该片长达165 分钟,气势如史诗般恢宏,其中也不乏奇思妙想,以及昆汀式的黑色幽默和血腥暴力场面,看点十足。该片于2013年荣获第85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剧本大奖,以及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和最佳音效剪辑的提名。
本片表面上看是一部典型的美国西部牛仔片,据说是昆汀向1966年由赛吉奥·考布西指导的经典意大利西部片《姜戈》的致敬之作。它包含了以往美国西部片所应该包含的所有关键词:牛仔、左轮手枪、马匹、歹徒、警长、酒馆、荒漠、仙人掌、篷车……这些都属于西部片极易辨认的符号。在常规的西部片中,情节和人物的处理也往往趋向于模式化、公式化:善良的人们受到暴力和野蛮的威胁;英勇的牛仔和执法者们除暴安良,结果几乎总是群敌尽歼;牛仔在此期间也会遇上一位纯洁美丽的姑娘,并最后带着她远走高飞。整体看来昆汀版的《姜戈》完全符合西部片的游戏规则:赏金猎人金·舒尔茨正在追捕嫌疑犯布利特尔兄弟,得知一名叫姜戈的农奴认识嫌疑犯的长相,便替其赎身,在姜戈的帮助下抓获犯人。姜戈在舒尔茨的帮助下也成为一名出色的赏金猎人,两人合作无间。但姜戈一直都没忘记自己的最终目标——去糖果农场救出自己的妻子布鲁姆希达,而他的这个决定也得到了舒尔茨的支持和帮助。最终,两人将目标确定在糖果庄园的主人——加尔文·坎迪身上,并以购买曼丁哥角斗士为借口骗取加尔文的信任,但最终任务失败,舒尔茨被杀。然而,姜戈并未放弃,在被送往其他庄园的路上,急中生智,成功逆袭,并救出了自己的妻子,炸毁臭名昭著的糖果庄园。事实上,《姜戈》的创作背景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即将打响之前,以解放黑人农奴为题材的。因此,《综艺》杂志评述其为“被装在通心粉西部片中的影片拥有一个讲述南北战争故事的内核,这种混搭令人非常满意”。[1]
实际上,昆汀的这种混搭在某种意义上,为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的美国旧式西部片开辟了新领域,颠覆了其趋于公式化的结构和布局,也为观众们重新呈现了美国内战前对黑奴的压迫和凌辱,给了丑陋的美国种族主义狠狠一拳。本文就通过对昆汀版《姜戈》的电影语言以及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进行“陌生化”分析,以此深化该片的主题。
二、理论背景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这个概念最初是由俄国形式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个诗学概念,属于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大众对周围事物的感知是不可能永远都保持着一种新鲜感,事物经过数次感知,开始为认识所接受,我们知道它,但却对它视而不见,这就是事物源于感知自动化(automatized)的结论。在他看来,浪漫主义诗人所鼓吹的自然并不真正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之内,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让我们感知到身边那些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件艺术作品的目标应该是将大众的感知模式由自动的、实用的变成有意的、艺术的。在其代表性论著《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什克洛夫斯基写道:“艺术的手法就是将事物变得陌生,将形式变得晦涩,事物的‘陌生化’程序,以及增加感知的难度和时间造成困难形式的程序,就是艺术的程序,因为艺术中的接受过程是具有自己目的的,而且是相当缓慢的。艺术是一种体验创造物的方式,而在艺术中的创造物并不重要。”[2]23
当然,陌生化理论最初产生主要是运用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使用公式化的模型和假设来阐释文学技巧是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发挥作用,并达到相应的艺术效果。形式主义者们强调文学是一种对语言的特殊运用,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离或曲解,达到“特殊化”的目的:日常语言仅用于交流,而文学语言则截然不同,是为了让人们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随着对“陌生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陌生化”手法的理解及应用已逐渐由对文学艺术中的语言、主题、人物等的研究扩展到影视、戏剧、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的运用。
实际上,早在20 世纪20年代,什克洛夫斯基便投入到对电影创造和理论的探讨之中,积极撰写影视评论,编写电影剧本,在其看来,电影是一种新型的艺术形式。1927年,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出版了论文集《电影诗学》,形成了自己的电影理论。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艾亨鲍姆在其《电影修辞问题》中以电影语言阐释为中心,探讨了电影是如何将“生活语言”转变为“艺术语言”的。在文中,艾亨鲍姆汲取了20 世纪20年代法国先锋派中的精华——路易·德吕克的“上镜头性(photogenie)”概念,认为艺术语言源于人类不可理喻的,所谓“自身即目的”的游戏冲动,这种冲动正是艺术创作的催化剂(catalyst)。[3]
三、“陌生化”理论在昆汀版《姜戈》中的运用
(一)语言
语言对一部电影而言,是一种催化剂、调味品、甚至可以说是开心果。因此,想通过语言来达到吸引观众注意力和好奇心的效果,就需要对语言进行“陌生化”的处理,使得观众产生某种心理反差和震撼,进而引起他们的共鸣。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的形式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4]。
在影片中,昆汀正是通过多种语言形式的使用赋予角色新的定义,给观众们焕然一新的感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舒尔茨这个角色。同旧式西部片来比,舒尔茨这个人物本身依然有着符号性,犹如《关山飞渡》中的警长一样,代表了执法者的正义形象,但从他一出场便由于其与众不同的话语和动作形态,紧紧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影片一开始就给观众渲染一种正统西部片的氛围:夕阳、荒漠、仙人掌以及欺压迫害黑奴的奴隶主的残忍形象,而就当观众们已经开始对这部看似非常纯正的西部电影有点不疼不痒的反应时,舒尔茨驾着他的马车缓缓出现了。他穿着考究,言谈举止就像是一位英国绅士,在谈到要购买姜戈时,他先后用到了“purchase”“parley”这样非常正式的词语,使得大字不识几个的奴隶主们只好用“speak English!”回击。甚至就在他出于自我保护而开枪打死其中一个奴隶主后,他还伴随着自己冗长而正式解释:“I am sorry to put the bullet in your beast,but I didn’t want you to do anything rush before you have a moment to come to your sense。”这句话无不使得在座的观众们忍俊不禁。而就在购买姜戈后,舒尔茨与道格特雷镇的宪兵长之间的对话几乎在未费一卒一马的情况下将本片推上了一个小的高潮。当道格特雷县因舒尔茨射杀其治安官而将其团团包围后,舒尔茨高举双手向宪兵长塔特姆解释道:
Marshal Tatum may I address you,your deputy and apparently town of Daughtrey to the incident that had occurred?My name is Dr. King Schultz,like yourself,Marshal,I’m a servant of the court.The man lied dead in the dirt was the good people of the Daughtrey thought fit to elect to be the sheriff who went by the name Bill Sharp is actually the wanted outlaw by the name of Willard Peck with price on his head of 200 dollars...
这段冗长的自我介绍几乎用了整整5 分钟的时间,其中夹杂了大量的正式用语和定语从句,舒尔茨活脱脱地像是一名正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律师,这与其身后的酒馆以及身边面目狰狞的恶汉是极为不和谐的。
实际上,昆汀正是通过这种角色语言与所处环境的错位,达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这些话语将整部电影的喜剧色彩和黑色幽默完美诠释,不仅妙趣横生,也处处绽放智慧。这种让人耳目一新的语言并非晦涩难解,只不过它们被独具匠心的昆汀在“不恰当”的地点和“不恰当”的时机所使用,进而达到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也正是这种效果,让舒尔茨这个角色得到升华:他绅士般的言谈举止、对自由平等精神的贯彻和坚持与当时整个西部颓废荒凉的沙漠及惨绝人寰的黑奴制度格格不入,成为全片的亮点。舒尔茨仿佛成为海明威笔下具有code hero(准则英雄)气质的人,而他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弗·瓦尔兹也因本片获得了第85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配角的殊荣。
(二)表达手法
从表达手法上来看,本片充满了含义丰富的象征。在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用一些具体事务来表达一些抽象的含义或者概念,而这一手法运用到电影里,就往往通过镜头对某一事物的特写来实现。在提尼亚诺夫看来,“特写”作为电影的艺术手段,更是能将对象从空间关系和时间结构中摄取,作为意义符号而加以突出和强调,因而具有比喻的艺术功能。在《论电影的原理》一文中,提尼亚诺夫写道:“无论是电影还是诗,有一点很重要,即不去表现注意力所关注的那一物体而表现与其有联想关系的另一物体(电影中的动作和姿态皆可构成联想关系)。这种用细节取代了事物的手法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用一种指示符号提供了各种对象(整体和细节)。而这种注意力的转移似乎把可见物体分割成了部分,使之成为具有同一意义符号的物体系列,成为电影中有意味的物体”。[5]
在本片中,昆汀就是通过侧面烘托和镜头特写等方式多次进行象征性的表达,达到反讽的效果。例如,对马的特写。在电影中,马不再仅仅是西部影片中必备的交通工具,而成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影片开头,昆汀并未用过多的镜头刻意展现当时的白人对黑奴的虐待或压迫,而是通过姜戈骑着马走过道格特雷镇子时,特写镇民们(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绅士淑女)看到一个黑人骑在马背上自由奔走时的惊讶眼神,使观影者们立即感受到当时黑人地位的卑微,几乎与畜生无异。此外,昆汀在舒尔茨每次驾着大篷车和姜戈一起出现的时候,都会有意用镜头去拍摄大篷车顶上的摇摇晃晃的巨大的牙齿模型。在许多观众眼里,这也许是很没有必要的,因为舒尔茨在一出场的时候就已经点名他是一名牙医,而昆汀没有必要之后多次用镜头强调这颗牙齿。实际上,这颗牙齿在笔者看来可谓是全片的中心和亮点,是昆汀有意在直接和观影者们进行交流:牙齿这里当然不再是舒尔茨的一个广告标志,而是昆汀作为编剧和导演的标志,暗示我们本片已经不是一部我们习以为常的通心粉式的西部片,反而是对这种传统西部片的反叛和颠覆。尤其是牙齿的摇摇晃晃,更是直接表明了所谓权威在本片中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片中除了特写镜头,也用文字来表达象征。最吸引人的就是该片的片名,叫做《Django Unchained》(中国大陆译为《被解救的姜戈》)。实际上,该片片名的中文翻译在笔者看来非常片面,因为这里的unchained 既可以被看作是形容词,表示一种被动,翻译为“被解救了的”;又可以看作动词的过去式,表示一种主动,译为“解开枷锁、释放”。由此看来,本片片名本身就是一语双关,也正好对应了本片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开始,姜戈确实是被舒尔茨所救才获得自由,但此时的他依然表现的唯唯诺诺,看到白人就局促不安,我们可以认定姜戈此时只是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之后,随着跟舒尔茨学习射击和识字,姜戈逐渐意识到自己与白人并无差别,甚至是个天生的神枪手,他逐渐找到自我,获得自信,并在舒尔茨死后,单枪匹马去糖果庄园报仇。这时的他才获得了灵魂上的自由,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那句名言:“人生而自由”。这种自由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需要自己赋予自己。
四、其他
本片中,昆汀除了运用语言与表达手法上的陌生化之外,也使用了离题(digression)、蒙太奇(Montage)等手法,而这些也属于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范畴。在有关叙事理论的研究中,形式主义者们反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情节(plot)”定义为“事件发生的排列”。在他们看来,“情节”这个概念更具革命性质,通过离题、文字游戏或是打乱文章的顺序,可以增强小说的形式。[2]33昆汀将这点应用到了电影之中,离题手法实际上就是打破人们潜意识中存在的情节发展顺序,让观众觉得出其不意,甚至是荒谬可笑。在奴隶主庄园的主人贝内特带着大批人马准备在夜间偷袭露宿野外的舒尔茨和姜戈的时候,大家一定认为下面的情节是一场恶战并为两位主人公捏了把汗,但此时,偷袭者们却为这场偷袭是否需要戴头套而争论起来,之后还气走了负责制造头套的杰妮的丈夫。这场历时五分钟,与全片剧情毫无关系的争论,让观影者们措手不及,当然更多的还是忍俊不禁以及对无厘头的“昆式幽默”的深入体验。
五、结语
“陌生化”作为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在当代电影中的运用已是屡见不鲜。导演昆汀·塔伦蒂通过“陌生化”技巧给他的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吸引观众的注意,并以此产生了更多的研究视角,进而提升了电影的内在审美价值,可谓一举多得。当然,“陌生化”的技巧在使用上也要适度,若过度使用来强调新奇而脱离了大众的可接受范围,便会适得其反,就如近年来一些大制作影片得不到观众们的认可,就是归因于它们脱离了电影创作的最初目的,从而变得没有意义。
[1]gmzyq.《迪亚戈》获媒体盛赞,风格轻松独特演员出色[EB/OL].[2012 -12 -13][2014 -01 -17]. http://news.mtime.com/2012/12/13/1503095.html.
[2][俄]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上海:三联书店,1989.
[3]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8.
[4]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2006:56.
[5]洪宪.简论俄国形式主义电影理论[J].当代电影,2004(6):127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