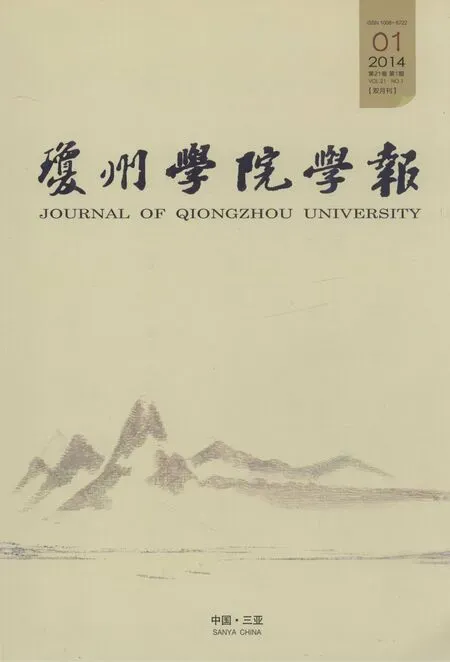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2014-04-07邱君奎
邱君奎
(台湾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80424)
历来学者皆认为《同声歌》为东汉张衡之作,且赋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同声歌》之完成,标志五言诗走向成熟,就形式而言,通篇用韵,不用虚词,观其内容,描写大胆,感情炙热,体现作者一改汉代文人空泛言志的审美情趣,对后代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极大。虽然后世学者对于《同声歌》的创作目的看法不一,认为张衡以比兴技巧“以喻臣子事君之心”如:郭茂倩、吴兢、朱干;或言此为男女艳情之作,则有郑文、吴世昌、钟来因、章培恒、骆玉明与王伟勇等人,然而对于此诗为张衡之作,皆无所疑。
近年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提出了新说①参见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认为具有“穷情写物”艺术特征的成熟五言诗作,产生年代应在建安十六年之后,如古诗中的《苏李诗》、《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及最具价值的《古诗十九首》等。王伟勇与赵羽亦皆认为古籍所载枚乘、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五言诗歌,经考证多是后人伪托。②参见王伟勇,王璟《张衡〈同声歌〉篇旨及所透显之房中文化析论》,载《中国学术年刊》,2010年3月,第107 页;赵羽认为“《文选》中又有题为苏武、李陵的五言诗共七首,合称‘苏李诗’。《文心雕龙·明诗》曾指出:‘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南朝宋颜延之亦云:‘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是托名苏武、李陵的伪作,其创作时间大致与《古诗十九首》同时,又苏李诗中亦有男女情爱之作。”参见赵羽《两汉文人艳情诗述要》,载《新学术》,2009年4月,第113 页。特别是宇文所安提出:“一首五言艳诗《同声歌》被匪夷所思的系于张衡名下;《饮马长城窟行》不再像《文选》中那样是无名的作品,现在成了蔡邕的作品。”[1]这便给我们对《同声歌》作者重探的动力,通过考辨源流、去伪存真的过程,以期厘清《同声歌》的创作年代与真实作者等谜团。
一、古今诸多说法辨析
《同声歌》最早见于《玉台新咏》卷一,内容描述一位新妇对夫婿的爱慕之情,有幸能结为连理,定当恪守妇道,侍奉夫君。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同声歌》,汉张衡所作也。盖以当时士君子事君之心焉。”[2]认为此诗乃张衡利用兴寄手法,表达臣子侍奉君王之心。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收此诗于《杂曲歌辞》中,承继吴竞说法,在《乐府解题》中提到:
思为莞簟,在下以蔽匡床;衾裯,在上以护霜露。缱绻枕席,没齿不忘焉。以喻臣子之事君也。[3]
清代朱干《乐府正义》:“张平子初为侍中,后卒外补,此疑追叙其事;而其愿出入禁闼之思,故托为妇人之言如此。”[4]与上述二人看法相同,就此诗内容来看,“幸得充闺房,愿勉供妇职”表面上描述一位新妇自陈与夫婿新婚之爱,愿意恪尽妇职,实际乃是张衡藉此兴寄,表达渴望侍奉君王的愿望;“恐栗若探汤”则是形容其既兴奋又戒惧的心情(实则为男女交合的用语)。
另有一说,认为本诗写作背景与张衡担任南阳主簿之事相合,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5]张衡自十六、七岁即离开家乡南阳负笈远游,期间曾被推举为孝廉,朝廷征召他出仕,但他并未应承。东汉和帝永元十二年,时任南阳太守的鲍德邀请张衡担任主簿一职,张衡原就景仰其人品及治才,便欣然应邀,因而有部分文人认为此首《同声歌》乃是张衡感激鲍德知遇之恩的作品。“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就这些句子似乎都可解读成张衡对于新职满怀理想抱负,亟欲协助鲍德处理好郡中政务的决心,并藉本诗表达他对鲍德的崇敬之情,亦体现了他俩间的深厚情谊。①参见王伟勇、王璟《张衡〈同声歌〉篇旨及所透显之房中文化析论》,载《中国学术年刊》,2010年3月,32_1 期,第102 -103 页。王志尧等人所著之《张衡评传》分析《同声歌》具有双重主题,其云:
从它所隐含的深层含意看,它实际上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作者在诗中以男女关系自比君臣,抒发了自己充任鲍德主簿的兴奋心情,并表达了帮助鲍德处理好郡政的决心。[6]
从表面上看此为一首爱情诗,就诗歌内容而言,是以女性口吻自叙对自己情人的爱恋,但其主要所欲表达之意涵犹如“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感念鲍德知遇之恩。元代曾绎曾《诗谱》便推崇张衡诗“兴寄高远、遣词自妙”[7]。
然而此种“以喻臣子之事君”之兴寄说法,也引起许多学者的批评,赵羽认为这种生搬硬套的兴寄比附之说未免太陷于迂腐,并且以《同声歌》的夫妇房事之乐比拟君臣鱼水之欢,也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现代学者大都倾向于把《同声歌》理解为男女艳情之作,吴世昌先生《<同声歌>跋》评此诗曰:“古今艳辞,除明人之直咏秘戏者外,当无艳于斯者矣。”全诗以新娘的口吻,描述了她在洞房花烛之夜的经历和感受。②转引自赵羽《两汉文人艳情诗述要》,载《新学术》,2009年第1 期,第110 -111 页。郑文《汉诗选笺》云:“昔人泥于夫妇以比君臣之说,谓此诗‘以喻臣子之事君也’,不为无据,但孔、孟所示:君君而后臣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倘臣之事君,竟至以闺房燕昵之私,拟君臣之鱼水,则臣之自视已成草莽,焉能‘以道事君,不可则止?’”[8]郑文说本诗乃“以喻臣子之事君”虽不为无据,然而以闺房燕昵之私来比喻君臣关系,如诗中“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甚至诗末“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等句,认为这种比喻已逾君臣伦理。钟来因则批评郭茂倩这种“喻臣子之事君”的说法乃迂腐之见,是对《同声歌》最大的曲解。他说:
张衡一生,对于从政做官极无兴趣,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科学研究、发明创造上,因此他既无兴趣,更无必要用《同声歌》中女子缱绻之情向汉皇邀宠。诗中男女邂逅、和谐极乐来比喻君臣也实在是不伦不类,因而这是强加给张衡的。宋儒把这种杂曲乐府中爱情硬要说成“臣事君”,完全抹杀了诗的内容特色,去适应君主专制的需要。[9]
钟来因从张衡人格特质的角度,反对郭茂倩的兴寄说,章培恒、骆玉明则根据张衡《七辩》一文的内容,反对《同声歌》篇旨兴寄的说法:“《乐府解题》认为此诗是“喻臣子之事君也”,乃是迂阔之见。与此诗内容相类的描写,另见于张衡的《七辩》,可见描写这种生活情景,在张衡来说并非觉得有什么忌讳,必须套上一个大题目。其实,张衡的诗所存虽不多,喜欢描写男女情爱的特色却很明显。”[10]这里点出《同声歌》的确是一首艳情诗,以真切热烈的笔法,毫无忌讳地歌颂男女情爱,并非所谓兴寄之说,陈新亦认为《同声歌》是“合欢诗”,一首大胆、炙热、赤裸的爱情诗。③参见陈新《优美的婚歌─以“诗”解读张衡〈同声歌〉》,载《阅读与写作》,2004年第9 期,第14 页。王伟勇评价此诗,“认为本诗虽将极为私密的闺房体验大胆呈现,但所表现的并非男女间的淫乐贪欢,而是自然情欲的真诚流露,成功表达新婚夫妻生活的圆满和谐;亦即虽写私亵之事,但读来并不让人觉得淫邪低俗。这样的写作技巧也反映了张衡在创作时汲取民歌自然率真的特点,但又不失文人创作的温雅,因此《同声歌》可说将‘情’发挥到极致,却未流于‘色’无怪乎张溥说它:‘丽而不淫’”。[11]
二、《同声歌》非东汉之作
近代学者们似乎普遍认为《同声歌》乃是东汉张衡以写实手法来歌咏男女性爱之事,且不流于淫俗,对后世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上有着重要意义,无论在题材上或风格上都有它一定的价值。然而,笔者却不敢认同此说,其一、两汉文人不太写诗,自汉武帝独尊儒术,《诗》已被神圣化与经典化,学者仅透过章句训诂,阐发经典的微言大义与旨趣;其二、就两汉儒家经术传统道德思想氛围,很难想象东汉士人无论是为了表达“士君子事君之心”或是“歌咏男女性爱之事”,有必要写出如此露骨之诗,而不顾当时的道德束缚。以下笔者就此二点,提出己见。
(一)儒家《诗》教说:
儒家素有《诗》教传统,重视诗歌的讽谏功能,认为诗歌可以“兴观群怨”,故孔子以六艺教弟子,特重《诗》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政治之作用。《诗大序》云: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12]
《诗大序》揭示了诗歌和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地道出诗的“教化美刺”功能,面对世道衰微,国家动荡之际,臣子透过“主文而谲谏”的方式,使君王了解王政之得失。张克锋《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提出:“孔子强调诗歌讽谏功能的诗教、诗学观,对汉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诗》大小序、三家《诗》、司马迁、班固、王逸、郑玄等皆继承了讽谏论诗的传统。汉儒不但在文学批评中强调诗歌的讽谏功能,还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以《诗经》当谏书,是汉代诗学的重要特点。”[13]
(二)儒家道德教化与清议制度
就《同声歌》内容而言,若是如前者所言,或喻臣子事君之心,或言男女情爱之作,在两汉儒家教化的时代,如此搧情之诗作,恐怕不为世人所接受,何况是饱学儒术之士,皆须受到严格的道德标准审视。自西汉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儒家道德教化的核心思想“三纲五常”,朝廷以此为法制,“所谓三纲,《礼纬·含文嘉》云: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14],主要阐述“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精神。所为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信,用以规范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至东汉白虎通会议,则又提出“三纲六纪”,对于道德的要求标准更加周延,并且立为法典,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清议乃是东汉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论,当时皇室腐朽,宦竖擅权,致使朝政日非,生灵涂炭。《后汉书·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15]2185
清议的内容非常广泛,所谓“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项,士人评论公卿的优劣,主要识其为官是否清廉,品德是否高尚,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为何,此种清议制度是颇具力量的,因此公卿士大夫相当重视个人的言行举止是否合乎于礼教。
在这种儒家道德思想氛围环境下,臣子不管是为了向君王表明自己忠诚之心,或真是抒发个人情爱思想,写作《同声歌》这种艳诗内容势必遭致严苛的批评。
三、《同声歌》非张衡之作
《同声歌》既然不太可能产生于东汉,还有可能是张衡之作吗?首先我们先探讨原诗内容:
邂逅承际会,偶得充后房。情好新交接,恐栗若探汤。不才勉自竭,贱妾职所当。绸缪主中馈,奉礼助蒸尝。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镫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16]
此诗主要以女子第一人称的口吻,自述有幸与丈夫邂逅从而结为连理,及其初为人妇的复杂心情与对自己能否扮演好妇职的担心,期勉自己能奉守礼节、恪尽妇职来服侍丈夫的生活起居。“思为苑蒻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此四句则透露出新婚女子对丈夫的缠绵深情,此诗自“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直至诗末,大胆吐露新婚男女享受鱼水之欢的床笫风情。
由此诗的内容来看,明明即是女子对新婚生活的直白陈述,很难让人联想到张衡为表达“士君子事君之心”的兴寄之作,犹其自“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以下,言及宽衣解带、陈列春图等房中之事,以及享受床第鱼水交欢之愉悦心情,如此详尽的描绘,作为兴寄之题材,不仅为当时的社会所不齿,礼教所不容,恐怕就连君王看了都觉得恶心,王伟勇亦认为“以床笫交欢来比拟臣子之事君,就君臣伦常分际而言,实在难以站得住脚。”[11]考察张衡生平素养,《后汉书·张衡传》云:“才髙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15]1897,由这些叙述可见其生性淡泊、不慕荣利的性格,决不至于为了名利爵位,背离社会伦理道德,来引起君王的关注与眷顾,是故赵羽、吴世昌、郑文与钟来因等学者反对《同声歌》篇旨兴寄的说法。
既然张衡不因功名利禄折腰,难道真如学者们所认为,张衡创作此诗的价值,即在“突破儒家礼教禁锢,大胆歌颂人类至真至性的原始需求”[11]。然而,既然学者们认为以“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如此露骨的男女初夜之乐,来比拟臣子之事君,以张衡的儒者性格及史书可考的学养修为,可能性实在不高。如何认定张衡能够冲破两汉道德思想的禁锢,荡其思虑,为床上男女的欢爱之情大唱赞歌呢?吾人可从《后汉书·张衡传》记载来看:“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徳之不崇”[15]1901;朱洁则提出“张衡以圣人之道做为衡量美德之标准”,[17]显示其对于圣人高尚品德的推崇,亦难以让人信服《同声歌》为张衡之作。
其次,东汉五言诗作寥寥可数,木斋、宇文所安与王伟勇等人皆提出古籍所载枚乘、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五言诗歌,经考证多是后人伪托,这便不免令人怀疑张衡是否有能力完成,通篇用韵,音律谐美,语言流丽,全诗不用虚字的《同声歌》,以下笔者将从张衡文学艺术的创作视角来看。
张衡(79 -139),自子平,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发明家,在天文与地理等自然科学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是最优秀的文学家,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并列汉赋四大家,最著名的赋篇是《二京赋》,虽然体制因袭前人之作,但讽喻的精神和批判色彩更见显著,内容也更加宏观。晚年眼见朝廷日渐衰败,贪官污吏充斥,加上仕途不顺,遂有归隐之意,《归田赋》道出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张衡晚年作品已由华丽的大赋转变为抒情的小调,运用清新的言语,描写自然风光的美妙,也抒发了自己恬淡安适的心情写照,《归田赋》带给缺乏生气的汉赋一股清流,这种抒情小赋,很快就被汉赋家所接受,并开启魏晋南北朝归隐与田园抒情小赋艺术之路,虽然张衡的写作风格以从早期模拟汉大赋时期,走向晚年归隐与田园抒情小赋,其作品主要还是以赋体为主。
历来文学史对于张衡的诗歌创作评价甚高,认为《同声歌》通篇用韵,音律谐美,语言流丽,全诗不用虚字,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走向成熟,其内容大胆的描写手法,将炙热的情爱思想表达出来。此外,在文学史上贡献最卓著的即是他的《四愁诗》,从形式看来,语言整齐,韵随意转,被喻为七言之祖,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有着深切的影响力。然而观看其晚年之作《四愁诗》的写作风格,尚未摆脱《离骚》藉物托词,以比兴手法委婉抒写他们在政治上怀才不遇的失意,《四愁诗》同样承袭了屈原以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以美人、珍宝象征理想君王的化身,藉以寄托政治理想。诚如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所说:
《四愁》,汉张衡所作,伤时之文也。其旨以所思之处为朝廷,美人为君子,珍玩为义,岩险雪霜为谗谄。其流本出于《楚辞·离骚》。[18]
再看《定情赋》也是借着叹咏“夫何妖女之淑丽,光华艳而秀容。断当时而呈美,冠朋匹而无双”,感慨“秋为期兮时已征,思美人兮愁屏营”的愁绪,同样也是以美女喻贤王的手法。[11]在用字遣词方面,《四愁诗》也尚未摆脱虚词的使用。曹魏时期,曹操写五言诗,也是经历了虚词使用的转换期,自此以后能写出整齐的五言诗,若是东汉末就有如此完美的五言诗,以曹操的聪明睿智,写出成熟的五言诗早已驾轻就熟,此外,五言诗的写作方式必定流行于后世,然而为何有种时空中断,好像大家都突然忘记如何写作五言诗,为何除了三曹六子等少数人会写,其他人都无作品留下,若再仔细深究,为何蜀国与吴国也没有任何五言诗的作品流传?木斋认为:
就诗人诗歌写作的规律而言,能写出一首好诗,往往意味着会有很多诗作的创作经验才有可能达成,而不会出现原本不会写诗,突然写出一首传世之作的现象。汉魏之际出现这么多一生只会写一两首好诗的现象,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论证。其结果无非两种:或是仅有的这一两首诗作并非真实之作品,或是这当下拥有一两首优秀诗作的诗人还有其它诗作遗失。[19]
若是张衡有能力写如此好的五言诗,为何作品只有留下一首,何况张衡真有能力创作五言诗,就其晚年写作风格来看,似乎应以清丽抒情的文句来描写个人的怀抱和感情,怎么可能写出如此煽情的字句?宇文所安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一书中提出:
刘勰毫不迟疑把“怨篇”系于张衡名下,正如钟嵘之列入班固诗一样,是为了试图填补江淹所留下的从班婕妤到建安之间长达两百余年的空白,所以人们不断把现有的诗系于知名作者名下。一首五言艳诗《同声歌》被匪夷所思的系于张衡名下;《饮马长城窟行》不再像《文选》中那样是无名的作品,现在成了蔡邕的作品。[20]
木斋与宇文所安皆认为,这首穷情写物,音律谐美,语言流丽的《同声歌》,应是建安时期的作品,至于真实作者为何,值得吾人去探索,至少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同声歌》非东汉张衡之作。
四、试析《同声歌》真实作者
辨伪古诗作者的研究有多种可能性,既然《同声歌》非东汉文人之作,亦非出于张衡之手,那么真实作者究竟为何人?笔者的推论或许正确,亦或许有误,然而我们要有求真的欲望与勇气,去探索《同声歌》或其他古诗背后所隐藏的诸多谜团,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既然木斋与宇文所安皆认为,这首穷情写物,音律谐美,语言流丽的《同声歌》,应是建安时期的作品,那么何人有能力写作此诗?创作的时间点为何?为何最后会被匪夷所思的系于张衡名下?以下笔者将就此三点分述之:
(一)《同声歌》真实作者为何人
汉代选官任用以道德考察为标准,王符《潜夫论·论荣》:“今观俗世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21],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求贤令”,以“不官无动之臣;不赏无战之士”为任官标准,并言“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22],认为承平之世以有德之人作为榜样,但在乱世之际,任官选人须“唯才是举”,打破了汉代儒家政治以德取士的观念。在此开放的风气之中,士人不再拘于礼教限制,人们凭借着自身实力大展其才。曹操不但解放了儒家政治思想,也连带解放了汉代长久以来的经术教化思想,诗人创作不再是为政治服务,宣扬儒家教条,诗歌创作回归到个人生命的体现。建安十五年冬,铜雀台建成,提供了曹魏集团的文人宴饮享乐,交际诗赋的场所,加上清商乐兴起①清商乐始于曹魏三祖的记载见于[梁]萧子显撰《南齐书·王僧虔》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94 页:“今之清商,实由铜爵,三祖风流,遗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弥贵。”。〔唐〕魏征等撰《隋书·音乐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7 页:“清商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相较传统雅乐的严肃,轻快愉悦的清商乐,更富娱乐性与抒情性,符合宴饮享乐的需求,爱好文学的曹操,便率领诸子文士,游宴享乐,创作诗赋。当时的文学作品除了以赋为主之外,以曹操为首的三曹六子,开始尝试四言、五言、六言与杂言的诗歌创作,特别是五言诗的创作,木斋先生认为:
清商乐对先秦两汉雅乐的革新,反映到诗歌领域中,就是五言诗的兴起和建安文学的自觉。从汉魏之际五言诗作的实际情形来说,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数量之变,建安之前的文人五言诗,尚属偶然零星之作,建安时期始出现大量文人五言诗;二是质量之变,或说是写法之变,两汉之作,囿于言志之诗学观念,故多空泛议论之作,后来所渐次形成的眼前景、身边事的情景交融式的写法,实际上开始于建安诗坛。这一转型,与曹氏父子倡导并参予的清商乐乐府歌诗写作关系密切。[23]
三曹六子的五言诗创作,摆脱了汉代经术的禁锢,将文学与艺术结合,透过对生活事物的具体描绘,搭配轻松莞尔的清商乐,使诗歌充满生命力与审美效果。依据木斋的新说,此种“穷情写物”的五言诗,创作的年代应发生于建安时期,同时有能力创作五言诗的文人,尚仅限于三曹六子。那么《同声歌》的作者是否为三曹六子之一人?其实不然,两汉时期之文人诗歌创作技巧尚处于兴寄手法,自建安十六年后,三曹六子的五言诗作,摆脱汉诗之兴寄,由代言转向自言,多以第一人称表述,不再有男子自称妾妇之言,故《同声歌》既然是以第一人称的新妇口吻自陈新婚欢愉之事,此诗就应为女子所作。那么在建安时期,有哪位女子有机会与能力能创作五言诗?木斋认为:
曹植甄后之间,这种特殊的人生经历,在曹操易代思想革命的大背景之下,在曹操“盗嫂受金”《求贤令》颁布的鼓励之下,从纯粹精神的爱恋而走向灵与肉的结合,而曹丕曹植兄弟均为当时代第一流的大诗人,甄后自身的个性禀赋,近朱者赤,遂使之具备同样成为五言诗人的诸多因素,从而成为汉魏时代唯一能写诗的女性,正如有学者所说:“魏妇人能诗,仅甄后一人而已”甄后现有《塘上行》传世,未被流传之作,或说是被有意湮没埋藏从而成为“古诗”“乐府”之作,不知还有多少首。[19]
在曹植的诸多诗作中,透露出他与甄后两情相悦的事实,这段不伦恋亦造成日后两人乖舛之命运,但不可否认的,就当时的环境背景,惟有经历植甄二人这般惊天地泣鬼神的刻骨铭心之爱,才有能力创作如《同声歌》、《塘上行》等诸多爱情五言诗作,故笔者推论《同声歌》之作者非“甄后”莫属。
(二)《同声歌》之写作时间
关于植甄恋情的最早记载,李善注《文选·洛神赋》引《记》:“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24]。曹植于建安九年在邺城初见甄氏,便“昼思夜想,废寝与食”。《七启》《九咏赋》《芙蓉赋》《离友诗》《远游篇》与《秋胡行》皆是曹植对甄后倾述爱慕与相思之情的诗作,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采遗芙蓉:曹植诗文中的爱情意象——兼论建安十六年对曹植的意义》与《论建安二十二年为曹植的人生转折——兼析曹植《美女篇》《蝉赋》《节游赋》的写作背景》等篇章,提供吾人许多有关于曹植与甄后相恋互赠的情诗考证,藉此亦可推论甄后《同声歌》之写作时间。
依据裴松之注《文昭甄皇后》引王沈《魏书》云:
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后与二子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后颜色更盛。”[25]161
曹操此次东征,随行者有卞太后、曹丕及甄氏所生的两个孩子,甄氏因病留在邺城。《魏书》明言武宣皇后、曹丕、曹叡与东乡公主皆随行,但并未提及曹植,说明曹植留守邺城的可能性很大。其中令人不解的是,卞太后归来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甄后一别夫婿与子女时间长达九个月之久,不仅容貌不仅没有因忧伤而枯槁,反而“颜色更盛”,笔者推论,自是曹植的呵护,不仅让她病体痊愈,更使恋爱中的甄后容光焕发,越发美丽。①胡旭亦认为:甄氏与孩子丈夫分别如此之久,不仅没有忧伤枯槁,反而“颜色丰盈冶,不禁大为吃惊。甄氏的回答虽然表面没有漏洞,但显然经不住仔细推敲。来自曹植的爱情,不仅让她病体痊愈,而且越发健康,焕发出特别的神采。参见胡旭《〈文选·洛神赋〉题注发微》,载《中国韵文学刊》,2013年第2 期,第65 页。再者,随着曹植与甄后的恋情渐渐曝光,热恋中的两人,行径越发大胆,此次曹操东征,便为两人带来难得独处的机会,就《同声歌》内容而言,即是甄后自述与曹植单独相处的生活写照,诗文中也透露出甄后能与心爱之人朝夕相处的雀跃之情。
(三)《同声歌》因何系于张衡名下
爱情的伟大在于彼此能为对方牺牲,随着曹植于建安二十一年以后“夜冲司马门”与“醉酒未能受命”,为爱放弃太子之位,甄后于黄初二年前夕上表请求另立新后,两人的恋情已渐渐从地下浮出台面,加上灌均、王机与仓辑等人的弹劾,曹植终至获罪。在两人临别之际,甄后吟唱《塘上行》,而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则为曹植回复之作。①参见清人宋长白云“甄逸女将终,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旁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子建伤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见《三曹数据汇编》,台北:木铎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 页。两人这段不伦之恋,令皇室蒙羞,也令身为甄后之子的魏明帝曹叡,处心积虑的想要湮灭两人这些不堪入目的来往书信。
曹叡由于不能容忍这种暧昧关系,对皇室的侮辱和损害,遂有景初中临终前整理曹植文集的行为。曹植作品的版本有二,一是曹植手自编次的,另一是曹叡下令编辑的。根据景初编辑的,计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曹植所写的《前录自序》所载,赋是七十八篇,两相比勘,显然已存在详略的差异。曹植《前录自序》所指的七十八篇,仅仅指的是“少而好赋”的文赋之作,并不包括诗作。而景初中所撰录的,则是诸体并包的曹植文集,景初中对曹植作品的重新“撰录”,数量为“百余篇”。就王玫先生引朴现圭文章所说:“宋人纂辑曹植集所载的篇数,增至二百余篇,近人所编的则有三百余篇,故知曹植集曾经聚而又散,散而又聚。”[26]可知曹植作品流失之多。从《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记载来看,曹叡表面上对曹植是宽宥的,说:“陈思王植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于离手,诚难能也”[25]576,但其实质,是要对所有有关曹植的档案材料进行掩盖封杀。从曹植文集的重新撰录“副藏内外”,以替代外面流行的曹集文本,就是要让不该出现的诗文全面消失。据《晋书·曹志本传》记载:“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于魏……遭母忧,居丧过礼,因此笃病,喜怒失常。”[27]在曹志喜怒失常的情况下,原先视为一家之传家珍宝的曹植“手所作目录”的丧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曹志之后,世人再也没有人提起曹植的这“手所作目录”。当然,若这份目录至今犹存,就不会有十九首和苏李诗存在与否的问题了。由上述曹叡下令对曹植诗集的重新删定,就不难理解为何才华洋溢的甄后仅有一首《塘上行》流传于世。
然而《同声歌》为何系于张衡名下,笔者推论魏明帝在替《同声歌》寻觅适合的归属时,为了不露破绽,找上了相似的内容语句,以掩人耳目,根据张衡《七辩》其中“指图观列”的“图”与《同声歌》中“列图陈枕张”所列之“图”皆有“图”字。又或是如宇文所安在提出:“是为了试图填补江淹所留下的从班婕妤到建安之间长达两百余年的空白,所以人们不断把现有的诗系于知名作者名下。一首五言艳诗《同声歌》被匪夷所思的系于张衡名下。”[1]则有待更多的文献来解开这个千古谜团。
结语
千百年来《同声歌》理所当然的被署名于东汉张衡名下,所引起之争议,亦仅止于针对诗中煽情的内容,究竟是否是张衡为表达“士君子事君之心”的兴寄之作,或是“突破儒家礼教禁锢,大胆歌颂人类至真至性的原始需求”的情爱诗,却从未有学者怀疑过《同声歌》作者的真实性。直至近年木斋与宇文所安等学者,提出具有“穷情写物”艺术特征的成熟五言诗作,产生年代应在建安时期之后,古籍所载枚乘、苏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五言诗歌,经考证多是后人伪托。一首大胆描写男女欢爱的艳诗《同声歌》,其作者是否真为东汉张衡所作,值得吾人去辨析,考证张衡生性平淡,品格高尚,以及所处于两汉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禁锢的时代背景,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张衡有勇气违背礼教的束缚,再者,就张衡文学作品的分析,尚不构成对《同声歌》的创作能力。笔者通过考辨源流、去伪存真的过程,大胆推测《同声歌》为建安时期“甄后”之作,至于为何一首写给曹植的闺房艳诗,会被署名于东汉张衡名下,应是魏明帝曹叡为免家丑外扬,在重编曹植诗集之时,有意识的将两人来往的书信,删除或修改伪托于他人名下。木斋于《古诗破译曙光出现》一文中,同样发现两汉这些无名氏或伪托他人名下之诗,与植甄之恋有着密切的关系。②参见木斋《古诗破译 曙光出现》,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 期,第73 -74 页。究竟《同声歌》真实作者为何人,值得吾人再去思索,然而就诸多证据来看,笔者推论应不是东汉张衡所作。
[1]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香港:三联书店,2012:59 -60.
[2][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M].台北:艺文出版社,1966:66.
[3][宋]郭茂倩.乐府诗集[M].台北:里仁书局,1983:1075.
[4]黄节.汉魏乐府风笺[M].香港:商务印书馆,1961:185.
[5][宋]李昉.太平御览:服用部十三:笥:卷七一一[O]//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王志尧.张衡评传[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172.
[7]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626.
[8]郑文.汉诗选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4.
[9]钟来因.《同声歌》简论[J].贵州文史丛刊,1985(3):107 -111.
[1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75.
[11]王伟勇,王璟.张衡《同声歌》篇旨及所透显之房中文化析论[J].中国学术年刊,2010(32_1):97 -127.
[12]毛诗大序[M]/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毛诗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13.
[13]张克锋.儒家《诗》教传统与汉代诗歌讽谏论[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1):29 -32.
[14][宋]卫湜.礼记集说:卷九八[O]//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16][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笺注[M].[清]吴兆宜,注.[清]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28 -29.
[17]朱洁.张衡美学思想初探[J].理论月刊,2009(6):139 -141.
[18][唐]吴兢.乐府古题解要[M].台北:艺文出版社,1966:12.
[19]木斋.古诗研究的多种可能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5 -11.
[20]宇文所安.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M].胡秋蕾,王宇根,田晓菲,译.田晓菲,校.北京:三联书店,2012:59 -60.
[21][汉]王符.潜夫论笺校正[M].[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152.
[22][晋]陈寿.三国志[M].台北:鼎文书局,1979:24.
[23]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0.
[24]张可礼.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87.
[25][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161.
[26][韩国]朴现圭.曹植集编纂过程与四种版本之分析[J].文学遗产,1994(4):24 -32
[27][唐]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89 -13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