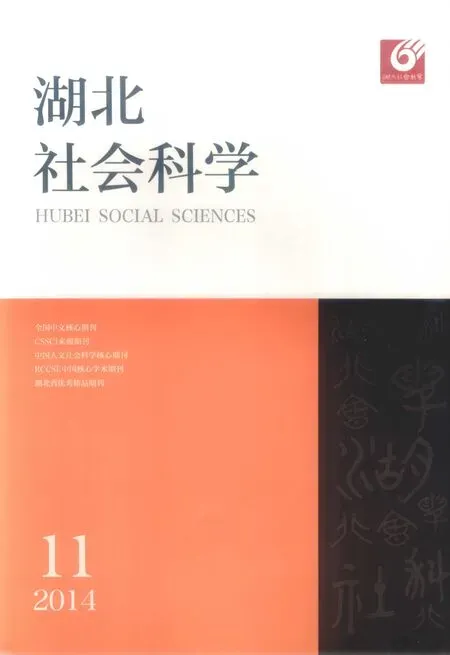论秦汉国—家秩序之形成原因
2014-04-06徐栋梁
徐栋梁
(1.通化师范学院 文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商周时期国家建构的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制度。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家天下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分封制。秦汉所确立的帝制,在将宗法分封制转变为皇帝郡县制的同时,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摈弃了周制的家—国次序,转而强化国—家系统。秦汉国—家秩序的形成,让国家意识正式凌驾于原始社会所遗留的家族意识之上,确立了后世国家建构方式的雏形。其形成原因大致如下:
一、政治集权之演进
周代立国之初便在新占领地区分封诸侯,并通过联姻等手段加强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的联系,其目的便是依靠诸侯监视地方,增强天子的控制力。然而周代的分封制度自有其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周天子对地方的控制不够有力。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周王朝对境内的控制缺乏稳固性。周武王虽然完成了表面上的政权因革,但其统治实际上并不牢固。终周一朝,北方的犬戎和猃狁诸族一直是个巨大的威胁,在戎狄诸部落的不断侵袭下,周王室被迫迁都洛邑,并从此一蹶不振。犬戎和猃狁等游牧部落对周王朝的影响固然巨大,然其终属于外部侵袭;殷商故地及东夷各族的叛乱,却真正彰显了周王朝对于自身统治范围之内不够强有力的事实。武王于克商三年后逝世,商纣王之子武庚联合管叔、蔡叔、霍叔叛乱,并得到奄人、东夷、淮夷的广泛响应。这次叛乱虽起因于殷商旧贵族的挑动,但九夷各部的响应和周王室内部的分裂,也都显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直到周公辅政,平定管蔡之乱并“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1](p155)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分封,西周之统治才初步延伸至全国。
其二,周王朝的治国制度缺乏普遍性。换言之,周代诸侯和方国在治国理念和制度上基本属于各行其是。西周初年,周王朝肯定了制度方面的一国两制,在“殷虚”实行“商政”,在“夏虚”采取“夏政”,这种因当地风俗而施政的例子在其他诸侯国也颇为多见。
秦始皇初定全国,丞相卫绾等建议始皇立诸子为王,恢复封建制,但李斯独排众议,力劝始皇以郡县取代分封,秦始皇之所以能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其目的不在于制约诸侯相互之攻伐,而在于解决天子之权日弱至不能约束诸侯的隐患。
大一统国家的建立,除在疆域上空前广阔之外,更体现在国家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当皇帝—丞相—百官的官僚体系取代了相对松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结构,相权、君权的日益加强让政治权力进一步集中,血缘关系在国家建构中的影响力被淡化,最终促使原先以家族为中心的家国秩序被以国家体制作为核心的国家秩序所取代。
二、尚贤思想之高扬
三代及之前圣君多能重视或任用贤人,如传说中尧对于许由的敬重,舜对皋陶、伯阳的重用,商汤对伊尹、武丁对傅说的任用,文王与姜尚的君臣相投等等。但这种对贤人、贤士的尊敬只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非整个社会的普遍意识。
西周初年,尊贤思想在上层统治者中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周太王有太伯、虞仲、王季三子,后因王季之子姬昌“生有圣瑞”,故舍长子太伯和次子虞仲,立王季为后。及文王,同样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次子发,理由是诸子之中“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史记·卷35)武王即位后,于诸弟中择岁数较小而能力出众的周公旦作为自己的辅助,也体现出这种择贤之倾向。
战国之时,“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凶之秋也”,[2](p41-42)所以尊贤之风渐起,并逐渐流行于诸侯。战国之初,魏文侯开门养士,其招揽之人才中,有名可考者就有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十余人,可谓开战国养贤之风。其后国君多有礼贤者,如鲁穆公亲访孔子之门徒泄柳,又重用子思。《孟子》中云:“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可知子思当时在鲁国地位之重,以至自高身份一至于此。今郭店楚墓竹简中亦有《鲁穆公问子思》一文,载鲁穆公问政于子思及变法事宜。
战国末期,养士的重心逐渐由国君转移到贵族。四公子之养贤,虽门客之中“真士少,伪士多”,但也有另外的功能,就是让越来越多的士人、学者进入到贵族的圈子,并因自身之才能而得到重用。如果说国君养贤只是对一流的贤人进行礼遇,那么战国末期的贵族养贤,就是将贤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同时也将尚贤思想的影响扩大化。
受先秦诸子任贤思想的影响,汉高祖十一年二月,刘邦向贤士大夫发出求贤令,要求郡守劝勉贤士应诏。汉文帝二年、十五年两次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直到武帝时以“举贤良”为一项固定的选官制度。
西汉末年,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禅国让贤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谶纬之说结合起来,一旦有灾异降临,便总会有儒生宣扬应该应天改命,物色贤人以让国。汉末谷永等所言“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其实即汉儒对于尚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尚贤思想从个人行为逐渐上升为社会思潮,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整个社会对于贤良才德之士的尊重,更深层地影响到了社会的组织结构。战国贵族之养贤、用贤让更多的士人崭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加速了世卿世禄制度的颠覆,同时也标志着家族和血缘关系凌驾于国家意识之上的状态被打破,以及以国家为中心、以家族为基层组织的国—家秩序的建立。而西汉儒生的禅国让贤思想,更是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论对一家一姓之国家的传统观念形成极大冲击,使得家族对于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降低。
三、家族观念之动摇
秦汉国—家秩序对于家—国秩序的取代,除受大一统国家建立、政治集权逐渐加强,以及尚贤思想逐渐高扬的影响之外,还与家族观念的动摇有关。虽然家族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存在,甚至在汉魏之后还曾有过门阀势力高涨的波峰,但如若只针对帝王家族中家族观念的变化进行分析,便可发现秦汉之前帝王家族中的家族观念是愈来愈淡薄的。
第一,以父子继承制的出现为标志,秦汉之前帝王家族内部的横向血缘关系逐渐淡化,家族观念也因之变化。原始社会中,先民为了部落的生存,必然要从众人中推举最具能力的人成为部落的领袖,部落首领有率领整个部族战胜困难的责任,但却不具备决定下一代首领的权力。首领的继承也不被限制在某个特定的家族中。当人类逐渐脱离原始社会,这种原始的“民主议事”式的传位方式依然有所遗留。如《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尧帝年老时咨之四岳,最后依照四岳的意见,对舜进行考察,后来传位于舜。这种传位方式发生于早期国家出现之前,是国君控制力不强,无法将政权纳入自己家族的一种体现。
夏商之时,国君对于国家的控制力已经有所加强,传位已经可以不再顾虑于他人,所以王位的承袭开始局限于宗族的内部,是以家族观念日益深化。商代早期所实行之“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说明政权的传递已经控制于本家族之中,然而由于政权为本家族所共有,所以不能在父子之间继承,而应在本家族的同辈兄弟间传位。殷商末年,自庚丁之后至帝辛(纣)的最末五世皆为父子相承。相对于兄终弟及制而言,父子相承制是对家族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标志着家族与血缘关系的疏离,从此直系血缘关系日益重要,而横向的血缘关系逐渐淡漠。
第二,分封制度的崩溃,更加体现了家族观念动摇之后,国—家秩序出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分封制的消亡是一种螺旋式的进程。
秦始皇建立起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将政权集中于一人之手,并彻底摒弃封建制,是第一次大的转变。但秦朝二世而亡,又给了分封制再现历史的可能。汉初仍然实行分封制,但实际上彼时的分封已经逐渐变得有名而无实。汉高祖所分封之诸侯王既有同姓诸侯,又有异姓诸侯,似乎与西周之制度所去不远,但实际上这种分封制是一种分封与郡县并行的双轨机制。[3](p40)在这种封建郡县的双轨机制下,方国之内由郡县长官和分封的王侯共同治理地方事务,让诸侯王的势力大幅度地削弱,与周代诸侯的实际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之后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一直致力于削弱诸侯。诸侯或被迫谋反,最后身死国除;或因犯罪或其他原因而被削掉领地;或在朝廷的推恩令下,封爵日多,而领地日小。即便如此,东汉建立后,诸侯的权势又进一步遭到削弱。光武帝所分封之诸侯王,不仅王国的封区比西汉初小得多,而且唯封食邑,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治民权,诸侯实际相当于有名无实的地方州郡长官。东汉末年割据之群雄中,虽仍有刘表、刘焉、刘璋、刘虞等刘氏宗亲,但他们皆是以守令之职权而能割据一方,而非以诸侯之势力割据,也是分封制度崩溃后,诸侯已无任何势力的又一体现。
在分封制度逐渐消亡的过程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异姓诸侯王的消失,说明在国家势力的组成部分中,不同姓氏或曰不同家族对于同一政权的分配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家一姓之天下的统治理念。二是诸侯封地的失去,意味即便是同姓诸侯王,也不复具有周代诸侯的地位和实力。这不仅意味着同姓宗族在帝王家族的权力分配中已经被摒除在外,更体现了家族观念动摇之后,国家意志取代宗族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秩序的必然性。
[1]杨伯峻.孟子译注·卷6[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孔鲋.丛书集成初编·孔丛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管东贵.从宗法封建制到皇帝郡县制的演变——以血缘解纽为脉络[M].北京:中华书局,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