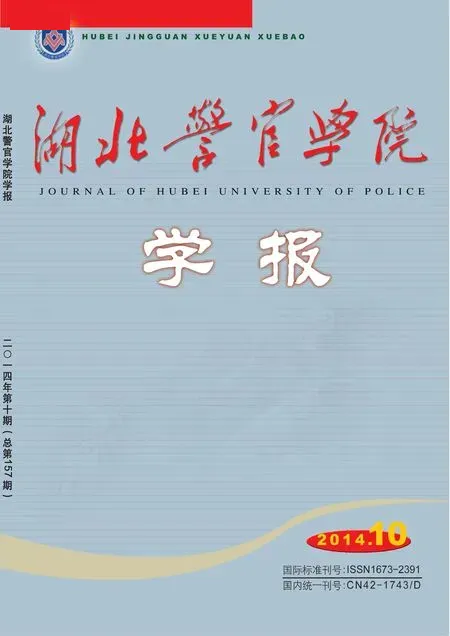家庭暴力的刑法规制和社会规制
2014-04-06马淑欣
马淑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家庭暴力的刑法规制和社会规制
马淑欣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5)
近年来,家庭暴力犯罪在我国日渐突出,不仅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而且危害社会的正常秩序。反思一起家庭暴力案件,有三点启示:无须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须明确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要合理考虑理性民意,化解非理性民意的干扰;完善我国社会救助机制,防止家暴悲剧的续演。
家庭暴力;民意;刑法规制;社会规制
2008年12月15日,董某某与王某某(男)登记结婚,之后王某某多次殴打董某某,最重的一次施暴是在2009年8月10日,王某某对董某某拳打脚踢,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直到妻子倒床为止。两天后的8月12日,董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据法医的证明,董某某的致命伤为肺挫裂伤、腹膜后血肿。
本案是一起严重的家庭暴力案件,年仅二十六岁的董某某在丈夫的折磨中衰竭逝去,一个年轻的生命至此终结,一个完整的家庭不复存在,董某某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更让人忧心的是,类似董某某一样处境的受害者在我国绝非个例。全国妇联2002年的一项调查[1]显示,在我国2.7亿个家庭中,约百分之三十存在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其中施暴主体九成是男性,且施暴手段越来越残忍,妇女受害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有些丈夫对妻子轻则拳脚相加,重则棍棒毒打、刀斧砍杀,甚至用汽油、硫酸焚烧等等;而面对丈夫的施暴行为,57.9%的人会选择“忍气吞声”,38.4%的人会选择求助家人朋友,选择社会、司法途径的少之又少。面对这种社会与司法救助软弱无力的情形,本文拟以此案为切入点,反思家庭暴力的刑法规制和社会规制问题。
一、无须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须明确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本案被告王某某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网民普遍认为判得太轻,司法的公正令人怀疑,甚至有民众称如果把家庭成员打死最多可判七年,把非家庭成员打死最少判十年,那么采用先结婚后打死人的手段何尝不是一种减少罪责的有效途径。本案被害人董某某是独生子女,老两口年岁已高,女儿的死亡使老两口的晚年无比凄凉,面对法院最终判处被告人六年六个月有期徒刑的结果,两位老人表示会誓死为女儿讨回公道,老两口晚年除了要接受女儿离开人世的事实之外,还要继续他们的申诉之路。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致死案件在判决结果上确实存在较大差别,有些按照故意伤害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有些则以虐待致死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有论者直接提出修改虐待罪法定刑的主张。该主张认为,现行刑法对虐待罪规定的法定刑与故意伤害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相比明显偏轻,究其原因,是立法者考虑到虐待行为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社会危害性小,以及出于对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的提倡,但是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实难充分保护受虐者的利益,是对违法犯罪者的一种放纵。正如梅因所言,迄今为止,一切进步都是一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应当树立人权高于亲权的观念,提高虐待罪的法定刑。还有论者规划了虐待罪法定刑提高后的具体适用标准,基本刑设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结果加重犯之刑设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2]
笔者不赞同上述加重虐待罪法定刑的观点。尽管家人对家人的残暴性在虐待罪中着实让人愤慨,正如本案,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被活活折磨打死,实在令人痛恨,但笔者要问,加重刑罚对遏制虐待行为真的有用吗?重刑主义思想是实施专断独裁统治的恶果,它过分强调刑罚的惩罚和报应,忽视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司法实践证明其遏制犯罪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在提倡人道主义理念和弘扬刑法谦抑性精神的时代背景下,不应当把提高法定刑作为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根本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虐待罪中规定的加重结果犯的刑期不能与故意伤害致死规定的结果加重刑期相提并论,两罪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区别:虐待罪在主观上追求的是被害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折磨和摧残,行为人并无意进行伤害,被害人之所以重伤,是长期受虐待的结果,并非行为人主观上希望或放任伤害结果的发生;而故意伤害罪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希望或者放任该伤害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的主观恶性远远大于虐待罪,而且在客观方面伤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也明显大于虐待罪,因此对虐待罪的结果犯给予较故意伤害罪相比较轻的处罚并非不合理。笔者认为,对于该类案件,关键在于正确对犯罪人进行定罪量刑,应该从司法上进一步明确区分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的界限,公布此类典型案例,避免法官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犯罪一律按虐待罪处理的思维惯性。尽管在理论上故意伤害罪与虐待罪的区分问题算是老生常谈,但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之间的脱节还是较为严重的,因此,须在立法层面对虐待罪和故意伤害罪的适用界限作进一步的区分,对违法犯罪者正确定罪量刑,防止家庭暴力实施者逃避法律制裁。
二、合理考虑理性民意
本案经《法制日报》、《中国妇女报》、《法制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后,在新浪网、腾讯网、雅虎网引起了巨大反响,上万人跟帖,引发了社会上的广泛讨论,如何看待这些讨论,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有论者认为民意与审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司法审判若受到民意的左右,其公正性和权威性必定受到破坏,并认为在我国,民意有干涉法官独立办案的嫌疑。也有论者认为民意是刑事审判的基础,是对法律人专业理性思维的补充,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笔者认为,对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进行区分是解决民意与审判关系问题的关键。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民意即人民群众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鉴于公众意见本身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情绪性的特点,再加上新闻报道可能对案件本身并非完全的客观描述而是掺杂着报道者本身的感性思维,这就决定了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可区分为理性民意和非理性民意。理性民意是指社会民众基于朴素善良的正义观以及对刑事审判工作的良性监督,反映社会主流价值的思想或意愿。非理性民意是指被某种煽动性观点左右或者掺杂了个体需求所形成的被表象掩盖了的思想或意愿。理性民意体现了公众的法律正义观,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行为的社会危险性和主观恶性的朴素评价,因此,如果司法机关在处理家庭成员之间虐待致死的案件时能够充分考虑理性民意,就能够更好地契合公众普遍的正义观念。在本案中,广大群众普遍认为,被告主观恶性较大,行为手段恶劣,对其处罚六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明显过轻,对于这些反映社会主流价值的理性的民意,法官在裁判时应当予以考虑。同时,对于非理性的表象民意在排除对本案产生审判影响的前提下,应当予以合理疏导。一方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抵制非理性民意对案件审判的干扰;另一方面,要以公开促进公正,以沟通化解矛盾,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了解真实的案件情况,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提高案件审判过程的公开性,保证案件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接受群众的监督。另外,司法机关可以考虑在法院网站上设立专门论坛回复网民对一些热案的异议,对非理性民意及时回应,消除部分民众心中的疑惑,将非理性民意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综上所述,在处理家庭成员虐待致死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对民意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应对民意进行鉴别,对理性民意予以考虑和吸收,同时排除非理性民意对裁判的干扰。
三、完善我国社会救助机制,防止家暴悲剧的续演
家庭暴力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在董某某报警之后,此类案件没有引起警察的高度重视,被看做是“家务事”草草了之,在董某某遭遇暴打之后,只能选择躲避在亲戚家中,被发现之后就被强行带走,社会没有为其提供一个安全的保护所,最终导致了被害人被活活打死。本案所揭示的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我国反家庭暴力机制的薄弱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其他论者对国外反家庭暴力制度的研究,以下重点建议两项措施:
一是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多机构合作防控家庭暴力机制,形成统一协调的社会救助体系。
目前,我国反家庭暴力社会援助机构大体包括各级政府内管理儿童妇女工作的相关机构、调解委员会、妇女联合委员会、村委会和居委会等,我国学者的调研显示,这些社会救助的作用尚未有效地发挥,反家庭暴力力量不统一,协调能力弱,工作内容较简略。[3]因此,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首先,以各级政府内负责儿童妇女管理工作的机构为代表,发起医院、鉴定机构、社区、妇女联合委员会、律师、组织、警察以及其他政府机构、民间组织的协同合作,并肩治暴,全面构建社会力量防治网络,实现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动态监督,组织各部门认真详细地落实工作,向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提供切实有效便捷的援助。
其次,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同时积极动员社会的募捐力量,设立受害者家暴避难所,防止受害者遭遇虐待之后无处可逃的现象发生,避免更为严重的伤害后果。
再次,重视“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在调和家庭纠纷和预防家暴中的功能,各级政府应调动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和宗教团体,共同参与家庭暴力的防治工作,也可以借助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志愿者、社团等力量,更加全面开展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把将要发生的家庭暴力消除在萌芽状态。
最后,在一些家庭暴力严重的地区,可以设立专门的法律援助和救助组织,在社区设立专门机构,安排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帮助。反家庭暴力专门组织有权提前干预将要或者可能发生的家暴案件,对那些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有权采取果断行动,将受害人及时救出,同时这些组织还可以代家暴受害人向法院提起民事或其他诉讼。例如,山东省烟台市安排专门负责人,建立反家暴庇护中心,庇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举措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其他地区学习。[4]
二是引进“干涉令”制度。
目前,我国公权力对家暴的涉及大都体现在离婚时受虐方提出损害赔偿以及发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尽管符合公权力有限干预的理念,但这种迟到的介入可能催生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恶果。而在英美国家、澳洲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普遍设立了干涉令制度,该制度成为法律赋予受暴者最直接的救济手段,具体是指当家暴行为已经实施或可能实施时,受害人可通过家人、同事、邻居、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人员以及律师向审判机关申请干涉令,证据确凿的,审判机关会向违法者或潜在的违法者发出干涉令,禁止施暴者进入受害人的住所或者尾随受害人等行为,更不得恐吓受害人,不得携带武器等,保障受虐者在一定期限内脱离施暴者。[5]法律赋予干涉令很强的效力,例如,警察对违反干涉令的施暴者有权随时逮捕,同时,对不遵守干涉令行为的人可判处罚金,该违反行为在法律上也被视为犯罪行为,这对于制止当场家庭暴力以及日后可能继续进行的家庭暴力非常有效;而且干涉令制度与刑事诉讼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衔接,如果暴力行为达到触犯刑法罪名的程度,干涉令并不阻碍对施暴者提起刑事诉讼。这样一来长短结合,可以充分为被害人提供司法保障。
家庭暴力不仅需要刑法规制,更需要全社会的综合治理,我国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需要为被害人提供切实高效便捷的救助手段,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家暴悲剧的续演。
[1]全国妇联调查显示:三成家庭存在家庭暴力[ED/OL].http://new 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11/25/content_7141041.htm,200 7-11-25.
[2]陈航.值得深思的刑法宽严倒错问题——以家庭暴力犯罪为例[J].犯罪研究,2007(1).
[3]顾天羽,叶英萍,张浩,宋莉.海南家庭暴力现状与防治初探[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
[4]刘国奎.家庭暴力存在原因及对策探析[J].政法论丛,2004(1).
[5]王春光.澳洲反家庭暴力法律机制及其启示[J].法律适用,2004 (10).
D914
A
1673―2391(2014)10―0102―03
2014-04-21 责任编校:陶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