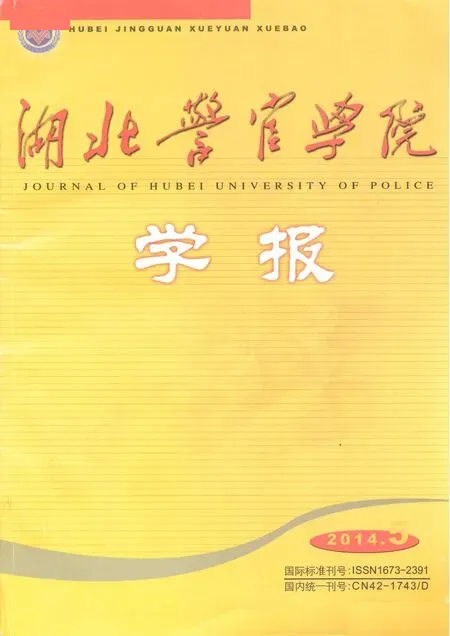我国人身保险利益规定之完善
2014-04-06郑晓薇
李 勇,郑晓薇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广东 广州510610)
我国人身保险利益规定之完善
李 勇1,郑晓薇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2.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广东 广州510610)
人身保险利益一直存有英美法系“利益主义”与大陆法系“同意主义”之争论。我国《保险法》继受此两大法系之时,常有冲突发生,规范方式亦未尽明确。我国《保险法》所采用之“同意主义”已架空“利益主义”,且“利益主义”适用于我国具有一定缺陷,应予摒弃。参照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之优点,应修正同意认定之方式,并规定被保险人撤销同意之权利,以降低道德危险,更好维护被保险人之利益。
人身保险利益;利益主义;同意主义
一、前言
保险利益之概念于保险法中所扮演之角色重要性无与伦比,其所涉及者,非只是保险契约效力之问题而已,更是决定保险标的、保险价值、损害之发生、复保险、超额保险及保险契约利益转移之准绳。[1]保险利益原则是防止保险契约成为赌博之必要条件。若被保险人缺乏保险利益,将有发生道德危险之疑虑,且违背公共政策之目的。该原则在人身保险利益中更为重要。过去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利益之规范,由于无法符合保险业发展的需要,产生了大量的保险合同纠纷。[2]于是,2009年《保险法》修订,针对保险利益的规定作了大幅修改,以适应实务与法制上的转变。[3]在投保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订立人身保险契约之情形中,任何人对自己的生命、身体、健康当然具有保险利益,且投保人亦可任意约定保险金额与指定受益人。此为无问题亦无争执之情形。然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时,对于人身保险利益一直有英美法系“利益主义”与大陆法系“同意主义”之论争,我国《保险法》在继受上述法系时亦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就我国现行法规进行评析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作为日后法律修正之参考。
二、“利益主义”之否定
所谓的“利益主义”,是指投保人以他人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契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益关系或者其他私人利害关系为判断依据,有利害关系则有保险利益。[4]英美法系学者认为,人不是物,具有人格权,故人身不能以金钱估价。人身保险利益需投保人与被保险人间确有利益关系之存在,始具有保险利益。英美法系学者一般认为,保险利益可基于以下两类情形而产生,即与被保险人之血缘或法律关系而生之情感与亲情以及对被保险人之生命、身体、安全有基于法律与实质的经济上利益。[5]
我国《保险法》第31条第1款第2至4项通过列举方式继受了“利益主义”原则。其情感或亲情利益关系表现为:配偶、子女、父母以及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其经济上利益关系表现为: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对于这种具有绝对人身保险利益关系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值得商榷。
(一)漠视生命的历史观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横尸遍野”的词语。一个“族”字当动词使用,意味着至少几百人就莫名其妙被夺去生命,连婴儿也不能幸免。腰斩、凌迟、杖毙等对于受之者会造成巨大的痛苦。王朝之大臣一旦获罪,几乎都是死罪,很少有徒刑。最轻的是“废为庶人”或出钱“赎为庶人”。按史书所记,即使回家成为一个普通百姓,也往往不能善终,一旦遇到有人揭发,仍不免一死。古代死刑以下有流放或者肉刑,后者即砍掉肢体与器官。在汉朝文帝时期,有一项“仁政”,就是部分地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废止肉刑。贾谊认为,公卿大夫既然被任命管理百姓,就应有尊严。即便获罪,也要待之以礼。可以罢官、赐死,甚至灭族,但要存体面,不能随意割鼻、砍脚,由一个小官吏对其进行侮辱或“弃市”。否则,上下都不知廉耻,也不利于获罪者以后改之。这其实就是“刑不上大夫”的意愿。“刑”是指侮辱人格的肉刑。文帝废除了一部分肉刑,而剃光头、打板子与“弃市”还是保存了下来。而且,打板子变本加厉,如该削鼻子的打三百,该削左脚的打五百,但真正受到上述惩罚的人却难以存活,故人称文帝此举有“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景帝时期再一次减刑,减笞五百为三百,减笞三百为二百。这种刑罚不但肉体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可杀,不可辱”,所以大臣们自杀的较多。因此,司马迁才作《报任少卿书》,解释自己何以受腐刑之大辱而未自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少卿自己还未自杀,却被腰斩于市。
还有一项就是吃人。灾荒年代会出现百姓“人相食”的惨状,并且汉高祖刘邦的刑罚之一就是“烹”。彭越被煮熟后剁成肉酱,还分于群臣食之。至于敌人,根本就不以“人”待之。汉朝武将评功是以敌人头颅数目计。杀人不够数目,不论战功具有多大意义,都不能封爵。对敌人“食肉、寝皮”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应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传唱至今。所以,对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不仅可作象征意义上封建礼教杀人的理解,实实在在的吃人是堂而皇之被载入史册的。
诚然,历史是从野蛮一步一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公社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与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一血腥的历史;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怎样衡量自己的生命,是值得反思的。人身保险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彼此尊重生命、呵护生命,要求人们具有正确的生命态度。这才是人身保险的本质所在。然而,我们的生命观是值得怀疑的。故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认定必须谨慎,才能更好地保护生命。
(二)情感与亲情之淡化
中国社会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中国传统文化中流淌的是伦理本位观念的血液。这一观念也可以被称为关系社会、熟人社会。社会中的个体都是伦理人。人一生下来,便有与他相关之人。人将始终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生活。如此则知,人生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即是种种伦理。[6]伦理关系是情谊关系,亦即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而一概伦理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伦理人之于社会中,即每一个人对于四面八方的关系各负有相当之义务;同时,四面八方与他有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并首先在经济上表现出来。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体皆以为不义,将受到道德的谴责。大家在交易过程中注重亲情伦理关系而较少选择陌生人,造成了交易半径的有限性,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这里却是攀关系、讲交情。[7]社会经济伦理化的结果便是市民社会的难以形成。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难以产生民商法的发展模式。
图2为长沙地区63年年雷暴日小波系数实部等值线。由图2可以看出,雷暴日演化过程中存在多时间尺度特征。总的来说,长沙地区雷暴日变化过程中存在5~6年、13~14年的尺度周期变化规律。其中,在5~6年、13~14年尺度上均出现了谷-峰交替的准3次振荡;同时,还可以看出以上两个尺度的周期变化在整个分析时段表现比较稳定,5~6年左右的周期振荡在1965—1980年表现明显,1980年左右,5~6年的周期信号呈减弱趋势,逐渐变为13~14年的周期振荡信号。
然而,全球人口的自由流动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社会的面貌,尤其是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伦理面貌。这提醒我们,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由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在《美国法简史》中首次提出。陌生人社会常常被看作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产生的。现代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在中国尤甚。而且,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得以经久保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突飞猛进,“陌生人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困惑才逐渐显现出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经济利益日益成为人们价值观的标杆,“一切向钱看”成为俏皮的流行语。从字面解读,“一切向钱看”就是拜金。这意味着经济考量压过了其他任何价值追求,如法律、道德,成为社会运作的首要原则。似乎只要抱定这一原则,就可以漠视法律,不屑道德,几乎没有任何边界。一个社会如果唯经济利益马首是瞻,缺乏法律和道德的规范,生存风险必然会增大,而安全感的缺失将进一步加剧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
“陌生人社会”的论述所隐含的话语逻辑恰恰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陌生化,即陌生人已然成为社会的主体,导致与加剧现代社会的疏离与落寞、复杂性与风险性。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父母杀害亲子女、子女伤害亲父母等一系列“人伦失常、道德失范、人性冷漠”的事件的出现,“现代化”发展模式才饱受质疑和批评。总之,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化,人身保险利益中的天然法定关系受到质疑。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相信,凡是与自己无关的,就一定是归社会管理的;反之,属于自己的,就应当拼命追求,不惜一切代价。情感的消失和伦理的失常使我们要求,在人身保险契约的订立中,人身保险利益应坚持被保险人同意原则和相信自己的选择、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契约价值标准。取消一些天然的情感关系,更能有效保护被保险人的健康与生命,契合保险的本质。
(三)劳动者团体保险之困惑
“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乃2009年我国《保险法》新增加的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雇主为职工购买团体保险的问题。由于实务中以团体形态签订保险契约能以集体之力量与保险人缔约,提升其谈判地位与议价能力,而且团体保险之运作可以节省保险人之行政管理成本,其保费通常较个人保费低廉,[8]团体保险因此而逐渐盛行。然而,团体保险之“投保团体”欠缺保险利益的问题并不限于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之劳动者,其种类尚包含学校为学生所投保之学生团体保险等非劳动关系构成之团体。立法者是否有意排除此等团体投保团体保险之可能,抑或仅为立法疏漏,尚有探求之余地。
我国《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为解决团体保险中“团体”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我国采取了修订《保险法》之方式。然而,此举并未完全解决团体保险中“团体”不具有保险利益的问题。若非基于劳动关系,团体保险则无本项之适用,且易使企业为一般员工投保人身保险,引发道德危险。虽然《保险法》第39条第2款规定了受益人的特殊范围,以此谋求补救,惟终属对雇主团体保险出于误解所为之舍本逐末之举。
笔者认为,在团体保险中,只要破除以“团体”为“投保单位”之迷惑,将团体成员视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将团体定位为投保人之代理人,即可在现行《保险法》与保险理论下解决实务之难题,而无需修订我国《保险法》第31条第1款第4项。否则挂一漏万,使劳动关系以外之团体保险徒生争议。将投保人定位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即可解决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同所产生保险利益及被保险人同意等问题;亦可由员工自行指定受益人,只要规定企业或雇主不得为受益人,即可降低道德风险,保障员工利益。至于投保人之人格问题,亦可因其为自然人而不需考量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当然,若被保险人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如学生团体),则需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实属当然。
三、“同意主义”之完善
所谓的“同意主义”,是指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契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不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均以投保人是否已经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判断依据,投保人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订立保险合同的,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9]采取此种原则的有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韩国等。我国《保险法》第31条第2款将被保险人同意视为具有保险利益,即属继受“同意主义”原则。
(一)增设被保险人任意撤销权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05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依前项所为之同意,得随时撤销之。其撤销方式应以书面通知保险人及要保人。”同条第3款规定:“被保险人依前项规定行使其撤销权者,视为要保人终止保险契约。”此规定使部分人身保险契约虽然于订约时已经取得被保险人同意,事后在有道德危险发生之担忧时,被保险人可通过撤销同意的方式使保险契约无效,以保护被保险人。然我国《保险法》采用同意原则时,并无被保险人的任意撤销同意之规定,对被保险人之保护似有不足,有待完善。
(二)同意认定形式之改进
我国《保险法》第31条第2款规定被保险人同意视为有保险利益,但并未规定同意的方式。2009年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将原《保险法》第56条第1款“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修改为“被保险人同意”,使被保险人同意的方式不再限于书面同意,而是口头或电子形式、明示或默示,甚至事后追认皆可。以相同理由解释,此处的“同意”亦可以任何方式为之,较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05条第1款要求之“书面同意”宽松许多。当双方对被保险人是否“同意”存有争执时,在欠缺有利证据之情形下,将增加保险纠纷处理判断及法院审理之难度,考验司法机关对“同意”如何认定的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应修改为“书面同意”方式,减少不确定性与纠纷,更好地维护被保险人之利益。
(三)特殊人群之保护
此处的特殊人群是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同意主义”要求被保险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若被保险人属特殊人群且参与保险,此时需特殊处理,即由其监护人代其作出书面同意。我国《保险法》第39条第3款规定:“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借鉴此款的模式,可修正特殊人群之同意方式,由其监护人代理,以保护特殊人群之利益。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保险法》对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规定采取“折中原则”,即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或者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为判断依据,或者以投保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判断依据,[12]体现为第31条“利益主义”与“同意主义”相结合,存在一定的冲突和适用困境,应予以修正。笔者认为,“同意主义”适应人身保险利益之要求,对人之效力更为灵活,更具操作性。其尊重被保险人之权利,能够有效防范道德危险。而“利益主义”具有一定的僵化性,缺乏对被保险人权利主体地位之尊重,甚至忽视情感与经济利益之变化,并不能杜绝赌博和道德危险之发生,也不能有效保护被保险人之利益。[13]故建议删除第31条第1款,修改第2款,增加被保险人撤销权及特殊人群保护之规定,具体法律条文如下:
第31条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作出书面同意。
被保险人或其监护人所作出的书面同意,可以随时撤销,其撤销方式应以书面通知保险人及投保人;其行使撤销权,视为终止保险契约。
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1]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7.
[2]晓静.论保险利益以及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6):96.
[3]邵祥东.论我国保险法中保险利益规则的完善[J].咸宁学院学报, 2010(8):9.
[4]吴定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85.
[5]Bloink,RobertS.Catalysts for Clarification:Modern Twists on the Insurable Interest Requirement for Life Insurance[J].Connecticut Insurance Law Journal,2010(1):55-59.
[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11:10.
[7]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26.
[8]林建智,彭金隆,林裕嘉.论团体保险当事人之法律问题及示范条款之修订建议[J].保险专刊,2009(25):77-79.
[9]张海棠.保险合同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36.
[10]许崇苗,李利.最新保险法适用与案例精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88-89.
[11]张秀全.人身保险利益质疑[J].郑州大学学报,2000(6):72.
[12]奚晓明.新保险法热点与疑难问题解答[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48-49.
[13]程兵.人身保险利益确认原则之解析[J].南京社会科学,2008 (11):92.
D922.284
A
1673―2391(2014)05―0123―04
2013-10-15 责任编校:王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