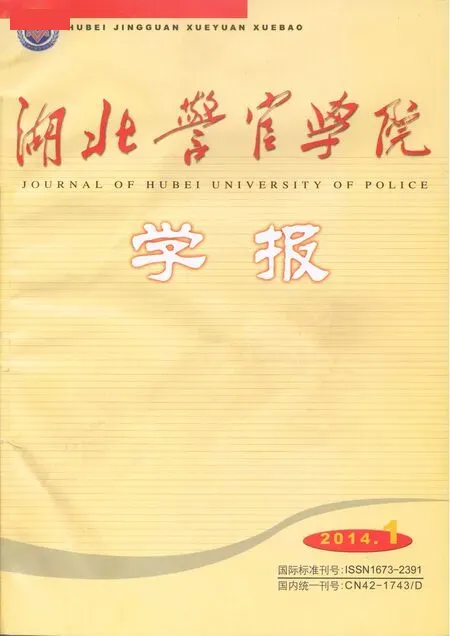论唐代恩赦中的免债
2014-04-06王栋
王 栋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215002)
所谓“恩赦”,泛指皇帝所颁布的大赦、曲赦、降罪、录囚等,乃是皇帝专属的仁德措施。古代帝王肆赦频繁,举凡践祚、立储、郊祀等,往往有赦。据学者粗略统计,中国自秦始皇至溥仪两千多年的帝制中,皇帝竟大赦了一千两百多次。若再加上曲赦、降罪、录囚等其他恩德赦宥措施应不下于两千次。[1]皇帝频繁而制度化地颁布恩赦,迥异于古代其他法系,实乃中华法系的一大特色。笔者在阅读“恩赦”制度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学界对“恩赦”效力和范围方面的讨论和研究往往局限在刑罚方面。即使是法制史著作亦在所难免,或以为恩赦“其用意在慎刑恤囚,与刑之宥减相互为表里者也。”[2]或认为恩赦系“皇帝以其恩赦权,原免或降刑之制”[3]。但实际上,恩赦的范围不仅仅限于赦过宥罪。其还包括恩赐部分。皇帝经常在恩赦中附带赏赐官人爵位、加阶,甚至免除民间公私债务等恩惠。但学界对其中恩赐部分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唐代恩赦中免除公私债务内容进行探析,从而更加全面地认知恩赦制度。
一、唐律中的恩赦以及免除公私债务的一般性规定
在唐律中,关于恩赦的规定主要涉及免罪、赦书执行等情况①唐律中涉及恩赦的条文主要有“正赃见在及会赦降之处置”(33)“略人等犯罪会赦限外故蔽匿之处置”(35)、“会赦应改正征收”(36)、“稽缓制书及官文书稽程”(111)、“改赦前不当之断罪及赦书定罪合轻而有违”(488)、“知有恩赦故犯及会赦犹流之犯罪”(489)等条文。。如唐律“略人等犯罪会赦限外故蔽匿之处置”条(35)便对遇赦自首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定。规定如“略、卖人及部曲奴婢”,“署置官过限及不应置而置”,“诈假官,诈死”,“私有禁物”等这类犯罪后果呈持续性的犯罪,在遇赦后必须在赦书到后的百日内自首,并且不使犯罪造成的非法状态继续,否则不予赦免。
但是对免除公私债务部分,就笔者目力所及,并无相关直接规定,可能有关恩赦执行的法律责任会间接涉及到一些。如唐律“负债违契不偿”条(398)的末尾部分,规定了百姓欠负公债“经恩不偿”“科罪如初”的处罚方式,即“……及恩不偿者,皆依判断及恩后之日,科罪如初”。[4]
在恩赦条件下,免除民间公债的大多数规定以及免除私债的规定,都以“特殊法”的形式,基本上都在赦书中体现。
二、唐代恩赦中免除公私债务之内容
恩赦乃皇帝非常之惠,为了普天同庆、雨露均沾,皇帝自然不会厚此薄彼,仅仅对罪犯赦过宥罪,也会对天下百姓施恩布德。所以恩赦中亦会有免除民间公私债务的内容。恩赦中附带免除民间公私债务最早可以溯至汉武帝时期,《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3月甲子条记载:“立皇后卫氏。诏曰:‘朕闻天下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三年以前,皆勿听治’。”
唐代免除公私债务,大致应始于高祖时。武德六年(623年)六月《劝农诏》记载:“其公私债负及追征输送,所至处,且勿施行。”[5]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且勿施行”,还不等于免除,只是暂时不施行。不过其后的恩赦中免除民间公私债务的传统,却一直保持下来。
(一)关于免除公债
在唐代,附带减免公债的恩赦,屡见不鲜。如代宗乾元元年(758年)五月《代宗即位赦》中记载:“大赦……免民逋租宿负……”。[6]德宗建中五年(784年)正月《奉天改兴元元年赦》中记载:“其除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酒钱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京畿之内……宜特减放今年夏税之半。”[6]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改元元和赦》诏曰:“京畿诸县,今年十二月苗钱及榷酒钱,并宜放免,地税率每斗量放二升。”[6]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南郊改元赦》,下诏:“天下百姓,今年夏税,每贯放一百五十文。”[6]
百姓欠负公债不偿,唐律中明确规定了处罚方式,依唐律“负债违契不偿”条(398)规定:“负债者,谓非出举之物,依令合理者,或欠负公私财物,乃违约乖期不偿者,一匹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若更及延日,及恩不偿者,皆依判断及恩后之日,科罪如初。”
由此可见,百姓若违约不偿,最高可处之以徒一年。即使是逢遇恩赦,刑事责任虽然可以免除,但是其欠负之公债仍然需要清偿,若仍不清偿,则对其处罚自赦后之日计算。所以,除非恩赦中直接免除公债,否则,对无力偿还欠债的百姓而言,恩赦只是画饼充饥罢了。
纵观唐代恩赦,虽然赦文中经常附带免除百姓对国家的债务,但其所免除的大多为年代久远之公债,而百姓大多早已缴纳,因此百姓实际受惠并不多。譬如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的德音,免除了贞元十一年(795年)至十年(799年)的欠债。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南郊恩赦,免除元和十三年(818年)以前所欠负诸色钱物斛斗。
(二)关于免除私债
由于史文有阙,除上述的高祖武德六年(623年)六月《劝农诏》,笔者仅在唐代史料中发现三处恩赦提及到免除民间私人债务: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上尊号赦》;穆宗长庆四年(824年)三月制书;以及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四月《册尊号赦》。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上尊号赦》曰:“门下……御史台及秘书省等三十二司公廨及诸色本利钱,其主保逃亡者,并正举纳利,十倍已上;摊征保人,纳利五倍已上及辗转摊保者,本利并宜放免。……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主保既无,资产亦竭,徒扰公府,无益私家。应在城内有私债,本主及元保人死亡,又无资产可征理者,并宜放免。”[7]该赦文对准予免除的私债的条件颇为严格:第一,范围仅限于京城处;第二、债务须已达十年以上;第三,债务人和原保人均已死亡;第四,债务人无资产可偿还。
至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年三月三日(其时敬宗已即位),制书确定:契不分明,争端斯起。况年岁寖远,案验无由,莫能辩明,只取烦弊。百姓所经台府州县论理远年债负事,在三十年以前,而主、保经逃亡,无证据,空有契书者,一切不须为理。[8]
与宪宗《上尊号赦》相比,出现了如下变化:第一,将范围从京城扩展为全国;第二,债务须达到三十年以上;第三,债务人和保人逃亡而非死亡;第四,只有契约而无其他证据。仅从变化的第二项来看,试问整个天下间有多少债务人能够安然欠债三十年以上,可见该内容可操作性不强,社会实效不足。
所以,在次年,即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四月的《册尊号赦》表达了与宪宗朝的《上尊号赦》类似的立场,赦书中记载:“应京城内有私债经私债经十年以上,曾出利过本两倍,本主及原保人死亡,并无家产者,宜令台府勿为征理。”[9]与宪宗朝的赦书相比,敬宗时改“放免”为“勿为征理”,不排斥民间债权人的私力救济。同时,又增加了“曾出利过本两倍”的条件,《杂律》对“出举”有计息不过本之规定,该条件只是将百姓私人间的债务回到法律立场,因为“曾出利过本两倍”,意味着债主已经取得了一本一利,官府再帮助追征便是支持违法积利。[10]
从上述的恩赦中可见,虽然恩赦中有附带免除民间私人债务内容,但是条件都比较严苛,试以《上尊号赦》为例,在债务人和保人均死亡且无财产可以征理情况下,有多少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到清偿,这不无疑问。
纵观整个唐代,即使史料有阙,但附带免除民间私债的恩赦,仅能够发现数处,同时免除私债条件严苛,以上种种从侧面反映出唐代恩赦极少附带免除百姓私人间债务。这或许是由于“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原则,对于民间有息借贷,官方秉持的原则是“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即一切权利义务,仅凭双方契约规定,官方并不干涉,官方只是对借贷双方作出一些基本性的规定。①当时官府对利息作出上限,即月息6%(年息72%)以及禁止复利计息等。同时,唐代私人高利贷兴盛,且放贷主体大多是富商大贾、官僚、寺院等等,如史载太平公主家“财贷山积,珍物侔于御府”,被籍没时“息钱收之数年不尽”。[11]这些权贵阶层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皇权的稳固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这亦或是皇权对当时庞大的放贷群体的一种妥协。
三、唐代恩赦中免债部分发生之原因
据台湾学者陈俊强统计,唐一代恩赦,共计四百五十三次[12],虽然附带免除民间债务仅有数处,但是大多恩赦都附带免除百姓所欠负之公债的内容。一项制度存在并长期发展,必然有其独特的原因,恩赦亦不例外。恩赦中的免债部分更是有其理论根源和深刻的时代背景。
(一)理论根源
1.仁政思想
杨鸿烈先生认为“儒家传统的理想为‘仁政’,赦也是‘仁政’的一端。”[13]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唐代君主为仿效前代明君仁主,纷纷恩赦,以彰显仁政。如僖宗乾符二年(875年)《乾符二年南郊赦》:“昔殷汤解网,实谓至仁;汉文措刑,永称至理。在宥乃人君之德,好生实有国之规。”[6]要行王道,惟悯物是先;要做明君,只有任德,而悯物、任德的表现就是多行恩赦。在该背景下,唐代皇帝为与前代明君仁主相比肩,常常施行恩赦,广布恩惠,以彰显其仁政。[14]
2.天人感应理念
董仲舒据《公羊传》集天道灾异说之大成,形成天人感应之理念,即天是最高的人格神,皇帝是天的代表,受命于天。天降祥瑞是在表彰君主顺天守时,而灾异则表明天子违背了天意,不仁不义,上天对此进行谴责。该理念论证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天的至高无上,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人间君主的统治。自汉武帝时起,该理念被历朝历代的皇帝所采纳,唐代亦不例外。所以,一旦出现灾异现象,唐代皇帝出于对上天的敬畏,一般都会进行恩赦,施恩布德,赦过宥罪,放免百姓租税,以反省修德。据台湾学者陈俊强调查统计,在唐一代因灾异而进行的恩赦多达84次,其中因天文异象而进行的恩赦13次,因彗星见而恩赦更是达到10次。[12]
3.家国同构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由于古代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国同构”亦长期根植于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家与国的系统组织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在“家国同构”的总体社会特征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万物实际上皆为皇帝一人所有,百姓对自己物的支配只是给皇帝代管罢了。按现今的术语作出类似的定位:皇帝乃所有权人,百姓只是用益物权人。同时,唐代高利贷发达,百姓因借贷被囚禁、破产的情况非常普遍。人君常出于”父家长“的责任心,借恩赦免除民间公私债务,以解黎民之疾苦,使其安居乐业,从而达到社会稳定。
4.道佛因素
终唐一代,李氏皇族对道教都极为尊崇,将道教视为“本朝家教”。如武德八年(625年),高祖下诏叙三教先后,以道教为尊,儒次之,佛最末。开元九年(721年)玄宗更是亲受司马承祯法箓,成为“道士皇帝”。武宗亦于开成五年(840年)亲受法箓。由此观之,道教思想必然影响唐朝皇帝的统治。睿宗曾就治国之道请教于司马承祯,其答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也。”睿宗对此赞赏不已。[15]司马承祯关于治国之道的解答,即是道教所提倡的“身国同构”理论,即《抱朴子·地真》记载:“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鉴于此,唐代皇帝时常施赦以解百姓生活之困苦,如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改元天宝赦》中记载:“古先哲王之教理也,皆上顺天心,下稽人事。时令赞发生之德,灵符叶纪年之称,考彼前载,斯为大猷。恭惟烈祖玄元皇帝,天宝锡庆……一家之中有十丁以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6]
唐代佛教亦十分盛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不翕然信之,“会昌灭佛”可见一斑。佛教提倡轮回和报应,功德轮回思想自然随着佛教的普及而深入人心。如刘后滨认为:“从民间社会价值观念看,尽管佛教因果报应在两晋南北朝时即有一定社会影响……而随着隋唐之际就日益扩大影响的阿弥陀佛净土信仰在中唐以后的广泛流行,因果报应的观念便深入人心,成为民间社会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6]在此社会风气下,皇帝亦不能免俗,也希望通过频施恩赦,以积阴德,佑其自身,延其国祚。如贞观五年(631年)五月,太宗以太子承乾疾笃,下诏降囚徒。希望施恩于百姓,以求太子之平安。贞观八年(634年),长孙皇后病危,或许承乾以昔日因太宗降囚徒祈福以致其病愈,遂密启后曰:“医药备尽,尊体不瘳,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但皇后最后以“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而拒绝。[15]
(二)现实原因
1.巩固皇权
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尤其穆宗朝后,皇帝内则受制家奴,外则强藩跋扈,皇权日益衰弱。皇帝时常下诏恩赦,赦过宥罪,免除民间公私债务。这一方面既可以强调其君主名分,提振其威权;另一方面,又可以安抚藩镇,收拢民心,缓解社会矛盾,稳固其统治。如宪宗朝的恩赦中,有三次是与藩镇有关,分别是元和七年(812年)田兴以魏博归顺,元和十三年(818年)平淮西,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以各处藩镇复听中央而加尊号等。[12]
2.遏制民间高利贷
唐代民间高利贷发达,其一方面促进了货币流通,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多数小生产者生活日益艰难,甚至破产,最终沦为佃农或奴婢。如大和十一年九月,据东都御史台奏称,从贞元十一年至元和十一年,东都洛阳借官高利贷利息超过本金十倍以上者二十五户,七倍以上者一百五十六户。有的举债人自己和子孙死殁后,放贷人向亲族旁支及保人追索,导致保人纷纷逃亡。[11]官高利贷既然如此,更毋论私人高利贷。上文提及的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上尊号赦》记载:“京城内私债,本因富饶之家乘人急切,终令贫乏之辈陷死逃亡”,京畿之内尚且如此,更勿论全国。所以,民间高利贷高度繁荣的同时,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危及皇权的稳固。所以在《上尊号赦》中,宪宗下诏有条件地免除了京城内民间私债,虽然条件严苛,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官方的态度,多少能够缓解过于激化的社会矛盾。
3.促进农业生产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同时社会经济又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因而农业生产最宝贵的莫过于劳动力。白居易在《奏阌乡县禁囚状—虢州阌乡湖城等囚事宜》一文提及的阌乡县百姓因欠负公债被囚禁,这应并非个别现象、一地之事。因此白居易以为“臣兼恐度支盐铁史下诸州县禁囚更是如此”,[17]提请人君谨慎处理此事。大量百姓欠负官物被禁系狱中,自然而然地会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皇帝经常下诏恩赦,赦过宥罪,放免百姓租税,解放劳动力,以促进农业生产。如开元十六年(728年)正月《兴庆宫成御朝德音》:“属春令为始,时惟发生……宜施惠以布德,况农祥在候,稼穑正兴。或幽彼囹圄,独隔阳合之泽;或迫于征徭,不遂农桑之务,言念及此,轸叹良久。其徒以下罪,日令责保并应当番兵、丁、匠等灼然单贫者,所由勘会,并放营农……非军国所要,余不急之务,一切并停,仍加劝课,循植农穑。”[14]
四、唐代恩赦免债之实施
法律在文字层面和社会实效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恩赦中的免除债务部分在社会施行的过程中与相关规定亦存在一定的脱节。但就总体来看,公债部分执行的情况,在唐中前期良好,至于私债部分,民间一直呈现出抵制的态势。
(一)官府的执行情况
从上述《户婚律》169条和173条规定来看,对恩赦中免除公债部分,官员如不执行或执行不到位,最重可处加役流,处罚可谓十分严酷。所以,在整个唐代,恩赦大致得到落实。譬如武后天册万岁元年,刘知几的奏章中记载,时人皆知恩赦每年必有,甚至有时不止一次,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怪像:“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了无疑惮。”[12]这样的社会现象,足以证明恩赦得到官府的执行。
但自中唐之后,藩镇割据,皇权旁落,君主的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恩赦的执行也出现了问题,有时地方官吏阳奉阴违,徒使皇帝恩德流于空文。如贞元二十一年(805),京师旱,有诏蠲畿内逋租,但京兆尹李实“诏征之,百姓大困,官吏多遭罚”。[15]晚唐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据《乾符二年南郊赦》记载:“朝廷大弊,在于令不行。只如经水旱州,三降敕命,不许将逃亡规摊见在人户;遭灾水旱处,有于见在户两倍征或至三倍。”皇帝并不是没有体恤百姓,朝廷已三度下敕严禁水旱州摊逃,但恩赦根本没有被落实执行,地方官员照样摊逃,导致见在户的税收竟至两三倍。[12]
(二)民间的施行情况
虽然唐代免除私债的恩赦条件十分严苛,抑或对债权人利益损害较为轻微,但皇帝的这种仅凭一纸诏书就免除百姓私人债务,仍然构成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侵害。为了保障其自身利益,民间的借贷契约遂发展出相关的抵赦条款。在敦煌出土的吐蕃和归义军的各类契约中,尤其是借贷契约,经常都订立抵赦条款。如《酉年(829年?)敦煌曹茂晟便豆种帖》记载:“如身东西,一仰保人代还。中间或有恩赦,不在免限。”[18]类似的条款见于同类契约中,如《寅年(834年?)敦煌阴海清便麦粟契》[18],《寅年(834年?)赵明明便豆契》[18]。不仅仅借贷契约,其他诸如租佃契约、买卖人口契约都有类似条款①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附带恩赦排除条款的买卖契约,都是以买卖契约为外衣来掩盖借贷契约之实的契约。,尤以买卖田宅契约最多。如《唐乾宁四年(897年)平康乡百姓张义全卖舍契》便记载:“或有恩敕赦书行下,亦不在论理之限。”[18]
借贷契约中的抵赦条款固然具有保障债权人的目的,不过恩赦与抵赦条款二者间,究竟何者的效力更高?敦煌文书中恰好有这样一个案例可以释疑。
《乙亥年(915年?)金银匠翟信子等三人状》:“金银匠翟信子、曹灰灰、吴神奴等三人状右信子等三人……判词:其翟信子等三人,若是宿债,其两硕衿放者。”[18]翟信子等三人于甲戌年向高康子借麦三硕,当年秋天本利已达六硕,其时偿还一硕二斗。乙亥年本利累计达九硕六斗,丙子年偿还七硕六斗,尚余二硕。丁丑年适逢恩赦,“衿割旧年宿债”,但高康子不肯放免剩余二硕的债务,翟信子等遂具状申诉。最后,判决翟信子三人无需偿还二硕的债务。
从诉状所交代的债务偿还状况,可知翟信子借麦三硕,前后共偿还八硕八斗,就利率而言,已超过官方规定的月息6%,亦违反了不得“回利过本”的原则。此外,翟信子等人与高康子所订的契约里,是否附带抵赦条款的规定,不得而知,但是按照敦煌订立借贷契约的惯例来看,应当是有相关条款的,否则高康子也不敢不遵守恩赦的规定。这样的判决结果,似乎意味着恩赦的效力仍然高于民间私约。
五、结语
纵观唐代恩赦,会发现,皇帝为行惠无偏,使兆民雨露均沾,其不仅仅对罪犯赦过宥罪,亦会对百姓施恩布德。皇帝直接免除民间私人债务的行为,明显是对百姓“私”权利的践踏,这也反映出唐代“公”、“私”领域不分,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何以唐代刑法成熟,民法却不发达的原因。然而,民间的借贷契约或某些特殊的“买卖契约”发展出相应的“抵赦条款”以排除“恩赦”的效力。这反映出百姓对“私”权利的认识程度,也从侧面反映了法律的社会实效问题即文字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的差距。
[1]陈俊强.中国古代恩赦制度的起源、形成与变化[A].张中秋.中华法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 007:178.
[2]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12.
[3]戴炎辉.中国法制史[M].台北:三民书局,1969:132.
[4]钱大群.唐律疏议新注[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46-847
[5]王钦若,杨亿等.册府元甲[M].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 70.
[6]宋敏求撰.唐大诏令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7]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卷 422.
[8]窦仪.宋刑统[M].北京:中华书局,1984:414.
[9]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卷 88.
[10]霍存福.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3):8.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 210.
[12]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3]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5.
[14]邵治国.浅析唐代赦宥实施的原因及其利弊的讨论[J].阴山学刊,2001(2).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6]刘后滨.传奇小说反映的唐中后期民间因果报应观及佛教净土信仰关系[A].郑学檬,冷敏述.唐文化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7]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355-3357.
[18]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