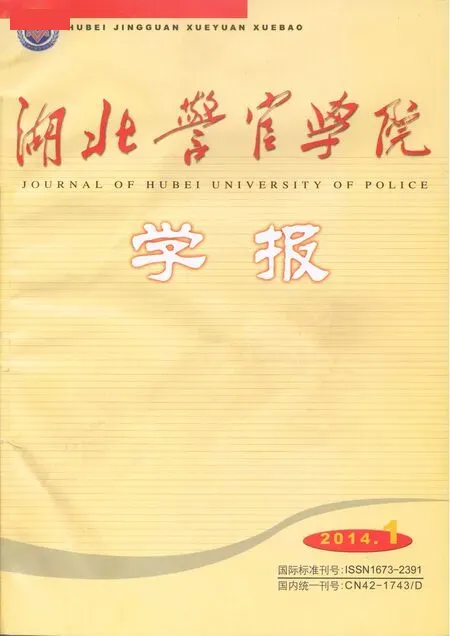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2014-04-06江兆涛
江兆涛
(宁夏大学,宁夏银川750021)
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江兆涛
(宁夏大学,宁夏银川750021)
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清代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出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清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对当时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终被近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取代。
法制史;清代民事诉讼;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民事诉讼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然而在如何认识清代民事诉讼性质问题上,中外学者仍存在较大分歧。那思陆、曹培、郑秦、张晋藩等诸位中国学者均认为在清代民事诉讼中,调处息讼广泛存在,州县官批令亲族等人调处或亲为调处;州县官对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无须完全遵照律例。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教授认为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缺乏“判定的契机”,实为“教谕式的调解”。美国学者黄宗智教授认为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严格按照律例进行;在州县官审判之外则存在一个介于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之间的“第三领域”,大量民事案件在“第三领域”获得解决。①参见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259页;曹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初探》,《中国法学》1984年第2期;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20页;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93页;[日]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姚荣涛、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6页;[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64-111页等。中外学者关于清代民事诉讼性质的分歧,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在清代民事诉讼中究竟存在哪些纠纷解决机制?二是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具体如何运作?
清代民事诉讼性质问题实质为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笔者以为从中国传统无讼的法律文化背景出发,考察、辨析清代民事诉讼具体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相互间关系,或许是探讨清代民事诉讼性质的一个有益途径。
当然在考察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及其运作之时,笔者并没有忘记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下,“县衙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院,州县官也不同于现代意义的法官”,“当时州县官是统管一方的牧民之官,审断诉讼不过是他们治理地方职责的一个部分”,“在整个审断过程中,没有现代司法意义上的严密程序性规则,更不会为了程序性的价值追求而牺牲实体问题的解决。”[1]
一、无讼价值追求下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基本处理方式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周易正义·讼卦》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孔颖达疏曰:“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得吉也。‘终凶’者,讼不可长,若终竟讼事,虽复窒惕,亦有凶也。”“在古人眼里,兴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威胁,是陷人心于不古的权利之争和使人格与族望扫地的恶行。”[2]
传统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深刻地影响了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基本处理方式。
(一)官箴书的记载
从官箴书的记载来看,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普遍秉持息讼政策。
州县官常以发布劝民息讼告示的方式,对民众晓以利害,劝民息讼。①这方面的记载在清代官箴书中颇为常见,可参见潘月山:《未信编》(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卷三,“劝息讼示三首”;黄六鸿:《福惠全书》(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卷十一,“劝民息讼”;刘衡:《州县须知》(宦海指南本),“劝民息讼告示”;觉罗乌尔通阿:《居官日省录》,卷四,“劝民息讼”等。
在州县官看来,“两造非亲则故,非族则邻,情深累世,衅起一时,本无不解之仇”[3],故“户婚田土细故,果能按事切理,导以利害,谕以情法,剀切批示,有以折服其心,使无可置喙,亦可随时消释;如开导之不足,则批亲邻调处,以次寝息。”[4]即对于当事人的起诉,州县官主张“先论以息讼或令乡保处和”。[5]
对于已经准理的民事纠纷,如在堂判结案前以调处方式获得了解决,本着息讼理念,州县官一般均予以批准。如汪辉祖曰:“间有准理后亲邻调处吁请息销者,两造既归辑睦,官府当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宁人之道。”[6]
(二)司法档案的记录
为具体考察州县官息讼的实践,笔者从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中随机抽取了发生于同治、光绪年间的100例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结案方式不详者36例;州县官直接驳回、“不准”者11例;州县官批饬保约族邻等人调处者20例;州县官已经准理、传唤,但在堂判结案前经州县官批准由保约族邻等人以调处方式和息结案者9例;经州县官堂判结案者24例。可以说,在同治、光绪年间,紫阳县历任县令对民事案件的处理总体上忠实地秉持了息讼政策。这与前文官箴书中有关息讼的论述是一致的。
事实上,紫阳档案所显示的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忠实地贯彻息讼政策的现象在清代是普遍存在的。这已为学界对各地司法档案的研究所证实。②可参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日]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法律制度),姚荣涛、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34页;邓建鹏:《纠纷、诉讼与裁判——黄岩、徽州及陕西的民诉案研究》,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88-89页等。
通过对清代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无讼观念的影响下,州县官普遍将民事案件视为“细故”,秉持息讼政策,较少直接审理,更多的是将其批饬保约族邻等人调处或者直接以“不准”的形式驳回。
在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中,有较完善的运作程序,能够对纠纷予以实质性解决的是州县官批饬调处与州县官审判两种。笔者以为对清代民事诉讼性质的考察,应全面、准确关注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各种处理方式,仅仅关注州县官审判并不全面;③滋贺秀三等日本学者早期的研究即仅关注了州县官审断部分。不过日本学者很快即意识到了局限所在并进行了矫正。参见滋贺秀三等:《明确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而将诉讼中的州县官批饬调处视为所谓的“第三领域”则因忽略了官方与民间在法律意义上的主次关系亦有失偏颇。④笔者认为黄宗智教授“第三领域”概念的运用虽强调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却忽略了双方在法律意义上的主次关系并且不自觉地过分突出了调处与衙门裁判二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另中国学者对黄宗智教授“第三领域”理论的代表性批评意见可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
二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
州县官批饬调处,亦有学者称为“官批民调”。⑤如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陈瑞来,肖卜文,《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肖卜文,陈瑞来:《清代官批民调制度与基层社会治理》,载《文史博览(理论)》2010年第11期等。在本文中,笔者采用“州县官批饬调处”这一术语,一方面是追求与清代相关文献表述的吻合,⑥清末《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所设计诉讼习惯调查问题即使用了“批饬调处”这一术语。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该纠纷解决方式的官方属性。
作为清代民事诉讼中普遍运用的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原非国法的制度安排。不仅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央对州县官批饬调处似有明确禁止之意。《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所附乾隆三十年修订条例明确规定:“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如有不经亲审批发结案者,该管上司即行查参,照例议处。”[7]
乾隆三十年“民间词讼细事,……该州县官务即亲加剖断,不得批令乡地处理完结”条例的出现表明当时司法实践中州县官批饬调处已相当普遍并带来了一些弊端。然而从前文笔者对清代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的考察来看,该条例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不无疑问。①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先生即对该条例提出了异议:“此防藉事串诈、假公报私之弊也。郷保内岂无公正之人。若如此例所云,则不可靠者居多,盖直以不肖待之矣。”参见薛允升:《读例存疑》,卷三十九,“告状不受理”条附例8。清末《钦定大清现行刑律》最终将此条例删除。清朝后期,州县官对批饬调处的运用可能较乾隆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载:“寻常民事诉讼,如婚姻、田土、债账等案,惯例上必经团保调处,不服始得控诉,否则地方官亦必发交团保调处或却下之。”[8]
作为在司法实践被普遍运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州县官批饬调处在运作程序上已具有相当的规范性。在此特以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中“同治十三年尚永德告谢仕仲换约累赔事”为例,具体展示州县官批饬调处纠纷机制的运作程序:②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卷2-2-174“同治十三年尚永德告谢仕仲换约累赔事”。
案情简介:尚永德于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呈控称其将三契地土作一契卖与谢仕仲,共应完纳熟粮六升,谢仕仲私自换约,约内只载粮四升,致原告连年粮被累赔。县令于三月十四日谕饬保约等查明调处。保约等人调处成功,具禀恳息。
三月十一日县令批尚永德呈词:候饬该管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据实禀覆。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谢仕仲不交契,则即唤究。
三月十四日县令发给保约的调处谕饬:谕高桥保长田生玉,乡约张正德等知悉:案。据尚永德以换约累赔等情具控谢仕仲一案,据此除词批示外,合行谕饬,谕到,该保约甲长等,即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如谢仕仲不认粮,则将老契缴案;如不交契,即据实禀覆,以凭唤究。毋得偏袒玩延干咎,速了。特谕。
三月□日保约禀覆及县令批词:
具禀
内权河保长监生田生玉、乡约张正德为奉谕禀覆事:情,尚永德以换约累赔告谢仕仲一案,蒙谕令谢仕仲交出老契,公同查明调处。遵即邀质。缘尚永德于咸丰六年,将业卖与谢仕仲,契载熟粮四升,谢姓照契过粮,无换契之情。是时尚永德业未卖完,全凭老约管业,老契未付谢姓。嗣后尚永德将业卖完倒户,纵有遗粮,更不与谢姓相涉,今尚永德尚有地土所遗之粮作为墓粮,仍归尚永德承还,均皆允服,为此禀乞大老爷案下审核息销施行。
紫阳县令批词:准息销。
据该案例可发现州县官在将案件批饬调处时,除在当事人呈词上直接作出批示外,也向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发出调处谕饬。保约族邻等人如调处成功,则向州县官如实禀覆,请求州县官批准;如调处失败,保约族邻等受委托调处人亦应向州县官如实禀覆,由州县官将案件转入审判程序。③调处失败由州县官将案件转入审判程序的案例可参看陕西省档案馆馆藏清代紫阳县正堂司法档案卷2-2-257“同治八年张守志告曾春发等掯贫难生事”。当然在清代亦有不少州县官在批饬调处时,并未向受委托调处人另行发出调处谕饬,而是直接批示当事人持批请求受委托调处人调处。如袁守定曰:“遇民来诉,批所知相近之士耆处释。即令来诉者持批词给之,立言剀切,足以感人,必有极力排解以副官指者,此或息讼之一端也。”参见[清]徐栋:《牧令书》,“袁守定”,“息讼之法”。此种情形在黄岩档案中有较明显体现。如黄岩档案第13号案件批词:“既经族理,著持批再邀族众劝令听理。”第50号案件批词:“著持批邀同亲族,妥为理明,若敢再抗,惩办提究。”分别参见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303页。
保约族邻等人的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反悔。《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明确记载:“由官发交团保族邻调处之案,既经了结禀覆,应即作为确定,两造均不得听唆翻控。”[9]
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的启动始于州县官谕饬,程序的终结亦由州县官决定,调处方案经州县官批准具有官方权威性,州县官批饬调处的官方属性与法律效力毋庸置疑。
批饬调处作为州县官贯彻息讼政策的重要方式,虽非国法的制度设计,却以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普遍性、运作程序的规范性、调处方案的法律效力性俨然成为清代民事诉讼中相对独立、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
三、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与制度化州县官调处的缺失
在无讼法律文化背景下,州县官对民事诉讼纠纷“可息便息”,即使不得已通过堂审以裁判方式结案,亦无须严格按照律例裁判,可以秉持息讼理念劝谕双方互谅互让,带有鲜明的调处色彩,这是中外学界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
传统主流观点有着官箴书与司法档案等充足史料的支撑。
方大湜曰:“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10]汪辉祖曰:“准情用法,庶不干造物之和”,[11]“情尚可以从宽者,总不妨原情而略法”。[12]刘衡曰:“如审系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宽免,只令对众长跪已足示惩。盖予负者以改过自新之路,即留胜者以有余不尽之情,亦长官造福之一端也。”[13]黄六鸿甚至提出:“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以留余惠而资福善可也”。[14]
在前文笔者所提及的随机抽取的紫阳档案24例经州县官审判的案件中,有5起案件的判词明确载有宽免败诉者之语。卷2-2-83“同治八年高其才告龙自珍笼勒串谋事”一案判词:“至今数载高其才始行翻控,殊属非是。本应责处,姑念高其才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4“同治八年罗永昌告罗玉典瞒税骗价事”一案判词:“迅悉前情,罗玉典不应瞒税骗价,殊属非是。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87“同治十一年徐明耀告谢朝聘串寡吞买事”一案判词:“徐明耀不应捏情妄控,希图拖累,殊属非是。本应重责,沐念徐明耀年幼无知,从宽免究。”卷2-2-105“光绪元年庞泰和告凃士党等串买漏骗事”一案判词:“庞泰和不应捏控。本应掌责,姑念庞泰和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卷2-2-217“同治九年刘仁兴告陈忠福等笼翻伙讹事”判词:“讯悉前情,查此陈忠福不应匿契不交捏词具控。本应深究,姑念乡愚无知,从宽免究。”在另外5起案件的判决中知县可谓忠实地贯彻了黄六鸿“负者实贫,力难归结,尤须婉劝借人量为减免”的原则。卷2-2-80“同治六年李长清告龙子贞屡卖屡卡事”一案判词:“断令还龙子贞市钱四十千文,……余钱俱行让免。”卷2-2-160“光绪五年全兴德告夏万崇、涂世臣恃刁抗骗事”一案判词:“本应照一本一利偿还。姑念远年陈帐,断令涂世成还给本钱三十六千文,所有利息概行让免。”卷2 -2-160“光绪六年贺三春告唐学朝等贪谋卡勒事”一案判词:“限本年内共还唐学朝当价钱二百千文,所有利息包谷唐学朝一概让免。”卷2-2-163“光绪五年唐泰兴唐泰德告马世元等卡买勒贱事”一案判词:“查马世元契明价足,并无勒贱等情。再唐泰兴母亲年老无有棺木。断令马世元外给唐泰兴寿枋一付,嗣后,均不得滋生事端。”卷2-2-214“光绪五年康景福告康俊儒等笼买抗庄事”一案判词:“康袁氏欠有当账二百余串,售业不敷又无度用,实属可悯。断令康景福再加补钱二十千文,陈学清让当价钱二十千文以资康袁氏贫难。”
近年来黄宗智教授提出:“清代的审判制度是根据法律而频繁地并且有规则地处理民事纠纷的”。[15]这一观点虽然颠覆传统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黄宗智本人亦不得不承认:“在民事案方面,知县作判决时很少援引具体的律例条文”,[16]“我对各个案件涉及的律例的排列,都出于我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基于县官的直接引用”。[17]
不过黄宗智教授由州县官的审判严格按照律例进行的论点出发而否认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观点对笔者颇有启发。中国学者在论述清代民事诉讼制度或考察中国悠久的调解传统时普遍认为存在与州县官批饬调处和州县官审判相并列的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①参见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220页;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293页;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陈瑞来,肖卜文,《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载《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曾宪义:《关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等。
清代州县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确实存在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导的情形,在方式上与调处颇为相似,如果仅仅用“调处”一词来指称这样一种事实状态,或者作为清代民事审判区别于近代民事审判的特点,应该说基本符合史实。但如果将“州县官调处”视为清代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则有待商榷。
虽然中国学者多认为存在州县官调处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举出了一些案例作为论据,然而颇让人困惑的是在一系列清代官箴书中,虽不乏有关州县官息讼及州县批饬调处的论述,却难以找到论述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方式的只言片语;②在清代官箴书中确可以发现少量“官为劝释”或“亲为谕释”之语,可谓最接近州县官调处的表述。如“凡事关亲族,遽绳以法,则其情愈睽;事关绅士,遽直其事,则其色不解而寻爨构难将未已矣。官为劝释,亦杜爨止讼之一道也。”参见徐栋:《牧令书》。卷十七,袁守定,“审讼为之劝释”。又如:“政尚清简,雀角之微亲为谕释,使和好如初。”参见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劝民息讼”。然而“官为劝释”或“亲为谕释”并非一定指州县官在审案时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释,州县官直接在诉状批词中表达自己的劝和之意即属“亲为劝释”。如黄六鸿曰:“事虽微末,而原情不得竞置者,即将原词批发,发承牌示,着乡长约地从公处释。或将词内情形略批数语,使平情息事。”参见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差拘”。又如张经田曰:“户婚田土细故,果能按事切理,导以利害,谕以情法,剀切批示,有以折服其心,使无可置喙,亦可随时消释”参见[清]张经田:《励治撮要》,“词讼”。而在清代司法档案中更无法从形式上辨别出所谓的“州县官调处”。如前文笔者所列举的紫阳档案中的5起知县作出明显偏袒一方判决的案例,可谓存在明显的“劝和”行为(当然对当事人而言实质上可谓是“命令”),但这些案件的判词形式及相关结案形式与其他知县堂判案件并无区别。综合清代官箴书的记载与司法档案的记录来看,笔者以为,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州县官主要通过寓调于批与批饬调处的方式来贯彻息讼政策;虽不乏州县官在堂审中亲自对双方进行劝和的案例,但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州县官审判的结案方式,故在清代民事诉讼中实不存在独立的州县官调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点也可以从清末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书中的记载得到印证。《甘肃调查局法制科调查各项子目》、《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等清末法制习惯调查书中,在诉讼习惯部分“调处和息”项目的调查问题设计上均开列了州县官批饬调处及保约族邻等公正人主动调处,但却未列州县官调处一类。《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稿本)》记载了当时山东省民事诉讼中存在的各类调处和息:“有由审判员批示调处者,有由原案仲裁人调处者,有由村长族长地保或戚友自请出为和解者,有由两造均愿罢讼商请仲裁人为之了结者,又有原告或被告自知理屈请求仲裁人设法和息者”,[18]唯独没有提到州县官调处。
不少学者之所以认为清代民事诉讼中存在州县官调处的制度安排,可能受两方面的惯性思维影响:一方面是清代民事诉讼中调处解纷方式大量存在,且州县官堂审裁判具有鲜明的调处色彩;另一方面是在今天民事诉讼法中法庭调解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相并立。
四、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
在“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词断辟,劝农赈贫,……靡所不综”[19]可以便宜行事的体制下,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化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对州县官而言,可以将相当一部分民事案件的解决转移给保约族邻等人,减轻自身繁重的工作压力,营造出“讼清人和”的政绩表象;对诉讼当事人而言,可以较好地维持双方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并可适当减轻讼累等。
然而若置诸历史长河,我们却会发现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从制度本身到其内在的理念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局限性。
第一,从制度本身而言,州县官批饬调处与州县官审判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张关系。“衙门绝对性地强调纠纷必须经调解程序或强行令大量纠纷经调解结案,甚至拒绝受理案件,无形中限制甚至取消了司法权力在纠纷解决中的应有作用,妨碍了当事人的合理诉求和司法权力的正确行使。”[20]
第二,从其内在的理念而言,清代民事诉讼的双重纠纷解决机制以无讼为基本价值追求,然而这本身却无异于缘木求鱼。从相关史料来看,清代州县官苦心经营的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实际发挥的息讼效果颇为有限,对无讼社会理想的追求更远未达成。清代知县黄六鸿的一番表述颇代表了当时州县官徘徊于无讼理想与健讼现实之间的无奈与尴尬:“地方官纵能听讼,不能使民无讼,莫若劝民息讼。夫息讼之要,贵在平情,其次在忍。……虽然,平情乃君子之行,容人亦非浇俗所能。惟恃上之有以劝之耳。然劝之道,亦甚微矣。世风媮薄,嚣兢成习,三尺童子,皆有上人之心;一介匹夫,每多傲物之态。……苟若区区文告而日相勉导焉,彼亦文告视之而已!”[21]
五、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终结
社会中矛盾本无处不在,对国家而言,与其追求虚无缥缈的“无讼世界”,不如冷静面对“健讼”现实思考如何建立更加专业、权威、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法文化的强势冲击下,近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伴随清末变法修律的开展被引入中国,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传统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宣告终结。
在清末变法修律中,沈家本等修律者曾有过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构建新式民事诉讼和解制度的尝试。在沈家本等人所编纂的中国第一部近代诉讼法典草案——《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中规定的和解制度主要内容如下[22]:
第一百八十五条:凡两造争讼,如有可以和平解释之处,承审官宜尽力劝谕,务使两造和解。
第一百八十六条:如两造情甘和解,俱应出具切结,声明愿遵守公正人决词,在公堂存案,由承审官将案内已讯及未讯各项事宜,委派公正人公议,持平决断。
第一百八十九条:凡公正人或中人所定决词,即认为完结该案之决词。如有不得已之处,可由承审官责令两造遵守。
该种和解制度与传统的州县官批饬调处如出一辙:承审法官仅劝谕两造,使其达成和解意向,纠纷的具体解决则完全委托给公正人;公正人所做出的纠纷解决方案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应予以遵守。
然而这种以传统州县官批饬调处为原型的“和解”制度在中国民事诉讼法近代化过程中如昙花一现,自此再无踪影。
宣统二年,沈家本等奏上《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中亦规定了和解制度:[23]
第二百八十四条:受诉审判衙门不问诉讼程度如何,得于言词辩论时试行和解。
审判衙门得因和解命当事人本人到场。
第二百八十五条:和解成立,审判衙门应将事由记明辩论笔录。
第二百八十六条:受命推事或受托推事,得以受诉审判衙门之命令、或嘱托、或因职权试行和解。
《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由承审法官亲自主持进行,这与此前《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所规定的由公正人主持的和解制度判然有别。
日本1890年《民事诉讼法》第221条规定:“不问事件至何程度,裁判所自身或受命判事、受托判事于诉讼或某争点有试为和解之权。欲试为和解,得命当事者亲自出头。”[24]《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和解制度直接移植于此,从本质上说是移植于西方近代民事诉讼法。
《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所规定的由承审法官主持的和解制度为中华民国成立后历次颁行的诉讼法所继承。①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详细规定了法院调解制度而未明确构建法院和解制度,仅于51条简单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我国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大致与清末民国时期的法院和解制度相对应。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与民国初年《民事诉讼条例》中均仅有“和解”无“调解”。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事调解法》后,在法律上明确区分“和解”与“调解”,二者共同点为均由法院法官居中主持。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和解发生于诉讼中,以终结已启动的诉讼程序为目的;调解则发生于起诉前,目的在于避免诉讼程序的启动。这一区分至今为我国台湾地区所沿用。黄宗智先生在《中国法庭调解的过去和现在》(载《清华法学》第十辑)一文中对新中国法庭调解制度与传统中国及西方调解制度的异同进行了较详细考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表达常常将历史上的和当代的调解相提并论”,“国家将调解制造成了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但“清代的法庭几乎从不调解”,“法庭调解很大程度上是现代—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创新,而不是清代的遗产”。对此论点,笔者赞同。不过,黄宗智先生的考察基本未涉及近代中国的法院和解制度,而根据黄宗智先生在文章开篇对“调解”一词比较宽泛的界定,近代中国的法院和解制度应当属于黄宗智先生所言法庭调解的范畴。法院审判与法院调解并立的近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在中国最终确立,传统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最终成为历史陈迹。
[1]里赞.司法或政务:清代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J].法学研究,20 09(5).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 9:329.
[3][清]汪辉祖.续佐治药言[M].清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4][清]张经田.励治撮要[M].清抄本.
[5][清]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M].青照堂丛书本.
[6][清]汪辉祖.佐治药言[M].清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7][清]薛允升.读例存疑[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8][9][清]李光珠.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M].清稿本.
[10][清]方大湜.平平言[M].清光绪十八年资州官廨刊本.
[11][12][清]汪辉祖.学治臆说[M].清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13][清]刘衡.州县须知[M].宦海指南本.
[14][21][清]黄六鸿.福惠全书[M].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
[15][16][17][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90,73,72.
[18][清]李书田.山东调查局民刑诉讼习惯报告书[M].清稿本.
[19]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0]陈瑞来,肖卜文.清代官批民调制度政治分析——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9(2).
[22][23]陈刚.中国民事诉讼百年进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 04:178-179.
[24]南洋公学译书院初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补译校订.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点校本)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42.
D909.9
A
1673―2391(2014)01―0145―06
2013-12-20责任编校:谭明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多元与一统:清代地方诉讼制度研究——以清末调查诉讼习惯报告书为中心”(项目批准号:12YJC820042)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