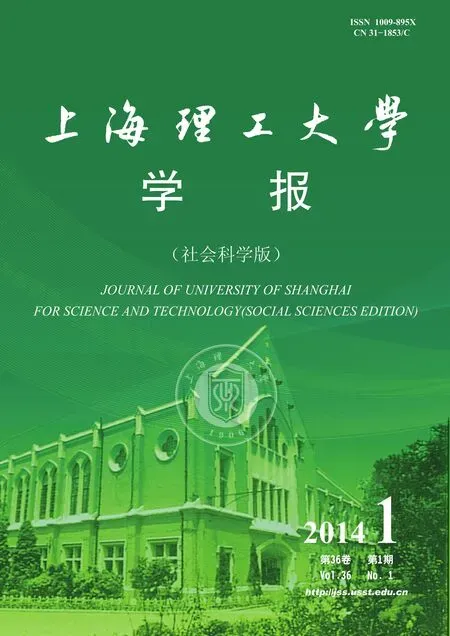“想象的共同体”与美国族裔作家的叙事策略
2014-04-03陈晓月
陈晓月,王 楠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875)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他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 (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本文基于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进一步对美国少数族裔的“民族性”和作为美国人的“美国性”进行界定:少数族裔的“民族性”建立在各自独有的族裔经验和长期的精神诉求上,同时作为美国历史的重要建造者和参与者,美国少数族裔难以抹去“美国性”的印记。
“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从文学、文化层面讨论国家民族构建”[2]的角度,是民族主义的基础。本文正是从族裔文学的角度,探讨族裔民族的“族裔性”和构建族裔民族的身份。族裔文学作为少数族裔的民族语言,传承了族裔的历史经验,表达了族裔部落的民族精神诉求。由于美国主流文化对少数族裔的种族和文化的偏见长期存在,少数族裔的作家和作品处于美国文学的边缘地带,少数族裔的生活和形象被限制在某种带有种族偏见的特定模式中,被忽视或被扭曲。得益于20世纪中期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 (Civil Rights Movement),少数族裔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他们中间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自身的种族身份在整体文化观念中严重错位。为此,他们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发起抗争,不断要求主流社会正视种族问题,一方面又在学术领域展开持续的反思、批判与创新[3]。
本文选取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及其作品,用以勾勒少数族裔文学在表达民族精神诉求和构建族裔身份方面的“异曲同工”。这三部作品分别是:美国印第安作家莱斯利·马蒙·希尔克 (Leslie Marmon Silko)的《讲故事的人》 (Storyteller,1981),美国黑人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ston)的《他们眼望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和美籍华裔作家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的《金山勇士》(China Men,1980)。笔者认为这三部作品在叙事方式上存在极大的相似性——用“讲故事”作为发声的方式。“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与族裔的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故事诉说着个人或者族裔的历史,是一个部落共同的记忆,凝聚了力量,传承了文化,凸显了各自的“族裔性”。这使他们清楚地认识自我的身份和历史,拥有归属感和感受民族凝聚力。这种认识对处于美国大熔炉中的少数族裔而言,非常重要。同时,作为对于主流社会来说是“陌生人”的少数族裔有必要首先“介绍”自己,“讲故事”以简单生动的叙事形式更好地充当了这一角色,有利于少数族裔作家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更为可贵的是三部作品共有一种“观众意识”[4],即预设的读者或听众,使讲故事、听故事与读故事三者相互呼应,形成一种感知过去、言说当下的情景。三类美国少数族裔在建构各族裔“共同体”的方法上可谓“异曲同工”,以各自的“异质”因素“同构”了作为美国历史参与者的身份和地位。
一、口传文学与族裔经验
印第安口头文学传统是其部落传承历史、维系团结的重要方式。流传下来的故事传说涉及印第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部落秩序、习俗传统、家庭结构、劳动分工和生活的地域环境等。希尔克在自己的作品中强调口头文学传统,以讲故事作为自己作品的叙事策略。这与她出生在拉古纳部落,从小听部落人讲故事的身世背景有关。希尔克曾这样解释:“我们需要故事。有了故事才有我们这个部落。人们讲述关于你、关于你的家庭或者别人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塑造了你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是从关于你的故事中了解或听说你自己是谁的。”[5]希尔克的《讲故事的人》就是通过口头文学传统显示印第安族裔特征的重要一例。
希尔克在其短篇小说集《讲故事的人》中,塑造了个性鲜明的“大地女人”(Yellow Woman)。大地女人作为部落中讲故事的人 (storyteller),把本族的历史用故事传承给下一代,以此,部落历史得以保存,文化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在印第安人传统中,印第安部落是母系氏族,女性往往是家族的中心人物,是睿智与和平的象征。保拉·艾伦 (Paula Gunn Allen)在对印第安女性传统和神话的研究中发现,女性神祇原型在印第安神话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拉古纳-普韦布洛人的“蜘蛛女”是流传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6]57。希尔克的这部小说集中关于“大地女人”的故事和部落的神话传说是印第安部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超越了文学文本本身,作为族裔经验的载体,成为了印第安人的民族志,与印第安的历史相互印证和交融,对传承民族历史、凝聚部落力量和保护民族独特性都非常重要。
同样,讲故事在非洲也有悠久的历史和重要的文化价值。随着黑人被贩卖到北美洲,讲故事成为黑人对抗奴役之苦、治愈心灵创伤和表达自我内心的独特方式,以“奴隶叙事”的形式被保留和发展,并最终在美国兴盛起来。这段被奴役的黑暗历史,编织在故事中,作为非裔美国人的族裔历史,在白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给他们归宿感和集体感。这种集体感是黑人精神的要旨,也正是黑人文学在民权运动中发展最为迅速、力量最为强大的原因,也是他们在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上独有的声音。
在一个白人价值观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把黑和丑等同起来的歧视和偏见深深伤害了黑人的心灵,黑人文学最初表达了对种族歧视制度强烈的抗议。在第一代黑人知识分子中,杜波依斯 (W.E.B.Du Bois)提出了“双重意识”的概念,精要指出非裔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和身份困境,但是他的思想框架中的黑人并不包括黑人女性。在种族和性别双重歧视下的黑人女性的命运更加艰辛,她们被透视、被消声,黑人女性不断抗争以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争取平等与自由。正如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所言:“我的工作要求我去思考,作为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作家,在我的社会性别化、性别歧视化和全面种族化的世界里,我如何能够变得自由。”[7]在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帝》中,黑人女性珍妮 (Janie)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了黑人女性的独立自主和自由的身份。
黑人社团在美国社会的声音必须建立在继承黑人文化传统上。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抵制主流文化的“同化”,不论对于黑人身份的确立和认同还是对于其他少数族裔,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黑人文学理论家霍伊特·富勒 (Hoyt W.Fuller)提出:“为了取得黑人社会内部的团结和力量,黑人必须找回并尊崇自己独特的文化之根。”[8]赫斯顿也意识到黑人在认同自身文化、对自身民族身份形成统一认识时,才能解决黑人的问题。在《他们眼望上帝》这本书中,她渗入了大量对本民族文化的描写,包括黑人口语、传统文化以及典故等方面。比如,在黑人传统文化中“骡子”这一形象与黑人女人相对等。在黑人男人眼中,他们的女人应该像骡子一样劳作。在珍妮第一次婚姻中,丈夫罗根给她买了一头骡子后,便要求珍妮到田地劳动,把珍妮视为骡子一样使唤。再者,黑人农民劳作后喜欢聚在门廊闲谈休息,善讲故事的人被称作“骡子闲谈者头目”[9],由他们唱主角,加上乡民插科打诨,就凑成了能持续好几个小时的“骡子闲谈”[10]87,这也正是我们在小说开篇所看到的场景。在《他们眼望上帝》中,珍妮充当了第一言说人,向她的好友也是唯一听众菲比 (Phoebe)讲述了她的故事,又是菲比将这个故事转述给他人,同时也是赫斯顿将这个故事讲给读者听。故事的一遍遍讲述,代表了黑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话语权的追求,也是黑人对民族和自我身份的不断探索。
种族和性别的意识形态是压制边缘文学群体发声、阻碍他们拥有读者的主要原因,华裔作家也不例外。得益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文化运动浪潮,华裔作家群体迅速崛起,其中汤亭亭的作品得到了美国文学界空前的关注,她的《女勇士》和《金山勇士》得到了高度评价。汤亭亭故事的叙事策略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10]260,是以美国文化的视角讲述中国传统故事,一种对中国传统故事的戏仿。具体而言,她基于从小听母亲讲述的故事材料,通过“讲古”,把家族故事、东西方神话传说,通过想象和回忆再创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记录了华裔在美国生活的历史,揭示当下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现实。
《女勇士》源自汤亭亭母亲向她讲述的家族和中国传统故事,经过她的想象和改写而成。母亲的讲故事对她影响深远,她从母亲那里获得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艺术表现手法,用真实和想象的艺术手法对抗社会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这一艺术手法在《金山勇士》的叙事策略中更加凸显。在《金山勇士》开篇,她化用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镜花缘传奇”,虚构了唐敖误入女儿国的故事。唐敖被打扮成女人模样,施以脂粉,裹成小脚,还被迫洗涤自己的裹脚布。这些暗指华人男子在美国被奴役化、女性化以及剥夺话语权的生存处境,他们被迫从事着洗衣、做饭等传统意义的妇女职业,过着如同阉割般的生活。在作品第九章“法律”,她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勾勒出美国法律对华人的残酷迫害,揭示了华人在美国被压抑声音、遭受残酷剥削甚至驱逐的历史。《金山勇士》超越一般文学文本的意义,作为和美国正统历史相对立的华裔民族历史,还原了这段悲惨的历史真相,显示出史诗般的宏大和深厚。《金山勇士》借助中国神话传奇故事言说华裔的族裔历史,其叙事方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再现,显示了在美华人身份的渊源和民族的独特性。
二、伦理生态和族裔性
谈到伦理生态就不得不首先提及生态伦理。生态伦理是以伦理道德或者强制手段,约束和限制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是人对自然的活动的合理性问题。然而“主客体 (人与自然)间关系直接受制约于主体 (人与人)间关系,主体间关系 (又)构成了人生存和发展的人文环境”[11],这正是伦理生态的研究范畴。伦理生态是指人生存、生活和发展的伦理环境,也可称为人文环境,它既和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相关,更与当下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相关联[11]。文学界对种族和族裔的研究从来离不开对它们所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处于美国社会边缘地带的少数族裔的生活和发展的人文环境就非常值得关注,这些边缘化群体所需要的正是来自主流社会的正义,从而摆脱在种族、性别和文化等方面遭受的歧视和排斥。正如很多生态批评所提倡:“从种族压迫、阶级压迫、性别压迫和自然压迫等角度探讨文学与环境的交集,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兼顾并举。”[12]
本文选取的三位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中:希尔克的《讲故事的人》展示了印第安部落人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人与大自然相融共生的生态图景;赫斯顿塑造了具有“健康的种族观——将黑人看成完整的、复杂的、不受贬低的”[13]黑人女性珍妮,揭示了黑人文学反抗主流文学中对黑人形象的扭曲和丑化;汤亭亭则以书写华人在美国的血泪史、还原历史真相的笔调,表现华裔在美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和剥削。她们在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本民族曾遭受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残酷迫害,以及长期以来主流文化对本民族的歧视和扭曲,进一步探讨了本民族在当下美国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这是少数族裔共同面对的问题,也是少数族裔文学相通的主题。
在希尔克的故事中,普韦布洛部落的生活环境非常严酷,“大地女人”为给家庭收集食物和饮水要走很远,她有机会接触外界环境,所以遇到水牛男人也在情理之中。这是故事关注地域环境的反映。正是近处水源的枯竭引导她逐渐走远,最终被异族掳走。在希尔克的作品中,地域环境不是简单的背景,而是影响故事发展、人物命运的重要因素,是印第安文化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元素。印第安文化要求人类敬畏自然,认为土地是无所不在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人与大自然相融共生,这揭示了印第安部落最为突出的族裔性[5]。印第安人把自己看作大地的一部分,对大地充满了敬畏,通过构建人与大地的联系,他们找到个体的身份和归宿。在希尔克看来,讲故事的意义正在于对个体身份的探寻、自我身份的构建。
赫斯顿在《他们眼望上帝》中塑造了一个在婚姻中追求自我觉醒、两性平等的黑人女性珍妮。在一个男权统治的社会,赫斯顿把珍妮放在勇敢追求独立自由和自我觉醒的艰难征途上,构建了一种完整健康、积极正面的种族形象。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外婆的强迫下完成,毫无爱情的浪漫与活力,珍妮青春萌动时对婚姻的美好想象由此破碎。不久珍妮偶遇雄心勃勃的乔 (Joe),跟他私奔到另外一个城市伊顿维尔 (Eatonville)。精明的乔成了市长和首富,他用话语统治着这座城市,也统治者珍妮,他禁止珍妮随意说话,只将她当作自己独自欣赏的玩物,完全剥夺了珍妮言说的自由。珍妮表面上屈从,内心却充满了对丈夫压迫的反抗,用了二十年时间才终于等来自己的独立自由。只有在与甜点心 (Tea Cake)的第三次婚姻中,珍妮才拥有了言说和视野的双重自由,自我意识得以真正实现。
珍妮对两性间平等的不断追求,也象征着黑人对来自白人社会的歧视的反抗。黑人女性在男性统治的父权社会中,毫无自由和平等可言;同样,在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黑人男性也是处于备受歧视和迫害的处境。白人作为“主人”的身份建立在黑人的“奴隶”身份上,这样的二元对立身份也适合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立。黑人女性对两性平等的渴望,是对正常、健康的伦理环境的需求,也代表了黑人对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追求。这也是黑人文学一直以来的主题。两者形成呼应,凸显黑人文学民族性的特点。
同为有色人种,华人和黑人在美国的地位有很多相似,同样遭受殖民话语的扭曲和排斥,但在伦理生态层面,两者也存在一些差别。汤亭亭的《金山勇士》通过记载和再创父辈人和自己共五代人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反映和探索处于美国边缘文化的华裔人的独特经历和心态。族裔意识、性别意识以及中美文化冲突是她作品的突出元素。
通过讲述和改写中国传统故事,以戏仿的艺术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汤亭亭以一个女儿的身份,认识到父辈在美国备受种族歧视和残酷迫害的痛苦。《金山勇士》开篇中被阉割的父亲形象,是几代华人在美国遭受屈辱的缩影,美国正是通过立法的强制手段,将华人不断逼迫至“非人”的处境。这属于伦理生态范畴的国家伦理生态一类,在社会中起到了价值导向的作用。正是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压迫,导致了整个美国社会,包括白人和华人自身,形成了对华人形象的“刻板化”和扭曲,华裔男子的形象不乏被刻画成“懦弱、胆小和失去了阳刚之气”[14]208,正如张敬钰 (King Kok Cheung)在《男人与男人之间:重建美国华裔男性气质》 (Of Men and Men:Re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y,2001)中分析美国主流文化对华裔男子所施行的“阉割”:
“阉割”一词确实唤起亚裔美国人遭受多重伤害的族裔经验,满含一种特殊的辛酸和愤怒。由于19世纪来到美国的中国劳工被禁止携带妻子,也不准与白人妇女结婚,历史环境使许许多多早起华裔移民成为事实上的单身汉……由于不平等的就业机会,这些华人男性被迫从事厨师、侍者、洗衣工以及其他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人活”的工作……文化和政治因素进一步导致了华裔男性的女性化[15]。
作为在美国出生、受教育的移民后代,汤亭亭受美国文化熏陶,接受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她也曾抗拒母亲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文化的冲突与隔阂。而故事通过想象和改写后的完美统一,显示了中美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汤亭亭通过对家族故事、族裔历史进行想象、再现和剖析,为本民族充当了言说的媒介,构建了华裔族裔后代的身份——一种不可调和的“双面公民身份”(double-citizenship)[16],一种处于中国与美国文化夹缝中、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双重身份。
经历过殖民主义和种族迫害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印第安人的土地被白人殖民者侵占,他们被驱逐,只能居住在仅有的居留地;黑人作为奴隶主的财产被当作牲畜一样使唤、交易,他们被禁锢在奴隶制的镣铐中受着奴隶主的鞭笞;华人在美国社会被剥削、被驱逐和被消声,美国的官方历史剥夺了一个族裔真实的历史话语的存在权利,华人的形象被故意扭曲、丑化。三位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各民族在美国主流文化压制下的生存状态,以及各族裔的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被美国主流文化同化的困境,显示了各族裔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沟通融汇中的和谐与矛盾。这是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伦理生态观念,是少数族裔文学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共性之一。
三、异质同构与身份建构
爱德华·赛义德 (Edward W.Said)在《文化与帝国主义》 (Cultural and Imperialism,1993)的导言中,对“美国性”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们要想对美国性达成共识,就得首先承认美国人性格错综复杂,不具单纯的清一色的同一性。”[14]193在美国的历史上,不论是对印第安民族的殖民主义时期,还是对黑人的奴隶主义时期,亦或是对亚裔的种族主义时期,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以及与主流文化的碰撞和沟通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文化相互沟通交流的结果,并没有出现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汇的“大熔炉”(melting pot),而是形成了“文化马赛克” (cultural mosaic)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景象[17]。在提倡文化多样性的美国社会,少数族裔文化以各自文化的独特性和开放性构建了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正是彼此间的“异质性”,“同构”了少数族裔美国历史构建者的身份和地位。
美国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以及华裔文化是异质的,但其中文本的隐喻、叙事的策略、被边缘化的处境以及被主流文化认同的渴求,都存在着极大的相似。三者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族裔经验寄托在故事中,以自己文化、历史的独特性“同构”了在美国多元文化中不可忽略的地位。在阶级分化明显的美国社会,不论是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贩运而来的黑人,或是移民而来的华人,在白人眼中都是外人。他们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被边缘化,被扭曲,作为“整体表征 (representation)[18]系统的 (美国主流)文学文本对女性、少数族裔以及许多被压迫族群的表征本身成为了批评的对象”[18]。随着文学多元化成为共识,少数族裔文学的地位已不容忽视,尤以黑人文学和华裔文学为代表。如何构建本民族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各自的身份成为关键,正如王晓路所说,“大多数边缘族群若要获得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就必须采取符合自身体验的方式,即非现成的主流表意方式,进行一种更为贴近自我的再现”[18]。少数族裔文学正是使用“讲故事”的叙事形式进行“更为贴近自我的再现”。这些故事记录、传承各族的历史记忆,显示其推崇的价值观和文化,揭示了主流表征系统对少数族裔形象的误读和刻意歪曲,表达了自身的文化诉求,建构了本族的文化身份,同时与主流文化不断地碰撞和融合。由此,美国少数族裔发出了他们独特的声音,塑造独有的身份意识。
三位少数族裔作家都以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作为本族文学的发声策略并非偶然,更为可贵的是她们拥有观众意识,以期讲故事与听故事、读故事之间形成呼应,使故事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共鸣。希尔克的观众意识表现在《讲故事的人》中段落布局的错落有致、行间字词的斜体和距离变化,来显示故事的发展脉络和语气变化,使得故事既利于阅读又便于口头讲述,真正做到“把故事里的味道传达到纸张上去”[6]50。赫斯顿的观众意识尤为明显。《他们眼望上帝》同时采用标准英语和黑人口语的双重声音作为故事话语,一方面暗指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权社会中的双重诉求,追求男女之间的平等和白人黑人社会地位的平等;一方面也指赫斯顿作为黑人女性作家的双重身份,以及非裔美国人作为黑皮肤的美国人的双重自我的矛盾。正如杜波依斯提出的“双重意识”概念:“一个人觉得他有两个部分,一半是美国人,一半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想法;两种无法调和的对抗;在同一个黑色躯体里有两种敌对的想法。”[19]这种双重意识的心理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华裔。汤亭亭的读者意识正如她自己所言:“我是个美国作家。像其他美国作家一样,我也想要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20]汤亭亭是为美国读者而创作,以美国人的视角改写中国传统故事。但是美国评论界出现了误读,她的作品的体裁一直被定义为非小说 (non-fiction)。中国读者也出现了同样的误读,过分地强调了她与中国文化的联系而忽视了她本人和作品的美国性。这也是中美文化两者间存在隔阂的表现。汤亭亭本身作为两种文化的混合体,以及其作品彰显文化融合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不能以单一绝对的眼光审视她和她的作品。
四、结束语
美国少数族裔的故事叙事,凸显了各自的历史记忆和特征,以彼此间的“异质”,“同构”了他们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彼此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少数族裔更加清楚地认识自我、定位自我,在文化多元化的环境中保留了各自的族裔性,成为“文化马赛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美国人的含义。这是他们共有的印记,不论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华人,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有着不可磨灭的“美国性”,各个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同建构一个多元的美国文化。民族性本身就是一个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基础,同时与外界文化反复碰撞、交融的过程。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也愿意创造共同的未来,这就是一个民族—— “想象的共同体”。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5.
[2]邹赞,欧阳可惺.“想象的共同体”与当代西方民族主义叙述的困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1):28-32.
[3]王晓路.种族/族性 [J].外国文学,2002(6):62-66.
[4]Brill de Ramirez S B.Storytellers and their listener-readers in silko’s“storytelling”and “storyteller” [J].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1997,21(3):333 -357.
[5]翟润蕾.莱斯利·马蒙·西尔克:美国印第安文化的歌唱者 [J].外国文学,2007(1):3-9.
[6]Barnes K.A Leslie Marmon Silko Interview[M]∥Melody G. “Yellow Woman”:Leslie Marmon Silko.New Brunswich:Rutgers UP,1993:47-65.
[7]Morrison T.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47.
[8]程锡麟.虚构与现实二十世纪美国文学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409.
[9]王元陆.赫斯顿与门廊口语传统——兼论赫斯顿的文化立场 [J].外国文学,2009(1):67-73.
[10]金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7.
[11]晏辉.伦理生态论 [J].广东社会科学,1999(5):71-76.
[12]石平萍.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历史与现状[J].当代外国文学,2009(2):26-34.
[13]Walker A.“A Cautionary Tale and a Partisan View,”in Search of Our Mother’s Gardens[M].San Dieg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3:85.
[14]蒲若茜.族裔经验和文化想象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08.
[15]Cheung K K.Of Men and Men:Reconstructing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y[M]∥Bernier L.Aspects of Diaspora:Studies on North American Chinese Writers.New York:Peter Lang,2001:121-122.
[16]Kingston M H.Cultural Misreadings by Chinese American Reviewers[M]∥Amirthanayagam G.Asian and Western Writers in Dialogue:New Cultural Identities.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2:60.
[17]杜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 [M].北京:中华书局,2007:62.
[18]王晓路.表征理论与美国少数族裔书写 [J].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33-38.
[19]Du Bois W E B.The SoulsofBlack Folk [M].Atlanta:Ga,1903:3.
[20]Kingston M H.Cultural misreadings by american readers[C]∥Critical Essays on Maxine Hong Kingston.New York:G.K.Hall,199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