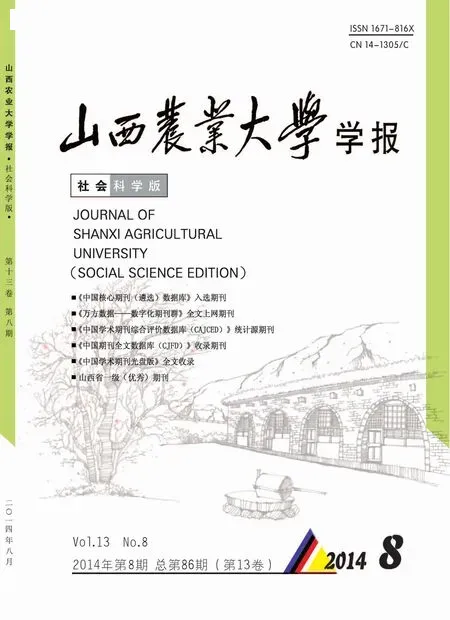创伤,记忆,心灵救赎
——《冷山》的创伤主题研究
2014-04-03王俊生
王俊生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创伤,记忆,心灵救赎
——《冷山》的创伤主题研究
王俊生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67)
查尔斯·费雷泽的《冷山》将个体的命运置于战争的宏大背景之下,表现了战争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带来的创伤。著名导演明格拉的电影改编用视觉化效果将小说主题进一步强化,将战争的残酷、人性的挣扎更加直观地呈现在观众和读者面前,引起了人们对战争、人性和爱的深思。小说中主要人物在身心上都因战争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严重创伤,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记忆,而爱使人们重新联系到一起,重新面对生活。
《冷山》;创伤;创伤记忆;救赎
1997年,查尔斯·费雷泽的第一部小说《冷山》正式问世,并且成功跻身全美十大畅销书的行列。查尔斯·费雷泽在《冷山》再现了战争的惨烈场面,反思了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探究了人性在战争中的迷失与回归以及爱对人性的救赎。该小说在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到了众多专业人士的称赞,并于1997年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英国知名导演安东尼·明格拉将其改编为电影,并取得了重大成功。电影忠实再现了原著,并且应用影像将战争的残酷更加直观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应用闪回等电影拍摄手法不断变换场景,叙事背景在惨烈的战场、艰难的回家路途与宁静的家园“冷山”之间来回转换。对比之下,更突显出战争的残酷以及给人们的身体和心灵上带来的无法愈合的创伤。直观的影像唤起了观众对战争、人性、爱与救赎更深的思考。
《冷山》以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一个伤员逃兵的逃亡历程为主线,夹杂着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展现了战争背景下人们饱受物质贫乏带来的身体上的磨难和战乱带来的心灵上的摧残与折磨。小说以主人公英曼为典型代表,深刻反映了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和苦难,不仅仅是物质资源的匮乏,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荒芜,人性的丧失。经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读者看到人性由绝望、无奈、漠视转变为爱、归回、和平,一段心灵的救赎历程、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令读者回味无穷。读者也可以透过小说的语言与结构看到查尔斯·费雷泽对于回忆的一种追溯与迷恋。
一、创伤
创伤是由临床医学引入到文学、历史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中的一个概念。20世纪70年代,民权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的繁荣引起了学者们对创伤理论和创伤文学的研究热情。历史性创伤和结构性创伤是创伤的两个主要分类。多米尼克·拉卡普罗(Dominick LaCapra)对这两种创伤分别作了定义:“历史性创伤是指特殊的、常常是人为的历史性事件,包括大屠杀、奴隶制、种族隔离、少年时期受到的性侵犯或强奸;而结构性创伤通常指超越历史的失落,比如和母亲分离、进入语言象征系统、不能完全融入一个集体等”。[1]凯斯 (Cathy Caruth)则将创伤定义为“对突发的或灾难性的事件的一种压倒性的经验,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以幻觉和其他入侵方式而重复出现在受创者脑海中,是一种后延的、不受控制的现象”。[2]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对于参战者、救援者、医护人员以及家属都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或心理创伤,留下了沉痛的创伤记忆。这些创伤记忆被文学创作者应用于文学领域,产出了许多以创伤为主题的创伤小说。典型的创伤小说包括海明威反映战争创伤的《永别了,武器》、华裔女作家谭恩美表现家庭创伤的《喜福会》以及托尼·莫里森叙述种族创伤的《宠儿》。查尔斯·费雷泽的《冷山》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其中隐含的创伤主题以及对人性的反思值得我们探讨。
“《冷山》弥漫着一种基于人性的反战情绪,作者对战争”以及战争的创伤“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理性的批判。”[3]在《冷山》中,人们在经历了残暴的战争之后被痛苦和伤痛的记忆所困扰,反复出现的噩梦、自我克制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疏离都是人们经历外部创伤之后的心理表现。朱迪斯·赫曼在她的著作《创伤与复原》中提到:对恐怖事件的否认与大声言说之间的冲突正是心理创伤的辩证法。[4]一方面,受创者努力克制自己,不愿提及和回想自己所经历的事件,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这些压抑的情绪。《冷山》中的几位主要人物,无论是直接参加战争还是间接受到战争毁灭性后果的伤害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这种创伤辩证法。他们都不愿触碰充满创伤的回忆,总是逃避,而在梦境中或者不经意之间又述说着自己的经历。
二、无法逃避的创伤记忆
(一)沉默与言说:英曼的创伤
战争的残酷带给参战士兵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更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当战争打响的时候,冷山镇的年轻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什么,而是充满了期待,正如鲁比所说:“他们把这场战争称之为‘笼罩在头顶的乌云’。可他们却没事找事,一边骂着‘该死,下雨了!’一边走进雨中”。 朱迪斯·赫曼在《创伤与复原》一书中如此描述一战期间士兵们的状态:毁灭性战争带来的灾难之一就是对战争带来的许多荣耀和自豪的幻觉。无数次面临堑壕战的恐怖之后,许多士兵的精神开始崩溃。[4]英曼与冷山镇其他的年轻人在得知战争即将打响时,都兴奋难耐,跃跃欲试,他们对于自己即将面对的生死考验浑然不知。作为一个幸存者,英曼既是战争的目击者又是受害者。他亲眼目睹了同样来自冷山的两个士兵的死亡。战争的残酷深深地埋藏在了英曼的内心,对他的身体和心灵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是,他却不愿意对外人提起任何关于战争的只言片语。这正是典型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反应。
“心理创伤的残忍就在于它让人们直面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脆弱以及人性中的恶的力量。”[4]凯斯在她的著作中也提到:当士兵们经历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突发性大规模死亡时,他们当时只是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这种经历只能在后来以不断重复的噩梦来得到释放。这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的、反复出现的创伤现象。[2]在目睹了嗜血的战场,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英曼只想将这段创伤记忆永远埋藏于心,并否认自己参战的经历,以此来对抗战争对自己精神的蚕食。
电影的一开始,英曼与其他南方士兵一起坐在战壕中,翻看着临走时艾达送给他的书和照片。与此同时,北方士兵正在放置炸弹。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土地开裂,浓烟滚滚,人、马、枪都被抛到空中。英曼也随着这次恐怖的爆炸被掩埋在碎片与泥土中。当他挣扎着从泥土中站起来的时候,他首先做的就是去找艾达送给自己的书和照片,全然不顾周围所发生的恐怖事件。对于这场战争,英曼已经失去了兴趣,自己曾经的信仰也随着一声声爆炸声而残破不堪,他惟一想做的事就是快点回到冷山,回到艾达身边。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这场战役变成一场梦魇深深地印刻在英曼的脑海,挥之不去。在弗雷泽的小说中,当英曼向盲人讲述这次可怕的经历时,我们可以看出这场战争对他造成的创伤之深。这些创伤变成梦境反复出现在英曼的脑海,无论如何努力摆脱,都无济于事。“在梦里,赤芒烧过夜空,散落在地上的血淋淋的断肢——手臂、头、腿、躯干——慢慢聚拢,七拼八凑组成新的怪异的人体。他们在黑影幢幢的战场上蹒跚着,摇晃着,不时扑倒,像瞎眼的醉鬼,腿脚完全不听使唤。”[5]弗洛伊德认为,“发生在创伤神经症里的梦具有重复的特征,将病人再次带入他遭遇的境况中,这种情景使他在又一次的恐惧中醒来。”[6]普通的神经症患者将过去不愉快的事件埋藏于心以逃避带来的痛苦,但创伤患者在脑海中不断重现所经历的可怕事件,这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失去了逃避该事件的能力。英曼也想将这一切忘记,但是创伤记忆却一次次复现,逼迫他不断地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英曼一方面极力压制自己的创伤记忆,另一方面却在想要将其倾倒,寻找释放的出口。从电影中他与盲人的对话可以看出他的刻意压制,当盲人说他不愿意为了十分钟的光明花一分钱时,英曼说自己也宁愿没有看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但其实盲人所指是不愿意失而复得。看似理解上的错误,其实英曼只是借此说出了压抑在内心的声音。由此,也可以看出,英曼想要努力将参战的经历抹去,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正是沉默与言说之间的创伤辩证法。
对于受创主体来说,时间无法带走对于过去的记忆,相反,那些记忆会一遍遍在梦中闪回,他们无法再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仿佛时间就此停留在创伤事件发生的那一刻,不断重复。那些创伤瞬间以一种非正常的记忆编码,“在清醒的时刻以闪回的方式,在睡眠时以创伤性噩梦的方式不自觉地闯入意识之中”。[4]弗洛伊德认为:“噩梦是压抑的思想、感情和记忆从意识中浮现”。[7]回家路途上,英曼每晚都会做噩梦,这些噩梦与他在冷山时与艾达的快乐记忆相交织使英曼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二)痛苦与守候:战争中的女人们
战争击溃的不仅是前方战士的精神,也包括留守家园的女人们与老人们的精神。冷山镇上的年轻人都被派往前线战斗,留下女人们和老人守候家园。战士们在前方浴血奋战,身心备受摧残,留守家园的人们也难以幸免于难。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自己的亲人可能永远不会回来的恐慌,另一方面,家乡护卫队横行霸道,到处作乱,让他们的生活永无宁日。
痛苦与恐慌使人们之间的信任逐渐瓦解,人与人之间变得疏远。习惯了富足生活的艾达先后经历了爱人的离开、父亲的去世、生活的困窘以及提格不时的骚扰,还要忍受对英曼的思念以及可能永远无法相见的痛苦。战争带给艾达的这些创伤更多地表现在她与周围世界的疏离。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决定了她们的活动范围大部分被局限在家中,而且作为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出身的孩子,艾达并未学会任何能产生实际结果的技能,她的父亲更侧重于培养她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战争的创伤使她更加封闭自己,逐渐退缩到了自己的世界,沉浸在对与英曼度过的幸福瞬间的回忆之中。创伤使人们丧失了言说能力,艾达同样失去了表达内心痛苦的能力。艾达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主要体现在她对他人的信任危机。当艾达的邻居萨利家有一口井,如果手持镜子,仰面躺在井口,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未来。当艾达从镜子中看到英曼蹒跚着向自己走来,并慢慢倒下的画面时,她并没有向萨利透露自己所见。
“创伤反应出现在创伤性事件之后。当主体无法反抗、无法逃避事件的发生时,人体的自卫系统会变得强大和混乱。”[4]构成个体对危险的一般反应的每个要素都失效了,当危险过去很长时间之后,这些构成要素仍然坚持着一种变异、夸大的状态。经历了提格的骚扰,萨利一家的悲惨经历之后,艾达对危险的反应被严重放大,对周围环境更加警觉。当英曼经过艰难的逃亡之旅终于出现在艾达的面前时,艾达几乎没有认出英曼,竟然举枪相对,命令英曼转身回去。战争的创伤给人们之间制造了巨大的沟壑,需要很长时间来修补。
电影中,萨利一家本来是幸福的一个家庭,战争却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在亲眼目睹了丈夫与儿子的惨死之后萨利便不再开口说话,用沉默来回避痛苦的经历。这是典型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症状。萨利的创伤经历缺乏语言背景和叙述功能,无法言说,留在她脑海挥之不去的只有痛苦的感觉和悲惨的图景。除萨利之外,电影中另外一个角色——萨拉也忍受着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折磨。萨拉的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症状与艾达更为相似。丈夫死于战场,独自带着孩子的她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随时会出现的危险,这些经历使她对任何靠近她的人都异常警觉。萨拉对危险的反应被过分放大,对敌人不再有任何同情之心。当英曼打算放走一个北方士兵时,萨拉手持猎枪,从屋里冲出来,愤怒地将其杀死,尽管这个士兵并未伤害到她。战争的创伤带给人们太大的改变,正如鲁比所说:“战争改变了我们”。
三、爱与救赎
在电影《冷山》的结尾,冷山镇上的人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恬静生活,然而,战争带给他们的创伤将伴随他们一生。身体上的创伤能够用药物消除,但心理上的创伤却会被埋在心底一生。当不小心触碰到这些记忆的时候,往事又重新浮现。
“心理创伤的核心体验就是虚无感和疏离感”,[4]“受创者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8]因此,复原是建立在“幸存者的心理授权和人际关系重新建立的基础上的”。[4]幸存者是自身复原的主导者,而他人的爱和帮助是受创者复原的一剂良药。然而他人的建议和帮助对于受创者的复原来说并非关键因素,复原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要与他人重新建立人际关系。只有在人际交往的背景下,复原才能成为可能。
这场战争带给英曼的除了身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有自责和内疚以及信仰的丧失。从他写给艾达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己、对这场战争的厌恶:“无论如何我就要回家了,不知我们之间的关系将会怎样。最初我打算在这封信里写写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做过的事情,以便你在我回去之前对我有所判断。但我相信,那些事情要用蓝天般宽阔的信纸才能写完,而且,我既没有那种意愿,也没有足够的精力。还记得四年前圣诞节前的那个夜晚吗?在厨房的炉子旁,我把你抱在膝上,你对我说你永远都会愿意这样相依而坐,你的头枕着我的肩。现在,让我痛苦的是,我相信如果你知道了我经历的一切,将再不愿坐在我的怀中。”[5]在英曼写给艾达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英曼已经丧失了信念,迷失了自我。他不确定在经历了这些之后,艾达还愿不愿意接受他。在逃亡途中,英曼得到一位老人的帮助,当老人问及他的经历时,他说:“这些天,我一直在杀人,当与敌人短兵相接时,我总是能够杀得了他,而对方却杀不死我。”电影中,英曼在诉说的时候,脸上表现出的是一种对自己的厌恶。最后,当英曼回到艾达身边,他对艾达说:“你会尽全力阻止我划入黑暗的深渊”。身处战场的时候,逃亡途中备感绝望的时候,英曼正是靠着与艾达相处的短暂时光的回忆以及仅收到的三封艾达的来信支撑着自己的意志。
当个体受到创伤时,被创伤后压力综合症所折磨时,爱成了惟一的救赎。《冷山》中,英曼与艾达之间的爱情成了残酷的战争背景下的一抹暖色,也是受创的英曼与艾达复原的灵药。爱是创伤后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关系的基础,也是打开受创者封闭的内心世界的钥匙,帮助他们将内心的痛苦释放出来,重新建立对自我的认识,重拾生活的信心,从而获得救赎。电影结尾处,艾达与女儿在农场上的幸福一幕让我们看到了爱的力量和生活的希望。
[1]LaCapra D.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189.
[2]Caruth C. 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 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1, 21.
[3]杨华荣,冯宪光.穿越时光的旅程——《冷山》文本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6):127-129.
[4]Herman J.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1, 20, 4, 26, 35, 133.
[5]查尔斯·费雷泽著.周玉军,潘源译.冷山[M].北京:接力出版社,2004:11,19.
[6]Freud S. Early Studies on Psych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C]. Rieff P. Early Psychoanalytical Writings. New York: Macmillan, 1963:34.
[7]Freud S.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M]. London: Hogarth, 1968: 97.
[8]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Trauma,MemoryandSpiritualRedemption——AStudyontheTraumaticThemeofColdMountain
WANG Jun-she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NanjingInstituteofTechnology,NanjingJiangsu211167,China)
Charles Frazier sets the fate of individuals in the spectacular background of war inColdMountainto depict the physical and psychical trauma the war brought to human beings. The film adaption by eminent director Minghella enforce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y the visual effects, presenting the cruelty of war and the struggle of human nature in front of audience and readers in a more vivid way, which arouses people's meditation of war, human nature and love. The main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are all left with physical and psychical trauma directly or indirectly due to the war. The traumatic memory in their mind has become indelible. Love makes them link together once more and gives them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new life.
Cold Mountain; Trauma; Traumatic memory; Redemption
2014-04-24
王俊生(1979-),男(汉),江苏大丰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西方现代小说方面的研究。
I06
A
1671-816X(2014)08-0818-04
(编辑:佘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