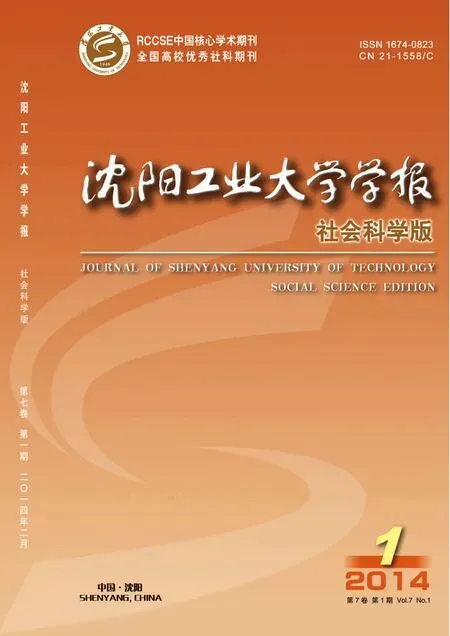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2014-04-03胡姗辰
胡姗辰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文化权利视野下的文化遗产权初探*
胡姗辰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人权,内在地包含了文化遗产权的某些方面,但文化遗产权概念的提出突破和发展了传统文化权利的内涵。文化遗产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是指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文化遗产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其主体包括个人、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面,客体是具有特殊资源属性的文化遗产,内容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
人权; 文化权利; 文化遗产权; 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开发; 文化遗产管理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中华民族对作为历史之见证的文化遗产的关注古已有之,文化遗产保护更是学界热议的论题。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民俗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等人文科学,同时也离不开法制为其保驾护航。法学作为权利义务之科学,权利义务之研究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权利同文化权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权利视野下对文化遗产权进行探索,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作为人权之一的文化权利
文化权利是随着人权理论的不断发展而从人权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1977年,法学家卡莱尔·瓦塞克创立了“三代人权”理论①其认为,三代人权是在世界3次大的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分别产生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为第一代人权奠定了基础,第一代人权相应地表现为公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核心在于自由以及对政治生活的参与;第二代人权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性质上主要是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内容从第一代人权中的“形式平等”发展至“实质平等”,以保障公民中不同阶层的成员可以获得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和待遇;第三代人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既包括民族解放运动所直接催生的自决权和发展权,也涵盖了集体权、健康权、自然资源权、分享文化遗产的权利、代际公平权以及可持续发展权等极其广泛的权利体系。,将文化权利划归在第二代和第三代人权中,虽颇具有建议色彩,却被频繁引用。然而,近年来“三代人权”将人权划分为不同代际的做法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对于“人权”这样充满争议的概念,简单地遵循其“代际”理念并不明智,因为“人权在各国演化的历史不可能使不同的人权出现在截然分开的阶段里”[1]4。例如:“某些公民权被接受为人权要比政治权利晚得多,在某些国家甚至要晚于经济、社会权利。”[1]4因此,将文化权利简单地划归为第二代人权体系中一支的做法并不利于我们理解其产生、发展和丰富的内涵。
准确地理解文化权利的内涵必须对该权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一定的了解。早在1919年德国的魏玛宪法中就已出现有关文化权利的规定②在魏玛宪法第2编“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中规定,公民可享有的文化权利包括公民的受教育权和从事艺术、科学活动的自由,还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和文化遗产等内容。。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对人权高度重视,文化权利随之进入国际法领域。在1945年拟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上就曾有不少学者和非政府组织提出将“基本人权宣言”或者其他人权法案作为宪章的一部分。但对于这一提案当时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讨论,而是就此被搁置下来。人权问题在《联合国宪章》中只有原则性的涉及。正是在二战结束后的这一时期,乐观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盛行,文化被期望在战后重建中扮演建设性的角色,因此,《联合国宪章》中已开始包含有关文化方面的纲领。
1946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68条的规定设立了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于次年起开始考虑制定“国际人权宪章初步草案”,并成立了起草委员会。1948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的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两个方面的《世界人权宣言》于12月10日被联合国第3届大会通过并公布,其27条明确提出:“(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化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一规定将文化参与权和享受创作收益的权利纳入其中。但是,《宣言》本身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起草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人权公约成为世界人权委员会自颁行《宣言》以后随即启动的程序。
1950年,人权委员会将仅仅涉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草案提交第5届联合国大会审议,但大会认为,这样一份缺少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给予保护的公约并不能全面体现《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并在第421E(v)号决议中指出:“享有公民、政治权利与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两者相互关联、不容偏废”;“人如果遇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被剥夺时,就不能体现《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自由人的理想”[2]343。因此,分别起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立法模式于1952年第6届联合国大会上被确定下来。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和审议,这两个国际公约终于在1966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被视为国际法律文件中关于文化权利的经典条款。该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与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此外,《公约》第1条还承认了人民的文化自决权。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总框架下,文化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权利也出现在一些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法律文件中。1976年通过的《阿尔及尔民族权利宣言》所论及的“民族权”包括一个民族对其拥有的艺术、历史和文化财富的权利(第14条)、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受到尊重的权利(第2条)、一个民族不被强加异域文化的权利(第19条)等。特别应指出的是,少数人的身份、传统、语言和文化遗产得到尊重的权利在这个宣言中亦有明确表述(第19条)。该宣言因没有任何国家签署而并不享有国际法地位,但是对后来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产生了深远影响,后者在第22条中提出一切民族都有在应有的自由和认同中、在平等对待人类共同遗产的同时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
1992年联合国《在民族或种族、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在开篇第1条就宣布:“国家须保护在各自领土内的少数人的存在以及他们的民族或种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特性,并须鼓励促进那一特性的环境。”第4条则呼吁国家采取措施以使那些属于少数的人能发展自己的文化。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将文化多样性提高到人类共同遗产的高度,并从文化多样性与创作的角度提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其第7条认为:“每项创作都来源于有关的文化传统,但也在同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得到发展。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此外,以1972年《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专门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建议和宣言等国际和区域性法律文件也陆续出台。
通过一系列有关或者提及文化权利的国际法文件,文化权利的概念已实现由“精英”向“人类普遍遗产”的转变,其权利主体亦由“精英阶层”扩展到包括民族、社区和每一个个人的广泛范围,成为每一个个体都必须享有的一种“基本权利”。目前,国际人权领域已认可的基本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完全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保护文化认同的权利、保护文化作品的精神及物质利益的权利、公开和私下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以及保护民族与国际文化财富和遗产的权利[3]16-22。应该说,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基本的文化权利之一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是,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并不是与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唯一形式,在国际人权法领域确认的文化权利的基础和框架下,包含更广泛的主体、更丰富的权利形式和内容的专门“文化遗产权”呼之欲出。
二、文化遗产权的提出及其对文化权利的发展和突破
近年来,“文化遗产权”或一些与之类似的字眼(如“文化遗产相关权利”)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学、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论著中,日益成为文化遗产法学领域一个新兴的概念术语。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文化遗产权正日益受到关注,但对其独立性问题学界依然颇有争议。大部分学者将与文化遗产相关的权利置于上述作为人权的文化权利之下,从文化权利的角度对文化遗产相关权利进行论证;相当一部分学者以知识产权制度为切入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权利进行研究,论证或者反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及相关制度中的可能性;亦有学者从生态法范式出发,用生态伦理学、生态正义论、生态秩序安全等来证明文化遗产权的正当性。但是,绝大部分现有研究只是部分地涉及到文化遗产权的某个方面,鲜有对其独立性、正当性、权利三要素及权利法律属性等问题展开系统论证的专门论述。
与此同时,文化遗产权这一概念在近年来国际社会的一些框架性协议中已经出现。2005年欧洲委员会的《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被认为是最早承认文化遗产权的国际法律文件。该公约在序言中就明确提出:“作为《世界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保护的文化生活权利的一个方面,在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人人都有权利与他们所选择的文化遗产密切结合在一起。”其第4条则进一步明确:“人人,包括个体和群体意义上的人,都有从文化遗产中获益的权利和为丰富文化遗产作贡献的权利。”此后,在2007年《弗里堡文化权利宣言》中亦提出形式和内容丰富的文化遗产权,指出:“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且使这种身份获得尊重;人人都有权了解自己的文化以及组成人类共同遗产的其他文化;人人都有权接触文化遗产,他们不仅是当代人,也是后代人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际法律文件将文化遗产权定位为文化权利的下位概念,由于国际法性质所限,其对文化遗产权的保障亦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等国际法主体一定义务的履行,但是文化遗产权这一概念突破了传统“文化权利”的范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权利的外延和内涵。通过将“文化遗产权”从“文化权利”中独立出来,亦引发了人们对二者联系与区别的关注。从权利产生来看,文化权利是在国际法中产生的、与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的文化自决与民族自决原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权利,是传统人权与“发展权”相联系所产生的新的人权体系中的一部分,并逐渐被引入到国内法的领域,作为个人追求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或者国内某些有着独特文化的群体维持和发展其文化的权利。文化权利主要涉及的是公法上的关系,包括国际法关系和国内宪法、行政法的关系,其主要立足于国家与国家、国家与民族地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文化遗产权则是包含着公权和私权两个方面的权利束,以混杂着公私关系的社会为立足点,可能涉及到国家与社会、某些自治文化团体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多种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权利的目的和宗旨上看,文化权利的目的在于平等而非歧视地鼓励一切对文化多样性有益的文化创造,促进个体、民族、国家和全世界的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而文化遗产权则以具有历史、社会和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传承为中心,着力于保障守护和发展这些珍贵的精神文化财富的人们的正当利益,肯定他们为社会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为他们继续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自己世代守护的文化遗产营造最有利的法制环境和法制条件。在实践中,文化人权和文化遗产权可能存在某些重合,但是二者也有各自独立的外延,不存在相互隶属或者相互包含关系,更不能合二为一。
三、文化遗产权之证成
要对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属性进行证成,应该首先明确法律权利的定义。一般来说,权利是指“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一方对另一方所享有的可以要求他方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并为法规范所认可的一种资格。”[4]286这个定义至少包括3个要素:第一,权利所反映和表达的是主体之间一种对等的法律关系。第二,虽然在“天赋人权”的观念下权利本身不是由法规范所赋予,但其必须由法规范予以认可。需特别指出,由于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此处的“法规范”不限于狭义的由特定的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成文法规范,还包括经国家认可的习惯、判例等多种多样的法规范形式。第三,权利表达了主体的要求和愿望,是一种法律上的资格。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法律上的资格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法律上的利益。
具体到文化遗产权上,在当前的法律秩序下,主体对一定的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传承和发展,这一系列活动都会形成一定的法律关系,即文化遗产权利的行使无时无刻不处在法律关系的调控中。由于文化遗产的文化、历史、艺术乃至经济价值及其公益性,对其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传承和发展必然会涉及到各种各样的相对方,而被赋予权利的主体要进行这些活动,必然要求相对方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予以配合,法规范的认可则体现在法律对这些活动所涉法律关系的调整当中。
从权利三要素的角度看:首先,在法律关系中,文化遗产权主体和相对方的关系具有对等性,这种对等性不是指双方主体各自所享有的权利的数量对等,而是指对法律关系的主体来说,一方的权利要通过相对方积极或者消极的义务来获得实现。这种对等既体现在私法关系中,也体现在公法关系中。其次,在法律的规定下,一定的主体对特定的文化遗产可以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传承和创新,对主体和客体范围的限定集中体现出权利的“资格”属性。最后,虽然现行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对文化遗产权的直接界定,但文化权利、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制度已经从侧面对文化遗产权给予了认可和肯定。
综上,虽然没有在法规范中直接加以明确,但文化遗产权完全具备法律权利的属性,这也部分说明了将文化遗产权直接确认为一项单独的法律权利的理论前提。当然,一项权利要被国家法规范所确认,还需要具备理念和内容上的正当性。文化遗产权的缘起有着多方面基础:
首先,“人类基于本性,需要享有‘多样性的,能够使心灵得到安详的’文化遗产的权利。”[5]在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对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已成为人类正当需求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为之提供一个能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作为历史之见证的文化遗产在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人们反思社会历史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成为文明发展之必须,更成为人性的要求和渴望,这就是文化遗产权的人性基础。
其次,从道德伦理学方面来看,现实具有时空性,而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却是超时空的。文化遗产作为历史和文明进步的见证,有着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文化遗产权的确立是生态正义、代际公平的体现,也是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之必须。
再次,文化遗产权的确立是当今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通过明确文化遗产的权属和权能,能够明确文化遗产的利用、保护的权利和责任主体、界定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方式。同时,通过权利的激励作用使权利主体更积极地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中,这是文化遗产权的现实基础。
最后,文化遗产权的确立还有其法理基础:“权利原生论”主张“社会冲突产生权利意识进而产生权利的确认和分配。在多元的社会冲突里,通过道德已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此时社会的各种利益如何分配,既得的利益如何禁止他人侵犯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设定权利,才能使利益的维护具有正当性。因此,社会冲突就是权利的原生点,社会冲突催生了权利。”[5]在实际的文化遗产利用和保护过程中,因权责不明而导致的社会冲突日益增长并激化,这使得通过法律权利的方式明确同文化遗产相关的利益与责任的归属成为必然。
四、文化遗产权之初探
(一) 文化遗产权概念浅析
对于文化遗产权应当如何定义的问题,学者们的观点见仁见智。对文化遗产权最狭义的界定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传承主体对该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展示、传承和发展的权利,这是文化遗产权最初也是最核心的内容。随着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不断丰富,权利的外延不断扩大,逐渐表现为由“法律主体对文化遗产所享有的方方面面的权利”所构成的“一组权利束”。
王云霞在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文化遗产类型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遗产权体系包括享用权、传承权、发展权和参与管理权等内容。在《论文化遗产权》一文中,她对文化遗产权概念的分析清晰地回答了这个核心问题,认为文化遗产权是“特定主体对其文化遗产享用、传承与发展的权利。享用是主体对文化遗产的接触(access)、欣赏、占有、使用以及有限的处分权利,传承是主体对文化遗产学习、研究、传播的权利,发展则是主体对文化遗产演绎、创新、改造等的权利。”[6]
笔者认为,王云霞对文化遗产权的界定与分析较全面地涵盖了文化遗产权的大致形态,但对这个定义仍需作以下说明和补充:第一,在文化遗产权的权能上,她并没有把“收益”作为文化遗产权的权能之一,这样的选择或许是出于文物保护公益性的考虑。我国《文物保护法》第24条明确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但是也应该注意到,文化遗产确实存在一定的经济价值,承认权利主体享有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产生经济效益的一定的收益权,不仅是权利主体的正当要求,而且具有提高主体开发和保护的积极性、促进保护与开发的效果。《文物保护法》明确禁止的只是将国有文物作为企业资产进行经营,并没有禁止对其他权属的文化遗产进行利用。因此,收益权可以纳入到文化遗产权的权能中。其次,承认权利主体对文化遗产的处分权,也必须承认其在一定范围内的收益权,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利主体的“处分”行为绝大多数都伴随着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这些因处分文化遗产而产生的收益,应该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或者参与分配的权利。再次,在精神形态的文化遗产权中,知识产权这种具体的权利形式也内在地涉及智慧财产的收益问题,收益权纳入文化遗产权中不仅可行,而且必然。第二,由于文化遗产的公益性特征,权利主体在行使文化遗产权权能的时候,会受到比行使一般权利更加严格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权能与一般权利的权能相比是不完全的。
综上,笔者把文化遗产权定义为特定主体基于对特定的文化遗产的某种利益或者与特定文化遗产的某种联系,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对该文化遗产进行享用、收益、处分以及传承和发展的一种复合权利,包括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两方面的多种复合性权能在内。
(二) 文化遗产权的性质探讨
将文化遗产权确定为法定权利的重要前提就是明确其属性和构成。文化遗产权到底是公权还是私权,这也是学者们热议的论题。一方面,文化遗产权具有显著的公益性。文化遗产权作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创造和传承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在;作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组成部分,亦与全人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人类共同财产”,体现出明显的公共利益的特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各国都通过公权力的方式对文化遗产的利用进行严格限制,用公权力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权也体现了受到一定限制的私权属性,这集中表现在文化遗产所有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两个方面。此外,亦有学者将文化遗产权与环境权作类比来理解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认为文化遗产权同新兴的环境权一样,是一种涵盖主体广泛、价值取向多重、权利内容丰富、与义务结合紧密的有限度的新兴人权。这也对理解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有关环境权本身的性质问题,在学界亦没有达成共识。
鉴于文化遗产权内容的复杂性,笔者并不主张将文化遗产权简单地归类为公权或者私权,而倾向于借鉴上述第3种观点的分析方法,将文化遗产权界定为一种复合的新型权利:环境权着重于在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开发利用,促进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文化遗产权则旨在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为人类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具有主体的多元性和广泛性;它体现着物质性与精神性价值的统一;它既具有文化权利属性,也具有环境权利属性,既体现着生态正义,又体现着代际公平;它是公益权与私益权的统一体。
(三) 文化遗产权之初步构架
作为一组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权利束,构架一个涵盖所有文化遗产相关权利的统一的文化遗产权概念实属不易。笔者采取对权利三要素分别进行阐释的方法,对文化遗产权进行分析和构架。
1. 权利主体
法律权利的主体即在法律关系中依法能够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在作为基本人权之一的文化权利的视野下,文化遗产权也因其在某种意义上的人权属性而涵盖了广泛的权利主体。文化遗产权的主体可分为个体、团体和全人类3个层次。
在个体层面,个人是文化权利视野下文化遗产权最典型的主体。前述国际法律文件中包含着文化遗产权某些方面权能在内的文化权利就是以个人作为主要的权利主体之一。换言之,作为一种人权的文化权利和其所涵盖的那一部分文化遗产权,就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个人作为“人”所必须享有的基本的文化自由和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事实上,“每个人不仅对其创作或传承的文化遗产有享用、传承和发展的权利,对其所属社区、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遗产享有接触、欣赏、利用、传承与发展的权利,对其他国家、民族的人民创造的文化遗产也享有一定的接触、欣赏和利用的权利。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众多保护文化遗产和文化权利国际法律框架的基础。”[6]
在团体层面,作为人权之一的文化权利与传统意义上人权的固有属性有一定的区别,其并非单纯地以全人类所共享的“人性”和“尊严”的基本理念为基础,而是依维系一个族群或者社群使之建立起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共同记忆的文化遗产被感知到的独特性而定[7]3。文化权利中的某些具体权能“只能由社会中的个人与其他人一起分享”[1]76,因为“这些权利的享有者可以是个人,但是离开了群体和群体的集体权利,这些权利也就随之消逝。文化权利属于那些生活在特定文化中并受其影响的人们——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与所属群体的其他成员站在一起时才能成为共同价值的拥有者。”[1]76“文化自由是一种集体自由,它指某一群体的人们奉行或采纳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权利。”[1]76因此,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政策会议上宣布“保持文化特性的权利”,同其认可的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一起,为文化人权由一种个人人权扩展至集体人权开辟了道路。在文化权利的视野下,文化遗产权的权利主体理应包括一定的团体,因为许多文化遗产并非某个人的作品或创造,而是历史上某些文化团体智慧甚至某个民族国家智慧的结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团体”是一个有着丰富外延的泛指,它可以指代某个创造了某种文化遗产或者为传承该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的社会文化团体、与文化遗产有着密切文化联系的文化遗产相关社区,亦可以指代世世代代为创造、守护和发展某些文化遗产而不懈努力的民族、国家。
将全人类作为文化遗产权的主体更多地源于环境法学“代际公平”的原则和理念,其强调和体现的是现今生活在文明社会的所有人对创造了如此丰富多样的文化的先代居民的尊重和对子孙后代能享受到同样丰富的文化生活的责任和保障。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已被提高到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所必需一样重要的地位,这就要求现今所有文明人通过保护和传承祖先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的方式,竭力保护并促进这种文化多样性,并将这个多元文化交相辉映、和谐相处的社会留给后代。这既是当代人的义务,亦是后代人的权利。
若以与文化遗产相联系的程度为标准从另一个角度对文化遗产权的主体进行划分,则可分为文化遗产所有者或知识产权人、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以及其他普通大众。这种划分方式突破了法学上对权利主体的分类范式,但对后文构建和阐释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内容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 权利客体
简言之,文化遗产权的权利客体就是文化遗产。有关文化遗产概念的讨论在民俗学、法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络绎不绝,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并不打算着墨过多。学界通常将文化遗产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这样顾及到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性质和保护方法上的不同特征,但是却产生了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区分以至于相互割裂的问题。事实上,法学和民俗学界的许多论著中甚至出现单独研究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权利或单独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现象,有学者甚至将这种割裂更进一步,明确地将文化遗产权分为物质文化遗产权和精神文化遗产权两大类,认为物质文化遗产权指的是对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和利益;而精神文化遗产权则指的是对以思想、观念、理论、习惯和风俗等形式存在的精神性文化遗产所享有的相关权利,包括思想和表达自由以及知识产权两种具体权利[8]。这样的分类方式严重破坏了文化遗产权乃至文化遗产法的统一性,亦不能涵盖现实中许多特定区域内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互依存、共同构成整体性文化景观(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等)的情形。因此,尽管我们在认识文化遗产本身时可以采取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分的方法,在统一的文化遗产立法的前提下,亦可以分章规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整体性文化景观的不同保护方式,但是在认识文化遗产权这一文化遗产法中的基础概念之时,则不宜对作为权利客体的文化遗产作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分,而应更多地关注二者的共同作用和价值,从整体上把握文化遗产作为统一的文化遗产权客体的含义。
3. 权利内容
文化遗产权主体的广泛性和客体形式的多样性增加了其权利内容的复杂性。为了更好地构架和阐释作为文化遗产法之基础概念的文化遗产权,笔者将采取前文所述的以与文化遗产的联系程度为标准对权利主体进行分类的方式,逐一阐述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文化遗产相关权利。
首先,对于每一个普通公民以及作为文化遗产权主体之一的全人类来说,他们对一切民族、国家和人民所创造的非私有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享有一定的接触、欣赏、利用以及对所有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依法同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作斗争的权利。这种权利来源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需要。诚如《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言:“每项创作都来源于有关的文化传统,但也在同其他文化传统的交流中得到发展。因此,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要实现《宣言》所言的“真正对话”,就必须将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遗产展示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所有人面前,保障其接触、欣赏、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利用不同文化遗产的权利,肯定其对文化遗产的珍惜之心和热爱之心,并保障其以合法的方式与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作斗争的权利,如确立其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地位就是其中一例。
其次,对于并非文化遗产所有权人的利益相关者来说,由于其与某些文化遗产在地域上以及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或在该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或世代以某种文化遗产为生,对该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的命运产生着深远影响,则其与文化遗产已经有了某种正当利益关系,且已基于自己对文化遗产的命运所给予的付出或产生的影响而对该文化遗产享有了某些正当利益。无论是出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目标还是出于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这些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正当利益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即成为文化遗产权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所应享有的这些正当权利包括对该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的开发利用权、传承与发展权、参与管理权以及收益分配权等。但这些权利应在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严格规制的基础上行使,且可能受到文化遗产所有权的制约。
最后,对于文化遗产所有权人或知识产权人来说,其能够在《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文物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法所规定的不同形态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例如,在遵守《文物保护法》相关公益性规制的前提下行使对文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所有权权能;在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相关规制的前提下行使自身所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如署名权、传承和发展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保护该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权利、决定该文化遗产命运和发展方向的权利、开发利用和管理该文化遗产的权利以及对文化遗产相关收益进行分配的权利等。然而,由于权利客体的特殊性,文物所有权或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产权的行使,与普通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相比必然受到更多公法上的限制。
综上,文化遗产权的内容大致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接触、欣赏和保护权,传承权和发展权,开发利用权和参与管理权,所有权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等。不同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内容和权利大小各不相同,受到公权和其他权利的制约也各异。
五、结 语
“法律的真谛在于明晰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国家或国际社会之所以要以法律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因为文化遗产是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更因为不同的主体对这种珍贵资源享有不同的权利,从而也承担着不同的义务。”[6]确立一套统一而完整的文化遗产权体系,一方面可以通过权利义务的明确界分来规范和约束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将政府的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另一方面,对私权主体来说,确立其所应有的文化遗产相关权利亦可对其产生激励作用,通过法律权利的赋予进一步激发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事业的热情。此外,在文化遗产法制建设过程中,文化遗产权作为一个基础性概念关系到文化遗产保护中各利害方权益的平衡,亦关系到文化遗产立法的基本路径、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当然,本文只是在文化权利的视野下对文化遗产权的产生、概念、性质和内容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初步探索,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文化遗产权如何与其他相关权利进行协调、如何实现以及如何保障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1] 艾德,克洛斯,罗萨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教程 [M].中国人权研究会,译.2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2] 艺衡,任珺,杨立青.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阿努拉古纳锡克拉,塞斯汉弥林克,文卡特耶尔.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 [M].张毓强,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 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 [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 杨婧.文化遗产权刍议 [D].南京:河海大学,2006:3-17.
[6] 王云霞.论文化遗产权 [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2):20-27.
[7] Francioni F,Scheinin M.Cultural human rights: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human rights [M].Leiden,The 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8.
[8] Mo J H.Legal protection for rights to cultural heri-tage [J].Social Science in China,2003(1):138-139.
Abriefanalysisonculturalheritagerightfromperspectiveofculturalright
HU Shan-chen
(Law School,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Cultural right is a new kind of human right developed gradually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human right theory, which inherently includes some contents of cultural heritage right. However,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ight is a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human right. As a kind of legal rights, cultural heritage right has validity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t is a combination of rights enjoyed by certain subjects based on some kind of interests to, or certain connections with certain cultural heritage, under the premise of priority of protection. The subjects can enjoy and use the cultural heritage, benefit from it, dispose it and inherit and develop it at their own will within the limits of law. Cultural heritage right is a unity of public right and private right. The subject of it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group and human being; the object of it is the cultural heritage as a special resource; and the content of it includes the right to access cultural heritage, enjoy and protect it, inherit and develop it, exploit it,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of it, as well as ownership right and relev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etc.
human right; cultural right; cultural heritage right;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ultural heritage exploitation;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2013-09-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32311019)。
胡姗辰(1990-),女,江西宜春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化遗产法、外国法制史、比较法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 本文已于2013-12-20 05∶32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31220.0532.011.html
10.7688/j.issn.1674-0823.2014.01.05
D 913
A
1674-0823(2014)01-0023-08
(责任编辑:郭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