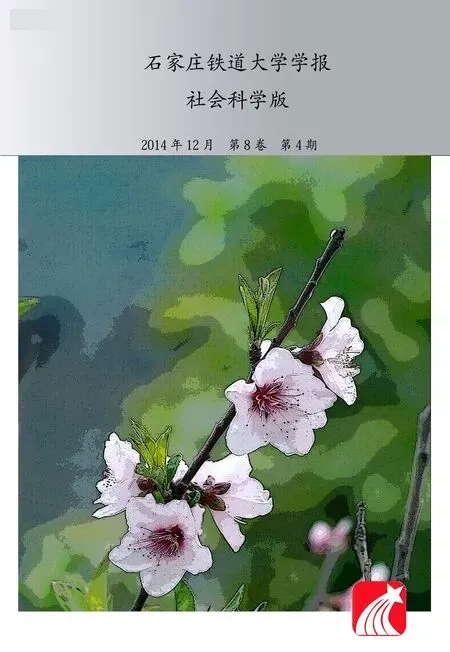启蒙与理性
——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2014-04-03马慧娜卢亚明
马慧娜, 卢亚明
(保定学院 中文系 河北 保定 071000)
正如《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前言中所写的,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个历史事件,但“什么是启蒙?”却是一个地道的德国问题。1783年,《柏林月刊》的一篇文章在脚注中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引发了随后十年德国人关于启蒙本质和限度的争论,这些争论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德1784年的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的第一部分便是对这一时期重要争论的收集与整理。该书的第二部分则收集了近年来对这一时期争论本身的历史情境和参与者进行探究的论文,第三部分则是福柯、哈贝马斯等学者对18世纪争论内容的反思。思想家们的论争与反思往往和他们关于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理性的认识密切相关。
一、启蒙运动:“理性时代”
启蒙运动常常以“理性时代”著称,“理性”在当时成为了衡量一切观念、学说和现实计划的标准。然而由于启蒙运动持续了一个世纪,影响遍布了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殖民地,所以“理性”这一术语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多重不同的含义。
在启蒙运动之初,以笛卡尔、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以自然法体系为基础,上帝依照数学模式创造出世间万物,因此人类的理性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他们宣称,人类能够识别出若干关于世界的简单假定,这些假定类似于几何学公理。正如几何学家能从少数简单公理推导出可靠知识的完备体系一样,人们也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说明世间万象。也就是说,人们可以运用理性来认识世界,获得确定的知识。理性不仅是活的知识的思维工具,也可以用来比作基本的宇宙秩序。一个根据理性建构起来的世界是一个自然法的世界,蕴涵着各种有序、可见和可操纵的关系。自然成为一个基本的隐喻,人为建构的人类社会也应以之为基础。启蒙时代的人们相信,由于自然是可以分析、理解和模仿的,所以人类领域也能建构起自然的形态。
不过,这种乐观的理性主义在启蒙运动时期慢慢受到怀疑,实际上,启蒙运动也可以认为是以一部质疑理性主义的怀疑主义著作——培尔的《历史批判辞典》(1697年)——开始的。培尔在《历史批判辞典》中质疑已有宗教、科学、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确立起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以对传统的怀疑态度为基础,成为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立场。启蒙学者在批判理性主义时,仍然声称是运用理性追求真理。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普遍的探究和怀疑心态,或者说,就是批判。事实上,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精神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致性因素。启蒙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以笛卡尔、莱布尼兹和斯宾诺莎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理性成为知性的工具,其目的不再是建构体系而是批判:用理性仔细考察、分析和质疑公认的知识,促进知性活动的发展。启蒙运动时期,单纯运用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与怀疑主义所提倡的质疑立场结合起来,形成了批判的精神。虽然自18世纪以来,学术界就形成了数种关于启蒙运动的诠释,但是如果说启蒙运动有什么东西能够打破国界和不同思想之间的限制,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那就是这种源自理性的批判精神。[1]
二、康德:理性的公开运用
启蒙思想家把理性推举到至高无上的法官的地位,以此来清除人们头脑里的愚昧、狂热、自大和怯懦。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后期的思想家开始对理性进行反思,试图深入到理性原则本身更内在层次的理解,“只有这种深入,才向我们展示了启蒙的全部深层意蕴。这就是由康德所代表的‘批判理性’的思想,它直接地反映在康德谈启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即《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2]
这篇文章是《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第一部分中最为著名的一篇,该篇文章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成竹在胸,因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毫不费力地对启蒙下了定义:“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如果不成熟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知性的决心和勇气,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自己招致的。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3]
康德在后面接着写道,这种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是由身体上的未成年导致的,而是由缺乏决心和勇气造成的。这种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是因为人类的懒惰和怯懦,因为处于不成熟状态真是太容易了,康德写道,如果有一本书能替我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具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就不需要我操心了。监护人也注意到绝大多数人都把步入成熟看作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为了使自己驯养的“牲口”变得愚蠢,避免这些温驯的动物从拴住它们的摇车里迈出一步,监护人向它们展示这样做就会碰到的那种危险——虽然这种危险的程度就像在最狭小的沟渠上做了一次不确定的跳跃,但是大多数人会害怕这种危险而吓得不敢去作进一步的尝试。所谓启蒙,就是要有决心和勇气不依赖别人的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去思考。这种“勇气”并不属于知性本身,或者通常所说的“逻辑理性”本身,而是属于一种超越型、实践型的“理性”,即自由意志。[2]11在康德这里,是否有勇气自己运用自己已经成熟的知性也就是批判理性,成为启蒙的关键。
康德认为,人们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言论自由)是启蒙唯一并且必要的条件。他小心翼翼地说这种自由是一切被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自由是无害的,康德将理性的运用分为公开的运用和私下的运用,[4]259这一分法与人们日常对于公开和私下的理解正好相反。康德所谓的对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想象自己是在对全世界讲话)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而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为私下的运用。举例来说,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是理性的私下运用,这时他必须服从他所服务的教会的教义,但是,这同一个人作为一个学者,就可以以写作的形式公开发表他对教义缺点的认识以及改善的意见,而后一种则是理性的公开运用,这种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即言论自由)是启蒙的条件。如果每个人都不仅有决心和勇气并且有权利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对这个世界(在康德看来主要是宗教)进行批判,那么启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康德认为任何组织如果阻止人类启蒙、阻止理性的公开使用、妄图把后来的时代置于一种绝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尤其是十分迫切的)认识、清除错误以及一般地在启蒙中继续进步的状态,那么这个组织就是在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
三、哈曼的讽刺:理性公开运用的可能性
按照上面的逻辑,启蒙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稍加分析就会注意到,理性的公开使用(言论自由)应该是启蒙的结果而非前提条件。康德说言论自由是所有被称为自由的东西中最无害的一种,但是自由应该是启蒙的目的,既然言论自由就包含在自由之中,那么这两种自由就不可能分头去实现。言论自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而获得其在现实中存在的依据,所以,康德是把启蒙呈现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在实践中,绝不会有任何一个统治阶层会允许其公民有无限的言论自由。
康德理论中的这个问题最早是他的好朋友,也是启蒙运动的反对者哈曼发现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的第一部分收录了哈曼的《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
弗雷德里克·C·拜泽尔认为,哈曼是对康德所辩护的“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普遍性和不偏倚性的信仰”“最具原创性、最有力、最有影响的批评者”。[4]308《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发表之后不久,康德的启蒙理念就受到哈曼的讽刺。在《致克里斯蒂安·雅科布·克劳斯的信》中,哈曼尖锐地指出,康德在对启蒙的定义更多地是从美学的观点而不是从辩证的观点得到了阐明和详述。哈曼敏锐地认识到理性公开使用的自由在实践中的不可能性,他嘲讽说对于那些可以在家中(诵经台上、讲道台上)喋喋不休谈论心里话的女工来说,一旦称为国家的合同工,理性的公共使用不过是一块餐后的甜点,而且还是一块奢侈的甜点,而理性的私人使用则是为了理性的公共使用而应该放弃的每日面包。
哈曼除了嘲讽康德划分理性的公开/私下运用的荒谬,还指出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实际上是在谴责受害者。哈曼说“自我招致”是个“可憎的形容词”,因为“自我招致”这个词在德文中的词根Schuld含有“内疚”、“罪过”或“过错”的含义。不成熟是问题所在,但是谁应该为不成熟负责?哈曼毫不客气地指出正是那位手握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来保证他的绝对正确和正统地位的“真正死亡的人”(腓特烈大帝)以及为其效劳的宫廷哲学家们(康德等启蒙哲学家)应该对此负责。哈曼拒绝接受这样的启蒙运动,他“宁愿要不成熟的天真,也不愿做监视者唯唯诺诺的或者被收买的仆人。”[4]151他认为启蒙只是“一线北方的光芒”,是“阴暗冷漠、毫无成效的月光”,只是给那些寻求统治他人的自我任命的卫士充当斗篷。他在致门德尔松的一封信中说,“我避免这个光芒,也许更多地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恶意。”[4]28
哈曼追问《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中的“别人”(“他人”、监护人)是谁,他认为康德不愿意指明“他人”是谁的原因是康德要讨好“别人”(国王),并将自己列于监护者之列。“别人”的出现涉及到康德的理论错位。他在“人类”之中分出“别人”(监护人),但并没有说明“别人”与“人类”的关系是什么,康德没有回答在“自己”中“别人”何在。有了“别人”,康德所讲的人,就既是类,又是个。在“人类”的概念中包含他者的存在,“别人”的存在消解了“个人”的意义同一性,并使“人”的概念暴露为一个权力的结构,造成理论逻辑推理上的错位。“人”的概念包含了“人们”与“别人”, “别人”有特权,是保护者; “别人”不同于一般人,拥有一种权力,不管是使人愚昧还是使人启蒙。但是,人是尘世间唯一具有理性的造物,在人这里,运用理性的那种自然禀赋,不可能在个人身上,而只能在人类中完全发展出来。(见康德《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命题二)也就是说“启蒙”概念是相对于“类”而言的,但是康德在对启蒙的定义中“人类”的含义发生了游移——出现了“他人”。
康德也意识到了他理论中的这种错位以及启蒙的长期性,他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不仅如此,康德还看到启蒙并不是仅仅凭借一场革命就能够完成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思想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改变:“一场革命也许会导致一个专制的衰落,导致一个贪婪的或专横的压制的衰落,但是它绝不能导致思想方式的真正变革。新的成见会像老的成见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乏思想的民众的缰绳。”[4]62对于康德来说,一方面他要鼓励理性的公开使用,另一方面他也要说服“别人”允许这种使用,因此哈曼所批评的对理性“公开”、“私下”运用的荒谬与对“别人”的讨好奉承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康德与哈曼的矛盾更多的在于启蒙的实践层面,更具体地说,在现实中理性的公开使用是否可能,这让人们不能不想起一句话:“哲学家总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四、福柯的态度:回到康德
哈曼从实践的层面质疑启蒙理性的光芒,而福柯则更多地从理论层面来考察康德的定义。福柯认为“何为启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难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个问题,现代哲学就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的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5]
作为尼采的忠实信徒,从他的第一部著作开始,福柯就努力表明启蒙的每一个胜利怎么会成为一种新的、阴险的支配的凯旋——启蒙的每一个进步也许只是迈向黑暗的更进一步。[4]27但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断地反思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回答,①认为启蒙就是批判,提出“回到康德”的口号。
在《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一书的第三部分,福柯在他的文章《什么是批判?》中认为康德描述为启蒙的东西正是他描述为批判的东西。[4]392福柯认为人们需要批判,批判的任务在于确定正当运用理性的前提条件,从而确定人们可以知道什么,必须做什么,又可能希望什么。福柯注意到启蒙和支配之间的关联,认为批判就是不被如此这般的治理的技艺,不愿意被治理,就是不接受权威所说为真的东西为真,或者至少是不因为一个权威告诉人们它们是真的就相信它们,只是在自己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接受时才接受它们。[4]390-391他认为批判就是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被统治者向自己提供了一个权力,以便就真理的权力来质疑真理,就权利对真理的述说来质疑权力。在福柯看来批判的焦点本质上是权力、真理和被统治者的相互牵连的关系。[4]391
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中,福柯着力于从知识、权力、自我以及三者关系的研究入手,他最终表示宁愿人们把他自己的工作理解为康德开创的“自我批判本体论”的一部分,“自我批判本体论”是“对我们究竟是什么的批判,同时就是对那些施加于我们的限制的历史分析,就是一种有可能超越那些限制的实验”。[4]46在对康德启蒙定义反思的基础上,福柯提出批判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而是深入某件事件的历史考察,这些事件曾经引导人们建构自身,并把自身作为人们所为、所思以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批判是具有谱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福柯认同康德的座右铭“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但是改变了对它的解释:启蒙首先意味着有勇气重新创造一个自己。[4]27-28总体上来说,福柯认为康德对启蒙精神的规定没有错,但他坚决反对启蒙理性的全面运用,认为这同启蒙的批判精神相背离。
无论如何,正像福柯所说,启蒙就是批判。作为从世界当中出来说话的人,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来运用理性,争辩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4]31我们也必须鼓起勇气运用理性来持恒批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身处的历史时代,从而走向漫长的“成熟”之路。
注释:
①主要有1978年的《什么是批判?》、1984年的“Kant on Enlightment and Revolution”以及1984年的《什么是启蒙?》三篇文章,前两篇参见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篇参见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年版。
②引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参考文献:
[1]彼得·赖尔,艾伦·威尔逊.启蒙运动百科全书[Z].刘北成,王皖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邓晓芒.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J].史学月刊,2007(9):10.
[3]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C].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2.
[4]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福柯著,杜小真编选.福柯集[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