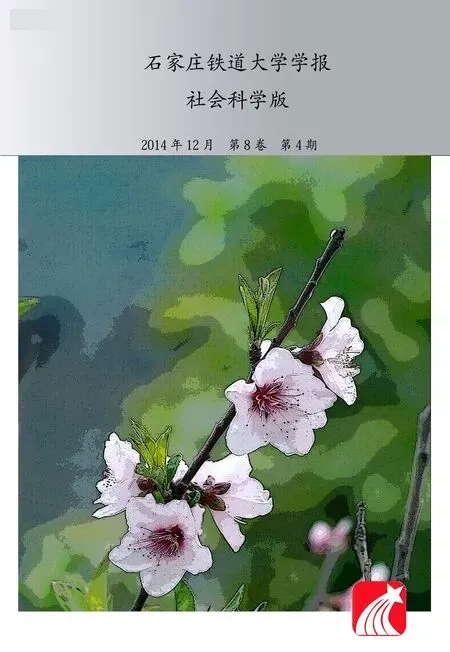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2014-04-03高传华宋益乔
高传华, 宋益乔
(1.山东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2;2.山东聊城大学,聊城 252012)
一、现代隐逸派的生成和概述
隐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和中国知识分子心理构造的重要内容。每个时代都会出现甘守一隅、躲避凡俗的隐士,他们或者寄身于山水田园,或者神游于琴棋书画的艺术世界,即使是那些不以隐逸为主要倾向的知识分子,如诸葛亮、王维、李白、苏轼等,在他们的行为、心态和文学作品中也包含着隐逸的追求或兴趣。辛亥革命前后,随着现代政治体制的引入和建立,中国从古典时期转入到现代时期。但是由于时局的动荡,民族的纷争,导致知识分子的理想不断破灭,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左倾和右倾之间选择了躲避的姿态,与当时的时代和主流刻意保持着距离,成为那个时代的隐士。他们或者隐身于佛门,如李叔同;或者闭户读书,如周作人;或者隐身于市郊研读佛经,如废名;或者隐身于名山大川,如黄宾虹。他们的隐逸之道是对传统隐逸文化的延续,无论是隐逸方式还是艺术创作,都有着浓郁的古典色彩,体现了文化过渡时期隐逸知识分子的两面性。
隐逸文学,则是由隐逸文士及有归隐倾向的羡隐文人共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它既包括隐逸文人本身,也包括了他们与“隐逸”相关的物质性实践与精神性实践。[1]
现代隐逸文学出现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伴随着五四的落潮,困倦、彷徨成为时代的普遍精神征候,理想破灭之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发生了分化。[2]以鲁迅为代表的左倾知识分子依然坚守文化的激进主义,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另一批文人逐渐离开了主流文学阵营表现出逃离意识形态的“出世”姿态,在文学上向隐逸文学传统靠拢,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文学染上了浓郁的隐逸色彩。作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学理论家之一,周作人的这一退隐姿态和退隐而作的大量闲适小品文,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流派——“隐逸派”。[3]
“隐逸派”文学发韧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新文学重要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周作人从浮躁凌厉的“叛徒”日渐消退为“绅士”,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隐逸思绪日渐抬头。由于周作人在新文学界的重要影响力,加之险恶的政治环境也使得许多作家纷纷远离时代潮流,开始经营自己的艺术世界。林语堂、废名、俞平伯等逐渐以周作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文学团体。阿英就认为 “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流派的形成,不是由于作品形式上‘冲淡和平’的一致性,而是思想上的一个倾向。”[4]现代隐逸文学的代表作家是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和沈从文,他们都属于京派文化圈,有着类似的从青年积极入世到中年退隐出世的人生经历,并且在性格气质、职业表现、审美趣味等方面有着相通之处。
二、废名的隐居生活和隐逸思想的形成
废名在乱世中曾经两度隐居。一次是1927年他卜居北京郊区西山正黄旗农舍,另一次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携家眷回故乡湖北黄梅县在乡村教书写作。废名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描述了自己的隐居经历和隐居生活。一方面,在隐居中他能尽享远离文化中心的那种田园般的风俗人情,从容品味自然人生。同时也体验着乡村简陋生活的某种窘迫。在隐居岁月中天远地偏,任性逍遥,这是庄禅返归自然的人生境界,也是他在乱世隐居中体验到的人生乐趣。
在早期的隐逸作家中,相比较于周作人、俞平伯、沈从文,废名的隐逸是真正自觉地切身实行的,废名的这种隐逸的“自觉”与他自身的性格经历、家乡的自然风情和禅宗传统以及周作人的影响密不可分,概括废名最终走向隐逸道路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归纳:
(一)废名的内向性格、童年经历和由此形成的自卑心理是促使他走向隐逸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直以来,废名给世人的印象不免有些怪癖、冷傲、不通世故,这和他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内向性格有关;又因为小时候曾一度被看得淡漠,因此也缺乏自尊心。总体而言,废名在他所成长生存的环境中显得孤独而自卑。废名自卑心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童年的诸多际遇:在家庭中遭到长辈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冷漠、长期病痛的折磨、从小被定下娃娃亲失去婚姻自主权的不如意。再加上“外貌的奇古”和没文化、谈吐装扮都很土的小脚太太,这些都使废名在北平文化圈内很不合群,他的这种自卑心理对他后来的人生选择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他从湖北来到北京求学的时候,从乡村环境中成长的废名在现代的都市文明面前就不免显得形单影只。他在农村与城市两种文化冲撞带来的苦闷中,最终选择了逃避现实,沉醉于回忆中的儿童世界(有论者就废名作品的儿童世界做过分析)。所以废名的性格带有封闭性,他有着一个独立的精神王国,固执而又善于自省,外表却极守规矩,很本分。废名有一种向往自由的精神,这使得他独立,但又不免耽于幻想。他留给外人的感觉通常是有些自负、狂傲,被看作是避世隐逸、特立独行的现代隐士。其实狂傲自负的人都有着自卑躁郁的一面,这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缺少底气而试图用别的方式来掩盖,废名也是如此。尽管这种矛盾的行为可能仅仅是潜意识的行为,主人公并未刻意如此。
(二)家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禅宗传统是废名隐逸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废名的家乡湖北黄梅山清水秀,这里既是黄梅戏的发源地,也是禅宗圣地。家乡秀美风光使得废名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他对故乡黄梅充满着无限的热爱,所以表现与赞美故乡的风俗景致成了他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自己的家乡美景,让废名从小对大自然就有着强烈亲近的渴望,这也成为了废名隐逸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湖北黄梅不但风景秀美,而且也是个很有佛学氛围的地方,自隋唐以来一直就是佛教圣地,禅宗思想也正是在这里发扬光大,走向了成熟。禅宗史上的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与黄梅有着莫大的历史渊源。城郊的东禅寺、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寺都是著名的丛林,废名从小就与这些地方有了接触,他后来在小学做教员时还专门写过《五祖寺》一文给学生作教材使用。黄梅浓郁的佛禅文化气氛对童年的废名乃至他以后的创作影响很大。佛教是偏重于出世的人生宗教,历史上凡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的文人墨客们大都走向了隐逸的道路,他们的文学作品或者朴素自然、平淡冲和,或者疏狂放达、灵秀飘逸。而废名的不入俗流,孤独地坚持着自己的人生道路,自然也与他的宗教情怀有关,这也使他的很多作品处处充满禅趣。废名的精神世界最终是在佛教禅宗的影响下改造完成的,他与佛教的亲近,禅宗思想正好契合了废名郁郁寡欢、自卑敏感的人格气质。佛禅文化的影响使废名的行为举止越来越偏行于现实,他对现实社会开始采取远距离地审视,他的小说也开始显露禅机,变得晦涩难懂。他创作的小说《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就渗透着浓厚的佛禅精神,这也说明废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为上都有着一个隐士的自觉。
(三)除了生活经历和性格因素之外,剖析废名在艺术上的审美倾向,发现文艺作品和师长、朋友(主要是周作人)对他的影响是他隐逸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在废名思想和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他的老师——周作人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适值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低潮时期。那时的周作人在正经历着从“叛徒”到“绅士”的逐渐转变,在局势动荡、兄弟情谊破裂和面临的人生不幸面前,他向往起不问世事的隐逸生活,开始提倡“闲适”,在“苦雨斋”里耕种“自己的园地”,作文也更冲淡平和,这一切都深深地影响了废名[5]。废名像喜欢陶渊明、李商隐等人一样,在现实的身边找到了“厌世诗人”的样板。在周作人的带动和影响下,废名也非常推崇六朝文章和陶渊明、庾信、杜甫及王维、孟浩然等慕陶诗人。这些诗人或者沉郁苦闷,或者精神放达,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同样具有强烈的精神内倾化,并且大多数是完全的隐逸诗人。周作人也一直把废名当作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之一,称他的思想最为圆满。因此,与周作人的惺惺相惜,废名在消极避世的人生道路上越走越远。
随着废名人生观的成熟与确立,特别是他在1926年废除了自己冯文炳的名字,开始沿用“废名”后,他的思想算是经历了一个完全地蜕变,他的“政治热情没有取得作用,终于是逃避现实”(废名语),[6]渐入隐士一途,介于出世与入世的半隐生活最终成了废名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生活的主要内容。废名对人对事的批评,内向、单纯、偏执、又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废名开始与社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才有了他在解放前两次总共长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
三、废名隐逸小说的渐变、人物形象的外化和意象的象征性
在现代作家中,废名不但是隐逸气息最浓、切身实践隐逸最坚决的一个作家,也是文学表现隐逸最深入全面的一个作家。废名持久而执著地编织着田园牧歌的幻景,如周作人在给废名的《桃园》作跋中就称,“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除了思想的表达外,废名小说的语言也自成一格,使读者在品读中感受到一种小小的田园带给你的那种恬静和悠扬。借用张爱玲评价路易士的一句话来评价废名的小说,“废名最好的小说全是一样的洁净、凄清,用色吝惜,有如墨竹。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7]
废名在隐逸中以童心和禅机来规避乱世,从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到1928年出版的《桃园》到1931年出版的《枣》, 再到1932年出版的《桥》和《莫须有先生传》,废名小说的隐逸情怀和庄禅色彩逐渐加浓,这也契合了废明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性格特质和思想发展道路。
(一)废名小说的渐变,从《竹林的故事》到《桥》到《莫须有先生传》
《竹林的故事》和《桃园》是废名早期的作品,也最能体现废名的素材的选取和艺术风格。他早期的小说描绘了静若远古,美如唐诗的田园风光。废名依附于古典情绪的生发,致力于生命的圆融。和同时代的乡土小说相比,它没有强烈的时代性,仿佛已经忘却了时间。也正因为如此,这里的人们才保持了远古的淳朴和美好的人性,安顿了漂泊的生命与灵魂。体现了一种参透生命的平淡和寄情山水的审美体验。
长篇小说《桥》也是废名小说中的隐逸色彩异常明显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表现了一种田园牧歌的格调,这不禁让人们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20世纪30年代即有评论者称它是“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引读者走入的世界是一个‘世外桃源’”。[8]
周作人认为从《竹林的故事》到《桥》,表现了废名创作的两个阶段。按照鲁迅的意见,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尚能“以冲淡为衣”,表现社会人生的一角;《桥》以后的创作就“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限于孤寂自我的狭窄范围”。周作人则强调了其中文体的变迁,即由“平淡朴讷”转向“简洁或奇僻生辣”,这种变迁既是向周作人的靠拢,又预示着对周作人的某种超越。[9]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认为周氏兄弟都从废名的创作中发现了废名的隐逸色彩的不断加强。
如果说《桥》建构了一幅审美的乌托邦,《莫须有先生传》则在内外的交流冲突中弘扬了一种对生命个体自主性的选择,这与其他隐逸作家所共有的个人本位主义相一致。但是这种过于内化的倾向也使废名与大众越走越远,最终蜷缩于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
废名在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高峰时期,从《桃园》到《桥》再到《莫须有先生传》,都显示出一种废名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风格和隐逸色彩。
(二)废名小说的人物与意向,充分暗示了废名的隐士倾向
1.废名小说的主要人物形象
刘文刚在《宋代隐士与文学》中提到隐逸文学的模式,他概括隐逸文学是用来表现隐逸生活的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用来塑造隐士形象的模式。周作人首开现代隐逸文学之风气,并用悠远平淡的笔调描写了过往的乡村记忆和他渴求的隐士的生活。但是塑造现代隐士形象,则肇始于废名。废名小说不仅是表现了对隐逸生活的赞颂,还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程小林、莫须有、陈聋子等,他们都具有浓厚的隐逸色彩,也是废名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形的变形。《桥》就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作者的隐逸思想,小林诗意地栖居在家园中,和废名回忆中的童年有着契合之处。废名对家乡和故乡人物的形象塑造通过优美的自然风景和单纯的人物性格表现了出来。《莫须有先生传》是废名自传性非常强的一篇小说,莫须有先生同废名一样,先是隐居西山,后来因战乱流离失所,他与官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追求精神的自由,甘于贫困和寂寞,莫须有身上充满了钱理群所概括出来的“废名气”。[10]《菱荡》里陈聋子作为一个平凡的乡村人悠闲自在,恬然自得,是作者老庄理想人格的投影,也是作者废名自己的夫子自道。
2.废名小说的意象:桥、塔、坟
善用意象是废名小说的特征之一,在废名的小说中,丰富的意象构成了废名人生理想的一种投影。桥是废名所喜爱的意象之一,它通常象征着此岸与彼岸,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曾经分析过这幅画中“桥”的原型意义:“它的唯一的意义似乎在于它表示出一种悬空感……表示出艺术家不希望完全出世,……但同时又希望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保持距离。”[11]废名最著名也是他用力最多的小说就叫《桥》,在其他作品中桥也反复被提及,对废名而言,桥不仅是一种事物,还是一种形式,象征着某种联接物“凡有这边渡到那边都叫做桥,不在乎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废名心中桥的哲学意蕴,他在《竹林》中曾写到“我的灵魂还永远是站在这一个地方,看你们过桥”。
塔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产物,在废名的作品中它象征着安全的隐逸场所,是代表着一种出世精神和隐逸情怀,废名曾多次提到他对“塔”的喜爱,在《桥》的序言中他这样写道,“这一卷里面有一章题作《塔》,当初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的在上面刻几个字”。[12]塔与桥由此构成废名乡土世界最具有意味的审美化形式。
坟作为乡土世界的重要景观也是废名小说中常用的意象之一。他在《桥》、《清明》、《钥匙》里描写坟时超越了坟的物理意义,而赋予它诗意的情怀,坟关涉着人的生死,是人生的装饰与大地的点缀,是诗情的负载体。坟和废名笔下的桥、塔一样,都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过渡。不过桥隐喻了一切形式的眺望与关怀;而塔是从入世到出世的转换,坟则是从生界到死界的象征,从隐逸的深度而言是逐步加深的,也反映了废名隐逸文学的丰富性和宗教情结。和许地山等宗教作家关注佛教义理的阐释相比,废名的“如羚羊挂角”的天然境界要高出不少。在缺少宗教氛围和出世情怀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废名这方面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
李健吾说废名“仿佛一个修士,一切都是内向的,他永远是孤独的,简直是孤洁的”。[13]废名的田园小说蕴含着现代人生的孤独体验,寂寞地走着自由主义者的艺术之途。
四、废名在现代隐逸派中的承上启下的地位:从周作人到废名,到沈从文
从周作人到废名再到沈从文,他们无一不是田园农耕时代的怀旧者,是渗透于传统文化之中沉溺于幻想时代的文人。就整体而论,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字有着独特的敏感,对于社会和政治则有出乎意料的迟钝。隐逸作家是现代社会的流浪者,无所寄身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对传统保持了一种迷恋乃至依赖的姿态。当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带着其侵略性和铜臭气蔓延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驱离或诱使世代生存其上的人们远离了家园。一部分敏感的怀旧者难免心情复杂却又无可奈何。在经历了“五四”潮起潮落的纠葛与缠绕,使他们转向艺术世界,用文字和不彻底的行为来营造自己的世界,故土的小桥流水、花草虫鱼,黄发垂髫,既是宁静的世外桃源,也是历来隐士们最理想的隐居场景。
废名是通过周作人和新文学走向作家之路的。在武昌学习期间,他就接触了新文学,并且受到了周作人的影响。1921年11月,废名给在北大任教的周作人寄去了自己的作品稿件,并有了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想法,这既是废名文学创作的开始,也是他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
废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以后,在1923年9月7日,他和周作人有了第一次正式见面,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师生情分。
京兆布衣的周作人虽然喜谈隐逸,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倡导者,加之那一代知识精英根深蒂固的辛亥情结,他真正隐居的日子并不多,或者说周作人隐逸得并不彻底,真正实行隐居的,正是废名。在上文所提到的废名隐居于西郊农家,读李义山诗,读老子庄子,渐及佛经,终于悟道,他超过了周作人,与周作人的差异也由此产生。
如果说废名受教于周作人又超越了周作人,那么沈从文也受到了废名的影响,同样也超越了废名。
沈从文的小说虽然在田园题材和优美的抒情风格上受到了废名小说的深刻影响,但也摆脱了废名后期小说中谈禅论道的名士气。沈从文早期复杂的人生阅历,使他对人生和自然有着比废名更为深切与复杂的体验。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乡村展现了一种发自湘西这片僻远土地的淳朴与剽悍,而不是废名的那种陶渊明似的安闲与宁静,是一种民间的原始与简陋,而不是士大夫的俯视的“华兹华斯格调”。沈从文介入废名的小说创作的视角与周作人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们共同艺术情趣的体现。行伍出身的沈从文熟悉那些真实而亲切的山水、风俗和人事,而周作人则通过回忆性散文的形式表达了对浙东小城镇世界中儒家温情格调的失落的怅惘。废名在中国传统的隐逸文化的背景中,上乘周作人,下起沈从文,为中国的现代抒情小说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沈从文等京派文人共同转身,以隐逸的形式苟全于那个乱世,既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选择,也和他们相似的出身环境,内向的性格特质和人生的种种不得意密切相关。
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虽然废名、沈从文不像周作人与废名那样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沈从文深受废名的影响是学界的共识。而沈从文在许多场合中也多次提到废名对自己创作的影响。
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代表了现代隐逸派的艺术成就。废名在周作人的影响下逐渐远离时代思潮,保持一种中立者的宁静姿态。他自己讲“终于是逃避现实,……我最后躲起来写小说了,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14]沈从文虽然也是隐逸一派,也有着性格内向沉静、在京派文化圈内不自信的一面,但他性格中又有着湖南人的那种倔强,那种逆境下对自我的高度认同(恰恰与湖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样)。所以沈从文在安静里有着躁动的一面,尤其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人性的积极探索。他曾经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5]在沈从文作品沉静安逸的背后有着浓厚的情感跃动。沈从文作品的这种审美的“静感”与思想情绪的“动感”增添了阅读的耐性与文章价值的厚度,正如周作人散文的朴素与浊感相兼融所带来的独特的魅力一样。而相反,废名作品的干净、清丽和宁静虽然自成一格,但品读的味道就单纯、平淡了一些。正如郁达夫所比较南国之秋与故都的秋的差别那样:“南国之秋,当然也有它的特异的地方,比如廿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之与馍馍,鲈鱼之与大蟹,黄犬之与骆驼。”[16]
沈从文在隐逸中不放弃对现世的关怀,是对废名沉溺于庄禅的一种反动,却是对周作人隐逸理论的一种呼应。废名把周作人的隐逸从羡隐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隐,沈从文又把隐逸的自觉回返成为一种审美,一种艺术叙事的方式,一种人类情感的家园。废名从隐逸实践上完成了对周作人的某种超越,沈从文又在隐逸作品的题材、人物多样化的塑造和情感表达的多样性上完成了对废名的某种超越,现代隐逸文化在看似循环中实现了隐逸行为和艺术审美的圆满。
尽管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的人生经历、地域风情、知识结构差异很大,但在审美意境的构造上,却有着某种延续和相通之处,那就是平淡朴讷的艺术风格。平淡朴讷,固然是一种语言的形容,更是一种气质和性情。这种沉静的气质和拙朴的性情就流动于周作人、废名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若隐若现、蹊径独辟的归隐泉流。[17]他们崇尚自然、倡导趣味的情怀、追求中庸和谐的人生态度及平淡朴讷的审美倾向,在20世纪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以进取、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主潮中显得异常独特,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居于边缘的,既具现代精神,又与传统相延续的另一种价值选择。
参考文献:
[1]许海丽.试论中国古代隐逸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J].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2(3):114-117.
[2]席建彬.隐逸:五四时期文学的一种转向[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3(2): 107-109.
[3]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初论[D].聊城:聊城大学,2006.
[4]阿英.俞平伯小品序,无花的蔷薇——现代十六家小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79.
[5]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体系初建[J].呼和浩特:语文学刊,2009(11):113-115.
[6]许海丽,宋益乔.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J].山东社会科学,2012(8):51-55.
[7]张爱玲.诗与胡说,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134.
[8]灌婴.桥[J].新月,1932,4(5).
[9]张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金昌庆.寄情林泉:废名小说中隐士原型的变形[J]. 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1(3):9-13.
[11]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2]废名.桥·桃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3]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14]废名.废名小说选·序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5]沈从文.序跋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6]郁达夫.故都的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
[17]杨联芬.归隐派与名士风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版,2005(2):5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