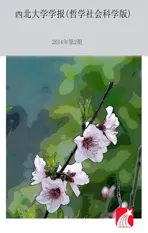仪式理论视野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探究
2014-04-03郭子林
郭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在古埃及人看来,宗教不是以广泛认可的神学原则为核心,也不是以普遍认可的特殊教规为基础,而是“由人们在与神联系时所做的事情构成的”。学术界将古埃及人在这样“做事情”时表现出来的行为称为“cult”(祭仪)。“cult”这个词在这样使用时基本上与“ritual”(宗教仪式)一词表达的含义相同,都强调具体的宗教活动或行为[1](P326),而非抽象的教义或神学理论。正如B.E.夏夫尔所说,在古代埃及,“仪式是宗教的中心”[2](P18),最能体现这种宗教的本质和思想。同时,宗教在古埃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而,宗教仪式可以为我们理解古埃及历史和社会提供洞见。
西方学者自19世纪末期就开始研究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中多运用人类学的仪式理论,主要考察仪式的程序及其宗教内涵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埃及宗教仪式固然具有宗教意义,但也必定有着深刻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内涵。那么,西方学者为什么更多地强调其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而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呢?他们是怎样展开研究的?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埃及宗教仪式?本文拟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的理论依据进行考察,阐述西方学者以仪式理论为基础进行的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实践,通过对古埃及新年节的个案考察和剖析,找寻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方法或途径。
一、仪式理论

在人类学领域,关于仪式内容的研究,经历了从早期的“神话-仪式”学派到“功能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解释主义”学派,以及从“宗教”到“社会”的内在变化;关于仪式的形式和范围的探讨逐渐由宗教意义的仪式扩大到日常节日和仪式;关于仪式意义的讨论也越来越宽泛[5](P2-6)。在这种学术基础上,罗纳德·格赖姆建构了仪式研究的基本框架[6]。凯瑟琳·贝尔的著作《仪式理论和仪式实践》重新建构起了有关仪式的学术讨论框架,《仪式:观点与维度》则对仪式进行了跨学科的综合介绍和探讨[7][8]。他们的研究都把宗教仪式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古埃及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文明古国,大多数仪式都与宗教有关。埃及学家B.E.夏夫尔从宗教角度研究古埃及的仪式,总结概括了学界关于仪式的十多种观点,涉及了仪式的概念、要素和特点等[2](P18-21)。
从罗纳德·格赖姆、凯瑟琳·贝尔和B.E.夏夫尔等人的研究来看,宗教仪式至少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首先,仪式是行为或实践,而非思想,与宗教思想比起来,更易于信徒理解和认识,甚至更易于信徒接受[7](P18-21, 112, 184-193)。同样的仪式实践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有不同意义[7](P81-82, 90)。这是仪式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学“神话-仪式”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特别关注的。其次,仪式的核心特征是仪式化,即为了某种目的,将普通事件仪式化,使其成为一群人参与的、具有相对固定程序和传统意义的行为或活动[7](P70-74, 90-93, 220)。这是仪式之所以成为仪式的根本要件。其次,仪式的最小单位是象征物,其意义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时相同,有时相异。因表现象征意义的程度和方式各异,象征物基本可以分为明显的、不明显的和隐藏的三种,往往与某种神圣性结合起来[9](P244-245, 246-248)[10](P19, 20, 26, 50-51, 36, 54)。这是仪式研究中必须重点考虑的特征之一,也是“象征主义”仪式学派的理论原点。此外,仪式当中充满了各种对立关系,或者说仪式建立起很多对立关系,例如有序与无序,但这些对立关系最终并未得到解决[6](P103)。这些关系往往体现的是权力关系,不需要使用强制力就可以指挥人们行动,实际上是将参与者置于事物的序列之中,使其产生一种效能感,使其自然地、有效地行动。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仪式不仅仅是权力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通过主张而非暴力、协商而非强制的方式规范社会秩序,使社会秩序合法化,甚至对社会变化和社会统一都有效用[7](P109-222)。这是仪式“功能主义”学派特别强调的特征。最后,仪式本身有生命周期,具有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过程[6](P57)。
纷繁复杂、形式各异、数目庞大的宗教意义仪式,一定还有其他很多特点,具体的仪式也必然有其独特性。人类学研究者正是基于对具体仪式表现出的某个或某些特征的强调,从而形成了一些研究派别,例如主张“仪式先于神话”,或“神话对仪式具有解说作用”,甚或“二者呈互疏关系”的“神话-仪式”学派,着重考虑仪式调节和统一社会秩序之作用的“功能主义”学派,着眼于仪式实践与宗教和神话观念性之间的结构对应关系的“结构主义”学派,以及侧重于描述仪式的程序和社会意义的“解释主义”学派等。这些学派的研究单方面地突出仪式的某个或某些方面,因而都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仪式特征,各个学派最终趋向妥协和折衷,对仪式进行“功能-结构”主义和“解释主义”的分析。
学者们认为,将庞杂的仪式归入各种类别更有利于对仪式的认识和研究[6](P33)。爱弥尔·涂尔干将仪式分为“积极仪式”和“消极仪式”两类[11](P413,574)。维克多·特纳将仪式区分为“生命转折仪式”和“困扰仪式”[10](P6)。罗纳德·格赖姆建议将大量仪式归入六种模式的仪式情感,即仪式化、礼仪、典礼、礼拜仪式、魔法和庆祝仪式[6](P35-51)。凯瑟琳·贝尔将仪式划分为六类:过渡仪式,历法仪式,交换和共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宴会、禁食与节日的仪式,政治仪式[8](P94-137)。仪式分类越来越具体,所涉及的仪式数量和表现形式越来越多,但宗教意义的仪式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在具体仪式的研究中,这些类别的划分只是一种参考,具体问题还需要具体分析。
学者们还提出了一些研究仪式的方法。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了基本路径:考察仪式的目的和原因、仪式的意义和效果[12](P37,185)。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研究仪式应该关注其展示了什么、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13](导论P17-18),即重视观察仪式的具体程序。凯瑟琳·贝尔指出,仪式的研究应该注重仪式化活动的起源、目的和效果[7](p. ix)。这些方法强调了仪式原因、程序、意义和效果的研究,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应该注意对仪式历史背景等予以探讨。
上述仪式理论观点较多地考察仪式活动和象征物的象征意义,重视仪式的人类学和宗教学意义,关注仪式对社会的作用,但仪式之于国家权力的作用等问题仍需深入探讨。
二、仪式理论背景下的古埃及宗教仪式研究
“无数的浮雕装饰着埃及人的陵墓和神庙,那些石头上雕刻的也正是仪式性的活动。”[3](P18)古埃及人的确实践了很多仪式,安娜·史蒂文斯主要根据考古史料反映的情况,将古埃及仪式分为“交换和共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和“过渡仪式”,但未能涵盖所有古埃及仪式,甚至偏重于社会仪式的考察[14](P727-737)。埃及学家D.B.瑞德福德将古埃及仪式分为国王的仪式、普通人的仪式、神的仪式和动物的仪式等四类[1](P326-337)。
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史料主要是浮雕、铭文以及纸草文献[14](P725-727)。从19世纪末期开始,西方学者就依据这些史料研究宗教仪式。1892年,E.纳维勒详细考察古埃及第22王朝国王奥索尔孔二世在布巴斯提斯的大神庙,发现并复原奥索尔孔二世的塞德节场面[15]。塞德节是古埃及国王的重要宗教仪式[8](P120-128)。纳维勒主要关注奥索尔孔二世塞德节场面和程序的复原工作,但他的研究工作开启了学界关于塞德节的研究之路[16],也从一定意义上启动了学界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随后,A.加德纳等人开始关注古埃及宗教仪式[17](P122-126),是通过对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的评述展开的。20世纪20年代, K.塞德详细考察了古埃及国王的“继承神秘剧”,这是研究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的重要史料[18][19](P222)。
如果说前述学者的研究还很难说是受到了当时人类学领域仪式理论的影响,那么A.M.布莱克曼于1933年在S.H.胡克编著的《神话与仪式》一书中,对古埃及神话和仪式的研究,则可以确定无疑地视作是受到了仪式理论的影响[20](P15-39),甚至是响应了人类学界关于仪式与神话之关系的讨论。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神话-仪式学派”关于神话与仪式的关系讨论非常热烈,弗雷泽提出了“仪式先于神话”的命题,爱弥尔·涂尔干、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则主张“神话是对仪式的言说”[5](第33、39页)。S.H.胡克主编的《神话与仪式》这本书里面的八篇论文,虽然研究对象不同,但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基本都承认神话对仪式的描述作用,认为古代近东的宗教仪式体现了一种近东文化模式的扩散过程[20](P3-14)。在《神话与仪式》一书中,A.M.布莱克曼明确认为几乎所有的古埃及宗教仪式都源于古埃及赫利奥坡里斯宇宙神学和奥西里斯-荷鲁斯神话[20](P15)。他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考察了古埃及奥西里斯节、敏节、加冕戏剧、荷鲁斯与哈托尔的婚姻节日以及欧派特节等,并着重探查这些活动中的仪式与神话关系[20](P19-39)。
随后,学界对S.H.胡克等人的上述观点提出很多质疑,主要是反对其关于近东文化模式的提法以及关于神话对宗教仪式之描述作用的观点,转而开始关注宗教仪式其他方面的内涵,例如宗教仪式的社会意义等。H.富兰克弗特详细考察了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神话、王权与宗教仪式之后,认为古埃及与巴比伦以及相关地区的宗教神话与仪式不具有相似性,不能描述为一种模式。虽然近东宗教是自然与社会的结合体,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也体现了人们的王权观念,但两地关于神话、仪式和王权的认识都不相同[21](P4)[22](P3-12)。S.H.胡克的观点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J.塞尔内在其著作中基本上是按照A.M.布莱克曼的观点展开行文的,首先介绍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进而阐述古埃及的献祭仪式和丧葬仪式等[23](P97-123)。1958年,S.H.胡克组织一批学者撰文对神话、仪式和王权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学界关于《神话与仪式》的质疑做出回应,强调国王在近东宗教仪式中的核心作用,认为这恰恰是近东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21](P1-21)。几篇论文都把重点放在对王权的研究上,H.W.费尔曼将一些古埃及宗教仪式称为“王权仪式”,在阐述古埃及王权的特点之后,重点介绍与古埃及王权直接相关的几个仪式,例如加冕仪式和塞德节等,证明国王在这些仪式中的核心作用[21](P74-104)。
这场论战将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很多西方学者投入到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当中,对古埃及国王的加冕仪式、塞德节、献祭仪式、丧葬仪式等都有所论及。这些研究大多关注具体仪式,或者某一类仪式。例如,A.加德纳研究了古埃及第18王朝国王郝列姆赫布的加冕仪式,C.J.布里克从节日的角度研究古埃及宗教,考察国王的节日,如塞德节等[24](P18-19)[25](P3-12)[26](P13-31)[27](P62-65)[28](P91-123)[29](P192-196)。这些研究体现了仪式研究中对仪式程序和象征物的重视,也体现了仪式研究从“神话-仪式”学派向“功能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仍在继续,但朝着综合和全面的方向发展,与仪式理论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埃米莉·提特为了探究古埃及人如何将宗教信仰结合进文化和社会组织中,考察古埃及人的宗教和仪式,重点探讨献祭仪式和丧葬仪式[30](P35-55, 119-147)。她在研究中既注重对古埃及宗教仪式程序的描述,也注重考察其体现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结构以及仪式与神话的结构对应关系,这基本上体现了仪式研究中“阐释主义”和“结构主义”相互妥协的状况。安娜·史蒂文斯将古埃及仪式分为“交换和共享的仪式”“困扰仪式”和“过渡仪式”,[14](P727-737)显然受到了凯瑟琳·贝尔的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成果当中,有些具体考察了某些与王权直接相关的仪式,注意到了古埃及宗教仪式与王权的关系。例如,B.E.夏夫尔在充分考察学界关于宗教仪式的观点之后,通过对一些国王参与的仪式进行简单考察,概括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在古代埃及,“仪式不是国王强加给人们、宣传社会统一或信仰的工具;它们是一种动态的、创造性的舞台,这个舞台使参与者经历社会稳定,创造出社会满意。仪式不仅仅是国王使他的地位合法化、控制人们经验的工具,仪式本身还是一种权力,允许和促使神祇、国王、死者与生者之间关系的修正和更新。”[2](P21)也就是说,B.E.夏夫尔认为古埃及国王参与的仪式主要作用是宗教意义上的,是为了仪式性地展现和修复古埃及人类社会宗教意义上的各种关系。实际上,H.W.费尔曼、H.富兰克弗特和C.J.布里克等人在论及古埃及国王参与的宗教仪式时,提出的观点与B.E.夏夫尔的观点基本一致,都强调这些仪式的神学或宗教学意义,而对其世俗意义的发掘不够。
可以说,学界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探讨,基本上是在人类学仪式理论的框架内进行的,重点考察仪式程序,通过象征物剖析仪式的宗教学内涵,对其世俗意义的探讨不够全面,有时甚至忽视这方面的分析。
三、仪式理论与史学视角的结合:以新年节为例
在古埃及大量宗教仪式当中,新年节占有重要地位,拥有悠久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特点。古埃及新年节的象形文字是wp-rnpt,意思是“一年的开端”。该节日最早可能从第五王朝就开始庆祝,直到希腊-罗马人统治埃及时期才被较详细地描绘在卡拉巴沙、菲拉、奥姆翁布、埃德福和登德拉等神庙中[31](P177)。
最完整研究古埃及新年节的著作是M.埃利奥特的《托勒密时期埃德福神庙的荷鲁斯祭仪》,主要介绍埃德福神庙记载的新年节的基本过程[32](P303-433)。H.W.费尔曼考察一个神庙当中的新年节场面,突出描述节日过程[29](P183-186)。J.G.格林菲斯综合介绍学界关于新年节的研究情况,详细论证新年节对于国王的更新意义[31](P178-180)。这些研究既考查古埃及新年节的程序,也关注其与古埃及国王的关系,但关于新年节与古埃及王权统治之关系的探讨仍有待深入[33](P1-6)[34]。
根据上述史料和研究成果,基本可以复原古埃及新年节的仪式过程。埃及的新年是埃及泛滥季第一个月第一天。新年节或许从上个月的最后一天开始庆祝,大约持续九天。节日期间,举行一些献祭活动和崇拜活动。节日开始于神庙的内殿(一般在神庙最内部,是与神庙大门正相对但相距最远的地方)。国王在高级祭司的陪伴下,在神庙内殿执行日常祭神仪式的开始仪式,即国王走上内殿的台阶,揭开神(太阳神)的面纱。然后,两支游行队伍在主祭者国王和高级祭司的率领下,沿着神庙圣所周围的走廊分别在不同的方向前进,到达食物祭坛和净化间,在这些地方举行日常性质的献祭和净化仪式。接下来,游行队伍再次经过食物祭坛和中央大厅返回来。祭司们扛着神圣王旗,抬着神雕像和各种祭品,游行队伍最终到达神庙屋顶。神被引领进屋顶的小亭子里。献祭仪式再次举行。节日的高潮发生在神庙屋顶的小亭子里:正午时分,神的面纱被揭开,太阳光线恰好照在神的雕像上,从而使太阳与神神秘地结合起来。最后,游行队伍返回到内殿。这是新年当天的活动,之前几天的仪式只是在规模上比较小,基本程序是一致的;新年之后几天的仪式略有不同,重点在于举行庆祝与现任国王和其祖先崇拜有关的仪式[29](P183-186)[35](P93-96)。神庙浮雕描述的仪式仍不够详细,《布鲁克林纸草》补充了一些细节。在国王进入内殿之前,国王要首先进行洁净仪式,这与国王加冕仪式的部分内容相似;然后,国王还要经历一个睡醒或复活仪式;一些颂诗强调指出国王复活以后变得强大了[31](P178-180)。
费尔曼认为节日期间神与太阳的“神秘结合不仅更新了埃及的丰产和繁荣,还更新了埃德福和住在这里的荷鲁斯神以及其他神的生命和力量”[29](P189)。实际上,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新年节的中心在于国王的复活和其力量以及权力的更新,甚至可能是在重复国王的加冕仪式,对于王权的运作和实施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
首先,新年节宣传国王的神圣性。新年节在神庙内部庆祝,以太阳神作为庆祝的主神[31](P177),国王是唯一有能力与太阳神交流的人,而且纸草文献强调了国王的神圣性。“法老是众神当中的一个神,他出现在埃尼阿德(九神团)的面前,他变成了天国和大地的大神;法老是获胜者之一,使拉神战胜了阿波菲斯。”[31](P178-179)其次,新年节通过仪式场面宣传国王的各种权力。根据布鲁克林纸草,新年节的某些环节是在庆祝国王的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这两个仪式是国王获得王权的重要方式,也是对王权的确认,至少非常明显地宣传了国王的宗教权力。正如J.G.格林菲斯所说,新年节的最终目的是使“国王重新掌握王权”[31](P178)。其次,新年节起到了增强民众社会认同和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新年节的主要场面和铭文都铭刻在神庙里,似乎只有部分特权人物可以参加,但这样一个与农业直接相关的节日,又是在埃及农业年的新年举行的全国性的节日,所以全国臣民都能参与。神庙里描绘的只是国王直接参与的部分,古埃及普通民众在节日期间的活动并没有记录下来。广大普通民众参与受到国王非常重视的节日,从内心深处增强了个人的身份认同,进而产生一种对社会制度的认同,甚至产生某种民族主义认同[31](P225)。再次,新年节还起到了更新国王体力和权力的作用,使古埃及王权统治每年以新的面貌继续下去。根据布鲁克林纸草,古埃及国王在新年节中仪式性地死去和复活,这既是国王的生命力的更新,也是其统治权力的更新。以下几段文献即体现了这点:“他没有做任何不利于其城市神祇的事情,他没有做恶事,他在两地书吏法庭上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去年附着在他身上的邪恶已经被驱逐,今年的邪恶被毁灭,他远离了邪恶……他面向女神:你再次受到欢迎。”“他从这一年开始受到保护,免于其对手之咒语的伤害,祝和平,和平,呕,新年快乐。”[31](P180)这些文献说明国王在仪式性地去世之后受到审判,又因为没有做过邪恶的事情而复活,并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受到神祇的保护,免于受伤害和被诅咒。当然,新年节对于王权统治的运作与延续所起的这些作用,不是通过暴力或强制力实施的,而是依靠仪式本身所具有的宣传效果实现的。从而,新年节可以视作古埃及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6](P18)古埃及的新年节能够在埃及实施近3000年,不仅由社会风俗所致,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和经济原因。

其次,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也是新年节长期存续的重要原因。古埃及人的王权观念比较复杂,但基本观念很清楚:国王是神,至少是半神,国王的权力来自天国的神,国王的统治神圣不可侵犯,国王拥有对埃及和人民的所有统治权,掌握着玛阿特(mc3t),是真理与正义的化身,负有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责任[30](P3-15)[42](P131-145)。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关于国王的神圣属性。韦尔东认为,大多数精英或统治阶级的文献宣传埃及人几乎一贯地认为任何国王都是神,但综合古埃及各个方面的史料,可以看出,在普通埃及人心目中,国王的神性是有时间、空间和范围限制的;国王活着的时候,在执行与神交流的活动时才具有神性,而且永远不能超越大神。在其他时间和场合,国王以人性存在;国王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才通过各种手段(例如建筑神庙、将自己的雕像或肖像与神像放在一起等)宣传自己的神性[43](P1-30)。宗教仪式是集中展示这些宣传手段的良好机会,新年节更是如此。
第三,归根结底,新年节的举行和长期存在是由古埃及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农业生产依赖于尼罗河水的定期泛滥[44](P12)。古埃及人从早王朝开始就每年测量尼罗河水位,足见其对尼罗河水位和泛滥的重视[45](P93-164)。在古埃及历史上,尼罗河能否定期泛滥,对农业和社会的影响非常明显。在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和第二中间期(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尼罗河水未能按时泛滥,致使农业歉收、社会混乱、政局动荡[46](P272,363-364)。涅菲尔提预言详细记载了古埃及社会因尼罗河低水位而出现的混乱局面[47](P234-240)。关于尼罗河泛滥,埃及人尚不能科学对待,认为神祇在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影响尼罗河水位变化和泛滥的大神是奥西里斯。奥西里斯被视作埃及的丰产神,甚至有时与尼罗河及其泛滥等同起来[23](P100),他的复活会直接影响到尼罗河泛滥。奥西里斯是去世的国王,还是冥界的国王。去世的国王能否顺利转变为奥西里斯,是尼罗河能否泛滥的重要原因。奥西里斯的儿子是人间的统治者荷鲁斯。国王去世以后,新国王的登基与去世国王转变为奥西里斯是同时进行的。这样,作为荷鲁斯的新国王能否顺利登基,掌握王位,直接影响着尼罗河的泛滥[48](P70)。另外,在埃及人看来,农业能否丰收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太阳。他们对太阳给予了极大崇敬,赋予了太阳很多神话。在一个关于国王的神话里面,国王是太阳神拉之子。国王去世以后,顺利通过来世审判,升上天国,回到太阳神拉那里。在埃及人看来,国王的去世意味着邪恶战胜了正义,混乱战胜了秩序。国王去世以后,留下来了一个短暂的宇宙混乱期。去世的国王在第二天清晨与太阳神拉一起升上天空才意味着宇宙秩序的恢复,其标志就是新国王的登基。从古王国开始,“拉之子”便是国王的五个伟大名字之一。国王的登基就是在太阳神拉的参与下进行的[49](P219)。也就是说,尼罗河能否定期泛滥,太阳能否按时升起,宇宙秩序能否恢复,农业生产是否可以丰收,都依赖于新国王能否顺利登基和加冕。这正是新国王选择在国王去世以后的第二日清晨举行登基仪式的原因之一。尽管学界关于加冕仪式举行的时间尚有争论,但无论如何加冕仪式都要在三个季度当中某一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的第一天举行[17](P122-126)。这三个季度都是根据尼罗河泛滥和农业生产的过程来划分的。很多登基仪式和加冕仪式的铭文和浮雕涉及了与农业直接相关的太阳神拉、神奥西里斯、荷鲁斯。从各种象征物体现的象征意义来看,新年节不仅在庆祝国王的加冕仪式,或者说在每年更新国王的加冕仪式,还在更新国王的生命和活力,进而最终更新自然活力,使农业丰产。
古埃及国王和统治阶级每年在神庙中举行大规模的新年节,既是社会风俗所致,也与古埃及人的宇宙观、王权观念息息相关,更是由古埃及的农业经济决定的,这种仪式对于王权统治的运作与存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以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用以宣传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拙文之所以能够对新年节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主要是将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学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通过分析仪式中象征物的象征意义来阐释仪式活动过程、场面和浮雕及铭文的历史意义,从而揭示古埃及新年节的程序、历史、社会意义和其得以存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根源。
总之,过去关于古埃及宗教仪式的研究基本上与西方人类学仪式理论的发展保持一致,即以人类学仪式理论为基础,着重阐发宗教仪式的宗教意义,而对其世俗内涵的发掘不够。新年节是古埃及宗教仪式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仪式。通过对新年节的考察,本文发现,古埃及宗教仪式具有一定的宗教意义,也具有很强的世俗内涵,尤其对王权统治的实施和延续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是以古埃及国王为首的统治阶级用于宣传“国王是神”的王权观念或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当然其长期存在是以古埃及的历史、社会文化和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可见,将仪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史学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埃及宗教仪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参考文献:
[1] REDFORD D B.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M]. vol.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 SHAFER B E. Temples of Ancient Egypt [M]. London: I. B. Tauris Publishers, 1998.
[3] HARRISON J E. Ancient Art and Ritual [M]. London: Willams and Norgate, 1914.
[4] ROUTLEDGE C D.Ancient Egyptian Ritual Practice: irt □t and nt-c[M].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2001.
[5] 彭兆荣. 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 GRIMES R L.Beginnings in Ritual Studies [M].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7] BELL C. Ritual Theory, Ritual Practic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8] BELL C.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 TURNER V, TURNER E. 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an Cultur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10]TURNER V. Forest of Symbol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11]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2] 拉德克利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夏建中,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 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 张云江,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4]INSOLL 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Ritual & Relig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5]NAVILLE E.The Festival Hall of Osorkon II in Great Temple of Bubastis [M]. London, 1892.
[16]郭子林. 古埃及塞德节与王权[J]. 世界历史. 2013 (1).
[17]GARDINER A.Review on The Golden Bough[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15 (2).
[18]SETHE K.Dramatische Texte zu altägyptishchen Mysterienspielen[M]. Leipzig, 1928.
[19]MEYEROWITZ E L R. The Divine Kingship in Ghana and Ancient Egypt [M].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 1960.
[20]HOOKE S H. Myth and Ritual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21]HOOKE S H. Myth, Ritual and Kingship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2]FRANKFORT H.Kingship and the Gods [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48.
[24]SHORTER A W. Reliefs Showing the Coronation of Ramesses II[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34 (20).
[25]GARDINER A. The Baptism of Pharaoh[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50 (36).
[26]GARDINER A.The Coronation of King Haremhab[J].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953 (39).
[27]JAMES E O. Seasonal Feasts and Festivals [M]. London: Thames & Hudson, 1961.
[28]BLEEKER C J. Egyptian Festivals [M]. Leiden: Brill, 1967.
[29]FAIRMAN H W.Worship and Festivals in an Egyptian Temple[J].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1954-1955 (37).
[30]TEETER E. Religion and Ritual in Ancient Egyp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GRIFFITHS J G. Atlantis and Egypt [M].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1.
[32] ALLIOT M. Le culte d’ Horus àEdfou au temps des Ptolémées[M].Le Caire, 1954.
[33]施治生、刘欣如主编. 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4]郭子林. 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古埃及公共权力的演变为例[J]. 史学理论研究,2008 (4).
[35]WATTERSON B.The House of Horus at Edfu: Ritual in an Ancient Egytian Temple [M]. Tempus Publishing Ltd., 1998.
[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7]CONNOR D O, QUIRKE EDS S. Mysterious Lands [M]. London: UCL Press, 2003.
[38]ALLEN J P.Middle Egypti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ieroglyph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9]LLOYD A B.Psycholog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Egyptian Cult of the Dead[M]. W.K.Simpson ed.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Ancient Egypt. New Haven: Yale Egyptological Seminar, 1989.
[40]SILVERMAN D P.Divinity and Deities in Ancient Egypt[M]. B.E.Shafer ed.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 Gods, Myths, and Personal Practi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41]SHAFER B E.The Nature of Egyptian Kingship [M]. D.O.Connor and D. P. Silverman eds.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 Leiden: Brill, 1995.
[42]HORNUNG E.Idea into Image: Essays on Ancient Egyptian Thought [M]. New York: Timken, 1992.
[43]WILDUNG D.Egyptian Saints: Deification in Pharaonic Egypt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44] BUTZER K W.Early Hydraulic Civilization in Egypt[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76.
[45]BREASTED J H.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M]. vol.1.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06.
[46]刘文鹏.古代埃及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7]FAULKNER R O, WENTE E F, SIMPSON W K.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and Poetry[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72.
[48] SPENCER A J. Death in Ancient Egypt [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49] FINEGAN J.Archae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ncient Middle East[M]. California: Westiview Press,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