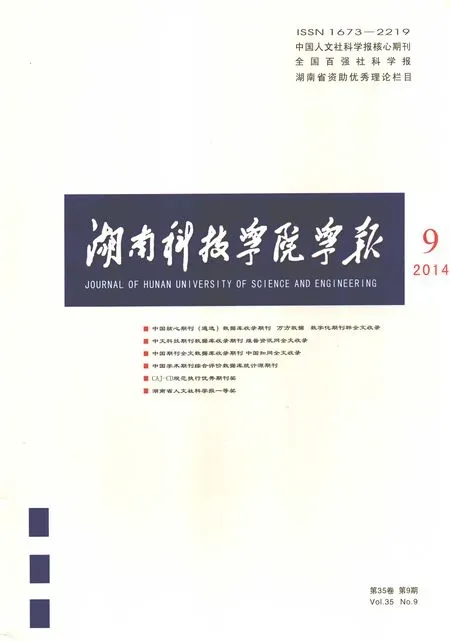贾谊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悲壮气质
2014-04-01刘范弟
刘范弟
面对自然的茫茫星空,置身社会的纷纷人事,人们难免会产生一种迷茫之感,常常会有这样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正是有了这些追问,人类社会才产生了文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才得产生和发展,社会才有了今天的繁荣和进步。这种迷茫永远不会消失,这种追问永远不会停止,学术和科学的发展永远不会终结,人类社会的进步也就将永远行走不息。
作为湖湘之人,生活在湖湘这块热土上,面对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湖湘文化,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迷茫和追问:湖湘文化是什么(内涵本质)?湖湘文化从哪里来(源流)?湖湘文化又将向何处(如何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并试图解释,就是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也可说是对湘学的研究。就个人来说,我更愿意使用湖湘文化研究这个概念,至少比湘学研究包容更广一些;这次的活动是“湘学溯源”,其实叫做“湖湘文化溯源”或许更合适些。
在谈“贾谊与湖湘文化”这个题目之前,必须先简单介绍他的经历,并说一下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18岁即有才名。汉文帝刘恒刚即位(前202年出生,前179—前156在位),就征召二十出头的贾谊为博士,不到一年又升他为太中大夫。23岁时,贾谊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任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32岁就抑郁而亡。其著作有散文和辞赋两类,《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政论散文都很有名,辞赋则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虽然仅活了32岁,也未担任过掌握实权的重要官吏,但他在中国历史上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检索一下四库全书,以“贾谊”检索,正文中共出现6229次,注释中出现4865次,以“贾太傅”检索,正文144次,注释11次,总共出现11429次;再检索一下屈原,以“屈原”检索,正文4283,注释4111,以“三闾大夫”检索,正文252,注释114,总共出现8760次。在中国历史上赫赫盛名的屈原在四库全书中出现的次数竟比贾谊少了2669次。即使加上“屈平”在四库正文和注释出现的1544次,也仍比贾谊少了1125次。
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在学者们的话语中,贾谊比屈原更受人关注。
这首先是因为贾谊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汉文帝即位,贾谊亦进入朝廷,当时汉朝(前206年)建立刚刚二十多年,文帝、贾谊都刚二十出头,君臣二人当然都想干出一番大事业。贾谊不断提出政治方策和治理策略,他认为汉朝建立已经二十多年,应当改变清净无为、墨守秦制的治理思想和实践,要创新制度,复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悉更秦之法”;要吸取秦亡的教训,以民为本,“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新书·大政上》);要施仁义 、行仁政(《过秦论》);要加强中央集权,“众建诸侯少其力”,以消除尾大不掉的割据危险(《论治安策》),这样才能长治久安。贾谊的策略和主张,就是要进行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要使儒家思想逐步成为统治思想的主流。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和思想,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汉文帝并未全部采纳施行,但对西汉一代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如汉武帝施行推恩令和独尊儒术,唐太宗“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思想及对农民让步政策,就是如此。毛泽东曾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贾谊的地位和影响也不容忽视。
他著有《新书》十卷五十六篇,这是贾谊政论、杂论(内容广泛)文集,反映了贾谊的哲学、政治、经济、教育等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后世学者研究引用者众多(以“贾谊新书”检索四库,有655条,如以“新书”检索,则有8286条之多);他的政论散文《过秦论》(收在《新书》中)、《论治安策》、《论积贮疏》(收《汉书·贾谊传》中)等,理据充分,逻辑严密,铿锵有力,气势浩大,而又文采斐然,刘勰《文心雕龙·奏启》称其“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对后世政论文创作影响极大。鲁迅曾说 “惟谊尤有文采……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
在中国文学史上,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旱云赋》等,也是璀璨夺目的明珠,尤其是《吊屈原赋》、《鵩鸟赋》更是其中的瑰宝,是中国辞赋史上的名篇,影响后世深远。
主办者规定我谈的是“贾谊与湘学”,我想还是“贾谊与湖湘文化”更好一些,具体说,我谈的主题是“贾谊与湖湘文化精神”。
关于湖湘文化精神,有过多种概括,如爱国主义、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不信邪有担当等。我曾在《善卷、蚩尤与武陵》一书中概括了两点:(1)强悍、坚韧、耐艰苦、不怕死;(2)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后来在2011年1月湖湘文化研究会年会上作主题发言“蚩尤与湖湘文化”时,又加了“湖湘文化的悲壮气质”一点。
关于贾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一般认为主要有二:
一是对湖湘迁谪文学的影响。湖湘迁谪文学发端于屈原,为贾谊承袭和发展,后世杜甫、刘禹锡、柳宗元、秦观等人则在屈、贾二人的影响下发扬光大。湖湘迁谪文学的基调虽有对个人遭际的感慨,但其主要精神则是对个人人格操守的坚持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国忧民情怀,而这些正是在屈原的《离骚》和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等作品中发端和发展起来的。
二是对湖湘士人人格构成的影响。贾谊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对社会政治有卓越见解,勇于担当直言,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的政策和制度建议,“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但却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最终远离权力中心。他在往长沙时“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实在也是借凭吊与自己有着类似遭际的屈原以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不平,以及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和满腔报国热血而无法施展的愤懑。朱汉民先生认为贾谊《吊屈原赋》“所诠释的屈原就是在穷困之境而彰显人格精神特质的”,并将“忠贞正道”与“任性孤行”的精神融为一体的典范人格的人物。贾谊自己其实也是一位这样的人物,他不管在权力中心还是在谪贬之远,始终心在朝廷,忧念苍生;他得志时锋芒毕露,失意之时也不与邪俗合污同流,清醒孤傲人格独立,他以困境中之“神龙、骐骥、凤凰”(《吊屈原赋》)比喻屈原实际上也是自许,可见他与屈原的心灵相通人格精神也是相同的。朱汉民先生在《屈原与湖湘士人的人格建构》一文中对这种人格于湖湘的几位著名人物(柳宗元、王夫之等)的人格形成的影响作了分析,认为屈原和贾谊对湖湘士人人格构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大家可以参看。
我今天想从湖湘文化精神中的悲壮气质这个角度来谈谈贾谊。
贾谊身上所体现的悲剧色彩是十分明显的,他有盖世才华,有过人的政治睿智,有极佳的机遇,有成为公卿的可能,有成就一番千古伟业的时运,但却因为种种因素而壮志未酬,三十二岁就郁郁而没(壮志未酬事堪哀);但他又是幸运的,少年得志,中枢挥遒,议论大政,君王点首,群臣服膺,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学成就,都对后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他的人生又是精彩和壮丽的。
毛泽东有两首以贾谊为题的诗,其一为《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其一为《七律·咏贾谊》:“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诗中对贾谊的评论,正是着眼于他的生平遭际和成就贡献,从“哀”和“壮”,即悲剧性和壮丽性的统一,亦即悲壮性这一点来展开的,而“千古同惜长沙傅”一句,则更是点出了贾谊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所以说,贾谊的遭际是悲壮的,贾谊的事功也是悲壮的,贾谊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这一点,与自古以来的许多湖湘精英人物是极其相似的。
炎帝,湖南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开启了湖湘人物的悲壮命运的宿命。他成就了多少伟业,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最初诗篇,但最后却尝药断肠而死。
袁珂曾说过:炎帝一系的人物多具悲剧性。
炎帝少女精卫,“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陶潜《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可歌可泣!何其悲壮!
共工,也是炎帝的后裔,《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生祝融,祝融……生共工。”《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看来他以失败告终,但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注说:“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何其悲壮!
夸父追日的神话为大家熟知。据《山海经·海内经》“炎帝……生后土”和《山海经·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的记叙,可知夸父是也炎帝的后裔。他追日而死,其杖“化为邓林”,荫泽后人,其事其情何其悲壮!
刑天,《海外西经》“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陶潜《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也是和炎帝神农有关的一个神话英雄。《路史·后纪三》说:“(神农)命邢天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邢天”,就是”刑天”的别写,可知他是炎帝神农的臣属;又刑天葬首的常羊山,也和炎帝神农有关。他的事迹何其悲壮!
蚩尤也是湖湘文明的一位开创者,但他的悲剧命运不言而喻,本是与炎黄同列的“古天子”,却身首分离,并在后世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奸人和恶人,这用不着多说。而蚩尤的悲剧命运,似乎与他的出身族属有关。如果追究起来,蚩尤应算炎帝一系的人物:宋代罗泌《路史·后纪·蚩尤传》说:“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可见蚩尤与炎帝是同族当为可信。孙中山1920年《合肥阚氏重修谱牒序》说“蚩尤为中国第一革命家,因轩辕氏夺其祖神农氏之天下,乃集其党徒八十一人,与轩辕氏血战多年,至死不屈”。其人其事何其悲壮!
说到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那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说可以一个“蛮”字概括的,有说是敢为天下先的,有说以天下为己任的,有说是敢于担当的,这些都对,在我看来,这些特质的共同点,似乎都有一种悲壮的底质或者说是一种悲壮的气质。
从湖湘精英人物身上尤其体现出这一点。从炎帝一系的湖湘上古人物之事功和遭际,到屈原的投江殉志和贾谊的“壮志未酬事堪哀”,到南宋末李芾的抗元,清初王夫之的深山著书,到近代曾国藩的打落牙和血吞,左宗棠的扛着棺材出天山,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陈天华的蹈海,黄兴武装起义的屡败屡战(与孙中山活动海外不同),直到当代彭德怀的出兵朝鲜、庐山上书,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胡耀邦的辞职,朱镕基的“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都强烈地体现了这一悲壮气质。
这些湖湘精英人物的行事风格,应该说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为周围环境和人事所迫。在面对责任和道义的时候,正是这种曾子所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丈夫气概,才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湖湘文化精神的悲壮气质。
这一悲壮气质与上古炎帝一系人物的命运及性格何其相似!与屈原、贾谊的命运及性格何其相似!这其中的渊源和关系可以深思。或许正如某些人所说的,湖湘人长于开创而拙于守成。在天崩地裂的乱世,在需要解民于倒悬的水深火热的时代,湖湘人或湖湘文化精神大放异彩,一旦天下太平,社会需要秩序,需要按部就班发展,湖湘文化似乎就有些格格不入了。毛主席有一首咏梅的词,我想可能较好地概括了湖湘文化的这种气质:“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