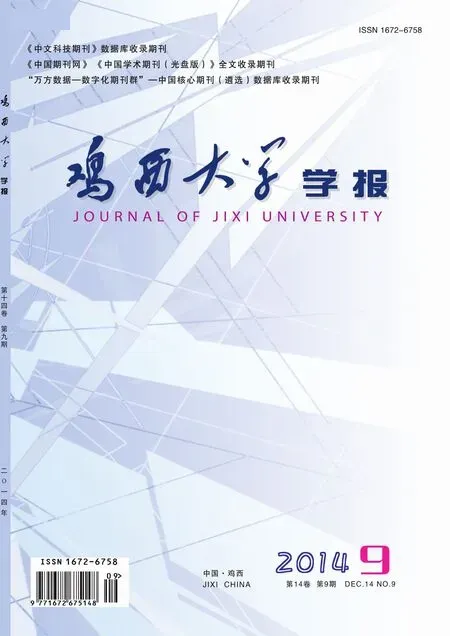论《乐府》等篇中体现的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
2014-04-01倪亚青周晓露
倪亚青,周晓露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1000)
一 从《乐府》等篇考察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
德国的格罗塞认为世界上众多的艺术起源有一规律,即都是“综艺”——诗、乐、舞一体,他在《艺术的起源》中说道:“最低级文明的抒情诗,其主要性质是音乐,诗的意义只不过占次要的的地位而已。”[1]我国早期音乐也具有这样的特点,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郭沫若关于此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他说:“中国旧时期的所谓的‘乐’,它的内容包含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的东西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仪仗、田猎、雕镂、建筑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音岳)者,乐(音洛)也’。凡是使人快乐的,使得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为‘乐(音洛)’。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大约是音乐的享受足以代表艺术,而它的术数是最为严整的原故吧。”[2]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百兽率舞”,[3]到《毛诗序》“诗者…….足之蹈之也”,[3]都认为音乐可以作为言的一种补充和发挥。而刘勰生活的齐梁时代,诗与乐的互动就更为频繁,“由于历代帝王的倡导于上,南朝自东晋以来,歌舞声色享受的欲望总在不断地膨胀着,王公贵族的歌舞声色活动有时候常常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们的主子,使得南朝的歌诗艺术呈现出独特的繁荣景象”。[4]
刘勰的文艺理论专著《文心雕龙》是总结了前世和当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经验再加上刘勰自己的创作体验而写成的,无怪乎清代章学诚称之为“体大虑周”。这本书充分体现了刘勰的文学观,在文学的起源流变、文学的分类、文学的教化作用等方面都做出了深刻的论述。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中也有不少关于音乐的论述,由此也可以对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做出一个梳理。但是考察其音乐美学思想,是不能离开诗歌观、文学观而专门谈音乐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诸种样式中,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从这里出发,就能理解对文学有深刻而独到见解的刘勰有不少关于音乐的论述。
1.音乐本质论。
从音乐本质论来讲,刘勰认为音乐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应。由此他在《时序》篇中依次梳理了三皇五帝时音乐的发展,“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熏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殆姬文盛德《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风动与上,而波动与下者也”。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从唐尧一直到周太王时期,政治都清明,统治者有贤德,因此这些时期的音乐是欢快的、平和的。而到了幽王、厉王的统治时期,统治者残暴,政治昏暗,音乐终究透漏出对政治社会的不满。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刘认为每个朝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不同,导致的这个朝代的音乐风格也就不同,音乐的发展变迁决定于政治经济的兴废盛衰。
刘勰的这一思想直接继承的是春秋战国至两汉的音乐美学思想。《荀子·乐论》中就有:“乱世之微,其服组,其容妇,其俗淫,其志利,其行杂,其声乐险”,[3]明确提出音乐反应现实生活,到了汉代《礼记·乐记》中云:“凡音者,生人心者……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声之道与政通”,[5]乐与政通思想的形成表明儒家对音乐与现实的关系认识的成熟。也正因为音乐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反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音乐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师旷觇风与盛衰,季札鉴微于兴废”。
2.音乐美感论。
在音乐的美感论方面,刘勰强调音乐应具有中和之美,应该是雅正的。他痛惜“自雅声浸微,溺音腾沸”的状况,认为自秦以下,雅正的音乐慢慢衰落了,随之兴起的是淫靡的音乐,因此毫不犹豫地给出对汉代乐府的批评,“《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燕》群篇,靡而非典,实韶夏之郑曲也”。对魏之三祖的批评也异常地尖刻,“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其实《桂花》是赞美汉朝疆土的辽阔,威德的卓著;《赤雁》是歌颂捉到赤雁是神所赐的福泽,根本就不存在“丽而不经,靡而非典”。而曹操、曹丕的乐府诗,是乐府中的名篇,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刘勰本人,在《明诗》中也高度评价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事实上,刘勰评价音乐的标准就来源于自古而来的雅乐的标准,而当时上至统治阶级,下至黎明百姓,莫不对俗乐趋之若鹜,刘勰批评的实质是不满当时以乐为享乐工具,旨在倡导乐府教化观风的思想,企图纠正当时重俗乐、重娱乐的不良倾向。他的这一主张从《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能够得到佐证。在开篇《原道》中就提出“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圣人写的五经等经典是按照“道”写成的,并且反应“道”。因此需要研读圣人经典的文章才能把握住道,这就是为什么刘勰在《原道》后紧接着就提出了要《宗经》《征圣》。在文学观上的提倡经典的雅正必然让刘勰在音乐上也提倡音乐的雅正。
3.音乐的功用论。
从刘勰的音乐本质论和美感论方面就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刘勰在音乐审美功能上的观点,刘勰几位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方。”音乐被刘勰赋予了特别重大的作用,能够感动天地、四时和人心,影响四面八方的教化,因此先王在制作音乐的时候很谨慎,“必歌九德”,期望通过歌声把“九德”宣传地更好,同时也要防止淫靡的音乐,“勿塞淫滥”。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从孔子对《关雎》的评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6]到《礼记·乐记》中的:“乐者,天地之和…..和,故百物皆化。”[5]可以看到儒家一直把乐限制在礼的范围里,合乎礼的便是“中和之乐”。早在刘勰所处的魏晋时期,儒家思想解禁,士大夫们更加注重自我感受及精神生活的自由,这就难免会追求一些非“中和之乐”。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简要地总结刘勰的音乐观,即他认为音乐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具有重大的教化作用,为了充分发挥音乐的这一教化作用,应该提倡中和、雅正的音乐。
二 刘勰这种音乐观形成的原因
上述是对刘勰音乐观简要的分析,笔者试着从几方面来分析这种音乐观形成的原因。文人是时代的产物,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的重大影响,不管是时代的社会风气,还是这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抑或是文人本身的遭遇也会对思想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几方面的原因都指向刘崇儒的思想主张。
1.当时政治经济状况的影响。
首先,刘勰提倡的雅乐是建立在周王朝的“礼乐制度”上的,商周时期是封建王朝开始形成的时期,建立一系列的严明政治军事制度,而“礼”作为维护这些制度的手段也慢慢形成了体系,又因为商周时期宗庙祭祀活动的频繁,“乐”承担了早期宗教维护的重要手段,因此从商周开始形成的礼乐制度就成为了维持中国封建社会的有效手段。但是在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社会,讲求“礼”等级的儒家思想遭到极大的破坏,由此作为等级表征的“雅乐”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沦落。“礼”的破坏一方面加速了“雅乐”的流失,“雅乐”的流失又反过来促使“礼”的进一步瓦解,因此魏晋时期走向了“礼崩乐坏”的境况。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可以知道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虽然战乱频繁,但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南史·循吏传序》中称刘文帝时“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7]史书记载南齐武帝时也是“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女士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化妆。桃花绿水之间,秋风春月之下,无往非盛”。[7]富足的市民生活,必然带动俗乐的兴起,上面的史料充分地展现了普通百姓对歌舞的非同寻常的喜好,而支撑他们这一喜好的正是以经济上的宽裕为基础的,至于掌握国家大量财富的统治者,就更不用说了,正是繁荣的经济为统治者提供了纵情享乐的基础,《南史·萧惠基传》曰:“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7]《宋书·乐志》载:“孝武大明中,以韩、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庭。”[8]统治者所热衷的正是俗乐,而这些俗乐正是刘勰在其《乐府》篇中强烈批判的,礼乐失去了其原本的教化作用,只是作为统治者享乐的工具,难怪刘勰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人要大声疾呼,提倡“中和之乐”。
2.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从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也可以为刘勰音乐观的形成找到重要的依据,正如白宗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9]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思想得到极大发展的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当时儒家正统地位日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儒、道、佛、玄各种思想交融在一起,刘勰正是身处在这样一个思想错综复杂的时代,受到各种思想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事,但正如很多研究者所认为的一样,刘勰的思想主导倾向始终是儒家思想,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这种说法源远流长,元代钱维善在《文心雕龙》序中就说:“自孔子没,由汉以降,老佛之说兴,学者趋于异端,圣人之道不行,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固自若也。当二家横流滥觞之际,孰能排而斥之?苟之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征,而立言著书,其亦庶几可取乎?呜呼!此《文心雕龙》所由述也。”[10]
3.刘勰个人经历的影响。
刘勰个人的经历也印证了他崇儒的思想主张,《序志》篇中言及他七岁时的一个梦,“梦若彩云若锦”,他上去采摘。后来三十岁的那个梦是追随孔子而行,可见前述绚烂的梦正是象征了孔子思想的丰富性,因此才会在成年后再次梦见,下定决心跟随。定居佛寺而梦随孔子,只能说明其功名心未灭。这正是其在《序志》篇中“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人生理想的生动体现,可以看出,刘勰著述的目的非常明确:有益于世用,是非常世俗的,这是典型的儒家的建功立业思想的印证。刘勰虽然对自己的著述的《文心雕龙》颇为满意,但庶族的地位决定了他只能通过装扮成一个小贩求于沈约的车前,“约便命取之,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11]这本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在一段时间得到实现。
以上通过对《乐府》等篇中有关音乐论述的分析,大体梳理出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从音乐本质论、音乐乐感论、音乐功用论三方面具体地论述,在此基础上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社会风气和刘勰本人的经历去着手分析刘勰此种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这些尝试性的论述有助于更好地、全面地理解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
注释
①《文心雕龙》引文均出自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德]格罗塞.蔡幕晖,译.艺术的起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184-189.
[2]郭沫若.青铜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187-188.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30,22.
[4]赵敏俐,等.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3.
[5]李学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77,1090.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30.
[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6,1697,1500.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52.
[9]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8.
[10]吴云.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701.
[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