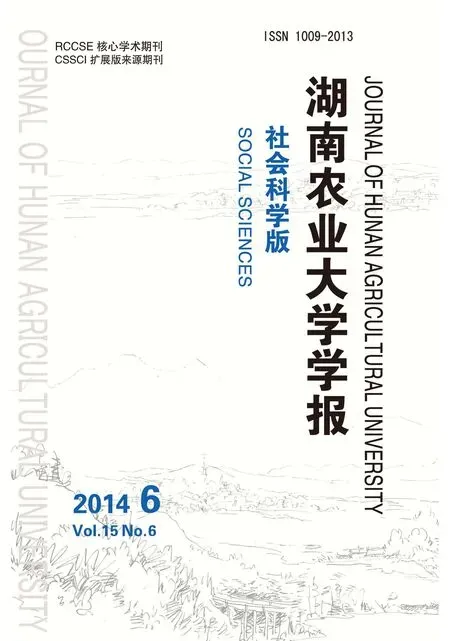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
——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2014-03-31田孟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与实践模式的演进
——基于成都市的考察
田孟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工作,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定点再分配行为。基于成都市的调查分析表明,其实施主要经历了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运作模式的演进。这三种模式虽然能吸引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积极参与增减挂钩项目,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会不同程度地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压力,不可能将增减挂钩项目惠及全部或大部分村庄,带来新的不公平和权力寻租等问题。
增减挂钩;土地整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持证准用;成都市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国土资源部确立山东、天津、江苏、湖北、四川五省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省市。截至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7个省(市、区)被纳入试点范围。增减挂钩“周转指标”,也从2006年的7.38万亩,增加到2014年的90万亩。随着增减挂钩政策试点范围越来越大,这一政策受到学术界和媒体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从事挂钩项目的人员和相关研究者主要基于增减挂钩项目的落实,对如何构建增减挂钩项目实施的技术体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研究”[1-7]、“增减挂钩规划研究”[8-11]、“增减挂钩项目过程管理研究”[12-13],以及“增减挂钩运作模式研究”[14-24]。当前学界对土地增减挂钩政策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张宇[25]、李旺君[26]、任平[27]、张怡然[28]等认为,这是一项有益的制度创新,是城乡统筹的一条有效路径;既有利于加速和规范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特别是调控土地和人口城镇化过程,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促进土地资源保护和土地利用规划实施。有利于优化土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同时强化农村集体土地资产管理,显化农村土地资产,反映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真实价值,有利于实现城乡双赢发展。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增减挂钩是新时期的“圈地运动”,是城市发展主义意识形态霸权对农村乡土生活方式的恶性破坏。陈锡文[29]指出,这场让农民上楼运动的背后“实质是把农村建设用地倒过来给城镇用”,“固然解决了城镇扩张缺地的问题,但却把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留给了乡村和农民”,“目前的土地增减持钩基本上都是拿劣地换良田,耕地质量打了许多折扣,同样的面积但粮食产量却差别很大,长此以往,将影响我国粮食安全”[30]。叶敬忠等[31]揭示了这一政策背后的“发展主义逻辑”。冯帆等[32]认为,农民合村并区后基层组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面临困境,农民社区化和楼房化的生活使村落文化面临灭失的命运,农村浓郁的血缘关系将被淡化。
上述研究尽管观点殊异,却同属一宗,即都是从增减挂钩所产生的具体结果进行评价和揭示。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极大,同样的政策在不同区域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单纯依据个别具体的结果就对宏观政策进行评价,不可避免会出现迥异的判断和认识。土地增减挂钩不仅仅涉及到单纯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涉及到“村庄”这个东亚社会特有的基本社会单元及其治理等诸多问题[33-36]。四川省成都市是最早开展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地区之一,多年来实施了大量政策试点项目,积累了丰富的政策实践经验。基于此,本文结合成都市的实践模式,在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及其本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实施模式的演进及效应,以辩明政策及实践模式的改进方向。
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及本质
中国的土地整理工作以农用地为主要整理对象。增减挂钩政策总体上可以归属于土地整理范畴。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将“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为贯彻这一基本国策,国土资源部于1997—1999年间出台相关政策,并最终形成通过土地整理新增耕地实现“占补平衡”的制度体系。
为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整理工作,1999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地方政府可根据土地整理后新增的耕地面积按一定的折抵比例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优惠政策。国土资源部规定的折抵比例是60%,地方上出台的具体折抵比例则有不同。当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也属于“农地整理”范畴,当时成都市称其为“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范畴,即“金土地工程”。但这种土地整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可供整理的后备土地资源越来越少,难度越来越大。二是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系数越来越低,折抵的土地指标越来越有限,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三是有些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土地指标,不惜破坏生态环境,采取“毁林造田”、“填湖造田”的办法新增耕地,从而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于是,国家土地政策的重点开始从农用地整理向集体建设用地整理的方向转变。
2004年10月,国务院出台第28号文,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首次出现在国务院级文件上。2008年国土资源部第138号文件明确规定,“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从此,增减挂钩开始在全国以试点的方式广泛开展。
这一政策直接针对的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耕地总量不受影响。土地增减挂钩设“项目区”,分拆旧区和建新区,项目区内各类土地总量要平衡。在建设用地方面,拆旧区和建新区“一减一增”,项目区内的建设用地总量保持动态平衡。与此同时,拆旧区将土地复垦后得到了多少耕地,理论上就可以在建新区占用多少耕地。因此,在耕地方面“一增一减”,项目区内的耕地总量也能够实现动态平衡。两相结合,不仅可实现项目区内各类土地的动态平衡,还能促进这些土地的改变和调整。
总的来看,近年来中国出台的土地相关政策,不断强化对耕地的保护。土地整理对象出现了从农用地向集体建设用地的变迁。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就是这一政策变迁的产物。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土地整理。由于土地整理一般采取项目的工作形式,因此增减挂钩同样需要通过“立项”才能被实施。那么,什么村能够实施项目,而什么村没有机会实施项目,便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很多没有机会被立项的农村,将不可能获得这种类型的反哺和利益照顾。项目立项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某种意图,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控制地向一部分农村输送相应的政策及财政资源。
三、增减挂钩政策实施模式的演进
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实践过程来看,成都市经历了从政府独立运作的增减挂钩,到引入社会企业参与的增减挂钩,最后发展为“持证准用”制度创新下的增减挂钩三种主要模式。
1.基于财政担保贷款的政府独立运作模式
增减挂钩项目从“立项”开始便涉及农民还建安置房建设、农民旧房拆迁、农民搬迁、还建安置中的过渡、土地整理复垦等诸多环节。整个过程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实践过程中,项目区农民的需求和地方政府对项目区内建设的要求两大因素决定了增减挂钩项目的资金投入。
一般来说,为了项目实施和验收的方便,地方政府倾向于进行连片拆迁和规模化复垦。这往往与参加项目农民的搬迁意愿和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政府增减挂钩项目集中连片的目的很难达到。农民需求越大,项目实施成本也就会越高。同时,地方政府对于增减挂钩项目的期待也会影响挂钩项目的成本。地方政府的意图和期待不同,项目实施的成本必然存在很大差别。如成都市把农村还建安置点建设作为“统筹城乡”的一个重要抓手,倾向于连片整理,并严格要求还建安置点必须执行“四性”标准,配套水、电、气、视、网、光纤等各项基础设施,以及超市、卫生室、运动场所、老年人活动中心、便民服务站等各公共服务设施。这必然抬高项目中拆旧还建支出。
实际上,增减挂钩项目的资金筹集主要通过项目的土地指标获得。征收项目建新区内土地后,将这些土地进入招、拍、挂,从而市场交易获得土地出让收益,以此来平衡增减挂钩项目的资金投入[37]。项目相关主体之所以愿意拿出土地出让收益来平衡增减挂钩项目的资金投入,与当前中国土地利用和管理体制机制,尤其是“计划外指标”和“计划内指标并存密切相关。
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基层政府每年都可从上级政府获得相应规模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亦称为“计划内指标”。这个指标由中央政府确定,然后层层下达到基层。为贯彻土地基本国策,中央政府倾向于向下偏紧地供应土地指标。同时,按照增减挂钩政策,地方还可通过项目实施获得部分土地指标,也可以用于建新区的土地征收,将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变为国有土地。由于以这种方式产生的指标不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范围之内,可以称其为“计划外指标”[38]。两类指标虽然没有本质差别,但从地方政府而言,获得“计划外指标”和“计划内指标”有较大的成本差异。“计划内指标”由上级政府直接下达,在获得环节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但在使用时需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开垦费”(以下简称“两费”),主要用于“占补平衡”。而“计划外指标”则是通过开展增减挂钩项目而获得,在获取时是有成本的。在使用增减挂钩指标时,已经提前交纳的“占补平衡”费用可以冲抵“两费”。可见,增减挂钩政策为地方政府获得土地指标提供了新路径。
按照现行征地制度,无论“计划内指标”还是“计划外指标”,征地都必须是基于规划的政府行为,其他市场主体均不具备资格。不管是哪个项目业主实施的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并取得土地指标,最终都需要交到政府手上才能够把指标落地。因此,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之下,“计划外指标”最终将汇入地方政府手上。一般来说,由于增减挂钩项目需要与成百上千家农户打交道,而且还涉及土地性质变更,项目资金投入周期长,风险大,投资回报没有保障,一般的企业都不愿意参与到这样的项目中来。在增减挂钩项目的早期运作模式中,大都由地方政府及其掌握的投融资平台以财政为担保向银行贷款,贷款所得用于开展项目。项目完成后获得的土地指标自然就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通过使用这些土地指标去征地,再通过土地出让获得的收益来还贷款,从而实现增减挂钩项目资金的周转。这就意味着,在政府主导开展的增减挂钩项目中,地方政府拿城市里的土地增值收益来支付农村里开展的增减挂钩项目。因此,政府独立运作增减挂钩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而且直接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
2.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
随着增减挂钩项目实施规模扩大,程序越来越复杂,单纯依靠地方政府财政作为担保融资以获得项目资金的传统模式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要。成都市开始引入社会企业参与到土地增减挂钩项目中来,让企业先行实施增减挂钩项目中的部分乃至全部工程技术环节,等到地方政府利用获得的土地指标得到收益之后,再来支付这些社会企业参与增减挂钩所付出的成本和应获得的利润。
地方政府为何要引入企业参与实施增减挂钩项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开展增减挂钩,必然采取行政推动的方式,通过“压力型体制”向下级政府层层压任务。基层政府为了完成上面的政治任务,往往不会顾及农民的合理诉求和实际需要,从而容易出现“强迫”行为。逼迫农民上楼的运动受到广泛关注和指责。这使地方政府感觉到直接跟农民打交道的成本很高,通过外包给企业来做,可以避免把矛盾引到地方政府身上。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融资能力匮乏。单靠地方政府的财力没法支撑越来越多的增减挂钩项目,亟需社会资本先行垫付资金。然而,对企业来说,增减挂钩项目本质上也是一桩生意,盈利需要通过指标价格来实现。调查显示,土地指标价格一般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实际操作方法是由政府制定保底收购价格,调控土地指标交易市场,但这个保底价基本上就是指标的交易价[39]。如在成都市郫县,土地指标保底收购价格是以实施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预算成本为制定依据,并考虑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当地政府与公司签订合同,在精细核算每亩指标工程成本需 28万元的基础上,确保公司每亩土地指标有2万元利润,即以每亩30万元的价格保底收购。
在这里,尽管有社会企业参与指标的“生产”过程(也即“新增耕地”的生产过程),存在一定的市场化竞争机制,但这些社会企业参与项目仅仅是帮助政府完成与农户打交道、并完成一系列工程技术的工作。土地指标的交易市场是一个受到地方政府严格受控的市场,土地指标的“市场化”程度十分有限。由于土地指标只有通过地方政府才可能落地,因此这些土地指标的最终实际收购者必然是各级地方政府。
政府这些工作交由市场上的其他主体代为完成,并给其提供投资回报,似乎改变了增减挂钩的工作机制,实际上却并不对增减挂钩的基本性质有任何改变。原因在于,最后为增减挂钩项目的成本买单的,还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的利润是指标的实际成本和政府提供的保底收购价格的差价。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社会企业参与就表明增减挂钩是市场性质的了——其实质还是政府行为,或者说是政府作为唯一的最终收购方与市场上的指标供给方的一个交易行为。如果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的话,也只能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市场交易方式。
3.基于开发商“持证准用”的运作模式
引入企业参与增减挂钩项目虽然解决了项目资金筹集问题,但最终由谁承担这笔资金支出依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为此,成都市先是实行“持证准入”,最终制定“持证准用”制度,即要求那些在成都市参与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招拍挂的房地产开发商,在进行土地开发前,必须持有相应的增减挂钩指标,否则即使这些开发商拿到土地也不允许进行开发建设。其政策意图无疑是想将增减挂钩项目的成本部分转移到开发商,让这些开发商拿出一部分资金来购买土地指标,从而承担农村里实施的增减挂钩项目的成本。于是,土地指标的最终收购方似乎不必然是地方政府了。实际上,成都市这一新的运作模式就是试图把土地指标的“最终收购方”转移到房地产开发商这个群体,或者说是将农村建设用地整理的成本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相挂钩。
问题是政府的这个意图并不容易实现。在现行土地市场状况下,对于政府推出的每一地块的价值和收益,开发商早就有了自己的评估和测算。一旦地价超出其接受的上限,开发商会选择退出竞拍过程。由于这是一个公开的市场竞争过程,政府不可能让开发商强制交易。因此,当政府制定规则要求开发商在拿到土地以后必须再拿出一笔开支用于在“土地指标交易市场”上购买相应面积的指标时,对于开发商来说,无非是增加了一笔获取该幅土地的成本。当开发商在进行地价评估时,必然将这一笔新增的成本纳入到该幅地块的成本核算之中。
举例来说,假设在没有“持证准用”制度之前,开发商对于政府推出的某一地块的竞价上限是 100万元,超出这个价格他将退出竞价过程。而当“持证准用”制度要求每亩土地必须配套相同面积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时,假定所需土地指标在市场上的价格是 30万元,那么,开发商在参与同一地块的竞价时,竞拍价的上限自然就降低为 70万,而不会是原来的100万。根本原因在于,在市场条件下,土地的价值主要是由其所在的区位决定的。当前,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这就意味着,成都市政府在制定“持证准用”以后,在上述地块的竞价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将由原来的100万元下降到70万元,“损失”的 30万元恰恰支付了开发商购买土地增减挂钩指标的支出。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财富。土地本身没有价值,因此也就不存什么土地价值的“释放”与“不释放”的问题[40]。成都市看似让开发商“多付出”的那一笔土地指标的费用,最终其实还是以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预期收入的减少为代价的,开发商依旧获得了房地产投资开发的社会平均利润。因此,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在为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提供资金支持[41]。
四、增减挂钩政策实施模式的效应简析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发展与演变,既是处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土地利用与管理制度等客观条件约束之下的结果,同时也是地方政府与参与企业博弈的结果。现对其效应予以简要分析。
首先,政府独立运作模式下的增减挂钩,微妙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增减挂钩政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关键的作用是在原先“计划内指标”之外形成了一种“计划外指标”的供应渠道,为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发展中的土地资源提供了一个口子,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在政府主导下,成都市快速启动了大量的增减挂钩项目,积极应对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与此同时,地方财政也逐渐捉襟见肘。
其次,项目外包与市场化运作模式吸引了社会资本,并规避了政府在实施增减挂钩过程中因为需要直接与民众打交道所可能造成的问题。同时,使得土地指标的生产由政府转向社会企业。由于地方政府不仅需要为增减挂钩的实施支付成本,而且还要保障社会资本的利润,以激励社会企业积极参与,土地指标交易价格不断提高,“指标市场化”交易模式突出。企业参与撬动了社会资本的力量,增加了项目业主实施增减挂钩的经济能力,从而延缓了地方政府支付增减挂钩成本的时间,进一步推进了成都市实施增减挂钩项目的规模和进度。不过,当项目逐渐完成后,地方政府面临越来越紧张的土地指标资金兑付压力。
最后,“持证准用”模式难以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地方政府试图采取这一政策工具,将土地增减挂钩的成本转嫁到房地产开发商方面,而开发商则直接利用现行土地市场机制,通过土地出让过程这个媒介,轻易地把这些成本又转嫁给地方政府。开发商支付成本只是表象,其背后还是地方政府在出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一次地方政府支付的资金是从其预期的、本应得到的“土地财政”收入中提前扣去了的部分。成都市的增减挂钩政策即使进行了“持证准用”的制度创新,但却最终不能免于“新瓶装旧酒”,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缓解。
土地增减挂钩政策亟待进一步规范和改进。其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至少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首先,作为增减挂钩项目主体的地方政府,究竟准备了多大的实力和决心向农村转移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因为,大规模推动增减挂钩项目上马,必然会在项目完成之后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的资金兑付压力。其次,作为增减挂钩项目的实施对象,也就是那些被立项了的农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并体现公平性?而对于那些没有机会被立项的大多数村庄及其农户,他们的参与和分享政府公共财政的权利和机会又如何保障和实现?最后,采取具有竞争性特征的“项目制”方式输送财政资源,如何有效防控私下“公关”和权力寻租?现行的增减挂钩项目管理制度尽管在不断健全和规范化,但仍然不仅没有解决私下“公关”的问题,反而加大项目实施的成本,使很多资金耗散在项目竞争和包装过程,并没有实质性地进入增减挂钩的实施环节,严重影响了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感谢吴建瓴教授的帮助。本文的调查是与夏柱智、王海娟共同完成的,文中部分观点受集体讨论的启发,特此感谢。)
[1] 林坚,李尧.北京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潜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07,21(1):58-65.
[2] 林坚,张沛,刘诗毅.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与思路[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4):4-10.
[3] 石诗源,张小林.江苏省农村居民点用地现状分析与整理潜力测算[J].中国土地科学,2009,23(9):52-58.[4] 陈荣清,张凤荣,孟媛,等.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现实潜力估算[J].农业工程学报,2009,25(4):217-222.[5] 贾玫.内涵挖潜,退宅还田——浅析吉林省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潜力[J].中国土地,1999(6):2-3.
[6] 张晓平,朱道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的农村居民点斑块整理模式评价[J].中国土地科学,2012,28(1):244-250.
[7] 刘咏莲,曲福田,姜海.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评价分级[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18-23.
[8] 刘云升.合村并居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价值选择[J].学术月刊,2011,43(4):77-82.
[9] 周小平.“挂钩”专项规划的几个问题[J].中国土地,2009(12):22-23.
[10] 程龙,董捷.基于生态位适宜度模型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划方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10):67-71.
[11] 林国斌,蔡为民,吴云清,等.天津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潜力测算[J].中国土地科学,2012,26(6):68-72.
[12] 黄金其.增减挂钩需要关注三个问题[J].中国土地,2013(2):40-41.
[13] 边振兴,于森,王秋兵,等.城乡建设用地挂钩中补充耕地质量等别确定方法[J].农业工程学报,2011,27(12):318-323.
[14] 程世勇.“地票”交易:模式演进和体制内要素组合的优化[J].学术月刊,2010,42(5):70-77.
[15] 黄忠.浅议“地票”风险[J].中国土地,2009(9):36-39.[16] 黄忠.地票交易呼唤顶层设计[J].中国土地,2011(12):13-15.
[17] 黄忠.让市场发挥更大能量——地票制度再创新的思考[J].中国土地,2013(2):19-21.
[18] 杨飞.反思与改良:地票制度疑与探——以重庆地票制度运行实践为例[J].中州学刊,2010(6):70-74.
[19] 杨继瑞,汪锐,马永坤.统筹城乡实践的重庆“地票”交易创新探索[J].中国农村经济,2011.(1):4-10.
[20] 王君,朱玉碧,郑财贵.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运作模式的探讨[J].农村经济,2007(8):29-31.
[21] 李海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实施的异化风险及预防[J].中州学刊,2013(1):39-42.
[22] 马宗国,田泽.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思考[J].理论探讨,2011(4):106-109.
[23] 王德钧,刘晓玲.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资金来源模式利弊探讨[J].资源与人居环境,2011(12):30-31.[24] 张海鹏.我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实践探索与理论阐释[J].经济学家,2011(11):22-27.
[25] 张宇,欧名豪,张全景.钩,该怎么挂?——对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政策的思考[J].中国土地,2006(3):23-24.
[26] 李旺君,王雷.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利弊分析[J].国土资源情报,2009(4):34-35.
[27] 任平,周介铭,杨存建.农村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及空间配置模式探讨——基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视角[J].河南农业科学,2010(08):55-58.
[28] 张怡然,邱道持,李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以渝东北11区县为例[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5):437-441.
[29] 涂重航.多省撤村圈地意在财政失去宅基地农民被上楼[N].新京报,2010-11-02(A16).
[30] 陈锡文.土地增减挂钩违规严重[N].新京报,2010-11-03(A18).
[31] 叶敬忠,孟英华.土地增减挂钩及其发展主义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2012(10):43-50.
[32] 冯帆,谭晓彤,杜骁,等.临沂市兰山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探讨[J].山东国土资源,2011,27(5):42-45.
[33]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土地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34] 贺雪峰.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35] 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36] 陈锡文.农业和农村发展:形式与问题[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11.
[37] 贺雪峰.建设用地制度改革的逻辑——以成都市城乡统筹实验中的土地制度改革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3,208(4):104-112.
[38] 田孟.一石三鸟?——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的批判[J].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3(7-8):110-120.
[39] 李元珍.央地关系视阈下的软政策执行——基于成都市L区土地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实践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13,10(3):14-21.
[40] 贺雪峰,夏柱智,王海娟,等.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笔谈[J].古今农业,2013(1):1-16.
[41] 贺雪峰.城乡统筹路径研究——以成都城乡统筹实践调查为基础[J].学习与实践,2013(2):74-86.
责任编辑:曾凡盛
“Linkage Between Urban-land Taking and Rural-land Giving”(LUTRG) policy and its evolution of the mode of 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in Chengdu
TIAN Meng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Rural Governanc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The LUTRG policy is a special form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a financial redistribution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Surveys and analysis about Chengdu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mode in Chengdu experienced three modes, from the government-led model to the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model and then to the land ticket "use license" model. Although these three models can attract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UTRG project actively and the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they will in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varying degrees,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benefit all or most of the villages, thus leading to new problems such as unfairness and power rent-seeking.
LUTRG; land consolidation, government-led; market operation; use license; Chengdu
F301.0
A
1009-2013(2014)06-0099-06
10.13331/j.cnki.jhau(ss).2014.06.018
2014-11-12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SH049);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创新创业基地项目(01-09-070108);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KS016)
田孟(1988-),男,苗族,湖南麻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土地制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