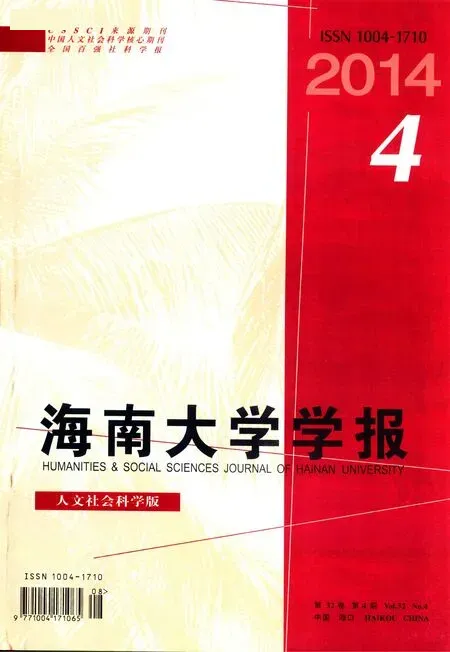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2014-03-31李树军
李树军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古学、今学是东汉学术研究中两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也是清代学者所构建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框架的基础,这一理论视域是有局限性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东汉今古学的理解有所偏颇,徐复观先生、钱穆先生都曾指出。对东汉今学、古学的进一步研究能够让我们了解东汉经学的发展情况,进一步认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一、东汉古学、今学的内涵
古学、今学作为一对词语在班固《汉书》、王充《论衡》中都没有出现,古学较早的出处是许沖的《上说文解字表》,蔡邕的《独断》和范晔的《后汉书》,也就是说古学、今学作为一对术语在东汉中期已经确立。
《上说文解字表》、《后汉书》等文献没有对古学、今学概念作直接说明,笔者只能通过这两个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探求它们的含义。首先,古学包含一组经典。徐复观先生说:“古学则是由刘歆们所发展出来的观念,指的是被博士们所排斥的一组经典。”[1]162《后汉书·李育传》“常避地敎授,门徒数百,颇渉猎古学。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左氏传》属于古学范围。《后汉书·卢植传》载卢植上书说:“臣少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颇知今之《礼记》特多回冗。……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庶裁定圣典,刊正碑文。……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共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在卢植看来,《周礼》、《毛诗》、《左氏》属于古学;《礼记》、《尚书》(今文)和《公羊春秋》属于今学。在《后汉书·郑兴传》中《左传》和《周官》也属于古学。可以看出,古学所包含的经典有《左传》、《毛诗》、《周礼》等,大致就是民间所传授的儒家经传;那么,今学所包含的经典当然就指五经博士学官即十四博士所传授的经传,即《公羊春秋》,《礼记》、《仪礼》、《齐诗》、《韩诗》、《鲁诗》,今文《尚书》、《易》等。经典上的这种差异,在许慎《五经异义》中也非常清楚,《毛诗》、《周官》、《左传》等经典前往往冠以“古”字,《韩诗》、《公羊传》、《齐诗》、《鲁诗》等往往冠以“今”字。
这种经典上的对立在《后汉书》“古今学”一语的语境中尤为明显,《郑玄传》:“中兴之后,范升、陈元、李育、贾逵之徒,争论古今学,后马融答北地太守刘环,及玄答何休,义据通深,由是古学遂明。”建武初年,范升与陈元等曾围绕《左传》设置博士与否进行争论;建初四年,在白虎观会议上李育与贾逵也针对《左传》与《公羊传》进行了论辩;马融与刘环也针对《春秋》古今学即《左传》与《公羊传》的意义进行过争论;何休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而郑玄针对这些写了《发墨守》、《针膏肓》和《起废疾》,他们围绕《春秋三传》的争论更是著名。《郑玄传》所说古今学的对立在经典上是围绕《春秋三传》展开的,但是其争论是以博士学官与民间经学的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古今学”在经典上的差异实来源于博士学官与民间经学的对立。
基于此,古学、今学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古学学派和今学学派,大致对应着民间经学学派和博士学官学派。需要指出的是,博士学官学派和民间学派都不是内部统一、学术观点一致的自觉的派别,它们内部都充满了矛盾。不同博士学官之间,同一经学博士不同家法之间充满了差异和论争,古学内部之间亦如此。这在西汉石渠阁会议,东汉白虎观会议中以及许慎《五经异义》中都有所反映。人们也发现博士学官中也有古学,许慎《说文解字叙》:“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孟氏《易》是立于学官的,应该属于博士学官派的,但是在这里却与孔氏《古文尚书》等并列,属于古文,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有这种疑问,完全是受清末学者的影响,把古学、今学与古文、今文完全对应,而且认为他们之间势同水火。其实,当时并不是这样。段玉裁说:“云皆古文者,谓其中所说字形字音字义皆合仓颉史籀,非谓皆用壁中古本明矣。”[2]就是说这些文献或学派的文字训诂都符合古文字的音、形、义。博士学官的文字训诂也有古文的、古学的,不过作为学派来讲这是极少数情况,博士学官整体看来还是属于今学的。
古学与今学的第三个内涵是治学方式和风格的不同。《后汉书·桓谭传》:“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李贤《注》说:“《说文》曰:诂,训古言也。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诂训”与“章句”对举,一是古学的代表,一是今学的代表。大致说来,古学以训诂为主,寻求经文大义,其训诂以即孔壁古文和古文大籀为基础;今学以章句学为主,注意经文字句及文意的寻求,其文字训诂以秦隶为基础。当然,两者也互有渗透。
章句作为一种解释体系源于西汉初年儒生研究经典的方法和文体。《史记·儒林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又说:“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汉书·儒林传》说:“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传,疑者则阙弗传。”《汉书·楚元王传》:“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西汉初年,儒家学者研究经书的主要方式和文体样式有传、内传、外传、故、故训、记、说等。故、故训等侧重于文字训诂,传侧重于文意,记、说侧重于礼制典故,当然它们之间会有所渗透,这些研究方式应该是继承先秦的。研究经典的最初的工作就是寻章断句,而传、故、记、说等已经超越了这种基本的工作,它们是章句之学的直接来源。章句是汉代经学研究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式和阐释体系,同以往的训诂、传、记等研究方式相较来说是新的,所以成为今学的重要内涵。从文体来看,章句之学的特征就是李贤所说的“委曲枝派”,即对文句、文意的解释详尽曲折,细碎繁缛。从这种特征来看,它不但可以对字句等语言信息,词汇上的礼制背景进行详细的解说,同时也容易应用适当的理论发挥自己的观点,所以章句之学同谶纬之学密切相关。章句一开始就有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意图,同时,其“具文饰说”在最大限度上消除了经文字句上的障碍,对经传的研究是非常积极的。
钱穆先生说:“汉儒经传有章句,其事亦晚起,盖在昭、宣以下。”又说:“五经博士置自武帝,而博士分家起于宣帝。则诸经之章句之完成,亦当在宣帝之后矣。”[3]224博士学官对章句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章句与博士家法相结合而形成章句之学。钱穆先生说:“若博士专守一经,则如《京氏易》、《公羊春秋》、《韩诗》,皆今学也”[3]245。钱穆先生还说“家法即章句”,他把章句和家法作为今学的主要特征是非常有见识的。《后汉书》中章句之学多与博士家法相连,而且经常同训诂大义的解释方法对举,《后汉书·桓谭传》:“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王充传》:“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这也充分显示了章句之学与博士学官属于今学的范畴,训诂大义和民间流传的经传属于古学的范畴。
古学则多继承西汉初年的传、训诂等经学研究方法。荀悦说:“中兴之后,大司农郑众、侍中贾逵各为《春秋左氏传》作注解。孝桓帝时,故南郡太守马融著《易解》,……及臣悦叔父故司徒爽著《易传》,……爽又著《诗传》,皆附正文,无他说。”[4]注解、解、传等文体明显是对前代传、故、训诂的直接继承,这些文体最为主要的方法就是训诂。训诂的方法局限于语言层面,侧重于对古代语义、礼制背景的解释,很难与谶纬融合。文字训诂往往被看作古学的内容,所以卢植上疏提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需要指出的是文字训诂也是章句今学的内容,但是古学与今学在这方面存在差异,大致说来,古学的文字训诂以古文字,特别是孔壁古文字和出土的鼎彝文字为基础,而今学的则以秦隶为基础。许慎《说文解字叙》说:“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
东汉末年,古学的观念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泛指儒家经典及其文化制度,在这种意义上与汉代典章制度相对。这在蔡邕的《独断》中有所体现,“古学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月令》曰:先荐寝庙。《诗》云:公侯之宫。《颂》曰:寝庙奕奕。言相连也,是皆其文也。”其所举古学经典有《月令》、《诗》、《颂》,《月令》是《礼记》的篇目,《礼记》是宣帝时博士戴圣编辑的,也就是说《月令》是今学的典籍,蔡邕称《诗》、《颂》而不言家数,蔡邕学鲁诗,鲁诗也是今学,而蔡邕统称之为古学,其古学显然是指先秦儒家的学问,从《独断》行文来看它指秦汉以前的礼制,与其相对的今学就是汉代的文化礼制。这种观念显然是汉代古、今学观念的自然发展。
二、今文、古文与今学、古学
今文、古文也是汉代经学中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们与今学、古学有所联系,清末之前的学者很少把这两对概念混在一起,而在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理论体系中,今文几乎可以指代今学,古文也几乎可以指代古学。但是,这两对概念在汉代差异很大,关系也较为复杂。
西汉初期,古文与今文除了指字体之外还有其他意义。《史记》中,“古文”共出现十次,《孝武本纪》中出现“古文”的一段文字与《封禅书》相同,前者为截取后者的文字,所以可以说“古文”共出现9次。关于《史记》中“古文”的含义,王国维在《史记所谓古文说》一文中说:“凡前秦六国遗书,非当时写本者,皆谓之古文。”王国维认为,古文作为字体指战国时期东方六国文字,同时它也指用古文书写的文献。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认为《春秋》、《国语》发明《五帝德》、《帝系姓》观点的,且都是孔子所传,因此,它们都属于同一性质,都是“古文”系统的。《封禅书》、《孝武本纪》的《诗》、《书》,《吴太伯世家》中的《春秋》、《左传》,《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春秋》、《国语》,《仲尼弟子列传》中的有关孔子弟子情况的书,都属于古文系统。可以看出,这一经典系统包括“六艺”经书及其相关文献,也包括记载孔子弟子的文献。除此之外,《史记》中的古文也指学统或学派。《五帝本纪》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此处“古文”显然不能纯以文字和文献来理解。对于黄帝、尧、舜历史的记载以古文为准,这涉及对这些历史人物的理解问题,主要是观点、历史记载的不同,是学统的不同。
可以看出,古文作为学统是以周朝礼乐文化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孔子及其弟子所确立的儒家是以《六艺》为学习和研究对象的,所以儒家学派是这一学统的代表。钱穆先生曾指出:“盖《史记》之所谓‘古文’,正指《六艺》,凡所以示异于后起之家言也。”[3]203钱先生所言极是。从知识体系上来看,它是以《诗》、《书》、《春秋》“六艺”为中心的,是体现周王朝礼乐文化制度的集成,自然也是先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因此作为史料,它也是最可靠的。
今文、古文的内涵在西汉中后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字体意义上,古文仍然延续之前古文字的意义,但往往特指孔壁中文献的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及亡新居摄,……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武帝时期,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经《逸礼》、《书》、《春秋》、《论语》、《孝经》等文献,其文字是古代文字,所以古文在西汉后期特指这些文献的字体。西汉初年,小篆与隶书并行,但当时很多书籍仍然是古文的。在当时的经学传授中,无论是学官的经书还是流传民间的经书,其文本都存在着由古文或篆书改为今文隶书的境况,或者由口授形式转为隶书写本,此改写过程在文帝、景帝时已基本结束。王国维说:“夫今文学家诸经,当秦汉之际,其著于竹帛者,固无非古文。然至文景之世,已全易为今文。于是鲁国与河间所得者,遂专有古文之名矣。”[5]由于汉武帝时经传文献已改写为今文隶书,所以《史记》、《汉书》等特别注明这些书籍为“古文”。
在文献意义上,古文也泛指这些后来发现的文献。除了孔壁古文文献,也包括其他古文文献,如河间献王得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等。西汉末年,古文也特指《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中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一卷等,都是古文,其中独《古文尚书》冠以“古文”二字,也就是说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古文”也特指孔壁中的《古文尚书》,王国维、钱穆先生对此都有说明。当然,《古文尚书》与流传的立为学官的《尚书》相比,不仅是字体的差异,也存在着观点的差异,所以古文、今文也对应着《尚书》的这两种学统。今文一词在西汉中后期仍然有隶书字体的意思,在学派上和文献上特指今文《尚书》。古文、今文这两个概念在东汉时期仍然延续了这些内涵。两汉之交,古文、今文的观念意识同经学研究中博士学官与民间经学研究的对立情形互相影响逐渐衍生出古今学的观念,徐复观先生说:“古学虽由古文孳演而出,但古学已突出了古文的范围。”[1]157今、古文与今、古学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
三、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
徐复观先生说:“因五经博士们对经学的垄断而又低能,激出了刘歆们的《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作了总的批评与暴露,并由此书而发展出东汉经学中与博士相抗的古学,这在经学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是一件大事。”[1]157徐复观先生对古学形成的描述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在这里他涉及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五经博士与刘歆们的矛盾,即博士学官和民间经学学派的矛盾;另一个是刘歆们及其《让太常博士书》的作用,即一些学者对古学形成的关键作用。另外,我们认为,西汉末年古文字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也是古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汉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明显变化,因此从学术流派和观点的发表来看,西汉前期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而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则是儒学内部不同学派和不同观点的争鸣时期。建元五年,五经博士得到确立,汉代官方思想学术由“百家言”时代进入到了经学时代。《史记·儒林列传》说:“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唐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司马迁这一段记述与后面公孙弘的奏请之言共同构成了五经博士的制度,对于这一段记载的制度内涵很少有人详细论述。从这一段的记载来看,武帝时期所确立的博士学官从制度上来讲可以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五经博士的确立确定了《六艺》唯一的学官地位,作为研习《六艺》的儒家学派和儒生成为学官机构人员即经师和弟子的人才基础,他们也是王朝政治机构人员的人才基础。第二,为博士学官设置弟子员,博士弟子的选择和任用制度化。第三,确立了五经师法。五经博士的确立是以师法的确定为表现的,即于《春秋》确立了《公羊春秋》胡毋敬、董仲舒两师法;于《诗经》确立了齐、鲁、韩三家师法;于《书》确立了伏生师法;于《礼》确立了高唐生一派;于《易》确立了田生一派。后来各家博士皆出自这些师法,这是制度性的。这是为什么后来《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周礼》、《古文尚书》、《毛诗》不能成为或难以成为博士学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种制度对西汉学术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学术流派上看,西汉前期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百家争鸣的状况被儒家独尊所代替,其他各家转入民间,其理论话语只能融入王朝的主流学术话语中,不能具有独立性。百家争鸣演变为儒家内部不同学派和观点的争鸣论辩。同时,对儒家自身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在社会地位上产生了分化。取得博士学官的各家师法地位尊贵,其弟子是王朝学校的生员,是王朝官员的预备人才,身份非常高。博士学官为王朝培养和选拔人才,参与王朝的礼仪制作,也是朝廷的政治、文化顾问官员,其学术研究自然受到王朝的支持和推崇。非博士学官的儒学研究则往往受到学官的压抑和排斥。博士学官儒学与民间儒学的矛盾成为西汉中后期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古学、今学形成的主要原因。其次,从研究对象上看,专经博士形成。博士为秦代职官,汉代因袭,武帝之前博士职官不限于儒经,诸子和传记皆有博士,而且儒家博士所治也不限于一部经书。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只限于儒家学派不说,而且博士学官学只限于教授一部经书。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说博士学官与民间经学的矛盾是形成古今学的关键和基础,并不意味着博士学官、民间经学是两个自觉的内部统一的学术派别。徐复观先生说:“其所以构成争论,乃来自博士们对自己所受、所传以外的,一概加以排斥,并不仅是以今文排斥古文,对他们传承以外的今文也同样排斥。”[1]157杨天宇先生也说:“认为汉代今古学两派出处立异,‘互为水火’,不过是清代学者的看法。”“今文学博士为保持其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以及本学派的垄断利禄之途,则竭力反对古文经学博士。然而古文经只要不争立博士,今古文两派就可相安无事。”[6]汉宣帝之后,汉王朝的态度总得来说对民间经学也是很宽容的,有些皇帝对民间经学持同情支持态度,但是往往因为博士学官的极力反对,而不能将民间的家法立为博士。
今古学的形成也与很多学者的努力密切相关,就是徐复观先生所说的“刘歆们”。《汉书·刘歆传》:“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在博士的强烈反对下,刘歆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就像徐复观先生所说,刘歆及其《让太常博士书》直接导致了古学的产生。《后汉书·贾逵传》载,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贾逵继承父学,许慎又从贾逵学习。可见,刘歆经学本身影响深远,贾逵父子、许慎都对古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杜林、郑兴父子、班固、卫宏、谢曼卿等众多学者也对古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古学的形成也与古文字在经学研究中的兴起有关。西汉初期沿用秦代书同文的政策,当时的标准字体为小篆和秦隶,秦隶的应用范围要更广一些,古文属于被消除的文字。古文在武帝时期基本退出了日常书面语的书写,退缩到小学的领域。随着王朝对文字的整理,两汉之际古文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汉宣帝时,《仓颉篇》中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征齐人能认读者教进行授,张敞从“齐人”学习,后来张传给外孙之子杜林。西汉末年孝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在未映廷说解文字,扬雄根据这次文字整理的结果编纂成《训纂篇》,东汉时期班固又续《训纂篇》。这些字书的编辑不仅整理了古文字,也对经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对非博士学官经学的研究影响较为深远,他们特别重视古文在经学研究中的作用。博士学官特别重视师说,民间学者则重视古文字意义的探寻,这样,古文与民间经学研究联系在一起,共同成为古学的内容。东汉中期,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就是古学重视古文字的集中体现。到了东汉末年,古文在经学研究中已具有重要地位,汉灵帝熹平四年所刻石经,古文就是其中一种字体。可以看出,古文的兴起对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东汉的今学、古学在经典、学派和治学风格上分别有着不同的所指,是东汉经学研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它们与西汉时期产生的今文、古文两个概念有联系,但是并不相同。今古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源于博士学官与民间经学研究的矛盾。
[1]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65.
[3]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荀悦.两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438.
[5]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8.
[6]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