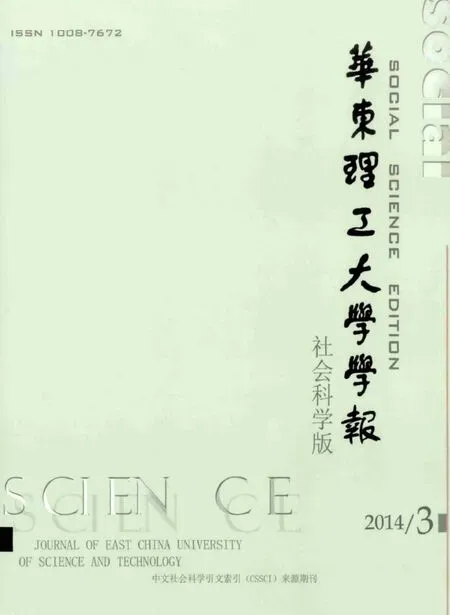新国家与旧家庭: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2014-03-31张婷婷
张婷婷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 201203)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变迁过程是与工业化、城市化同一向度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庭将有助于个人摆脱扩大家庭、亲属、国家的控制,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大平等自由和权利,并认为这一趋势是任何国家必走之路,“世界各地,所有的家庭制度都在或快或慢地走向某种形式的以平等关系为核心的夫妇式家庭模式”。①[美]古德:《家庭》,魏章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页。中国1949年建国后以“现代化”为目标追求的新国家中的家庭是否按照该理论预设的路径发展演化,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始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不但深刻影响了乡村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同时对于传统乡村家庭制度也造成了颠覆性冲击。集体化时期国家动员机制和体现“家国一体”的社队体制,不但重构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组织体系和资源分配机制,同时对于传统的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乃至于家庭伦理基础等无不构成了根本性的挑战。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集体化时期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下的乡村家庭现代化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解构的意志和能力?现代化理论所乐观认为的家庭束缚减弱和个体自主性增加究竟在多大程度得以实现?传统旧家庭在这场变革中是否仅是被动的改造对象?
一、新国家的抱负:对旧式家庭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之初,新生政权以带领人民奔向共产主义为其伟大抱负,抛弃以私有制为特征的家庭式小农经济形态、否定建立在孔孟纲常基础上的旧式家庭伦理遂成为新政权的首要政治任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就要解放并改造封建旧式家庭。因此,新生的国家政权全面开展了以解放、改造旧家庭,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庭为目的的社会改造运动。
初期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即通常所说的大公社时期①一般以1961年《农业六十条》作为分界线,将之前称为大公社,此后称为小公社,一直持续到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瓦解。1958年到1961年末的一段时间内,全面的集体化,使家庭大部分功能丧失。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规定人民公社规模不宜过大。1962年撤大社、建小公社,确定产权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即“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允许家庭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归家庭所有,恢复家庭一部分生产职能,并全面恢复了家庭的抚育、赡养、消费等职能。参见曹锦清、张乐天:《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373页。,是在“实现共产主义”号召下向村民传统的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宣战的过程。农业集体化所奉行的意识形态坚信,家庭乃是私有制最后、也是最顽强的一个堡垒。因此,要搞农业生产集体化、要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传统的家庭职能逐渐移入正式集体组织。而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正是落实这一抱负的实验性行动。它使得作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及经济核算单位的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家庭层面所拥有的土地、生产工具、耕畜等生产资料悉数交给集体,家庭本身不再承担具体的生产组织功能;同时,家庭的独立经济核算功能也渐遭消解。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农业集体化的过程是向传统家庭不断挑战的过程。在这一场运动中,通过“政权建设”这一合法性使命,国家卓有成效地将家庭建设纳入到国家建设的实践逻辑之中。在这种语境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事实上获得了嵌入于家庭生活之中的合法性和必然性。个人是“国家”的人,“家事”也是“国事”,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家庭的生产、消费、赡养、抚育等诸多职能都被纳入国家统管的范畴。同时,“国事”也即是“家事”,在“先大家、后小家”,“顾大家、舍小家”的政治动员下,国家用社会主义集体忠诚取代了家庭忠诚,个体和家庭的独立性均被约定一个给定的框架内。②蒋永萍将这种模式称之为计划经济时期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参见左际平,蒋永萍:《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第21-54页。通过集体化运动,国家把家庭乃至于个体置于一个由国家机构组成的庞大组织体系之中,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没有限制的组织权力向家庭乃至于个人生活领域无限扩张。③李默:《百年家庭变迁》,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作为一种旧有的社会微观组织以及整个旧制度的组成部分,传统家庭在新的国家政治动员机制下受到批判。与之相伴随的是,以孔孟纲常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伦理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秩序也痛遭挞伐。国家鼓励那些受压迫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去批判、怀疑现存的家庭权威结构,“几千年来,在我们的家庭关系中,无非是儿子不能违抗父亲的旨意,妻子不能违抗丈夫的旨意。我们怎样与这种观念展开斗争呢?……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状况……。在家庭中规定谁可以发号施令,谁必须俯首听命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谁的话符合毛泽东思想就服从谁。”④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宋践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6-417页。无疑,在集体化时期特有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政治动员下,乡村家庭的关系秩序以及权威结构受到了挑战。
对于新国家建立之初实行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以及随之展开的集体化运动对家庭的影响,多数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同这是国家对旧式家庭全面征服的主要表征。阎云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多种方式直接参与了对家庭变革的推动,尤其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国家干预得更多。①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龚小夏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萧凤霞(Siu,Helen F.)认为,“社会主义集体化运动把农村社区变成了国家的细胞组成。人民公社化运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了组织严密政府官僚网络中……从而在中国建立起了国家有力控制农民日常生活的权力。”②Siu,Helen F.,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已有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乡村家庭在集体化时期基本丧失主体性地位。家庭的一切资源包括对劳动力的支配权,都无条件地交付给国家。家庭完全被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没有“主体性”可言,也无私人领域可言。③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C.K.Yang早期的一项研究也认为,集体化的浪潮鼓励和推动个人放弃对家庭的忠诚,而为超越家庭的集体做出牺牲。④Yang,C.K.,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Cambridge:The M.I.T Press,1959,P.173.
毫无疑问,借助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力量,国家不遗余力地对旧家庭进行了改造,着力将家庭建设纳入到国家建设框架之中。表面上来看,乡村家庭几乎基本丧失主体性地位,完全被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但实际上,乡村革命的推动者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巨大惯性对这一努力的影响。权建设的实践策略。
事实上,自1950年代以来,国家主观上并没有、客观上也不具备彻底摧毁传统家庭伦理基础的决心和能力。尽管经济的集体化以及消灭私有制的革命行动大规模地破坏了之前形成家庭忠诚的经济动力,同时,对祖先崇拜和家族文化的批判直接打击了传统大家庭的组织体系和伦理信仰,但并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共产主义运动解构了传统中国家庭。事实恰好相反,很多关键的政策实际上进一步稳定、甚至强化了家庭的作用。 中国乡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造成传统的断裂,附着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动员并未真正改变封建社会基础,一些基层政府甚至还倾向于利用那些和政府的主要目标没有明显冲突的传统因素。⑥kayAnn Johnston,Women, theFamily and the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3,P.220.如“两勤方针”的提出。
“两勤”方针是指“勤俭持家,勤俭建国”的妇女工作方针,其目的在于,将家庭建设与国家建设统合起来考虑。新国家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利用了传统的家庭角色期待,对妇女进行了双重身份建构。周恩来总理的一番话深刻体现了国家的这种用意所在,“家务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参加家务劳动也是光荣的。家庭妇女能够勤俭持家,把家务搞好,使丈夫、子女能够积极从事各种劳动,同样是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⑦《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二、制度导入与传统家庭制度的延续
数千年累积下来的传统家庭伦理以及家庭秩序显然非一次社会运动所能颠覆。党的管理层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导入乡村的制度性安排如果不以某种方式与传统相衔接,就不可能发挥作用。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试图消解家庭的大公社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灾难,1962年开始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主义生产体制恢复并重新赋予了乡村家庭诸多传统职能。此举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国家在自己的体制框架内部分地承认了传统家庭制度的合法性。⑤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因此,出现了颇为有趣的一个现象是,集体化时期,国家一方面致力于对旧式家庭进行改造,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不断对诸多传统家庭制度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利用着这些传统家庭伦理和秩序结构作为国家政可见新国家利用延续了数千年传统生活对女性在家庭分工格局中角色定位,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不平等,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但又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角色分工密切相关的性别角色建构模式:两性同样是国家人前提下的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①左际平、蒋永萍:《社会转型中城镇妇女的工作和家庭》,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实际上,妇女在“国家人”、“家庭人”双重角色期待下,承受来自国家和传统家庭的双重压力。因此,正如张乐天所言,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妇女整体地位确实有所提高,但对集体化时期女性在乡村家庭中的地位作过高估计的倾向也需要警惕。②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家庭结构延续性非常强,传统社会保留下来的亲属关系结构照样搬到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单位。宗族在表面上有些改变,但是深层的结构特点仍然被保留下来。大队的户口登记簿几乎与族谱完全一致,土地改革原则上虽是土地按人口分配,可实际上,土地使用权仍归家庭中男性家长掌握,家庭成员的收入如工分仍归家庭的家长所掌握,个体并无支配权。因此,任何外部性导入都不能改变这一架构,充其量不过在社会生活的表面刮擦一下而已。③S.H.Potter&J.M.Potter.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267-269.传统家族结构和文化在经历封建帝国晚清、民国时期、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和去集体化时期,仍体现出延续性,即使在对传统家族制度破坏最为激烈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从夫居和以血缘为基础的居住模式导致了生产队和生产大队仍然是以父系关系为基础的传统模式的延续。尽管在公开的场合下,对人民公社和国家的忠诚以及阶级成分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原先对亲属关系和对家庭的忠诚,但在日常实践层面上,村民对血缘关系的认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④韩敏:《回应革命与改良: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8-265页。
一个并不为多数研究者所注意到的事实是,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抑或是在建国之后,乡村家族制度特征之一的父权制不但没有受到挑战和削弱,反而获得潜在加强,并更加“民主化”,即一般男性农民都能享有。这种父权制不仅见诸于家庭内支配领域,同时也在其他生活层面产生极大影响,出现了所谓“社会父权制”(public patriarchy)的现象。⑤Stacey Judith.Patriarchy and socialistrevolution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128-216.
一个颇具悖论性的现象是,为了发动更广大的农民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力倡性别平等的《婚姻法》,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屈服于男权利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事实上妥协了性别平等的主张。革命乃至于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一方面着力动员女性广泛参与,但在另一方面,却在体制框架内默认了压迫她们的家庭内性别权力结构的存在。⑥Phyllis Andors.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1949-1980,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3.1949年以后,国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传统孝道大为批判,但是却从来没有批判过农村的养老传统。⑦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集体化体制下家庭生产资料甚至部分生活资料被“一大二公”之后,老辈们掌握的交换性资源不复存在。因此乡村家庭的关系秩序以及权威结构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基于乡情、面子与社会舆论形成的村落文化仍然对子女与老辈之间关系有制约作用,代际之间“服从”机制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对老人赡养造成危机。参见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建国以后虽然妇女解放的话语和集体经济制度极大地改变了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但传统社会代际平衡的关系仍然维持,父慈子孝、长幼伦理仍然得到国家有力的倡导。乡村家庭普遍的代际紧张基本上是在市场化改革导入乡村社会之后才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
由此可以断定,那种认为农业集体化完成后家庭完全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的观点无疑过于简单。尽管新国家志在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旧家庭进行改造,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国家不但对诸多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秩序结构进行妥协,甚至还间接地加以利用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在乡村社会的实践策略。
三、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
集体化时期国家之所以未能彻底瓦解乡村家庭,反而有着潜在地利用家庭传统的企图,其中原因,固然是传统惯性使得基于村落文化建立起的家庭伦理和秩序仍然顽强,但一个可能被忽略的事实是,这可能出于新国家的另一层考虑。
美国学者萧凤霞(Helen F.Siu)后来改变了原先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变化的观点。在1993年的一项研究中,她做出了更为审慎的结论。她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农业合作化完成后,家庭完全被纳入到国家控制之下。事实上的情况可能恰好相反。由于国家的强大以及资源的稀缺,个人即便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按照正式的体制规则行事,可能并不足以构成生存发展的全部要件,因此个人对家庭的依赖以及家庭对非正式亲属网络的依赖,在集体化时期都有显著增加。①Siu,Helen F.,Reconstituting Dowry and Brideprice in South China,in Davis,Deborah&Harrell,Steven.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65-188.事实上,本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集体化非但未能削弱传统乡村家庭伦理,相反,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强化父系家庭作用的潜在趋势。
这种强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威权国家严格的制度控制——如人口流动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得乡村几乎不存在依据正常的社会流动或市场手段来谋取个人和家庭的发展机会,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他出生与生活的村庄和家庭网络中。此外,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十分落后,高度计划经济下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的不均衡发展策略,造成乡村物质资源匮乏问题更加严重,这使得来自家庭网络的物质支持对个体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50新《婚姻法》的颁布。这被普遍认为是农村青年特别是女性获得长期所渴望的婚姻自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物质与经济相对短缺的年代,以及其他发展机会受到限制的前提下,父母们仍将姻亲关系视两个家庭之间财产、人力以及生殖能力的一项交易,德国社会学家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trr)曾指出,中国的婚姻形式与行为尤其在农村主要是由家庭经济的逻辑所决定的。中国家庭婚姻策略、婚姻形式以及婚姻行为应该主要在家庭的经济背景中解释,而不能主要被看成个体的行动或国家政策的目标——一如《婚姻法》所宣称的那样。尽管政治上力图倡导家庭以及婚姻制度的改革,但家庭经济以及与之并行的父母支配能力不仅没有遭到削弱,实际上反而可能得到加强。特别是当资源短缺日益恶化的境况,婚姻作为双方家庭扩充非物质资源(亲属与团结关系)和符号资本(社会地位和名望)以弥补家庭资源匮乏、积聚家庭可用资源时,家庭经济的逻辑便会再次占支配地位。②罗梅君:《19世纪末以及今日中国乡村的婚姻与家庭经济》,载张国刚:《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53-357页。因而,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的婚姻自主权仍没有摆脱传统父家长权威束缚以及家庭经济逻辑的限制,家庭利益超越男女双方爱情成为婚姻方面首要考虑的因素。
历史地看,从1949年新国家成立至1978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内,国家政权关于家庭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中。一方面着力摧毁传统家长的权力和权威,鼓励人们摆脱家庭束缚,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任和服从,取代对家庭的忠诚;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政权在公众健康和解决饥荒方面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口死亡率,这导致人们可能比1949以前拥有更大和更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③Davis ,Deborah&Harrell,Stevan.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1-2.同时国家在人口流动方面的严格控制,不仅符合国家控制个人自主的需要,而且由于它将大多数成年男子和他们的子女牢固地绑在他们出生的村庄和城镇,因此新政权产生的人口和物质条件有助于产生近亲之间经济和社会联系紧密的多代同堂大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庭内代际之间的互助以及个人对家庭的依赖。
由此可见,虽然国家企图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实现“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化建设,试图通过将个体忠诚越过家庭而直指国家以及将家庭经济纳入到集体计划中,但在巨大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建国之后数十年的乡村贫困化现实压力之下,这种尝试也仅限于借助家庭的作用来安置个体和保证国家建设意图的实现,如鼓励妇女“勤俭持家”来保证“勤俭建国”目标的实现,借助子女姻亲关系作为扩充家庭资源的手段,维系“养儿防老”的传统以解决农村老年赡养与生活支持问题,这些对妇女、子女、长辈的制度性安排,都导致家庭制度中的传统伦理因素难以从根本上被消解。
从以上分析可知,家庭传统未能被彻底摧毁,有些反而被转化为国家的政权建设和治理的策略,这可能不是因为国家力量不够强大,反而恰恰是因为国家政权自身的过于强大而不自觉地强化了家庭的作用。这导致家庭角色的双重性建构,即一方面是“被改造”的对象,另一方面“再利用”,这昭示了强势国家下的家庭改造悖论。
四、国家政权建设与中国乡村家庭的改造
中国集体化时期新国家虽然以“现代化”建设为目标,但乡村家庭变迁远非如西方国家那样与工业化、城市化同一向度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家庭成员自主性的增长。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古德模型”(Model of Goode)是基于西方,主要是欧洲和北美的经验基础之上演绎而成的一套解释体系。但这一理论越来越受到中国本土经验的挑战。
尽管中国社会主义新国家政权力量强大,但嵌入于乡土秩序体系中的传统家庭事实上处于现代国家动员与传统伦理文化的双重规限之中,这是中国语境下乡村家庭的独有特征。在后革命时代,政府在公众健康、教育和公共经济等方面一系列的政策虽然将中国乡村家庭以西方所未有的速度推向一个“现代家庭”模式,但传统家庭制度以其特有的方式回应并不断调适这一变革,因其所具有的整合功能及其对于秩序建构的作用,非但没有被乡村改造者彻底摧毁,反而与国家政策的推进相衔接而被转化为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策略。因此并未出现在西方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呈现的家庭制度变迁图景:传统家庭制度遭彻底摧毁,个体性权利在真正意义上被得以强调。集体化时期,党在乡村家庭改造中的政治动员有时表现为一组有着内在矛盾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强调个性解放,强调年轻一代敢于向传统家庭表达个性,但在另外一方面却不断强调原子化的个体应服从包括家庭、社队在内的集体式组织,强调某种被修正了的整体性利益和集体主义价值。①李楯:《家庭政策与社会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社会学研究》,1991年第5期。
作为分析家庭制度演化的主要解释范式,家庭现代化理论主要的局限在于它存在某种线性思维的缺陷,即把家庭演化的可能走向比附于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而忽视了家庭自身对社会所具有的调适性和传统再生性,实际上,家庭具有回应社会变迁的能动性,这使得家庭制度演化路径有着更复杂、多样和曲折的面相。
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建国后的新国家是这个变革社会的创造者而非如西方那样是被创造物。因此相对于西方社会自发的、彰显个体性价值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诉求对传统家庭制度内在持续的瓦解能力来说,集体化时期中国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导下的乡村家庭现代化实践,虽不乏极具革命性的手法,但对传统的家庭制度的解构意志和解构能力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话题,远非单向度发展模式所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