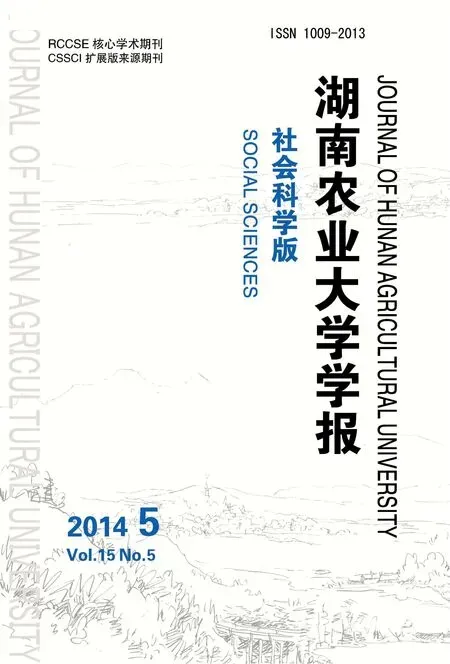农村灾难救援中社工跨部门合作困境及其治理——以“5.12”汶川地震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为例
2014-03-31张粉霞张昱
张粉霞,张昱
(华东理工大学公共与社会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随着全球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府部门也愈来愈寻求一种多元主体的跨部门合作关系①以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议题。例如在重大灾难救援中,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够拥有救灾所需的所有资源,跨部门合作成为灾难救援的主要处理机制。正如有学者所言,“政府有潜力提供更为可靠的资源,非营利组织比政府更能提供个性化服务”[1],跨部门合作为公共危机介入与灾难救援提供了一条新的治理路径。
在国外农村灾后救援与重建中,跨部门合作并不常见,相关事务多由社区自行完成。地震前已有社区组织运作的农村社区,在救援应变阶段可顺利发挥组织运作、统筹协调功能,进行搜救、援助等相关事务处置,以保障农村社区居民在地震初期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而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灾难救援的响应系统、预警机制、救灾资源和技术能力远不如城市,这就必然导致农村灾害救助自救能力弱的特点[2]。此外,由于农村社区组织化程度比较低,具有一定自救能力和复原能力的社区非政府组织相对匮乏,因而一旦遭受自然灾难,大部分农村地区将更加依赖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救援与支持。正如有学者指出,面对农村灾难救援与重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极其复杂、所涉及的项目内容和资源种类非常广泛的系统性工程,没有哪一个组织能够独立完成或承担责任,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往往需要整合各级政府、各种组织乃至于整个社会的力量[3]。由此,对于本土情境下的农村灾难救援而言,大力推进跨部门合作之重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正是这种中西语境的差异,为人们研究本土农村灾难救援中的跨部门合作带来了挑战和空间。
遗憾的是,目前对于我国农村灾难救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紧急救助、风险管理、社区重建和生计发展等议题,对跨部门合作经验的提炼与反思不足。而且,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脉络和社会条件,农村灾难救援中的跨部门合作实践起步较晚,仅有的少量案例呈现出临时性、被动性的形态特征,并未发挥应有的联动效应和功能。基于此,笔者拟通过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介入“5.12”汶川震灾救援服务的实践和访谈材料,探寻我国农村灾难救援中跨部门合作的困境、内在根源及其治理路径。
一、农村灾难救援中社会工作跨部门合作的困境
在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上海市民政局与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等多家组织机构联手合作,组建“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服务团内设四支服务队(华东理工大学服务队、复旦大学服务队、阳光·上海师大服务队和浦东新区社工服务队)进驻都江堰市四个过渡安置社区②开展服务。
从组织架构来看,服务团是由政府、高校和社会组织等多主体构成的跨部门联合体。其中,上海市民政局作为牵头者与主导者,承担着组织决策的角色功能;以高校力量和社会组织组成的四支服务队则是具体执行者,发挥着介入灾区开展社工服务的功能;上海市社工协会,既负责服务团团部的行政后勤工作,也发挥着民政局与服务队之间的信息传递桥梁与协调沟通的作用。尽管服务团围绕“以社会工作的专业视角协助都江堰市开展灾后重建服务”的总体目标,进行了精细化的任务分工,但在充满困难性和复杂性的实践运作中,服务团内部治理很快出现了分歧和异化,致使跨部门合作不仅未能显现出预期优势,反而陷入重重困境。
1.身份困境
目前我国尚未有相关政策法规对社会工作参与灾害救援的介入环节、介入渠道和服务功能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在10 个极重灾区和29 个重灾区中,除都江堰市、汶川县、理县等少数几个县因为对口援建省份要开展社会工作外,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救灾体系中并没有主动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灾后重建中,也没有主动与社会工作站形成合作或提供资金支持[4]。
服务团在成立之初,尽管通过上海市民政局的途径上报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及国家民政部的承认,并获得都江堰市民政局的支持[5],但是由于都江堰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对于安置社区的居民和管委会来说,社会工作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这导致服务团在介入灾难救援之初即面临身份困境。在进入安置社区之后,四支服务队虽然努力想要“嵌入”进以管委会为中心的灾后救援组织架构中,但是管委会并没有将这支“外来的队伍”视为“自己人”,而且党支部、居委会等负责人并不知道“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因此事实上,四支服务队并没有被正式编列进灾后救助、灾后生活重建和社区重建的正式的灾后救助框架内,社工服务队对安置社区中社会政策层面的参与更是极为有限。“当我们上海社工进入到都江堰的时候,已经是震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当地的救灾组织体系基本已经组建完成并开始顺畅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管委会也不可能再把我们加入到他们的体系之中;另外一方面,说实话,当地管委会确实不知道‘社工’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社工能做什么,更不知道如何把我们纳入到制度化的救灾体系之中,所以刚开始,管委会的态度就是你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访谈对象W)
尽管从表面上看,社工服务队努力通过“嵌入式”[6]的发展路径来取信当地政府和受灾民众,以获得最大化的身份合法性。但是,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尚且不足的前提下[7],以及“当地政府的不接纳,民政不放心,国家没政策”[8]的制度环境中,服务队只能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尴尬状态游离于正式救灾体制的边缘。这种身份困境导致:一方面,由于无法整合到政府整体的救助工作架构中,服务团的各类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无法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另一方面,这种低效的无序参与,不仅打击了服务团的参与热情,而且容易在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服务团)之间形成互相怀疑、指责的不良互动格局[9]。
2.责信困境
责信是指在任何情境下,执行权力的个人或组织应该受到外部机制,以及某种程度的内部规范的合理规制[10]。在我国对服务团这类临时性救援组织的监管方面,长期以来缺少财务、服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外部规制,这是一个存而不论、无可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条件下,如何发挥服务团的内部约束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各主体之间并未形成平等的合作关系与有效的相互约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非政府组织难以制衡政府部门。从经费提供、政策决策和地位平等的角度来看,服务团在成立初期,其内部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上海市民政局相较于其他几家组织机构而言,其在服务团内部占有相对优势的主导地位。非政府组织一旦接受政府机构的资助,则必须要承担机构自治权丧失的风险。换言之,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因为接受政府经费赞助,而导致机构自主性因政治干涉而导致的政治妥协[11]。“你会发现政府还是习惯于那种大的什么抗震救灾总指挥部,他们可能还是觉得我政府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那你们NGO 组织就是我们下面的组织,做什么要跟我们汇报的理念。其实整体来讲,这个架构是有问题的。关键问题还是不要把非政府组织什么嵌入、吸入到政府里面,也就是说政府不要把非政府组织吃掉,而且要平起平座,要合作,要有这样一种态度和理念。”(访谈对象W)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难以监管非政府组织。权力关系的平衡是一个动态过程,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专业力量和信息优势等因素来牵制政府的权力。虽然政府作为组织方和资助方,拥有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对非政府组织的责信要求和绩效评估。然而,由于政府往往难以深入到实践中去掌握信息和动态监管,因而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责信衡量与绩效评估之困难,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虽然是民政局派到都江堰的上海对口援建都江堰灾后重建指挥部的,不过四支服务队到底在安置社区做些什么,说句实话,我真的不知道。一来他们(社工服务队)很少跟我们指挥部汇报,二来我跟他们沟通确实也不多。”(访谈对象C)
再加上四支服务队在都江堰开展的灾后重建服务是“提供社会服务”而非“生产公共产品”,其服务通常是无形且很难测量的。在此种情况下,上海市民政局很难从四支服务队的实务运作特质来评估他们的服务成效。正如有学者指出:“事实上,政府机构对非营利组织的责信要求与控制,要远比想像中来的微弱。”[12]本文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理论判断。
3.信任困境
信任是组织间能够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特别是在灾难情景下,若组织之间先前已经具有社会网络的基础,信任则较容易建立,这对于灾难时的集体行动有非常大的帮助[13]。长期以来,上海市民政局就一直承担着上海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的推动者角色,与其他几家组织机构负责人有较为密切的人际互动和不错的信任基础,这为“5.12”震灾后“服务团”快速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在合作关系建立后的后续运作中,上海市民政局与四支服务队之间以及四支服务队之间的信任关系却出现了波动和流失。
从纵向层面来看,上海社工协会的功能不彰导致了组织间信任关系的流失。合作关系的契约化,是维系组织间信任、防范组织投机行为的关键所在。尽管服务队在进驻都江堰安置社区之前,都与服务团团部签署了“上海社工服务团合作协议书”,看似完成了这一“契约化”过程。但实际上,社工协会的强行政背景(在人员构成方面,仅仅配备1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他13 名人员都来自上海市民政局相关处室和事业单位),导致其“官本位”情结比较浓重,往往采取行政指令而不是履行契约的方式来指挥四支服务队。服务队的工作人员经常要承担额外的、临时性的、行政性的事务,精力被无谓地消耗,士气被严重削弱,对社工协会也缺乏信任感。再说,这种临时性抽调的团部工作组,存在对工作任务不熟悉、人员之间的重新协调配合等问题,对于服务队的合理诉求不能及时向上反馈,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组织间的信任根基。“整体感觉,我们服务团是没有‘腰’的,就是没有那个可以起到传递、沟通、整合的平台。这些功能的发挥本应该是上海市社工协会来承担的。但是就感觉社工协会当时就没有存在感。5.12 地震发生之后,社工协会其实应该尝试着先和政府沟通,发挥桥梁作用,看看我们能不能联合来做一些事情。四支服务队进驻都江堰之后,在服务队之间的横向沟通,服务队与团部之间的纵向沟通等方面,社工协会也应该搭建平台,发挥沟通协调作用。但事实上,这些作用发挥的都不太好。”(访谈对象W)
从横向层面来看,四支服务队在都江堰的四个不同安置社区开展服务,由于空间距离较远,服务队之间横向专业交流沟通甚少,在面对灾区的共同性问题时,有限的专业力量并未进行有效整合。甚至,四支服务队之间的“专业竞争”甚至超过了“专业合作”。在合作优先于竞争的灾后救援中,这种专业竞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四支服务队之间各自经营、信息资讯分享较少,服务项目无法整合,形成“各拉各的琴,各唱各的调”的信任流失局面。
信任本身具有高度脆弱性、且其建构过程具有高度动态性,细小冲突与微妙矛盾都可能使已经建立的信任关系瞬间产生裂缝。从服务团内部关系的演变进程来看,在人员频繁轮换流动的冲击下,再加上合作主体之间减少信任波动及安定各方信心的努力和行动并不充足[14],导致这种初期建构的并不牢固的人际关系纽带遭到严重破坏,服务团内部的信任资本存量逐渐被消磨至尽。
二、农村灾难救援中社会工作跨部门合作困境的根源
上述的三大实践困境表明,我国农村灾难救援中的跨部门合作机制还远未成熟,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质性授权不足
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和充分授权,是组织之间进行有序、有效合作的前提基础,即使是拥有高度的自有裁量权的组织也概莫能外,因此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不论几个组织合作,均需要有高层级的领导的承认与支持[15]。在此次农村灾难救援过程中,上海服务团缺乏合法身份之根源,主要在于各级政府部门的制度性、实质性授权不足。
从表面上看,政府高层领导的认可与对口援建制度为服务团的整体性介入提供了保障。“5.12”地震发生后,中央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全民紧急响应机制,于2008年6月11日印发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确定东部、中部地区19个省市作为援助方,援助四川省18个县市及甘肃、陕西等受灾严重地区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16]。这为服务团整体性进驻都江堰开展灾后服务提供了政策上的授权。2008年5月15日,上海市民政局印发《上海市民政局关于组建“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的请示》,向上海市政府请示,将组建的“上海社工灾区援助团”(后更名为“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纳入市政府派出的专业救灾团队范围管理[17],为服务团的成立赋予了一定的合法性。
但客观而言,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授权,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仅仅解决了服务团的“出生”和“入场”问题,但是对社会工作在现有救灾服务体系中的参与权限、职责分工、功能定位等议题并未做出明细界定。如我国台湾地区的灾害救助政策就明文规定:“社工员需访视所有的罹难、失踪及重伤家庭,以了解个案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天然灾害受灾户在生活重建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需经由社工员评估后发放。”[18]相比之下,我国诸如此类实质性授权则严重缺失。“这和我们的体制有关,政府一直是个强政府,他(政府)感觉你们是来辅助我的,把社工当成志愿者来看待的,你是志愿者那你就在救灾服务体系的外围做一些工作。看我们的关于救灾的很多制度性的文件中,是没有‘社工’二字的。其他的比如教育、卫生、治安等工作,这些灾后重建文件中都有规定,但是我们社工是没有的。”(访谈对象D)
显而易见的是,非实质性授权远远不足以维系跨部门合作关系的长效运行。换言之,现阶段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正是通过法律制度、政策文本等方式获得实质性授权。尤其是在农村灾难救援这样一个民间救援组织相对弱势、同时又缺乏对政府公共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的实践场域,可以说,实质性授权不足是导致跨部门合作关系受到权力侵蚀、进而丧失其平等性与有序性的最主要原因。
2.主体间目标冲突
在此次农村灾难救援中,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部门、社会服务机构、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等,形成了多主体、多层次的责任。而当不同责信主体之间的目标期待与责任取向不一致,同时又缺乏对相应责任的制约以及对多元责任的有效调和机制时,就很容易产生责信困境。
其一,对于一线的社工服务队来说,其目标关注是如何面向安置社区和受灾群众有效开展社会工作服务,以及进行各项评估与研究资料的收集。因此,他们希望政府提供更周全、细致的保障性支持,而不要过多干预和影响服务的专业性。
其二,对于中间层级的行政协调和后勤服务的服务团团部来说,由于其工作人员多为民政系统下属工作人员,因此在协调服务的过程中,“对上负责”的认知惯性导致“对下服务”的功能发挥不足。
“可能因为他们(服务团团部)都是体制内的人。给我感觉,这种体制内的人员有一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他们没有要推动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积极的态度,而是××局长(民政局领导)要推动,我不得不去做的那种被动的状态。没有整合、协调的平台,到最后,就成为我们四支服务队自拉自唱了的松散的局面。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作用没有发挥好。”(访谈对象D)
其三,对于高层的行政决策团体来说,关注焦点更多在于服务的效率、效果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度方面,潜在的理念导向是对“政绩工程”负责。这种互有错位的职能期待差异使得服务团内部、服务团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重重、难以调和。“在那种场域中,大家都关心民众的需要。但是民众需要的实现方式、实现程度、实现的节点上,可以说四支服务队与上海民政局之间,甚至四支服务队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比如,就某个服务项目而言,对学术团队来讲可能希望能够用专业策略和专业方法推进,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可能会觉得这样做(专业模式的推动)太慢了,我需要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说白了,政府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甚至是能够被宣传报道的效果明显的业绩。”(访谈对象S)
由上可见,服务团内部多元主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目标冲突,政府部门与四支服务队之间并未形成真正的平等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服务团的重大决策上,基本上都是由上海市民政局相关领导决定,缺少目标主体之间的协商与调和。这种“政府主导式”的不平等合作关系严重削弱了其他几家非政府组织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进而使联合救灾的服务效果以及跨部门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受到影响。
3.组织间沟通不畅
在灾后救援服务中,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内部横向和纵向层面的交流沟通不畅则是信任困境的根本原因。尽管服务团在成立之初制定了旨在信息分享和沟通互动的《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报送制度》,但其实际运行效果并不理想。
第一,从纵向沟通来看,四支服务队与上海市民政局之间的信息报送与分享制度是失效的。信息报送制度要求四支服务队以《工作日志》和《工作简报》形式,将服务期间富有特色的工作情况、服务案例、感人故事和经验反思等有关信息及时报送上海市民政局。在为期四个月的服务过程中,服务队采取“分批次轮流服务”的方式(每批队伍约10人,服务周期为20 天),共有24 批206 人次参与服务。人员的频繁流动,导致信息报送工作不及时和不稳定。再加上相关人员对信息报送工作的不同理解,致使原本计划一天一报的《工作日志》变成不定期的服务小结,信息的丰富性、深入性和全面性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参与者之间的理念差异以及执行过程中频繁的人员交替,导致信息分享并没有理想中的那样充分、全面、及时。
民政局信息收集的工作人员表示:“作为信息收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感觉四支服务队信息报送方面并不太积极,一方面,四支服务队的人员轮换太频繁,20 天轮换一批人。每换一批人,我都要重新联系相关人员。而且每批队伍的负责人对信息报送工作的理解和执行都不一样。另外,作为高校的专家学者,他们在报送信息方面还是有选择的,毕竟有些资料要作为他们今后开展科研以及发表文章的参考的,所以那些重要的一手资料,他们可能并不太愿意给我们。”(访谈对象L)
而一线的服务人员对于信息分享失效的困境实际上也有难言之隐:“从技术上来讲,信息整理与分享其实是一个专业平台。无论从技巧或能力或精力方面来说,当时的民政局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民政局可能更多的还是平时的行政工作流程,就是简单的信息收集、信息报送等模式。当时我们一线社工都很忙,要写工作日志之类的,写完之后交给你,你又不能帮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只做资料收集,我们更要组一个专家团来会诊,比如服务队遇到专业困难,那你把个案提出来,那我们这个信息开放平台就要有一个反馈机制,或者提供建议,或者提供资源,或者是提供社会关系的链接等。(访谈对象W)
第二,从横向沟通来看,服务队之间的联系会议制度、召集人制度也是失效的。四支服务队在实务推进中各自经营、信息资讯分享较少,一些服务项目无法整合。如联席会议制度规定四支服务队每周至少召开一次碰头会,特殊情况下可随时召开,以充分确保服务队伍之间的资源同享、信息互通和问题协商。但在实际中,由于政府和服务队疲于各项事务,导致联系会议制度难以常态性召开。正如有服务队所言:“后来等到我们那批(第二批)之后,才开始搞联席会议制度,就是大家推一个召集人之类,但是在推召集人的时候,还是出来一些小问题。因为大家在这里面考虑个人因素多的话,其实做起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到最后那个召集人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发挥作用。包括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各个队伍(学校)自己在开自己的总结会。就感觉有限的专业力量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形象一点比喻,就是五个手指头之间是分开的,没有联接的。”(访谈对象W)
第三,由于四个安置社区地处城乡结合带,彼此之间的空间距离相距甚远,阻碍了服务队之间的经常性沟通。正如Zakour(1996)所研究的“组织关系路径模型”显示:地理距离对合作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且呈负相关关系[19]。“灾难本身确实太大了,我们一头扎进安置社区之后,相互之间也来不及交流。每支服务队都驻扎在一个安置点。而且安置点与安置点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是蛮远的。因为我们平常工作是没有时间去的,大家都要工作到很晚,一方面很累,另一方面对当地的地理情形也比较陌生,感觉不安全。”(访谈对象W)
三、农村灾难救援中社会工作跨部门合作困境的治理路径
1.构建以授权为核心的制度化参与机制
这是确保非政府组织获得身份合法性,有效、有序参与灾害救助的前提条件。尽管在2010年颁布的《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红十字会、慈善会和公募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依法协助人民政府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非政府组织以身份上的合法性,但是在具体操作细则上,参与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远远不够。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害救援的制度化机制。以民政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可以尝试与非政府组织签订“防救灾合作备忘录”,明确非政府组织主动参与农村防救灾的责任义务、参与方式、参与途径以及经费来源等内容,促使跨部门合作职能规范化;随着合作的进一步加深,政府部门可以探索建立“非政府组织参与防救灾工作”的行政规章或制度性规定,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防救灾提供合法性来源,为灾难救援多元主体的跨部门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2.达成平等合作的共识
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当摆脱过去“老大哥”的主导心态。要认识到农村灾难救援过程中政府能力的局限,主动将本地或外来的非政府组织纳入到正式的灾难救援体制中,提高非政府组织在偏远农村提供服务的活动能力,扩大服务传递的地域范围,使农村地区受灾民众能够及时、充分获得救援物资和救助服务。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要摒弃“非我莫属”的盲目自信。不仅要认识到农村灾难救援过程中政府作为核心“协调者”和“主导者”的角色,还要意识到现阶段自身在能力和资源上的局限,要结合农村社区分散、需求多样的特点,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及农村基层组织开展偏远地区物资配送、受灾家庭需求调查、受灾村民关怀访视等服务。
3.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模式
防灾备灾阶段,建立多元的跨部门沟通联系渠道。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互动联系:政府主动、经常邀请非政府组织参加防救灾的重要会议;建立系统完整的非政府组织资源库、灾害社会工作人力资源库,并根据职能分工进行编组,使其作为政府在农村灾后救援中的重要补充力量进行统一管理;政府联合非政府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在农村社区举办防救灾课程训练和行动演习,协助村民掌握灾害防救和应对技能,培养组建防救灾志愿者队伍,从而增强农村社区防灾备灾能力。
紧急救援阶段,建构灵活机动的“支援”模式。由于救援时间紧迫、任务紧急,需要最短的时间内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帮助受灾民众脱离危险。鉴于目前我国救援物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政府手中、非政府组织发展刚刚起步的现状,因此在合作方式上,非政府组织需扮演好“支持者”的角色,在人力资源、物资资源、信息资源等方面配合政府开展紧急救助,并协助受灾村民开展自救、他救和互救。
恢复重建阶段,建立正式的“契约式”合作模式。在恢复重建阶段,灾后农村面临根本性的生计恢复、生活恢复、家庭功能恢复、社区功能恢复等结构性、持久性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稳定的物资资源、固定的人力资源以及持久的服务资源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方式,已不能采用紧急救援阶段的临时性、非正式的“支援”模式,而需要建立正式的契约化合作关系。例如针对灾后农村需要特别关注的弱势人口群(如留守儿童/青少年、妇女、残疾人、孤寡老人),政府可以制定出专门服务方案,委托有能力的社工组织驻扎农村开展持续性的专项服务;在社区层面,政府可以成立“社工服务站”、“生活重建中心”等常驻性机构,委托非政府组织管理经营,为受灾民众提供福利服务、心理支持、辅导训练、资源链接等多元全面的综合服务。
注 释:
① 跨部门合作:旨在探究第一部门(公部门)、第二部门(私部门)与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与公民社会)在共同处理具有跨领域、跨组织特性的社会议题时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是建立在不同行动主体间的相对自主、公平参与、责任明确、程序透明的相互镶嵌与相互认同的互动模式上,其核心内涵是强调跨部门互动关系的形成可以提升并增补政府职能(参见:Brinkerhoff Jennifer M. Government-nonprofit Partnership : A Defining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2, 22. p. 19-30.)。本文所指的跨部门合作主要是指第一部门与第三部门之间的合作,文中与政府组织相对应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第三部门组织,不包括第二部门。
② 四个安置社区位于蒲阳镇,分别为勤俭人家安置点、城北馨居安置点、滨河新村安置点、幸福家园安置点。安置群众身份主要是居住于城乡结合部的务农人员、小经营业主。
[1]Salamon,Lester M.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s:The 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 Nonprofit Relations[A].In Powel,W.W.(ed),The Nonprofit Sector:A Research Handboo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99-117.
[2]张怀承,杨婧瑜.农村灾害救助的现状与特点[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2):14-18.
[3]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7):6-11.
[4]边慧敏,林胜冰,邓湘树.灾害社会工作: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社会工作服务开展情况的调查[J].中国行政管理,2011(12):72-75.
[5]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工作报告[R].2008-11.
[6]徐永祥.建构式社会工作与灾后社会重建:核心理念与服务模式——基于上海社工服务团赴川援助的实践经验分析[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4.
[7]张粉霞,张昱.灾害社会工作的功能检视与专业能力提升[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98-106.
[8]王曦影.灾难社会工作的角色评估:“三个阶段”的理论维度与实践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29-137.
[9]张粉霞.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自灾害救助条例》[J].城市与减灾,2011(11):1-5.
[10]刘淑琼.绩效、品质与消费者权益保障——以社会服务契约委托的责信课题为例[C]//.官有垣、陈锦棠、陆宛苹.第三部门评估与责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86.
[11]Salamon,L.M.,Musselwhite,J.C.,& Abramson,A.J.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J].New England Journal of Human Services,1984,4(1):25-36.
[12]刘丽雯.非营利组织:协调合作的社会福利服务[M].台北: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4:59-66.
[13]Kapucu,N.Public –Nonprofit Partnership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Dynamic Contexts of Emergencies[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6,84(1):205-220.
[14]郑锡锴.社会资本建构与灾害防救体系运作之研究[J].竞争力评论,2004(6):9-38.
[15]孙本初、郭昇勋.公私部门合伙理论与成功要件之探讨[J].考铨季刊,2000(4):95-108.
[16]新华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6/18/content_8 391394.htm.
[17]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上海社工灾后重建服务团工作报告[R].2008-11.
[18]陆宛平.社会工作在重大灾变服务提供的角色及民间非政府组织介入所遭遇的挑战[R].灾害救助与社会工作(2010 两岸社会福利学术论坛),台湾中华救助总会、财团法人中华文化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2010:261-270.
[19]Zakour,Michael J.Geographic and Social Distance during Emergencies:A Path Model of Inter-organiza- tional Links[J].Social Work Research,1996,20(1):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