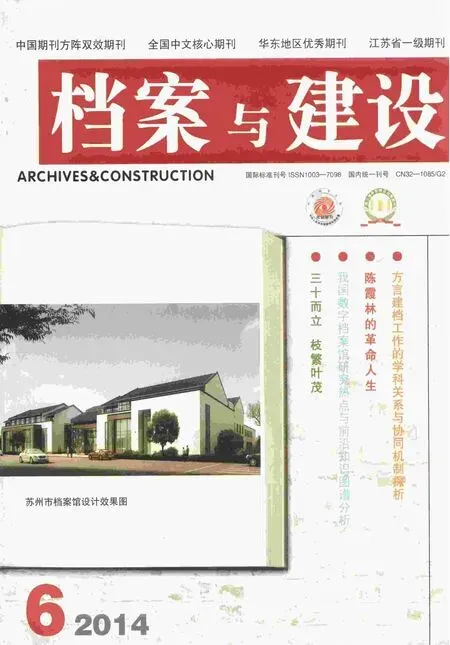档案资源的瑰宝 传统文化的精华——敦煌历史档案价值浅析
2014-03-30晏周
晏 周
(中共安徽省直机关工委,安徽合肥,230001)
敦煌历史档案,同徽州历史档案一样,被认为是20 世纪发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两大地方历史档案之一,其发现被列入中国历史文化的五大发现。敦煌历史档案,指的是甘肃敦煌地区历史上形成的遗存至今的文书材料,又被称为敦煌遗书、敦煌文书、敦煌写本等。主要指古敦煌郡(即瓜、沙二州)境内(今敦煌、安西境内)的遗存材料。包括1900年5月26日在藏经洞发现的和1944年8月30日在土地祠残塑中发现的经卷、古文书等,其中藏经洞出土的历史档案总数达5万多卷件。这些历史档案按内容分主要有地志大事记、族谱家传、籍账、差科簿、社邑文书、行用水细则和行人转帖、会计历等财政文书、契据、便物历、牒状公验、法律文书、私人账簿、僧官告身和寺职任免、度牒戒牒、请僧疏、诏敕、军事驿传、治安文书、书启、墓碑别传功德记等。敦煌历史档案中绝大多数为佛教经卷,其中大多数为手写本,仅少量为印刷本,最初它们都由民间收藏、保管,最后通过民间渠道发现由有关机构和私人收藏的。敦煌历史档案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材料,它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更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藏,是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文化财富。研究敦煌历史档案的价值并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对促进敦煌学的研究和发展,丰富我国档案资源,促进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学术价值
敦煌历史档案的材料来源主要是原敦煌地区各级官府、军事机关和寺院,因此仅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 万多卷经卷和社会文书,内容就非常丰富,涉及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如天文、历法、医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社会、民俗、民族、哲学、逻辑、经学、文学、曲艺、戏剧、语言、文字、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法律、婚姻以及农业、水利、交通、旅游、建筑、石油等方方面面,尤其难得的是,有大量失传古佚文书,大大丰富了我国文献宝库;其书写文字,除汉文之外,又有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此外,还发现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刻本印刷书籍、绘品。其价值之大,无与伦比,被学术界誉为“古代学术的海洋”。
敦煌历史档案是历史上从未面世过的原始材料,其记载的有许多是人们不知、知之不详或不清的东西,或是从未见过的实物。因此,它们对学术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在敦煌历史档案中,有许多是历史上已失传的东西。如《玉篇》是我国比《说文解字》稍晚的一部解释音义的重要字典,经后人大量删节,现传世的《玉篇》刻本已与原本大不相同。敦煌历史档案中的《玉篇》是梁朝顾野王的原本,基本保持了这本字典的原貌。再如《切韵》,是隋朝陆法言等人编著的一部写诗押韵的重要工具书,宋以后逐渐失传。敦煌藏经洞中的发现,使许多《切韵》的手写本重见天日,给学术研究增加了活力。敦煌汉简主要来源于汉代烽燧出土的2400枚汉简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1000 枚汉简。汉代烽燧是汉代军事重地,来往公文涉及政治、军事防务为多;悬泉置遗址是汉代邮政通信的一个驿站,驻地有官府各职能机构,其出土汉简反映了汉时西北边郡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政通讯等情况。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汉烽燧长城遗址出土的简牍,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从此便产生了一门新学科——简牍学。同时,还出土有题记、诏书、药方、四时月令和西汉哀帝时期的麻质纸,均属国内首次发现。特别是有一块写有近30 个汉字的西汉麻质纸的发现,改写了蔡伦发明造纸之说,把我国造纸技术发明的时间向前提前了200 多年,说明西汉时我国已具备相当高的造纸技术,已开始应用纸张书写文字了。
2 史料价值
敦煌历史档案具有真实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启发性,是我国民间历史档案的典型代表。它作为敦煌学这一新学科的创建基础,在于其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档案史料,亦即证明了“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现”这样一个科学规律。
尽管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不尽于敦煌历史档案,但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重大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敦煌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起和形成,缘于敦煌历史档案的发现和研究。比如敦煌学的形成、发展历史,有的专家将其归纳为三个时期,有的学者归纳为五个时期。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从藏经洞敦煌历史档案的发现后开始研究的。前两个时期也均为敦煌历史档案的搜集、辑录、校勘、编目、整理和初步研究。1930年,陈寅恪第一次提出“敦煌学”这一词时,其含义也只是仅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敦煌历史档案而已。第四时期以后,即在1950年以后,敦煌学才在研究方法、理论、领域等方面逐渐形成和成熟,才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敦煌学。
敦煌历史档案不仅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历史的重要依据,还能从中窥见我国古代公文写作、公文处理和传递及档案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如在公文撰写方面,既有对公文格式、行文关系、运转程序的规定,如《开元公式令》,对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等撰拟官府文书的规定,又有对公文撰拟中平阙制度的规定。如《唐天宝公式令》,对平阙式、不阙式、旧平阙式、新平阙式均有规定,为研究唐代公文书写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在档案整理方面,唐代规定:“凡文案即成,勾司行朱讫,皆书其上端,记年月日纳诸库。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谬,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这是对收文和发文归档工作的具体要求。从敦煌遗书卷子中可见,所有归档文件归档前都必须进行认真整理,即将各份相关文件进行分类,对同案或同问题文件按顺序粘连在一起,当时称作“案连”,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组卷环节。文件经“案连”后记明时间和题目,方可存入档案库房集中保管。
3 经济价值
敦煌历史档案的经济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其经济类文书占的比重最大,表明其实用价值最大,因而决定了民间档案的取舍和收藏,这是敦煌历史档案得以保存和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敦煌历史档案中,以经济类文书为主体,在此以《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5辑中收录的敦煌文书为分析案例。这5辑释录共收录敦煌文书1391件,应包含了敦煌古文书的主要部分,其中经济类823 件,占59.2%;法律类195件,占14%;僧尼类193 件,占13.9%;书仪书启类68件,占4.9%;军事、驿传治安类42件,占3%;地志、谱牒类23 件,占1.2%;告身任免类14 件,占1%;其它类31 件,占2.8%。由此可见,敦煌历史档案同以往发现的重大历史档案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摆脱了中国传统史料以王室类政治史材料为主的传统模式,表现出鲜明的民间特色和经济特色,十分具体和实用。经济类文书档案,是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利用价值最大,最受民间重视,因而能保存和流传下来。二是敦煌历史档案本身是一种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较高品味的人文景观,对其开发利用,可以创造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敦煌历史档案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其产生、形成并能保存下来,与敦煌莫高窟和敦煌石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敦煌莫高窟和敦煌石窟文化,就没有敦煌历史档案,所以,敦煌石窟本身就是敦煌历史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敦煌历史档案的区别仅在于,敦煌历史档案是以抽象的文字为符号来记录历史,而敦煌石窟是以各种形象(如壁画、彩塑、飞天、反弹琵琶乐天和建筑等)来直观地记录历史,因而被称为“形象的历史博物馆”、“东方艺术史”、“人类文化珍藏”。由此可见,敦煌石窟文化和敦煌壁画,是一种珍贵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较高品味的人文景观,它们既是古代实物遗存,又是古代美术杰作,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宗教、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丰富内容,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科技价值以及旅游观赏和艺术审美价值。它们是人们了解敦煌历史、熟悉敦煌文化最直接的窗口,每年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前来游览。那奇特壮观的建筑艺术,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跨越千年的历史画卷,美丽动人的壁画故事,千姿百态的飞天伎乐,把人们带进了一座座美妙而神奇的古代艺术殿堂,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和精神熏陶,令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因而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安徽省档案局,甘肃省档案局.首届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讨会文集[C].兰州:[出版者不详],2001.
[2]甘肃省档案局,安徽省档案局.第二届敦煌历史档案与徽州历史档案开发利用研讨会文集[C].兰州:[出版者不详],2003.
[3]罗培.徽州历史档案与敦煌古文化共性探析[J].档案学研究,2003(2):2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