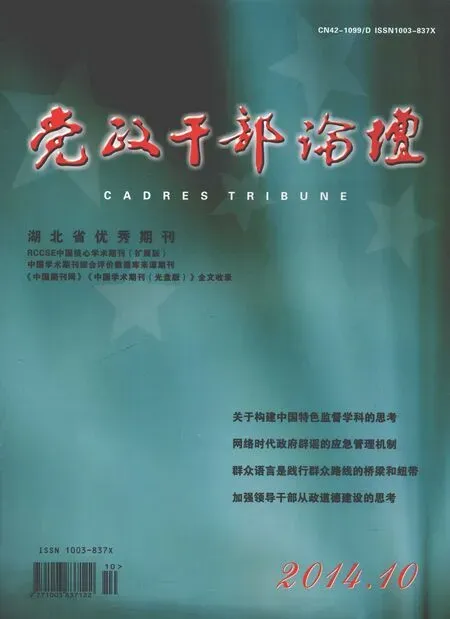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宁波“PX”事件为例
2014-03-29林丽丽鲁先锋
○ 林丽丽 鲁先锋
政策议程设置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政策制定者对外部众多要求进行考虑和选择,并将部分要求纳入行动计划的过程。豪利特(MichaelHowlett)和拉米什(MichaelRamesh)认为,如果要理解政策议程,“必须知晓个人或群体的政策需求是怎么形成的,以及政府是如何对政策需求做出反应的”[1]。从政策议程的发生过程看,政策议程设置或依赖于内部主体的发动,如“内在动员型”、“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或依赖于外部主体的发动,如“外在创始型”、“外压模式”等;或依赖于内外部主体的共同发动,如“政治动员型”、“借力模式”、“动员模式”等。在封闭的、垄断的、集权的政治环境下,政策议程设置更多地受制于政府内部精英主体的理性和价值取向影响。而在民主的、开放的、多元的政治环境下,政策议程设置则取决于外部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动员能力。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如何建立反映社会多元利益诉求的政策机制已经成为公共政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外,公众可以通过听证会、协商会等方式参与政策议程设置。但有些时候,公众缺乏参与的渠道或者公众的意见并不被决策者所接纳,因此,公众则容易通过抗议、上访、游行示威等方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迫使决策者改变政策议程。
一、宁波PX事件中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过程
2007年5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浙江省签署了关于天然气、成品油销售等内容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在浙江选址建设1000万吨级炼油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800亿元,项目一期工程包括年加工原油2000万吨、年产乙烯120万吨及建设30万吨原油码头等,项目将为当地增加10万个就业岗位。该项目最后选址在宁波镇海区,即中石化宁波分公司炼化厂扩建工程[2]。
但消息传播后,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2012年10月22日,南洪村、湾塘村、岚山村等村400多名村民因不满村庄距离化工企业太近,且不能划入拆迁范围,开始集体前往镇海区政府反映情况,导致镇海部分道路出现严重拥堵。10月26日,群众聚集在镇海区公路上进行游行示威活动,此后镇海区又发生了多次封路抗议活动。到27日和28日,抗议活动已经蔓延至宁波市中心的天一广场和宁波市政府。为缓解公众的紧张情绪,宁波市委市政府分别听取了镇海蛟川街道、招宝山街道、澥浦镇等相关农村和社区居民的代表以及区老干部、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的意见和建议,并表示市委、市政府将进一步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使镇海炼化扩建一体化项目的决策充分地体现民意[3]。10月28日,宁波市与项目投资方研究决定:坚决不上PX项目;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停止推进,再作科学论证。
二、公众参与政策设置的问题及阻碍因素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受到不同因素影响,包括政府、公众、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的认知和决策地位,国家整体政治制度的设计,公共决策体制的结构,传统文化和参与意识等。从宁波PX事件的发生过程看,影响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具体因素主要体现在传统精英决策理念的阻碍、公众参与决策机制的不完善和公众民主意识的薄弱。
(一)传统精英决策模式的阻碍
美国学者约翰·金登(JohnKingdon)认为政策议程是“政府官员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政府外人员在任何给定时间认真关注的一系列问题的编目”[4]。从公共政策主体的结构看,直接或间接影响政策制定过程的政策主体大致包括国家公共法权主体、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国家公共法权主体是体制内的国家法定的公共权力主体[5]。因此,公共政策主要被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机关以及相关决策者所掌握,而体制外的社会政治法权主体和社会非法权主体只能对政策过程施加影响,且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外部主体力量的强弱和内部核心的态度。在宁波PX事件中,政府主导了政策议程的设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与地方政府签署了项目合作协议,决定了项目的选址、投资和规模。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政策议程设置,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的作用,公众参与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在宁波PX事件中,地方政府一直声称环境评估合符要求,但这并没有得到地方居民的认可。公众与政府的认知偏差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不对称。对于PX项目而言,公众一直排斥在决策范围之外,且公众一般缺乏专业知识,无法对其环境影响作出合理评估。尽管政府一再声称项目合乎环保要求,也无法消除公众的担忧。二是地方政府的GDP导向和“经济人”行为的利益偏向。地方居民认为政府引进的项目投资与自身并没有多大关联,相反,可能伤害自身利益。因此,游行示威的目的就是为改变自己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的不利地位。
(二)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
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必须建立在信息充分的基础上。理性主义认为,完备的知识和信息、非冲突的决策目标、一致的决策偏好、充足的决策方案是最优决策的必要条件。这种理性至多是体制内少数精英理性的体现。虽然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公民参与政策议程的方式趋于多元化,但公民参与仅局限于某些环节或者部分事项,公民参与程度取决于核心决策者的态度,并不能成为决策体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从参与时间看,公民往往是事后参与,即决策议程设置结束之后,公众只是作为决策的象征性表达。有些决策者为了便于控制决策的过程,将信息尽量控制在少数人范围内,以减少异议、争执和阻力。在政策制定之后,才向公众公布。此时公众只有喝彩和拒绝的权利。在宁波PX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公众刚开始并没有获得参与的机会。后来附近村民只得选择游行抗议的强烈方式来影响决策过程。为缓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2012年10月23日,宁波市成立了以副市长为组长,市级相关部门和镇海区政府参加的项目推进协调小组,下设项目说明组、宣传报道组、项目实施组、社情民意组、现场执行组,并在当天召开了第一次协调小组会。主要针对那些强烈要求拆迁的村民进行沟通。公众的这种参与实际是一种被动式沟通,是决策体制之外的应急措施。双方往往缺乏相互信任和认知基础,从而导致合作失败。
(三)民主观念的缺失
我国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统治,集权主义和宗法血缘关系使广大群众排斥在公共决策之外,少数封建精英和广大公众之间在政治上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政治冷漠心态潜移默化地支配着公众的行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奠定制度基础,但传统的消极的政治参与文化仍然滞碍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一方面,决策者自身缺少民主观念,认为政策议程的设置只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多元的政治参与自然增加了协商的难度。因此,有些决策者倾向于将议程设置限制在少数人范围之中。尽管有些制度规定公众必须参与的环节,如国务院2009年8月17日颁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规定:“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采取调查问卷、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意见。”然而,制度实际运行过程中公众参与环节仍然被操纵,形成“虚拟”参与。另一方面,公众秉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狭隘理念,对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公众参与政策过程是一个讨论、协商和争议的过程,客观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这种参与成本并不一定能够从预期的政策中获得回报。公众在“经济人”思想的支配下,往往选择自利的、维权式的参与。在宁波PX事件中,最早采取抗议行动的居民主要集中在南洪村、湾塘村、岚山村等距离化工企业较近的村庄。
三、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对策
政策议程设置是包括政策议程设置主体、政策议程设置客体及政策议程环境的综合系统。从公众参与政策的可能性而言,主要取决于六个方面因素:重视可以得到的报酬;认为选择是重要的;相信自己能够帮助改变结局;相信如果自己不行动,结局将不会满意;拥有关于当前问题的知识或技能;只要克服较少的障碍便可行动[6]。概言之,推动政策议程设置的有效运行,需要培育公众参与的意识、完善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
(一)培育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意识
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积极性与政府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积极的政治参与,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开放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将关注更多的公众诉求。消极的公民参与则容易导致少数权力精英垄断议程设置。相反,如果长期存在“关门式”政策议程设置又会弱化公众参与的热情。这就要求,政府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要及时公布相关信息,使不同主体平等地获得政策信息。宁波镇海居民对 PX项目可能产生的污染产生极大恐惧心理,如果政府能够在决策之前能够及时进行科普宣传,加强科研专家、环保人员、社区居民和政府之间的沟通,让居民对项目的设计、运行、排污处理和环境评估有清晰的认识,而不是采取事后解释或被动式协商,就会有利于提高公众的自主意识,增加多元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美国学者约翰·托马斯(JohnClaytonThomas)认为公民教育也是提升公民参与意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通过一些不直接与决策相关的学习过程使公民得到适当锻炼。如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些市政府创立了由政府官员、公民领袖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学习圈”,在公民讨论具体政策项目之前,一般讨论涉及“公民资格意识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不讨论十分紧迫的问题。这些讨论的确能够促进公共利益和公共参与的达成[7]。
(二)拓展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渠道
群体事件的产生“往往依赖于内部统一性和外部冲突性”[8]。“内部统一性”是群体内部不同个体通过交互行为获得认知和利益上的一致性。如通过手机、网络等传播方式,PX项目的环境危害性的信息为地方居民所接受,并共同意识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正处于危害状态,自然容易形成较一致行为——上访或游行示威等。“外部冲突性”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利益和行为上的分裂,甚至演变为冲突或斗争。在这种情形下,政府所要做的是如何化解群体意识的异化,使公众意识与政府意识保持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缓和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矛盾。为此,政府要创新沟通渠道,尤其是“法定的民意渠道如人大、政协、信访等机关和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9]。约翰·托马斯认为,增进政策接受性为目标的公众参与渠道主要包括公民会议、咨询委员会和斡旋调解三种。其中,公民听证会或公民会议可以让不同主体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上能够表达清晰的意见,并在政策问题方案获得共识。但公民会议的效果依赖于各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信息的对称性。咨询委员会是一种代表较大公众利益群体利益的少数人,能较快地作出决策,但容易导致政策议程为少数强大利益群体所俘获。因此,提高咨询委员会的协商效果需要尽量保持多元主体的参与和利益均衡。斡旋调解是借助不代表任何利益的第三方介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斡旋调解依赖于各对立主体势均力敌,且各方有和解的意愿[10]。
(三)提高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能力
在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公民有权利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而且有能力在一定范围内施加政治影响。同时并非所有的公民都有能力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并非所有的社会政治都需要和可能由所有公民直接进行管理[11]。也就是说,有效的公众参与是在一定的决策和公共事务管理范围内公众有能力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其能力诉求主要包括:(1)利益表达能力,即公众能够对政策问题和相关信息有清楚的认识,且能做出恰当的判断,从而提出自身的利益主张。(2)参与行为能力。公众参与政策议程的方式有人大议政、听证会、全民公决、建议、司法申诉等,也包括堵路、阻塞交通、游行示威、集体上访等非正常方式。不同方式的选择折射了公众自身的自身素质,有些人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甚至通过犯罪和破坏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迫使政府让步。(3)沟通和协商能力,即公众与不同主体的交流和讨论中,能够表达自己观点,在批判和商谈中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培育能力适度的公众不仅是民主决策的必要前提,也是民主决策体制的一个目标。政治社会化过程是公民主体和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交互过程。公民参与能力的培养,既需要通过主体自身的学习,也需要政府通过引导和创造平等、合作的政策交谈环境。这包括:一是加大民主理念的宣传,纠正政策制定只是政府的职能和公众只在利益受损前提下的被动式参与的观点;二是创造形式多样的参与渠道,让公众与政府之间获得平等、充分的协商;三是推动多元主体之间的讨论、批判和接纳。
[1][加]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1页。
[2]郝成、李艳洁:《宁波PX:一个石化产业的尴尬样本》,《中国经营报》2012年11月5日。
[3]《宁波就炼化扩建项目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民意见》,2012-10-28,http://www.guancha.cn.
[4]Kingdon,J.W.Agendas,Alternatives,andPublic-Policies,2ndEdition.NewYork:Longman,Inc.,2003,p.3.
[5]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6][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
[7][美]约翰·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页。
[8][9]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