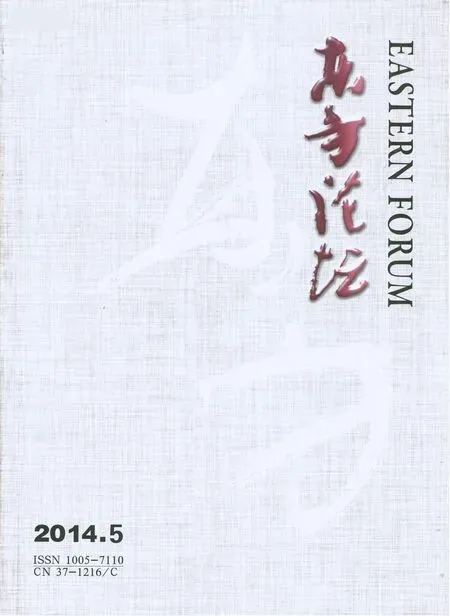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阿维斯塔》在中国
2014-03-29王汝良
王汝良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阿维斯塔》,又称“波斯古经”,是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①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教。圣书。同时,也是波斯古代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的最早载体,是伊朗古代历史、宗教、哲学、社会生活和民族风习的百科全书。
“阿维斯塔”词义为“坚实的根基”(可引申为“中流砥柱”)②参阅元文琪:《帕拉维语和帕拉维语文学初探》,载《外国文学研究》,1990年第1 期。在《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著中,元先生详致列举了国外学者对“阿维斯塔”的几种争议性解释:一是同“吠陀”为同根词,意为“知识”“福音”;二是意为“基础”(“根基”)、“原件”;三是意为“颂扬”“火的赞颂”。元先生取第二说。。作为伊朗最古老的文献,《阿维斯塔》的成书年代至少可以上溯至公元前10世纪以前。相传古人曾用金字将这部圣书用阿维斯塔语③对于《阿维斯塔》原书写语言是否为阿维斯塔语,学界存在争议。刻写在一万两千张牛皮上。阿维斯塔语是伊朗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它与古印度梵语和古波斯语等雅利安人的古老语言非常接近,专门用来书写宗教著述。
由于年代久远,又历经战火洗劫,原本《阿维斯塔》已荡然无存,现在所看到的帕拉维语《阿维斯塔》残卷只有八万三千字,分为六个部分:(1)《伽萨》,即“颂歌”,相传为琐罗亚斯德本人吟咏的诗篇,故有“琐罗亚斯德之歌”之称,享有特殊的荣耀和地位,被公认为是《阿维斯塔》的核心部分。《伽萨》是古波斯人“善恶二元论”宇宙观和以“抑恶扬善”为主旨的宗教信条的表述,它热情地讴歌了造物主善神阿胡拉·马兹达及其六大助神,同时,对恶神阿赫里曼及其众妖魔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2)《亚斯纳》,主要是对善神马兹达、众神祇以及世上一切美好事物的赞美。含有不少激情洋溢、词句优雅的神话传说故事。(3)《亚什特》,也是对众神祇的歌赞,是现存《阿维斯塔》中篇幅最长、文采最为生动的部分。含有古史传说和世界末日的预言。(4)《万迪达德》,主要讲述琐罗亚斯德教徒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的仪规和戒律。(5)《维斯帕拉德》,是对善神马兹达所创造的各种美好事物(尤其是品德高尚的行善者)的赞颂。(6)《胡尔达·阿维斯塔》,是《阿维斯塔》的精选普及本,又称“小经”“小阿维斯塔”。
国内知晓《阿维斯塔》是从对琐罗亚斯德教(祆教)的了解开始的。陈垣的《火祆教入中国考》是近代以来系统考辨祆教的第一文。他在该文中认为,祆教徒在中国“并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近年来敦煌发见大秦、摩尼二教经典,各有数种,而火祆教经典独无闻,此其证也。(近日本《世界圣典全集》刊行会新译有火祆教经名《阿威士陀经》)”[1](P124)。这段引文中,关于祆教徒中没有中国人的说法后来受到质疑,但从中可以得知,当时的陈垣先生对作为祆教经典的《阿维斯塔》已有一定了解。此后,诸多交通史、宗教史、文学史著述中较早提及该圣书。如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论及琐罗亚斯德时,云:“其事迹吾人所知甚少。唯一可佐考证者,即其教圣经《阿维斯塔》(Avesta)也。”[2](P141)随后论及该教教义及中国人称之为“火祆教”的由来。龚方震、晏可佳的《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汉文撰写的系统祆教史,在《导论》中对《阿维斯塔》的篇章结构、主要内容等做了详细介绍,并在书中多次加以称引。张鸿年的《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季羡林先生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东方文学史》 (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梁立基、陶德臻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均对《阿维斯塔》有专题介绍。作为文学史著作,张鸿年着重对《阿维斯塔》的文学价值进行评价:“ 《阿维斯塔》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的古经……《阿维斯塔》不仅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经书,而且还可以视为波斯古代诗文总集,在历史和文学上都是珍贵的文献。”[3](P12)并且称“ 《阿维斯塔》是后世叙事文学的源头。可以说没有《阿维斯塔》也不会有后世光辉灿烂的巴列维语和达理波斯语文学。”[3](P17)此外,一些历史、哲学、美学、文化史著作中也对《阿维斯塔》多有简略提及或详细介绍。从这些著述所涉及的领域如此广泛来看,《阿维斯塔》的确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符合上古时期文化元典含混包容的特征。
在《阿维斯塔》的译介方面,工作于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元文琪先生功不可没。1986年,他在《外国文学研究》第1 期发表文章《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对《阿维斯塔》的成书过程、主要内容做了学理性介绍,并在文章末尾着重强调了《阿维斯塔》的研究价值所在:“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不仅为我们了解古代伊朗社会的历史、宗教、哲学、神话和语言等,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而且对后世伊朗乃至中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言而喻,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在伊朗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完全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4]1995年,元先生首次将《阿维斯塔》(贾利尔·杜斯特哈赫选编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翻译成中文,使国内读者得以真切地感受到这部古波斯典籍的文化魅力,也给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元典依据。2000年,元先生又将易普拉辛·普尔·达乌德①易普拉辛·普尔·达乌德(1884-1967),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和《阿维斯塔》学权威。为该选编本所作的校注序言加以整理,以《〈阿维斯塔〉研究小史》为题发表,为国内读者了解国外《阿维斯塔》的研究历史提供了简明扼要的介绍。②参阅元文琪:《〈阿维斯塔〉研究小史》,载《世界宗教文化》,2000年第1 期。
《阿维斯塔》精深驳杂,是研究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明的重要文献。它的价值不但被伊朗学者和西方学者所推崇,也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除以上所引元文琪先生的评价外,波斯文学研究专家张鸿年先生认为:“ 《阿维斯塔》既是古老的宗教典籍,又是伊朗最早的诗歌选集和神话传说的总汇,是一部研究伊朗古代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珍贵文献,在世界为数不多的古代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3](P13)但目前国内对《阿维斯塔》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元文琪先生除1986年发表《波斯古经〈阿维斯塔〉》外,次年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善恶·祥瑞·神权——波斯古经〈扎姆亚德·亚什特〉剖析》一文,着重对包含神话传说最多的《亚什特》部分第19 篇《扎姆亚德·亚什特》进行研究。他从对本应热情颂扬地神扎姆亚德的这一部分何以变成“灵光颂”这一疑问入手,从灵光神话的三个源头(与琐罗亚斯德“善恶二元”论直接有关的灵光神话,反映古波斯人“祥瑞观念”的灵光神话,反映古波斯人“君权神授”思想的灵光神话)进行追溯和剖析,认为灵光观念是伊朗雅利安人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过渡这一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表现在《扎姆亚德·亚什特》中的“灵光颂”则与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们插手篡改不无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元先生在该文中认为,“‘灵光’说称得起是古波斯人的独创,但灵光神话所反映的神权观念,亦即君权神授的思想,在中国却是古已有之。”并用中国《尚书·洪范》中所载周武王与箕子的一段对话(鲧、禹治水的失败和成功分别是因为违逆和顺从了上帝的意志)以及西汉董仲舒的“谴告”说、“符瑞”说进行平行比较,以此加深对《扎姆亚德·亚什特》的理解和认识①,体现出可贵的比较文化的视野和意识。1997年,元先生的著作《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问世,书中在对《阿维斯塔》在不同时期流行的不同版本进行了详致校核之后,以《阿维斯塔》和帕拉维语文献为依托,着重对琐罗亚斯德教神话的源头、历史衍变和体系结构、基本内容、原型模式和哲学蕴含做了考辨研究,并对琐罗亚斯德教(民族性二元神教)和摩尼教(世界性二元神教)做了比较考察。元先生认为,研究宗教神话应跳出表层叙事的圈子,深入探讨其深层结构的哲学蕴含(指宗教宇宙观和建立在这种宗教宇宙观基础上的宗教观、道德观和社会观),才能把握其最本质的特征。在探索《伽萨》神话源头时,元先生再次以比较的视野将印度《吠陀》中的神话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得出“水中之火”和“水中之光”是早期印伊人和伊朗雅利安人原始神话的母题,从而对印度婆罗门教视大梵天为“生命之源”和“万物始基”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②参阅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黄心川先生在为该著所作的出版推荐意见中高度评价,称“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波斯宗教、神话、哲学的专著,对于了解东方宗教文化、东西方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5](P3)邱紫华在《东方美学史》“古代波斯民族的美学思想”一章中专设一节,对《阿维斯塔》所蕴涵的诸多原型意象做出美学阐释,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强调在善的领域中,部分与部分之间要协调,部分与整体应当和谐的思想,这就为确立形式美的观念奠定了基础”[6](P509)。2008年,宁夏大学的王丽完成了其硕士学位论文《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宗教哲学思想探析》,该论文以元译《阿维斯塔》为底本,通过对《阿维斯塔》经文的详细解读,对祆教哲学的神灵观、天使系统、伦理道德、末世论以及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做了探讨。③参阅王丽:《祆教经典〈阿维斯塔〉宗教哲学思想探析》,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此外,施安昌注意到了《阿维斯塔》记载祆教礼仪所用的植物,罗世平则因关注祆教美术提及《阿维斯塔》,虽均非针对波斯古经的专题研究,却也体现出其多领域研究价值。④参阅施安昌:《祆教礼仪所用植物考》,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3 期。罗世平: 《中国的琐罗亚斯德教美术》 ,载《中国书画》2012年第5 期。
1986年,元文琪先生曾将前伊斯兰时期的古波斯文学研究视为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4],道出了包括《阿维斯塔》在内的波斯文学研究的尴尬。近三十年过去了,国内已有以上所述等针对《阿维斯塔》的研究成果出现,涉及宗教、文学、神话学、哲学、美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但相较于《圣经》《古兰经》和佛经研究的热络,《阿维斯塔》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语言的障碍、资料的缺乏、研究的难度(贯穿文、史、哲、宗教、美学、民俗学等各个领域)、对研究价值的认识不够、研究人员的匮乏等,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由所在。当下,伊朗学、东方学研究队伍正不断壮大,回归元典也已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识,相信《阿维斯塔》研究会有更大的改观。
[1]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A].陈垣史学论著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 张鸿年.波斯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元文琪.波斯古经《阿维斯塔》[J].外国文学研究,1986,(1).
[5] 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