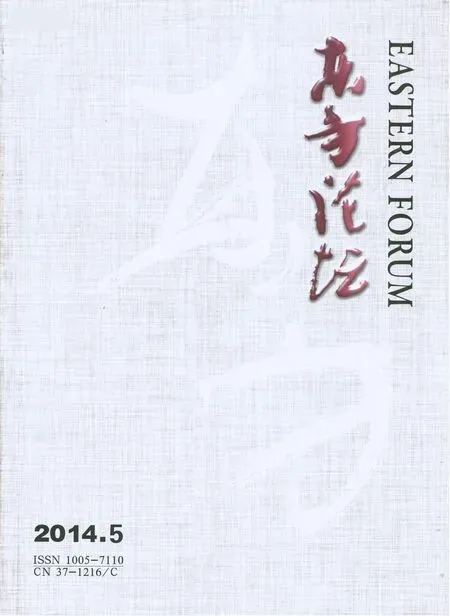民国新闻管制研究
2014-03-29李金凤
李金凤
(西南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管制
(一)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新闻管制
清朝末年,满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大清报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等新闻法律法规,但新闻管制是比较松动的,严格说来,民国建立以前,满清政府并未形成一套有效的新闻管制制度,所以有慈禧太后不走司法程序以口谕处置新闻从业人员沈荩的事例。从《苏报》案来看,清末时期的租界,初步的形成了自己的新闻管理体制。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听任了新闻的自由报道(由于当时反满思潮的兴起,临时政府所在地的江南地区的新闻媒体基本上是倾向孙中山临时政府)。孙中山退位后,由袁世凯建立的北京政府出于对《临时约法》的表面尊重,出现了短暂的新闻繁荣时期,仅1912年就出现了一个办报的浪潮,报纸多达500 种。这一时期以宋教仁建立责任内阁的尝试为高潮,以宋教仁遇刺为结束。宋教仁遇刺以后,新闻媒体受到巨大的压力,持政治异议的国民党系的报纸除了在租界可看到外,在国内基本上看不到。《民立报》编辑敖瘦蝉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对联没有直接提及当时的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政府是将敖瘦蝉枪决,此举有效地震慑了新闻媒体,在袁世凯去世以前国内基本上没有对袁世凯本人的公开批评。二次革命后,南北对峙局面宣告结束,国内政治势力发生变化,袁世凯用武力统一全国,执政自信力增强,公开用《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先后出台了《报纸条例》《出版法》《新闻电报章程》等法律法规,形式上建立了一套新闻法律管理体系,开始了对新闻管理的全面掌控。在他执政时期内,残酷镇压不同政见的党派,扼杀不同声音的舆论。1916年,欲意称帝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在华北几乎没有报纸敢发表,只能发表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在袁世凯执政四年间,“全国报纸至少有七十一家被封,四十九家受传讯,九家被反动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二十四人被杀,六十人被捕入狱。从1913年‘癸丑报灾’,到1916年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而实行的对舆论的残酷压制,全国报纸总数始终只维持在130-150 种上下,几乎没有增长,形成了民国以后持续了四年之久的新闻出版事业的低潮。”[1](P720)
(二)皖、直、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新闻管制
随着袁世凯去世,北洋系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等大小军阀势力。这些军阀相互牵制,最后真正占据总统职务的反而是无嫡系部队支持的徐世昌。为了平抑当时武人干政的倾向,徐世昌试图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约束和调解军阀矛盾,有意识地放松了新闻控制。当时的华北媒体,出现了对政府甚至是总统本人毫不留情的批评挖苦。在各省督军进京召开督军团会议时,陈独秀毫不留情的挖苦现任总统徐世昌:“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历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厉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2](P239)犀利批评督军团武人干政和外交团干涉中国内政,相关媒体和撰稿人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北洋政府出于外交交涉的技巧,有意识的泄漏巴黎和会山东交涉失败的信息于媒体,利用舆论打击亲日政敌(实际掌握军队权利的皖系军阀)。北洋系的内斗及南方的革命政府也借助新闻媒体打击政治对手。所以在当时的华北,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新闻管制。据周策纵估计,1917年到1921年间(“五四”时期)全国新出的报刊就有1000 种以上。[3](P182)胡适估计,仅1919年就增加了400 家新闻媒体。而且此时的新闻媒体更加侧重于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的宣传。[4](P134)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之间相互牵制与斗争,加之对民主制度的形式上的维护,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新闻管制环境。
北洋政府时期的地方新闻管制区分很大,在军阀混战的重庆、四川,报界对大小军阀的报道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新闻自由度反而很高。在驱逐干涉川政的顾品珍、赵又新部滇黔势力时,重庆四川的报界一反在军阀混战的调停腔调,积极鼓励川军大小军头主战,批评作战不力的川军将领,报界的调门远超过川军大小军头。在统治比较稳定的云南,基本上看不到对唐继尧的批评,新闻自由度反而较低。但北洋时期的地方新闻管制有个特点,就是对其他地区的报道基本放任,所以张敬尧成了湖南以外新闻界军阀暴政的典型,湖北新闻界如赵一曼毫不留情的批评杨森部队为匪。北洋时期的军阀合纵连横很难对新闻界保密,孙传芳拜山事件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地方政治势力常通过帮派等地下势力影响新闻界,上海的青帮和四川的袍哥都有妨碍新闻自由的记录。
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闻一多、梁启超等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报刊杂志纷纷披露该事件。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段祺瑞执政府未敢加以新闻钳制。但以张作霖上台为转折点,标志着北洋时期较宽松的新闻管制的结束。张作霖进京后派奉军闯进北大、女师大、中俄大学及报馆,大肆查禁进步书刊,搜捕进步人士,查封《京报》馆并杀害知名记者邵飘萍。同年8月,《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害,这使新闻媒体受到很大震动。
(三)南方政府的新闻管制
护法战争以后,中国南方也建立起了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南方政府前期,政府忙于战争和内部斗争,并且由于地方势力强大,如商团势力,政府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新闻管制。因此,在当时的南方政府辖区,和北方的北洋政府类似,政府干预新闻报道的现象并不明显。在七总裁合议时期,南方政权的有力人士常常通过新闻媒体爆料南方政府内部政敌的内幕,孙中山先生接受德日援助等当时并无实证的新闻报道,成为南方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但随着南方政府的统一与整合,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系逐步获得南方政府的实际控制权,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党系开始了对新闻的整肃,其中以广州新闻整肃为典型。广州新闻媒体原本是亲地方商团势力的,南方政府镇压商团叛乱后,新闻媒体逐步转化为倾向南方政府。在陈炯民叛乱事件中,广州媒体一反在军阀混战时期慎言的惯例,普遍是倾向南方政府一方的。在港英势力试图介入中国内政时,广州媒体也对国外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提出了批评,这在港英势力强大的广州并不常见。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
1928年北伐胜利,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国民政府逐步取消北洋时期的新闻管理状况,以“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原则,推行“党化新闻界”“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科学的新闻统制”“新闻一元主义”等新闻政策,在思想上对新闻界进行统制。先后制定了《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出版法》《新闻检查标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指导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等大批新闻出版法令法规,控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建立报刊登记制,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和禁载制度,删削检扣进步书刊,建立起了一个以统制为核心的新闻管制。
国民党执政期间,各地方军阀势力依旧盘根错节,增加了新闻管制的复杂性。在东北易帜期间,国民政府和国内新闻界出现了良好互动,有力的促进了中日交涉。但在“济南惨案”事件中,国民政府出于对日本的暂时忍让,有意限制对日军暴行的报道,山东军阀却有意识的利用山东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在中原大战中,第三党的地方活动分子利用四川军阀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受二十八军江防总司令黄隐资助的《成都庸报》以整版篇幅综合报道不利于蒋的消息,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蒋介石末日快要到来了。”[5](P391)这标志着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还受到地方军阀势力的很大制约,国民党内部不同党派势力的牵制与制约也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新闻统制。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胡汉民、孙科的再造派以及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各自办刊,各自为阵,宣传不同的思想理论,制造了复杂多元的言论空间。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新闻媒体作为民意的反映,开始出现大量的抗日仇日宣传。由于国民政府认为推迟中日战争对中国有利,国民政府采取了低调抗战、高调亲日的新闻策略,集中进行“民族主义的新闻建设”,提倡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宣传策略。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国民政府实际上增调了多只部队增援,但出于外交策略只能说在上海抗战的只有十九路军。不了解国民政府实际军事部署的新闻界有大量的对国民政府的批评。中国海军以军火方式(非直接出兵)支援十九路军,上海媒体对海军也有大量的批评报道。国民政府的反应是严厉的,新闻管制的力度很大,甚至采用了以杜月笙为代表的帮派势力和以军统、中统为代表的特务手段,普遍引起国人非议。1936年日本国内爆发二二六兵变,兵变后上台的广田弘毅内阁为缓解中日冲突,对中方发出形式上的友好信息。国民政府出于利用日本国内斗争情形,在媒体上呼应广田内阁掀起亲日言论。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在加紧整训军队,修建吴福线、锡澄线等国防工程,积极进行中日战争的准备工作。由于军事保密的原因,这些信息无法对新闻界披露。新闻界特别是在租界的媒体,因获取信息的不完整,对国民政府有很多批评。国民政府利用特务组织严厉整肃不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租界媒体,“种荷花”成为让上海记者毛骨肃然的话。客观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新闻界的报道对国民政府而言不能说是完全实事求是的,比如上海媒体对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报道显然有过度吹捧的嫌疑,后来的史实说明马占山抗日的态度并没有国民政府坚定,但这都不是国民政府压制新闻自由的理由。
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有一个特点,出版前的审查并不十分严格,但报纸杂志如有宣传赤化、共党思想以及不利于政府言论的则查禁取缔。以左翼报刊杂志为例,《巴尔底山》《世界文化》《五一特刊》《文学导报》《拓荒者》《十字街头》《萌芽月刊》《北斗》《文学月报》等都因带有较强的党派色彩,宣传与国民政府不一致的意识形态,出版几期即遭到查禁。1933年以后,国民党的新闻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改变了这种后置的审查模式,建立了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直接干涉新闻业务工作。新闻界对此意见很大,报界频繁出现“开天窗”事件(官方审查删除后,报纸有一保留版面空白以示抗议)。《闲话皇帝》风波事件之后,杂志的审查力度也更加苛刻。为对抗蓬勃发展的左翼文艺运动,国民党实行“文化围剿”,查禁了大量书刊报纸,查封了大量报馆书店出版社,特殊情况下,采用特务手段恐吓、杀害新闻工作人员。由于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上海报界如《申报》有大量的衍射时政甚至直接批评政府的报道,如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为“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文章以及数篇《剿匪评论》,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刊登宋庆龄的抗战宣言等一系列新闻报道。国民政府下令禁止邮递《申报》,最后暗杀了《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这使上海媒体以致全国媒体自我审查、自我设限,报纸上难以再看到对政府的直接批评。国民政府开展新生活运动以后,全国报界已经无法对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批评,和北洋时代总统可以被公开批评相比,这是新闻自由的严重倒退。
三、抗日战争期间的新闻管制
七七事变后,中国引发全民抗战热潮,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也一改往日的专制,以比较开明的方式对待新闻管制,允许共产党、青年党等其他党派在国统区办报。中共办理的《新华日报》,因此在国统区获得较大发展。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也由郭沫若、阳翰笙等人负责,允许他们组织抗战文化宣传。在抗战前期,国内政治势力团结程度比较高,新闻一致性也比较高,国民政府除对涉及军事部署的军事信息等予以管制外,基本对新闻管制力度很小。在著名的长沙文夕大火事件中,国内舆论一边倒的批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对此作出反应,严惩了相关责任人。但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内政治斗争加剧。以“皖南事变”为标志,国民政府强制删除了《新华日报》的报道,《新华日报》开天窗抗议,周恩来在版面空白处写下著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基本看不到中共方面对皖南事变的意见。国民政府也利用其他党派的报纸打击政敌,如在赵侗事件中,国民政府大量转载国社党、青年党等党派发表的不利于中共的言论,而代表中共言论的观点是看不到的。国共矛盾上升之后,国民党下令取缔中共刊物、捣毁其报馆书店,采取恐怖手段对《新华日报》等报刊进行摧残。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对新闻管制是很严厉的,严格战时新闻审查,强化战时新闻监控,依据《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等法律法规实施严格的新闻专制。为防止虚假消息、不良事件动摇人心,大量的胜利消息充斥报纸版面,报纸的真实报道是要冒相当风险的。以1942-1943年发生的河南大饥荒为例,除了极少数尽职的中外记者为这场大灾难留下了片断记录外,它在历史上几乎一片空白,一场300 万民众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如此地被人忽视甚至遗忘,这是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新闻的结果。曾有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唯有《时代》不顾阻挠发表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而协助白修德报道河南大饥荒的中国记者、电报员被处分。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管制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这本是恢复新闻自由的良好时机,但国民党政府出于戡乱的需要,拒绝恢复新闻自由。凭借手中掌握的政权,迅速收复沦陷区的大量新闻报纸,如著名的民营商报《申报》《新闻报》,将其变为国民党的宣传工具。及至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时,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个比战前更为庞大的新闻网络。这一时期的新闻自由度实际比抗战时期还要小,“国民党对新闻的管制变本加厉,内容审查更加严格,言论追惩极为频繁,暴力事件不断出现,舆论环境恐怖森然。”[6](P279-280)诸多进步报纸如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联合日报》《建国日报》以及民主人士主办的《民主报》《民主》《文汇报》等出版不久及遭查封和停刊。国民党严酷的新闻出版统制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呼声在战后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国民党被迫废止在国统区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国民政府对新闻出版事业的些许让步,文化界出现了较为宽松的新闻舆论环境。在国共政治谈判期间,和平民主运动日趋高涨,引发了数量庞大的民主系列报刊。但国民党并未真正放弃其一贯的新闻统制政策,以“李闻惨案”为例,说明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仍然是残酷的。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国民党在加紧军事行动的同时,严格控制社会舆论,强化新闻统制。先后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戒严法》《出版法修正草案》《动员戡乱期间军事新闻采访发布办法》,企图垄断新闻的报道权力,封锁不利于其统治的新闻消息,放大符合自身需要的新闻消息,如对宋埠事件、长春围困事件的大肆报道,而对不同意见的民盟等党派实行严厉的新闻管制。军事上的节节溃败、经济上的通货膨胀、金圆券货币改革的破产等等,导致国民政府的信用降到最低,反映国民政府观点的《中央日报》在上海几乎无人相信,多数中立媒体此时也对国民党政府不再持同情态度,如倡导“第三条道路”的《观察》主张“中间路线”的《大公报》最终都与蒋介石集团分道扬镳。傅斯年在《世纪评论》《大公报》《观察》连续撰文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以言论呼吁他下台。《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发表不过半月,宋子文继傅斯年抨击孔祥熙之后被迫辞职,这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以言论罢免政府首脑的重要例子。如傅斯年所言:“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7](P334)政治上、经济上的崩溃,导致此时的国民政府,对新闻界的管制实际上已处于失控状态。
结论
在对民国时期新闻管制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在国内多股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的时期,新闻自由度反而要高于政治力量缺乏异己势力制约的统一时期。因此,从总体上讲,在军阀混战的北洋时期,新闻自由度要远高于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时期。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复杂的国民政府前期,新闻自由度要高于蒋系一系独大的国民政府中后期。在国内非主流异己派系较多的抗日战争前期,新闻自由度要高于整合了非主流异己派系的抗战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威权政府,而威权政府的新闻自由度是和威权政府受异己势力制约程度成反比的。此外,民国时期政府的权威统治与近代报人的政治参与热情形成了矛盾与冲突。新闻出版自由本质上有助于权威政治的建立,专制独裁统治某种程度上与新闻出版自由形成了内在的矛盾。
[1]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 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3]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5]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6] 杜宝花.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新闻管制与民众的反抗[J].中州学刊,2010,(5).
[7] 傅斯年.傅斯年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