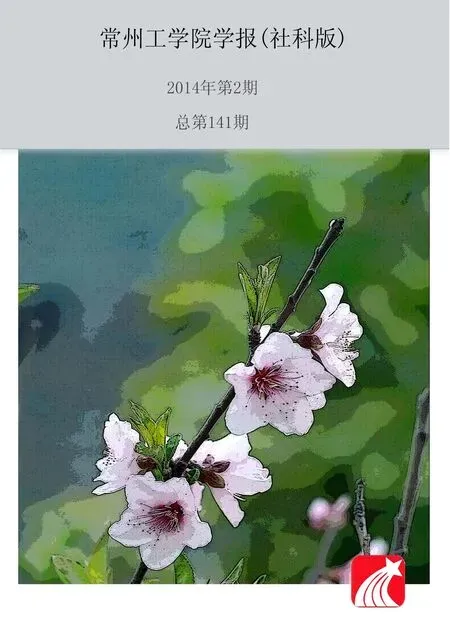反抗与僭越
——论陈雪小说的女同书写
2014-03-29石松华
石松华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反抗与僭越
——论陈雪小说的女同书写
石松华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陈雪是台湾著名的女性作家,其创作目的主要为同性恋者尤其是女同性恋者立言,在其前期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女同性恋者的成长经历和人生体验。陈雪的《恶女书》《蝴蝶》《爱情酒店》是典型的女同文本,主要从对传统性别观念的颠覆、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对传统同性恋观念的突破等三个方面,展现了其反抗和僭越传统的书写姿态及反叛精神。
陈雪;女同书写;反叛精神
陈雪原名陈雅玲,1970年6月3日生于台湾台中,1993年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是台湾著名的、极具才华的女作家。其创作题材多样,风格独特,其中同性恋题材尤其是女同性恋题材的书写在其创作历程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恶女书》《蝴蝶》《鬼手》等,长篇小说《恶魔的女儿》《爱情酒店》《桥上的孩子》《陈春天》《无人知晓的我》《附魔者》,及散文《天使热爱的生活》等。《恶女书》收录《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夜的迷宫》《异色之屋》《猫死了之后》四部短篇小说,堪称其女同书写的代表之作,于1995年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华文女同志小说的经典。《蝴蝶》收录《蝴蝶的记号》《色情天使》《梦游1994》等三部短篇小说,其中《蝴蝶的记号》由香港导演麦婉欣改编拍摄成电影《蝴蝶》,曾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同时被选为“2004年香港同志影展”开幕片。陈雪在小说中主要书写女同志的成长、生活、命运轨迹,表达她对台湾同志运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她的同志题材的创作实践对传统观念进行了挑战,展现出一种鲜明的反叛与僭越的书写姿态。
一、对传统性别观念的挑战
在传统的性别研究中,有三个主要概念: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欲取向,它们主要以两种对应形式存在:生理性别——男/女、社会性别——阳刚特质/阴柔特质、性欲取向——异性恋/同性恋[1]。在异性恋为主体的社会中,具有阳刚气质的男性和具有阴柔特质的女性之间产生异性恋才会被认可。这种二元对立的性别/性欲规则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被视为社会的常态。而陈雪以其超越常规的书写姿态彻底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的对应关系,颠覆了传统的性别论。这种颠覆在其女同志题材的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表现之一即对男女形象的塑造上。
陈雪塑造了一系列俊美的非传统的女性形象。《爱情酒店》中英俊潇洒的“阿青”是妈妈酒吧里的酒保,初见阿青时,作者用这样的文字描述她:“削瘦的脸白皙而透明,忧伤的神情迷离的眼神,单薄的身体在宽大柔软的白上衣白长裤底下随着手臂的晃动起伏……俊美得令我几乎尿湿了裤子”,“嘴角叼着燃烧的香烟,烟雾弥漫了她的脸”,“光是潇洒帅气不足以形容,除了俊美斯文还有更多”[2]50-51。通过陈雪的描述,我们似乎很难用传统意义上温柔可人的“美女”来形容和概括阿青的俊美,在阿青身上更多体现的是男性的帅气与魅力,虽然多少缺了些阳刚之气,却更符合我们对古代白面书生的想象。在烟雾缭绕之中,我们感受到的是阿青如男子一般的忧郁、冷漠和放荡不羁。除了那一头乌黑的长发,从阿青身上我们感受不到任何女性该有的阴柔气质。
其次,在小说中陈雪也塑造了许多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形象。最典型的莫过于《爱情酒店》中的黑社会组织头目“黑豹”。黑豹,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有着花岗岩一样的皮肤,身形高大壮硕,是“用他强壮的肉体去冲撞生命发出火光的人”[2]43,可在这样强壮的、极具男性特征的外表之下是一颗有着传统女性气质的无比柔软的心灵。他会在宝儿床前哭泣,像小孩子一般,有着如母亲一般温暖的怀抱,他像母亲一般容忍和包容着身边所有人的放肆、撒野和无理取闹,还会为宝儿一针一线地缝紫色碎花窗帘……这也绝非是传统意义上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
此外,八面玲珑、可男可女的“妈妈”,一心想做变性手术的设计师“桥”,通过爱“我”而爱着黑豹的“小五”,性别上是女人、长相举止都像社会定义中的男人的“阿猫”……这些行走在性别模糊的灰色地带的人,无不僭越或颠覆了传统的性别想象。在陈雪的作品中,我们很难归纳出具体的男女形象,用男性或者女性来定义其人物性别。作品展现的更多的是性别不明,非男非女的形象。在行文之间,陈雪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一种社会性别是“真正的”,社会性别也没有绝对的男性与女性的划分,也许模糊的性别才是人真正意义上的性别。
二、对异性恋霸权的挑战
陈雪作为极具反叛精神的女作家,其反叛传统的精神不仅表现在颠覆传统性别观念方面,更重要的表现为对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异性恋霸权的挑战。在性价值等级制度中,性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和等级,其中“异性恋的、婚内的、一夫一妻的、生殖性的和非商业性的”,“一对伴侣之间、一代人之间、家里”的性实践才是“美好的”“正常的”“自然的”,它们占据最高层。而那些性行为或者性恋模式超越常规的则处于最底层,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非法的”“应惩治的”。在传统男权异性恋体制中,“男—女—异性恋”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性恋模式。异性恋模式占据着性体系的统治地位,然而“性就像性别一样,也是政治的,他被组织在权力体系之中,这个体系奖赏和鼓励一些个人及行为,惩罚和压制另一些个人和行为”[3]68。因此,在异性恋霸权的统治之下,一切不符合常规的性恋方式都将受到压制、排挤甚至毁灭。人们长期生活在异性恋体制的监控之下,很少质疑这个体制本身是否公平。作为为数不多的对异性恋体制进行反思的作家之一,陈雪用其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触描写了一系列在异性恋霸权之下喘息甚至遭毁灭的生灵,大胆地质疑和否定异性恋体制的权威性。
首先,陈雪对异性恋是美好的提出质疑。《蝴蝶的记号》中,妈妈和爸爸表面上是一对和谐幸福的令人嫉妒的夫妻,实际上夫妻之间却充满着欺骗、虚伪和背叛。爸爸背着妈妈偷偷和“阿姨”们约会,而妈妈在怀疑、猜忌的折磨下几次曾拉着“我”去投海自尽。而“我”在家庭和社会的重压之下,被迫离弃同女“真真”,和开店的阿明堕入寻常婚姻。然而,“我”和阿明看似美满幸福的婚姻背后,只是在用我“难以言喻的痛苦”和行尸走肉般的躯体维持着阿明渴望已久的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梦想。最后,无论爸爸、妈妈,还是“我”和阿明,都不免走向离婚的结局。除此之外,在陈雪其他作品中,一如《色情天使》中“我”和牙科医生,《爱情酒店》中宝儿和阿豹,《夜的迷宫》中“我”与丈夫阿丁……更把异性恋体制之内的爱欲完全转变成了发泄肉体欲望的工具。主人公没有在异性恋婚姻或“爱情”中找到幸福和归属感,这至少证明了异性恋不是性实践唯一的最完美的形式。
其次,陈雪大胆展现异性恋霸权对人以及人性的压制和毁灭。在《猫死了之后》中,主人公“我”在父权异性恋霸权控制下的家庭、社会、教育之下,被灌输以同性恋是非正常的、病态的思想。因此,在面对同女阿猫炽热的感情时“紧张的想逃跑”“总觉得害怕”。“面对阿猫炽热的情爱和模糊的性别,我简直束手无策,我甚至无法处理自己对她萌生的热情和性欲,只觉得好羞耻……”[4]这种“害怕”和羞耻最终导致了“我”对阿猫的逃离。然而同女在逃离同性情谊之后,不但没有在异性恋的天空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反而变成了折翼的天使,失掉原有的灵魂,只能“践踏自己、践踏一切回忆”,“空洞地在世界上飘来荡去”。而阿猫一类,以扮演男人的方式否定自己身为女人的事实,企图符合男权异性恋的规范,又何尝不是父权异性恋霸权压抑、扭曲人性的一种表现方式?在《蝴蝶的记号》中,异性恋霸权更展示了它不可僭越的权威。高中生心眉和武皓因为“怪怪的”,“好像是同性恋”而被社会、学校、家庭视为“坏孩子”,被同学“指指点点”。终于在“私奔”未遂之后被强制分开,最后导致武皓在被送出国的前一天自杀,心眉精神失常被关在家里的仓库。本是两朵娇艳的花朵,因为纯洁的同性情谊而走向毁灭,这无疑是对异性恋霸权的强烈否定和控诉。诚然,千百年来,异性恋模式长期占据着性体系的主体地位,定有其得以存在的合理之处。在此,陈雪也无意否定一切处于异性恋模式之下的婚姻和爱情,只是希冀在异性恋霸权笼罩的天空之下,为现存的其他性恋方式求得一席之地。
陈雪对异性恋霸权挑战的另一方面则表现在用大胆的笔触展示同女被压抑的欲望。在父权异性恋霸权法则之中,女性的情欲遭到压抑,身体遭到禁闭。女性不能主动要求,只能被给予,拥有欲望是一种罪恶,而女同的欲望则更被视为天地之大忌。千百年来,那些有同女情谊的女人们,只能在教育、家庭、社会的重重包围、封锁与压迫之下“安分”地走进婚姻,“一生都在做违背自己的事”,像小蝶一样,将自己训练成行尸走肉般的“什么都似乎感觉不到的人”并以“错觉”来解释自己对女人的欲望。然而,同女的欲望却像蠢蠢欲动的岩浆,压抑得越久,积攒的爆发的愿望也就越强烈,一旦爆发就是惊天动地的力量。
陈雪的代表作《恶女书》以惊世骇俗的笔触大胆书写同女们间的欲望。“灰绿蚊帐顶端冒出一缕黄烟雾向上飞升,屋内充满甜腻的味道让蟑螂疯狂起舞,孩子听见兽类撕咬的追逐的叫嚣,听见蜻蜓扑扑鼓翅,听见猫儿痛苦狂喜的呼喊,沿着昏黄夜灯的照射,蚊帐底下两条人影变得好巨大,彼此纠缠、翻滚、碰撞,在孩子眼中蜷曲交叠幻化……”[5]“她那足以切割人的声音让我无法承受,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叫出来,满心盼望着妖兽般的女人快点将我撕扯下腹”[[6]。这近乎野兽般的呼喊,或许如其他评论者所说尽是秽物、垃圾、不堪入目,但那是千万同女的心,是重压在火山之下的欲望。惟有这欲望才能让同女们逃离异性恋的枷锁,让“已经死寂的疯狂因子又重新跳动在我的肠胃心肺里”。陈雪不仅大胆展露女同们的欲望,而且还赋予这欲望以拯救同女们死寂灵魂的力量。通过释放同女情欲实现同女们的自我救赎,这无疑是对父权异性恋霸权彻底的反抗和颠覆。
三、对传统同性恋书写规范的突破
异性恋模式作为一种社会常态,长期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同性恋文化虽然溢出了异性恋的轨道,却也不免受到前者的深厚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台湾的同性恋小说中存在着大量同性恋对异性恋复制的现象,“在挑战异性恋模式的同时,模拟了异性恋的身份认同”,最主要的表现即“T/婆”含有异性恋角色的划分。“T的角色常常以异性恋模式中的男性身体再现,婆则复制传统视野中女性的身体气质,只不过身体的情欲发生了转变”,“而被书写的身体依然为二元对立的性身份认同限制”[7]。如果说同性恋模式是对异性恋模式的反叛与突破,这种潜在的复制异性恋现象却体现了同性恋对传统二元对立的性身份认同的限制以及企图突破性别认同的困境。这种现象在90年代“酷儿理论”登陆台湾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较于纪大伟、洪凌等人的同性恋书写,陈雪作为“酷儿理论”的实践者,在其一系列女同题材的文本中,通过对性身份的越界描写和对情欲的肯定实现了对传统同性恋书写规范的突破。
在陈雪女同题材的作品中,她尤其擅长展现身体和欲望的互相穿梭与交织。身体通过情欲的流动呈现出不同的表演形态,因情欲对象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性身份之间转换。《爱情酒店》中“我”同时可以在阿豹和阿青之间流转。和阿豹在一起时“我”是一个犹如天使一样的女孩,安然接受阿豹如父亲一般浓烈的关爱,扮演着“婆”的性身份。而在阿青面前,“我”又是一个主动出击的“T”的角色,渴望温暖和治愈阿青受伤而冰冷的心灵。因此,“我”的性身份完全取决于“我”所欲望的对象。“妈妈”更是如此,“她这人忽男忽女,可男可女,从小我也已经习惯她经常是不同性别的打扮……妈妈不是在舞厅就是在酒店上班,上班的时候打扮得妖娆美丽在那儿跟男人打情骂俏,下了班回家就变成英俊潇洒的俏公子跟她的女朋友在客厅里搂搂抱抱。”[2]17在此,情欲将身体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性身份中解放出来,使身份具有表演的性质,打破了性和性别身份一一对应的关系。
传统同性恋书写对情欲的描写多指向自我性身份的认同,在辨别自身情欲对象的基础之上把自身定位到T或者婆的性角色之上。而陈雪却把情欲书写成一种个体取得生命认同、证明自我存在的方式。《蝴蝶的记号》中“我”——那具背负着“好女儿”“好妻子”“好老师”等各种身份的如行尸走肉一般的躯体——在真真的爱抚中“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似的,充满了惊喜,我也从她身上看见真正的美丽”。情欲的力量使“我”就此得到重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命。《异色之屋》中陶陶“唤醒我形容枯槁的灵魂”,《色情天使》中在哥哥死后,“我”放纵情欲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证明自身的存在。《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中“我”通过欲望阿苏实现对恋母的确认……因此,在陈雪笔下,情欲并不是生理欲望的简单释放,也不指向性身份的认同,而是指向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确认。诚然,陈雪如此大胆地书写流动多变的情欲,绝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为了跟上时代的风,而是借由着流动的不可归类的情欲,反抗已然定型的不可逾越的传统。
作为才华横溢、风格独特的女作家,陈雪用大胆而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女同世界,其僭越传统的反叛姿态也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在其作品中,除了蕴含着上述几种意蕴之外还包含着许多可以探讨的议题,如女同的身份认同、女同身份与母职、家庭问题、精神疾病等等,这些议题都具有多重解读的意义。笔者从反抗与僭越传统的角度解读陈雪的女同书写,试图抛砖引玉,为研究陈雪的学者们提供一点借鉴,以期有更多的学者从更多的角度挖掘和解读陈雪作品中蕴含的丰富意义和独特价值。
[1]艾尤.变幻与越界:当代台湾女性小说性别与情欲的多元展演[J].文艺争鸣,2012(3):138-141.
[2]陈雪.爱情酒店[M].台北:麦田出版,2002.
[3][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M].李银河,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68.
[4]陈雪.猫死了之后[M]//恶女书.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192.
[5]陈雪.异色之屋[M]//恶女书.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67.
[6]陈雪.夜的迷宫[M]//恶女书.新北: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2005:112.
[7]朱云霞.试论台湾酷儿小说的身体叙事及跨文类实践:以纪大伟、陈雪、洪凌的酷儿文本为例[J].台湾研究集刊,2012(2): 78-85.
责任编辑:庄亚华
I106
A
1673-0887(2014)02-0014-04
2014-03-04
石松华(1988—),女,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