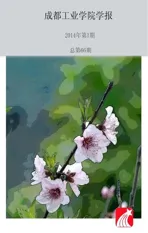古蜀语音发展散论
2014-03-29汪启明
汪启明*
(西南交通大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成都 611756)
一、语音即方音
西方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共同语与方言的概念,并指出,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现代汉语教学体系也沿用了这一体系和术语①。但是学术界对什么是共同语,什么是方言,意见尚未统一。②古代汉语更是如此。鲁国尧曾详细地讨论过古代汉语中“方言”的含义。他指出,在19世纪以前(含19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方言”即语言,无所谓外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之分。“在现代汉语里,‘方言’词义缩小了。‘方言’既是各方的语言,一个地方的语言也是‘方言’了”。自东汉近千年来,“方言”一词的含义“并不单纯”,而目前掌握的用例也还“不足以确定他在各个时期的意义,也难以推阐他的演变史”。③这样的观点很精辟。
古代的方言即语言,古代的方音亦即语音,反之也成立。今天的方言与共同语(或叫标准语)与历史上的“方言”完全不同。不能以今律古,将今天才有的种种概念,如共同语、地域分支、标准语等等,强加于古代的语言及其发展现象。与此相应,古代语音也可做如是解。
张琨说:“在中国的历史上,不同的方言曾在不同的时期里占有标准语的地位,在描写汉语音韵史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随着政治及文化中心的转移,标准语的基础也由一个方言突然换成另一个方言。”④林语堂以文字为例,持有同样意见:“汉字的读音其初每每实只是方音之读法而已,后来因为‘经学家’之注释,乃成为普通读音,若‘傩’读为‘娜’(鲁卫音),‘洧’读如‘鲔’(郑音),我们因为不细究古方音之差别,故不明其原委。”⑤张琨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所谓“标准语”,认为是方言;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并非一成不变。林语堂则从源头上论证,汉字初始读音即方音,与之相对的是读书音而并非共同语音。现代语言学理论又认为,任何共同语都是在某一个优势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本质上也是一种方言。赵元任说:“在学术上讲,标准语也是方言,普通所谓的方言也是方言,标准语也是方言的一种。”⑥
针对汉语,胡适认为:“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⑦沈兼士批评过把古代语言看成大一统的偏见:“盖诸家之所谓古者,统三代秦汉之总称:或以三百篇为本,等而下之,摄及秦汉音,无不同也;或以《广韵》二百六韵为本,等而上之,摄及三代音,无不同也。虽其考订排比,部类秩如,要皆以一地概四方,以一时概千古,汗漫支离之病又焉能免?”⑧胡适说,国语即方言;沈兼士说不能把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的汉语语音看作统一且不变的整体。就现代而言,方言、共同语是对立统一的,没有方言也就无所谓共同语。现代汉语共同语是以汉民族所使用的某种方言(北方方言)为基础,以某一个地点方言的语音(北京音)为标准音的。而在远古时期,方言与语言同时产生,雅言的历史较之方言的历史短得多。在不同的时代都存在过优势方言,比如我国先秦时期便有各种地区方言,而文化较高的齐语、楚语是势力最大的方言;秦汉时期,古蜀语和秦晋语一道,成为汉语地位较高的优势方言。虽然有所谓“通语”“凡语”“凡通语”,但它也是以秦晋地区(今陕西山西一带)的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共同语音的基础是北方方音;例之古代,不仅雅言即方言,所谓“雅音”也应该以某一种方音为基础,只是使用人口较多、使用场合较为正式的方音,而不能理解为共同语音的地方变体,这是应该强调的。
二、古蜀语音的发展与规律
1931年,德国著名学者哥德尔(Kurt)提出了“不完备定理”,他和塔斯基(Tashchi)的形式语言的真理论及图灵机(Turing Machine)和判定问题的理论,已被国际逻辑界赞誉为现代逻辑的三大成果。其精髓是:真与可证是两个概念。可证的一定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可证。转换为本文的论题,即我们确认的蜀语,应该不在量上,而在质上。提出的蜀语语音现象,一定要有充分的文献证明,以证其“真”。诚然,目前蜀语语音还有很多未解之迷,我们还不能科学地证明其形成、发展及规律。
在秦汉以后的几百年间,蜀人的语音与北方语音发展道路不尽相同。在听觉上也能让蜀语区以外的人感觉出来。这里有这样两条材料:
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谏官欧阳修言:伏见差孙抃等使契丹,臣谓朝廷新遭契丹侮慢凌辱之后,必能发愤,每事挂心,凡在机宜,合审措置。及见抃等被选,乃知忘忽虑患,依旧因循,今西贼议和,事连契丹,中间屡牒边郡,来问西事了与未了。今专使到彼,必先问及,应对之间,动关利害,一言苟失,为患非轻。岂可令抃先往!抃夲蜀人,语音讹谬。又其为性静默自安,军国之谋未尝与议,凡关机事,多不谙详。”⑨
2)范成大《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耳畔逢人无鲁语,鬓边随我是吴霜”下自注:“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虏语。或是僣伪时以中国自居,循习至今不改也。既又讳之,改作鲁语,尤可笑。”⑩
按:这两条材料均出自北宋时期,并共同提到古代四川方言难以让外地人理解和听懂。欧阳修(1007—1072年)所言“抃本蜀人,语音讹谬”应该是以文学语言为标准的,根据他所在的年代可知,他所评价的蜀人语音,当为中上古时期的蜀音。《范石湖集》作者范成大(1126—1193年),宋吴郡(郡治在今江苏吴县)人,较欧阳修稍晚,曾在蜀地做官,是诗题记:“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旙,以禳兵火之灾。”《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全诗是:“岭梅蜀柳笑人忙,岁岁椒盘各异方。耳畔逢人无鲁语,鬓边随我是吴霜。新年后饮屠苏酒,故事先然窣堵香。石笋新街好行乐,与民同处且逢场。”可见是实地调查,足证其对蜀地蜀人的语音非常了解。范成大之诗,宋代袁说友《成都文类》卷九、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百三、《佩文韵府》卷三十六均有记载。范成大之诗所提及的蜀人语音,是指宋初以前的蜀语语音,去唐五代不远,亦可以看作中上古时期蜀语特色。验以文献,黄震《黄氏日抄》卷六十七“读文集”:“蜀音难晓,反以京洛音为虏语。或是僣伪时以中国自居也。既又讳之,改曰鲁语。见《安福寺礼塔》诗注。”说明宋初以前蜀人用“鲁语”一词,以称中原语音。范成大又有《送同年朱师古》诗:“遥知梦境尚京尘,哑咤满船闻鲁语。”自注:“蜀人以中原语音为鲁语。”宋普济《五灯会元》:“师给侍之久,祖钟爱之,后辞西归,为小参。复以颂送曰:‘离乡四十余年,一时忘却蜀语。禅人回到成都,切须记取鲁语。’”宋代释晓莹《罗湖野録》卷三、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九、卷一百三载同。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车上看《范石湖诗抄》,有二事足记:(1)《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诗》自注云:‘蜀人乡音极难解,其为京洛音,辄谓之鲁语。’此可见宋时四川土音必与今日大异,今则蜀音为全国最易解的音了。”⑪据胡适说“今则蜀音为全国最易解的音了”,可推知宋代以前的蜀音与中原语音有较大的差别,元明以后,尤其是经过几次大移民,发展到现代则已融成一体。诗中除“鲁语”一词外,“逢场”一语,至今仍是活跃在四川方言中的成分。
宋时蜀人称中原人为“虏”,还有其他的证据,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有这样的记载:“南朝谓北人曰‘伧父’,或谓之‘虏父’。南齐王洪轨,上谷人,事齐高帝,为青冀二州剌史,励清节,州人呼为‘虏父使君’。今蜀人谓中原人为‘虏子’,东坡诗‘久客厌虏馔’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为‘虏官’。晁子止为三荣守,民有讼资官县尉者,曰:‘县尉虏官,不通民情。’子止为穷治之,果负冤。民既得直,拜谢而去。子止笑谕之曰:‘我亦虏官也,汝勿谓虏官不通民情。’闻者皆笑。”⑫蜀人称北人为“虏子”“虏官”,其语为虏语,又为鲁语。这只能出现在蜀地割据时期。
从上述可知,在中上古时期,蜀语语音并非一直都由“别”到“同”,直线发展的。如欧阳修所言,虽然也有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寻找一个并不充分理由,但蜀语在听觉上外地人不易懂则是一定的。从范成大的两诗自注来看,蜀人将北方方言称为“虏语”,又称为“鲁语”,既说明了蜀地方音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封闭式发展,与汉语其他方言并不同步,也说明它在某一段时期内具有存前代音的特性。
中上古蜀语发展过程中既的某些变化具有有规律性的特征。“四方之音有讹者,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秦人讹‘青’字,则谓‘青’为‘萋’,谓‘经’为‘稽’;蜀人讹‘登’字,则一韵皆合口;吴人讹‘鱼’字,则一韵皆开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然谓‘絃’为‘玄’、谓‘玄’为‘絃’,谓‘犬’为‘遣’、谓‘遣’为‘犬’之类,亦自不少。”⑬陆游曾说“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可见这段文字是以洛阳音为基准音的。陆游指出蜀人在当时将“登”这个开口韵的全部字都读成了合口。登,都滕切,端母登韵,开口一等,曾摄,董同龢拟 [- ə ŋ],合口读[-uə ŋ]。陆游一句“他放此”,说明这是规律性的现象而非小概率事件。
三、古蜀语音与中原语音的一致性
古蜀语作为汉语的一支方言,虽然语音上有自己的特色,但不是说蜀语语音与文学语言语音之间完全不能通话,它们有很强的一致性。
1)《抱樸子·卷九·道意》:“或问:李氏之道起于何时。余答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传世见之,号为八百岁公。人往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颜色欣然,则事皆吉;若颜容惨戚,则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则有大庆;若微叹者,即有深忧。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后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后有一人姓李名宽,到吴而蜀语,能祝水治病颇愈,于是远近翕然,谓宽为李阿,因共呼之为李八百,而实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而升堂入室高业先进者,不过得祝水及三部符导引日月行气而已……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⑭
按:李八百事,《晋书·周扎传》、号称“宋代百科全书”的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三十、明代彭大翼、张幼学所编类书《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有引,文字略有不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著录:“《锦绣万花谷》四十卷,续四十卷。”未著作者。这些材料的来源都应该是《抱朴子》一书,书为东晋葛洪所撰,后此的文献文字有详有略。《云笈七签》卷二十八《二十四治》曾记李阿在平冈治修道,其“下八品”第五平冈治注:“山在蜀州新津县,去成都一百里,昔蜀郡人李阿于此山学道得仙,白日升天。”
葛洪《神仙传》分李八百、李阿为二人,人各为传,表明葛洪认定他们为二人,前者为李八百,后者李阿之号“八百岁公”,实为李阿对“李八百”的假托。这条材料提供了这样的信息:1)东汉末三国时期,蜀语有自身的特点,李宽“到吴而蜀语”,让被传道的人们能明显地感到蜀语和吴语有区别。2)蜀语并非不能听懂的汉语方言,吴蜀语之间可以进行交流,甚至可以用蜀语进行教学。“自公卿以下,莫不云集其门”,“依宽为弟子恒近千人”,显然这些弟子又不全系蜀人,而是当地人为主。3)葛洪《抱朴子》又说“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这里“千许”没有说明占籍,但可推知李宽的再传弟子应多为吴人或南迁的“北人”。
2)《容斋随笔》卷七:“王观国彦宾、吴棫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它未有明证。’予案《杨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憔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⑮
按:这条材料说明在先秦两汉时期,蜀人扬雄的韵文中,阳部与耕部读音相近。王显曾著有《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一文,⑯说道:“古韵阳部包括《切韵》的阳唐两个韵系的字,还有一部分庚韵系字。”在三等开口,便举了有“庆”字,在“扬雄”目下,未列《容斋随笔》所举的例子,另列有《元后诔》例“王明荒庆央”,《童》:“庆明”,又“庆伤”。《盛》:“光疆庆”,《居》:“庆疆享庄臧长”。“庆”字与阳部相者,不限于蜀地,下面这些例子皆可佐证:司马迁《天官书》:“行庆方昌亡”;《易林·否之豫》:“享庆”;《噬嗑之屯》:“光庆”;《晋之艮》:“祥庆”;《明夷之睽》:“羊庆”;《明夷之损》:“当庆”;《夬之损》:“行明庆”;《渐之大壮》:“光庆”;《巽之夬》:“惶伤庆”;《小过》:“惶庆”。从这样一些例子来看,除蜀语将把“庆”“羌”放在一起相押外,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情况,说明蜀音、中原音之间的一致性。
四、古蜀语音与中原语音的差异性
蜀语和与中原语音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别性。例如《太平广记》卷第93“宣律师”记载,大唐乾封二年春二月,西明寺道律师逐静在京师城南故净业寺修道。“律师积德高远,抱素日久”,这时忽然有一人来至律师所,致敬申礼,自称为吴人,叫王璠。“不久复有人来,云姓罗氏,是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用忽忘。”这段材料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释道世所撰《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载文字相同。《大藏经》第五十二册载《道宣律师感通录》:“会师初至建邺。孙主即来许之。合感稀有之瑞。为立非常之庙。于时天地神祇咸加灵被。于三七日遂感舍利。吴主手执铜瓶写铜盘内。……且令弟子等共师。言散不久复有天来云。姓罗氏。蜀人也。言作蜀音。广说律相。初相见时如俗礼仪。叙述缘由多有次第。遂有忽忘。”
按:文又载《中华大藏经·律相感通传》的《道宣律师感通录》,是书为唐代乾封二年终南山沙门释道宣所撰。道宣(596—667年),唐代僧人。律宗创始人,俗姓钱。原籍丹徒(今属江苏),一说长城(治所在今浙江长兴),20岁即入长安大禅定寺从智首律师受具足戒,并随之学律10年。他应该既懂吴语,又懂秦语。这说明,唐时蜀语和吴语、蜀语和秦语在语音上有着显著不同。“乾封二年”(666年)是唐高宗年号,这时距秦灭巴蜀时的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已经过去了近千年。
五、中上古蜀语语音的内部差异
蜀语语音发展不是全蜀各地都一致,前代文献记载了蜀语区域中部分地方的读音分歧。
《老学庵笔记》卷二:“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独’,故鲁直得借用,亦因戏之耳。”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八:“至于五方音异,自古已然,不能谓之不协,亦不能执以为例。黄庭坚词用蜀音,以‘笛’韵‘竹’。《林外词》用闽音,以‘扫’韵‘锁’。是可据为典要,谓宋韵尽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数叶,亦如今韵一字而重音。‘佳’字‘佳’、‘麻’并收,‘寅’字‘支’、‘真’并见,是即其例。使非韵书俱在,亦将执其别音攻今韵之部分乎?盖古音本无成书,不过后人参互比校,择其相通之多者,区为界限。犹之九州岛列国,今但能约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犬牙相错之形。(蒋)骥不究同异之由,但执一二小节,遽欲变乱其大纲,亦非通论。以其引证浩博中亦间有可采者,故仍从原本,与《余论》并附录焉。”
按: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省试第一名,先后在河南、河北、江西、山东做官。绍圣元年(1094年)十二月,黄庭坚被贬为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县)别驾、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县)安置。黔州四年,寓居开元寺摩围阁。绍圣四年(1097年)十二月,朝廷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在州南的一个僧寺居住3年。他在四川做官的时间为7年。《老学庵笔记》提及的《念奴娇》词写于绍圣元年(1094年)谪居地处西南的戎州时。此时距五代不远,地处偏僻,蜀音当变化不大,可以作为中上古蜀语材料。独,定母,屋韵,开口一等,通摄;笛,定母,锡韵,开口四等,梗摄;竹,知母,屋韵,开口三等,通摄;屋韵读[-juk],锡韵读[-iuek]。独、笛、竹三字均为入声。屋韵读[-juk],锡韵读[-iuek]⑱说明中上古蜀语中部分地方有锡音读成屋韵的情况。陆游居蜀,刚听到这种读音,怀疑“笛”字不入韵,时间久了才知道,蜀地有的地方读音与他所居的蜀中地域有所不同。这表明了蜀语内部的语音分歧。
六、人名、地名中的古蜀音
中国自古以来即有所谓“名从主人”的说法。在对蜀语语音和词汇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人名和地名中保留的蜀语语音特色。
1)《古今图书集成》氏族典第三百六十六卷录郑樵《通志》:“镡氏音寻,又音淫,望,出广汉。今蜀中有此姓,乃呼为蟾,蜀音之讹也。”蟾,禅母盐韵,淫,喻母侵韵,寻,邪母侵韵。盐韵是开口三等,属咸摄,读[-jæm],侵韵也是开口三等,读[-jem]属深摄。《新修潼川府志》卷十九:“《氏族略》:‘镡望出广汉,今蜀中有此姓,乃呼为“蟾”,蜀音之讹也。’按:后蜀陈宠为广汉太守,主簿镡显,郪人。李贤注:镡,徒南反。蜀汉有太守谭承,亦郪人,今人又读镡为寻,与章怀太子读异。”⑲这说明蜀人把闭口韵[-m]的两个韵混读,当然,他是不是中上古时期蜀音的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宋孙奕《示儿编》卷二十二:“杨文公《谈苑》云: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宋代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六十一:“今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汉雍齿、唐雍陶皆是也。蜀中作上声、去声呼之。盖蜀人率以平为去。(出《笔谈》)”宋代孔平仲著有《谈苑》《杨文公谈苑》,《郡斋读书志》著录八卷,《直斋书录解题》作十五卷。此书明代尚存,大约明清之间散佚,今有《说郛》辑文。杨文公,杨亿(974—1020年),字大年,浦城(今属福建)人。距唐不远,所言可信。所谓“名从主人”,语音变化不会太大,说明这种“以平读去”是一种中上古蜀语的普遍现象,与陆法言《切韵》“梁益则平声似去”相吻合。
3)光绪新修《潼川府志》卷第二十九“射洪”条下:“《蜀典》:‘李吉甫《元和志》:“蜀人谓水口为洪。”按《益州记》:“娄偻滩东六里有射江,魏因置县。土人讹江为洪,后周从俗改县为射洪云。”《寰宇记》引李膺《蜀记》云:“郪江滩东六里有射江,土人语,讹以江为洪。”又与李宏宪说异。盖古人为石梁绝水,水激而洪大,如吕梁洪、鸡翘洪、落马洪皆是也。’”⑳
按:苏子瞻诗集,亦有百步洪题目,洪字取义,当以洪大为近。江,古双切,见母,江韵开口,读[kɔŋ],洪,户公切,匣母,东韵合口,诚[ɣuŋ]。李吉甫(758—814年),中唐赵郡人,所录文献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这条材料说明,中上古时期在蜀地有些地方,把江韵开口误为合口。
4)还有一些人名、地名的读音肇自远古,如明代杨慎《升庵集》卷六十四“涂字音”:“涂字从余,余有三音。一音余剩之余,又音蛇。今人姓有余氏,即余之转注。而俗书从入从示作畲,乃小儿强作解事也。一音賖,故畬字从余,可证也。东方朔传老拍涂解曰:涂者渐洳径也。柳子厚诗:‘善幻迷冰火,齐谐笑拍涂。’叶入麻韵。又雨多涂,则滑而颠得其音矣。李义山《蜀尔雅》云:《禹贡》:‘厥土惟涂泥。’《夏小正》:‘寒日涤冻涂。’二‘涂’字音在巴荼之间,盖禹本蜀人,故涂泥、冻涂皆叶蜀音。今蜀人目濡土曰涂泥,肉烂曰涂肉。盖禹时已有此音,蜀之土音亦古矣。”
前人对蜀语音的感受,往往以后代的蜀语音来说前代的蜀语音。例如宋代末方回的《桐江续集》卷三十一《送汪复之归小桃源序》:“惟魏公之文有佳者,三十二章:苣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乃蜀人押韵也。六十七章:植麦欲获黍,运圆欲求方,竭力劳精神,终年不见功。七十章:广求名药,与道乖殊。七十三章:牝鸡自卵,其雏不全。语意皆佳。用韵皆蜀音。”这段文字中的4个韵段,均来自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从时代上说,如果是方回说的蜀音,是魏伯阳的用韵,那么这正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语音,如果不是中上古时期的蜀语语音,而是宋代蜀语语音,以今之音律古之文献。则不可作为中上古时期蜀语的材料。分别来看:口,溪母侯部;朽,晓母幽部;宝,帮母幽部。方帮母阳部,功,见母东部。药,喻母药部;殊,禅母侯部;卵,来母元部;全,从母元部。侯、幽相押,药、侯相押不是蜀汉方音特点。
注释:
①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民族共同语……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内部一致,……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统一的形式,也叫做文学语言,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内容是无限丰富的,对方言有无比的约束力,自身在一定意义上是超方言的。”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6页。
②曾毅平《略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学术研究,1997年4期,70页。
③鲁国尧《“方言”和〈方言〉》《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8页。
④张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张贤豹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8月,62页。
⑤林语堂《前汉方音区域考》,《语言学论丛》,上海书店,1990年,20页。
⑥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101页。
⑦胡适《吴歌甲集·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74页。
⑧沈兼士《魏建功古音系研究·序》,中华书局,1996年,11页。
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3418页。
⑩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232页。
⑪胡适《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三册,112页。
⑫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119页。
⑬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77页。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四川方言》讨论了11种四川方音的特点,其中说“登字一韵皆合口—开合口相混”,《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2期,38页。
⑭晋·葛洪《抱朴子内篇》,王明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174页。
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羌庆同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2 页。
⑯王显《古韵阳部到汉代所起的变化》,《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84年3月,131页。
⑰陆游《老学庵笔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16页。
⑱拟音参董同和《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10月,下同。
⑲何向东等《新修潼川府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10月,1246页。
⑳何向东等《新修潼川府志校注》,巴蜀书社,2007年10月,1234页。
[1]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2]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6-45.
[3]董同和.汉语音韵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