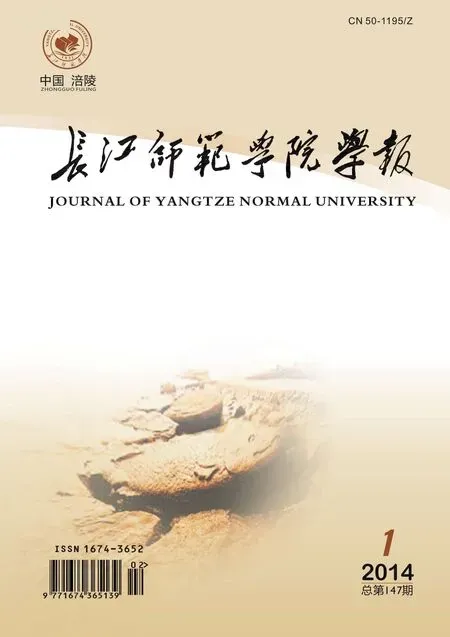乡镇变迁和流浪者的言语
——《一句顶一万句》主题解析
2014-03-29陈镭
陈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所,北京 100101)
□茅盾文学奖作品研究
乡镇变迁和流浪者的言语
——《一句顶一万句》主题解析
陈镭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文化所,北京 100101)
《一句顶一万句》微妙地折射出中国乡镇近百年的变迁,特别是在变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感受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当故乡已无法回去,家族变得若即若离的时候,当基督教的上帝和夫子之道都不能抚慰心灵的时候,人们该如何认出并说出自己,被言说的这个 “我”又该如何与他人相遇。
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现代性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用明清小说笔触写成的 “反传奇”作品,刘震云自评为 “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书”、“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1],这部小说却不迎合一般读者的趣味,叙述人的讲述拖拖拉拉、有始无终,主人公吴摩西 (杨百顺)、曹青娥、牛爱国的处境可能与普通民众相同,但他们平凡又有点执拗的人生缺少传奇性。中国老百姓从戏台到纸本再到今天的网络文学,喜欢的大多是充满 “虚假意识形态”的演义、神魔、公案、世情、才子佳人……对他们自己平淡人生的冷静审视,尽管模拟了家长里短式的絮叨,仍属于从他们中间走出来、试图回去的知识分子。《一句顶一万句》展示了正在进行现代性转变的乡镇,其中一部分人是如何从宗族社会和家庭生产中摆脱出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重新确认自己,开始回答 “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2]的提问(“摩西”的意义所在),正因为这极难回答,吴摩西们才觉得哪知我心者、能顶一万句的 “一句”始终找不到。小说容纳的思想内涵颇多,本文围绕这一中心问题,择其要者分述于下。
一、乡镇的变迁
《一句顶一万句》上卷的故事大致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书中交代吴摩西在私塾读过五年 《论语》,曾有机会进入县长办的新学,经过一番磨难之后流落他乡;下卷牛爱国 (外孙)生活的个体经济繁荣、“洗浴城”、“美食城”出现的时代,距吴摩西定居咸阳约七十年。有评论家认为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种 “去历史化”的另类叙述,没有写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阶级斗争激化,“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要抵达这种 ‘无历史’的状态并不容易,读读那些影响卓著的文学作品,无不是以意识到的历史深度来确认作品厚重分量。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动乱、没有革命、甚至没有政治斗争的 ‘现代中国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历史,但刘震云居然就这样来书写中国现代乡村的历史。准确地说,是无历史的贱民个人的生活史”。[3]在笔者看来,《一句顶一万句》上卷截选的年代特意与战争、瘟疫保持了一些距离,但它并没有形成所谓“大历史/个人史”的对立,作品呈现出丰富的社会图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吴摩西漂泊异乡的缘由。
吴摩西 (杨百顺)生活的延津有着丰富的趋向现代世界的特征,首先是商业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小说上卷浩繁的人物组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社会网络,涉及农业、商业、教育、铁路运输、准工业的工场作坊、大小公务员、各种小手工业、各种饮食服务,还有营利、非营利的戏班以及教会、当铺、药堂等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职业分类里,没有提到的可能只有采矿和建筑两类。尽管这时没有建立真正的工厂,还保留了某些实物交易(如杨百顺替人杀猪,获得猪下水作为报酬),作品塑造的延津已经容纳了不同的服务种类,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换。主人公先后干过卖豆腐、杀猪、染布、竹业、挑水、扛货、准公务员、卖馒头、贩葱、卖熟食等行当,跟杀猪师傅闹翻之后,他一度想当个佃农,因为冬季没有东家招长工而作罢。作品描写了大量农耕之外的农民,这不能说是非写实或 “去历史化”,恰恰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正如费孝通 《江村经济》写到的,由于土地上的产出只能供给基本温饱,农民必须从事不同类型的副业或雇佣劳动来增加收入,包括种植经济作物、畜牧、渔业以及非农业的运输、手工业、小买卖等等,市镇上也基本都是非农业人口。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和阶级关系激化,近代以来自耕农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逐渐被破坏,大量丧失生产资料的农民变为雇佣劳动力。社会分工的细化和职业流动,促使杨百顺们与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对他们来说正是一个在交换和交往中重新确认自身价值的过程。
宗族、家庭对个人的控制减弱。在农业社会,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元和生产单位,实现着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近代中国的宗法社会,对个人的控制尤其严密:
交通不便,农民居于乡里,足迹所到不出数十里外,其日常生活,对于政治从无密切之关系,终生或未见一州县官……其堪注意之点,则家族裁制之力,远过于政治权力,幼年时期,无论何事决于父母,中年分家自立门户,负有家室子女之累,扶助族人亲友之谊,人生一世,不受家族影响,自由决定取舍者,为事无几。自由人之在中国,盖不甚多。[4]
作品在多个人物的故事中写到了与家庭、宗族式生产的矛盾,特别是外来人口对原有农村一体化结构的破坏,如同一篇人类学观察:故事开端的老裴受不了娘家哥摆布,想杀他,途中偶遇被赶出来找羊的少年杨百顺而打消了这个念头;杨氏三兄弟中,老大杨百业希望通过结婚、分家来摆脱老杨的控制,不愿白磨豆腐;老三杨百利做了铁路上的司炉工人;杨百顺因受到不平等待遇,对父兄怨恨到了起杀心的程度,最终离家出走;作为 “无产化”的闲散劳动力,杨百顺没有经济能力娶老婆,只好接受县城寡妇吴香香的条件,改姓 “吴”入赘,而吴香香招赘的真实目的则是:通过在县政府跑腿的杨百顺,摆脱前夫姜家的控制、继续占有原属于姜家的馒头房。在 《江村经济》考察的江苏吴江县,夫家为寡妇招赘的新女婿必须改姓前夫的姓,在整个家族中处于最低的位置[5],中原地区的河南延津或许风俗有别,这一角色实际的经济、社会地位不会有太大差异。然而小说里杨百顺不但没有改姓“姜”,反而持刀大闹延津城,逼使姜家让出了对馒头房和孩子的所有权。这一主题的描绘延续到下卷曹青娥 (巧玲)的故事,巧玲是曹满仓买来做女儿的,类似的收养行为通常要得到族人的承认,甚至会付出一些经济补偿,因为这实际上损害了族人(例如原本应当过继的叔伯兄弟的儿子)的经济利益,何况收养的还是一个将会外嫁的女孩。书中写到曹满仓的弟弟处心积虑想要过继一个孩子给他,但最终从延津来的拐卖儿童取代了亲侄子。作品三分之二的篇幅围绕这两个更名改姓、终老异乡的延津人来写,他俩都没有继承自己家族的小产业,重组成一种非血缘的亲密关系 (巧玲是吴摩西的继女、最能 “说得着”的一个人,她被曹满仓夫妇收养,又一次组成非血缘的亲人关系),他们都促使另一家庭与宗族的关系变得松散。
吴摩西的漫游历程还有学徒和工场作坊阶段。杀猪老曾对待杨百顺 (吴摩西)的方式,已超越了当时一般的行会师傅水平 (学徒通常没有工资,师傅供给食宿和少量零用钱,可任意打骂学徒,支使各种劳役)[6],不但没有特别严厉的家长式人身控制,还能每杀一次猪分给他一点猪下水,比在老杨家中磨豆腐要实惠。杨百顺虽然也说过 “确实不赖”,但最终表现出对师傅/学徒 (帮工)制度的不满。之后他到延津邻县的染布作坊工作,书中描绘染坊的十几个伙计来自四省五地,均为流动的雇佣劳动者,但这种生产关系并未表现出 “资本主义萌芽”的优越性,实为半学徒制,杨百顺承担的换水工作有怠工的空间。与杀猪不同的是:在染坊没有 “出师”的那一天,单靠伙计们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转变为小业主的,即使成为 “染布师傅”也只是高级熟练工人。这时的杨百顺已经完全脱离杨家庄,彻底 “无产化”,再也没有回过他出生的村庄。
在经历了 “家庭生产—手工业学徒—工场伙计”的转变之后,杨百顺意外地成为 “准公务员”。在类似民间狂欢节的社火表演里,他颠倒自己的社会角色,出色地扮演了 “阎罗”,被喜欢戏曲的县长叫去县政府种菜,兼为其他差员打杂。小说不仅写了杨百顺这样的流动人口被纳入公务员阶层 (杨百利就读的新学也是作为 “预备役”公务员学校开设的),还描绘了几任延津县长对乡镇的不同影响(办新学、搞公共服务、处理与教会的关系等等,政府的力量前所未有地延伸至底层),漫画式地写到官场形状,小县城与民国总理的关联以及官员的私生活 (同性恋)。这些社会图景源自同一个现代性转变,即民族国家的兴起,杨百顺们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和进入政府工作的职业机会,看似因为几任县长喜欢办学、讲演、戏曲的个人爱好,实际上缘自政府机构扩大,拓宽了底层民众转变为中间阶层的通道。
《一句顶一万句》由祖孙三代 (吴摩西、曹青娥、牛爱国)的故事连贯而成,微妙地折射出中国乡镇近百年的变迁,特别是在变化的生存环境中,人们感受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吴摩西不同阶段的漫游经历以及曹青娥、牛爱国的远行是精心设计的,并非完全脱离 “大历史”的 “个人史”。而另一方面,刘震云的作品不是对社会的镜式反映,也没有卷入一些更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例如,他没有把吴摩西对家庭、宗族、师傅的反对以及对个人认同感的不断追求,与接触外来宗教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挂钩。吴摩西虽然当过意大利传教士詹善仆的徒弟,但后者影响他的方式并非教义,老詹不但传教生涯颇为失败,晚年还很喜剧地以邻家大爷的口吻而不是主的名义开导吴摩西[7]。如果吴摩西的个人史有所谓 “现代性转变”的话,这断断不能与 “新教伦理”的命题对接;同样,从他并不成功的染布工场生涯,也不能得出他日渐理性的思维来自新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结论;作家为底层的吴摩西设计了一段在私塾读过五年 《论语》、颇不寻常的教育背景,并用 “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众”来为不善说话的人物点睛,但也不能就此认为吴摩西日后的个性与理性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生力量;又或者,以上三种元素混杂起来,都只是 “杨百顺”变成 “吴摩西”的种种因由之一。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曾作出判断:近代中国农村的分化演变、大量雇用劳动力出现,并没有导致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只是一种 “准无产化”,农场的实际生产效率仍然不高,这与传统的 “本土资本主义萌芽被帝国主义入侵阻断”一说不同[8]。无论这一结论是否正确,社会分化和雇佣劳动力大量出现都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现象,它带来的对个人的影响和冲击是可以想见的,即使是今天,乡镇的现代衍变也没有最终完成。刘震云小说的重点并不在于回答社会学或历史的难题,而是把这近百年的乡镇变迁连在一起,把底层民众的内心生活呈现出来。在小说末尾牛爱国的故事里,作家关注的问题延伸至亲密关系的转变之上,这在牛爱国的祖辈吴摩西那代人的生活里,甚至还没有构成一个问题。
二、流浪:乡关何处
《一句顶一万句》由 “出延津记”、“回延津记”两部分组成,却讲述了一个流浪的主题,因为吴摩西再也没有回延津,下卷曹青娥、牛爱国 “回延津”只是去寻访一个陌生的县城,延津已不再是故乡。杨百顺七十年前的出走被作家赋予了摩西出埃及一般的意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和赤地千里的大饥馑之前,他已经流浪到了陕西咸阳,他可能是社会分化之后第一代出延津的人。
吴摩西精神上的疑惑、痛苦、孤独都与人的分离、流浪有关。《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版者把这部作品包装成 “中国人的千年孤独”[9],其实孤独对中国人来说只是这一百年的事。刘震云关注了从乡镇走出的现代流浪者之孤独,其抵抗 “影响的焦虑”的野心,不在于跟马尔克斯竞争,倒是在 “流浪”这个主题上与 《尤利西斯》呼应。他用 “摩西”来形容杨百顺的故事,似乎是向乔伊斯致敬——后者正是用奥德修斯的流浪来结构现代人布卢姆在都柏林街头的一日漫游。刘震云写到两个重要人物想要杀人,在偶遇并父亲般救助了一位少年之后冷静下来,这与 《尤利西斯》中布卢姆与斯蒂芬的关系近似;吴摩西、牛爱国都遭遇了妻子的不忠,这也是乔伊斯为布卢姆设计的一种身份。
刘震云写出了一部乡镇版的现代漫游记,但它的故事结构没有真正与 《出埃及记》对应,可以把摩西与吴摩西稍作比较:摩西在出埃及之前放过四十年的羊,《旧约》把他刻画成一个笨嘴笨舌、对自己能否当好先知充满疑虑的人。他的兄长亚伦能言善辩,经常扮演以色列人实际上的指挥者,也曾犯下拜金牛的大错;吴摩西同样是放羊出身,心事重重、不善言辞。其弟杨百利能说会道,是一个善于 “喷空”(一种天马行空的胡侃)的人,后来依附于工业文明的象征——火车。在 《旧约》中,先知摩西没能走到耶和华应许之地 “流淌着奶和蜜”的迦南,这一代以色列人大都死在路上,由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带领后人实现最初的梦想;吴摩西同样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或者那个 “说得着”的人,最终他在精神上而非血缘上的第二、三代人继续着这种寻找,像先辈一样远行。延津人出走之事被赋予了非常高的意义,他与摩西出埃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流浪是对个人价值和认同感的追寻,与宗教信仰无关,没有与神的复杂对话。他的流浪全然是现代的、个人主义的,传教士詹善仆打动他的是一名异乡客的理想主义激情,包括那从未实现的伟大教堂的图纸:
吴摩西要离开伤心之地;这时吴摩西想起师傅老詹生前讲经时说过的一段话,亚伯拉罕离开了本地和亲族,往神指引的地方去。但吴摩西与亚伯拉罕不同,吴摩西离开本地和亲族,离开伤心之地,却无处可去,也无人指引。[10]
刘震云在讲述吴摩西、曹青娥、牛爱国的故事之时,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将其中断:吴摩西刚刚显露了一点令人惊叹的水浒人物气息,就遭遇妻子的不忠、被人拐走巧玲,在悲伤和茫然无措中踏上了去宝鸡的火车,上卷至此结束;曹青娥 (巧玲)直到养母晚年才真正与她沟通,直到自己晚年才开始与儿子牛爱国沟通,然而她在 “爹呀”的呼喊中离世,留下牛爱国们无法猜透的遗言;牛爱国饱受妻子不忠、朋友无情的痛苦,在路边餐馆遇到有夫之妇章楚红,最有故事性的段落即将展开,作家却安排了一场牛爱国的内心挣扎,最后他想寻那“说得着”的情人已寻不得。书中还写到一些重要又很含混的细节——教堂图纸背后的两行字、多个人物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包括章楚红的那句话。这些略有些犹太色彩或者说卡夫卡色彩的含混、破碎、中断正是小说的优点之一。吴摩西们舍弃了稳定生活,沉醉于有些神秘的不确定的寻找,仿佛在持续的精神流浪中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基。作家中断叙述,只是为了返回尘世,为下一次的漂泊寻找理由,“这不是一道裂缝,它是实际上无所不在、从未获得承认的不可能的标志:不可能群居,不可能独居,不可能解决这种不可能”[11]。
如果回到社会学视角的 “外部研究”,《一句顶一万句》呈现的流浪可以从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来探讨:从身体上讲,农民的无产化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他们脱离家庭和小农经济,进入小县城、大都市,如今要步入异乡的各种 “园区”,服务于资本主义体系的 “世界工厂”。资本突破了地域限制,根据市场需求在全世界寻找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的流动造成了各种漫游者。对于从乡镇走出来的漫游者而言,尽管这是一次勇敢的变革,他们却被历史推到了一种既不想回去,又没有被城市充分接纳的 “半无产化”状态。这些漫游者已经被冠以工人之名、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角落,却无法成为市民阶层的主体之一,在教育、福利、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受到不平等待遇。他们只能在农村人的城市——县城获得较为平等的身份,因为这里绝大多数的家庭刚刚脱离或者尚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从精神上讲,流浪也许来源于诸神退隐的现代世界里,人们普遍的、无法克服的 “无根性”,但对这一特定群体而言,他们昨天还都生活在家族的怀抱中 (还有与祖先冥冥之中的精神交流),今天就要把决断权握在自己手里,无法勘定自身位置的困惑更加突出。在多数时候,他们会选择拥抱更高阶层的意识形态,把城市中蔓延的各种关于成功的神话变成生活信仰。
《一句顶一万句》没有直接写出这种处境,吴摩西在咸阳定居下来的事被一笔带过,曹青娥生活在比延津更小的山西沁源县乡下,牛爱国住在沁源县城,开车拉货挣钱,但实际上 “回不去”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们都还在寻找自己脆弱的根基。吴摩西出走后将遭遇中国的大动荡,他比今天的漫游者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社会阶层,同时抗战也会把大量的城市人向边缘地区和乡镇迁移,社会生活将重新洗牌。书中提到他在咸阳以卖熟食为生、斩断了与家族的全部联系,只惦记 “说得着”的巧玲,这对中国农民来说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第二代的曹青娥在河南延津生活五年,经历了生父、继父抚养的阶段,又被拐卖到山西襄垣县,跟养父母一起生活了十三年,最后嫁到沁源县,直到去世。她似乎不存在 “无产化”问题,但 “从哪里来”的困惑更加严重,临终呼喊的父亲吴摩西只是一个跟她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第三代的牛爱国开着车满世界地替人拉货,故事的结尾他开始满世界地寻找一个在路边餐馆偶遇的年轻女人。《一句顶一万句》自始至终也没有告诉我们,人物迷恋的、能顶一万句的那些知心话分别是什么,因为这样的认同和慰藉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三、陌生的言语
就像小说题目所示,刘震云这部作品是关于说话的故事。“一句顶一万句”的潜台词是:如果“说不着”,一万句也不顶用;寻找 “说得着”之人的潜台词则是周围的人大多说不着了。周围的人都说不着?这恰恰是传统社会发生分化之后,个体生成的标志。传统乡镇有着狭小的生活圈子、生活空间和生产半径,同族人、同姓人组成一个村子是常有的事。在这狭小的农业社区里,生产方式大致相同,公共事务由德高望重者主持,新闻事件被整个圈子共享,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对他人产生影响,而整个乡镇有某种统一的文化个性,阻止圈内人的个性发展和向外部发展。在宗族或宗教奠定基本秩序的社会里,个人说不说得着,原本不是一个问题。然而这种情况在乡镇的现代进程中被瓦解,书中吴摩西对喊丧人罗长礼的崇拜,几乎就是一个颠覆语言秩序的隐喻:罗长礼本是个五短身材的麻子,在卖醋这一行中做得比较差,酿出来的醋容易长白毛、泛酸,但他一旦扮演起喊丧的角色,便气势如虹,把客人安排得井井有条,仿佛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和个性自由 (吴摩西喜欢舞社火,通过扮演“阎罗”获得了在县政府打杂的机会,同样是从原有的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喊丧人”还在刘震云的其他作品中出现:《手机》里主持人严守一的大哥严守礼在老家帮人写喊丧词,某丧主家的四个儿子都是不孝之人,严守礼决定 “有一说一”地讽刺他们,被四人揪住殴打,严守礼搬出在京城掌管媒体话语权的弟弟,威慑住众人。此后喊丧生意反而兴旺,因为村民认定,胆敢请他的团队来喊丧,即是问心无愧的孝子。“喊丧”这种仪式化、节日化的行为,本是用来宣布死者、生者都是集体的、社会的、互动的,现在却成为罗长礼、严守礼实现自我价值、在村里说得起话的一个途径。吴摩西对罗长礼的崇拜渗透了对个性自由的向往,他在断了与所有亲人的联系、彻底离开延津之后,决定用 “罗长礼”这个名字度过此生。
“说不着”代表了大量不同性情的现代人已经从乡镇诞生。吴摩西起初只是觉得家里和杀猪师傅对他不公,在县城的手工工场里,他感到了更大交流的困难——十几个伙计分成六个小团体,同乡之间说不着,陌生人反而结成好搭档,染坊老板更是一个极难沟通的人,他对管家和伙计的最大威慑力就是不说话、盯着人看。下卷牛爱国的故事发生在当代,“说不着”的问题同样严重,起先说得着的几个熟人 (冯文修、杜青海、曾志远、陈奎一、李克智)随着故事推进,渐渐都说不着了,这表明说话人自己对世界的感受、认知在不断调整,只要现代世界的变化永不止息,“说不着”就会成为一个难以消除的心理问题。
从微观的视角来看,“一句顶一万句”的问题还在于:为什么是那一句?为什么说话人要苦心寻找藏匿于时间之中、微茫不可寻的信息?在多个人物的故事里,被寻找的其实不是在当下可以说着话的知心朋友 (既然是知心朋友,又怎会遍寻不着?)。曹青娥两次回延津寻找吴摩西,牛爱国去求证母亲和姥爷的最后一句话,牛爱国寻找章楚红……这些行为都超越了说说知心话的范畴,他们大多是在寻找自己这一生中关键的印记,这些人和事都是自我赖以确认的基础。如果说,曹青娥寻找吴摩西还是出于对继父的亲情或 “说得着”这个基本原因,那么她寻找当年拐卖她的老尤,从新乡到长垣到开封一直找了二十多天,又不是出于复仇,则充分说明了那些偶然的印记对于自我形成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些事物在他人看来或者在更宏大的意义网络里面,可能并不十分重要,对我们自己而言却是极其微妙、隐秘的东西,寻找和重温它们成为了一种人生的文学化活动,作家只不过是恰好拥有诉诸文字的能力罢了。理查德·罗蒂借弗洛伊德学说分析过这种隐藏于人类思维中的诗的功能,“由于每一个人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实现其个人的幻想,因此,人类生活中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部分,就在于人会为了达到象征的目的,而在后来的生活中使用早先碰到的每一个特殊的人、物、情境、事件和字词。这过程就等于是对过去碰到的这些事物加以重新描述,从而对它们说:‘我曾欲其如是。’”[12]我们平常对知心朋友最爱说的正是一些秘而不宣的私人事件,对这些事物的重新描述是一种理解自我、从时间中暂时解脱出来的文学化活动,拥有文字才能的作家则恰好是获得了较多听众的那一类人,这种文学化活动对经历各种人生苦痛的我们有无穷的吸引力。在小说中,曹青娥数次讲述一个关于没有头、没有面目的爹的恶梦,这一情节以及她与继母晚年的和解都是这部作品极其动人的部分。
当故乡已经无法回去,家族变得若即若离的时候,当基督教的上帝和夫子之道都不能抚慰心灵的时候,人们该如何认出并说出自己,被言说的这个“我”又该如何与他人相遇?在过去的时代里,“我”并不只属于我,或者首先不属于我,当人生的意义由我自己来判断、理解之时,它仍然不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是与世界联系、对话的产物。那些过去时代的或美好或压抑的文化传统仍在延续,只不过削弱了它们的力量,而新的传统还没有形成。如果要恰如其分地说出我们自己,可能会用到他人毫不在意的细节、他人颇为陌生的言语、他人并不认可的评判标准,在绝大部分没有知心人倾听的时刻留给旁人去猜谜。另一方面对倾听者而言,有相似境遇固然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但更多时候首先要尊重这种陌生性。
刘震云的作品本身可以看做是一次倾听并重新说出的努力,说出的既是别人的故事也他自己的故事,同时还是思考历史的结果。他试图在语言风格上继承一些明清小说的市井风、达到 “遒劲”的语言效果,又在叙述上分出许多枝节,使用重复、延宕的写作技巧。这样混合的手法与他想表达的东西相对应,都属于一个新旧传统混杂的时代。刘震云多数时候选用了受限制的第三人称叙述,极为小心地进行心理描写——这些有限的描写也都能通过人物之口转述,并不是直接为人物代言,这体现了他对那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不过这样一来,小说的表现力似乎有所不足,他在曹青娥的故事里不得不多次使用梦境、呓语来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在我看来,这一部分恰恰比吴摩西和牛爱国的故事更加动人,即使选用了较为传统的叙述视角,人物内心也有可以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是我写得最好的书[N].大河报,2009-03-17.
[2][7][10]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94、144—145、206.
[3]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J].南方文坛,2009(5).
[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701—702.
[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74—75.
[6]李家齐.雇佣制度[A].上海工运志[Z].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8]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安波舜.一句胜过千年[A].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1]Maurice Blanchot.Reading Kafka[A].The Work of Fir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6.
[12][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M].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5.
[责任编辑:黄江华]
I206.7
A
1674-3652(2014)01-0047-06
2013-10-13
陈 镭,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