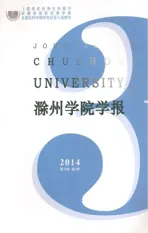吴敬梓笔下的娄氏兄弟形象及其叙事意向
2014-03-28甘宏伟
甘宏伟
吴敬梓笔下的娄氏兄弟形象及其叙事意向
甘宏伟
娄氏兄弟是《儒林外史》第八至十三回里出现的人物。吴敬梓塑造娄氏兄弟的形象,是为那些科举考试中所谓的怀才不遇者画像,并对读书人因科举不第而生出怀才不遇的心态进行嘲谑和调侃。写娄氏兄弟与写周进、范进、严监生以及马二先生一样,都是为了烛照科举考试制度下读书人的精神与心态。吴敬梓是在通过他们反复告诫读书人:不能让举业功名迷了心窍,读书人应当生活得不失尊严,读书人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应该去做。
《儒林外史》;吴敬梓;科举社会;士人心态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八至十三回里塑造了娄三、娄四公子的形象。娄三公子名琫,是个孝廉;娄四公子名瓒,在国子监读书。他们的父亲是太保、大学士①,位居三公,官正一品,在朝二十余年,死后赐葬赐谥,极享尊荣。长兄在京师为官,时任通政司大堂,官属正三品,这个职位掌管内外章奏,诸如四方陈情建言、申诉讼告等事。娄氏兄弟称得上是出身高官显宦之家。只是他们未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觉科名无望遂放弃了举业,却又因科名蹭蹬激成了一肚子的牢骚不平。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塑造的娄氏兄弟形象应该如何理解?或者说,吴敬梓为什么要在《儒林外史》里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真实理解《儒林外史》的文本意蕴和创作意图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娄氏兄弟也是吴敬梓为烛照科举考试制度下读书人的精神与心态而塑造的形象。
《儒林外史》里与科举考试有关涉的主要人物,娄氏兄弟之前有周进、范进、严监生,娄氏兄弟之后有马二先生。如果从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精神心态所造成的影响的角度看,周进、范进、严监生是被举业科名诱逼、磨耗得或颠狂或猥琐,以至失去做人的最起码尊严的一类形象;马二先生则是因虔诚于举业科名而生活得很迂拙的一类形象。那么娄氏兄弟呢?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显著的就是落第士子的习气,代表了科举社会里读书人当中所谓的“怀才不遇”者一类。《儒林外史》塑造他们时所用的笔墨则表明,吴敬梓对读书人因科举不第而生出的怀才不遇心态,是持调侃和嘲谑态度的。
一
《儒林外史》里,娄氏兄弟一出场,就很快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自视才高,时常怨愤不平,喜欢发表些与时宜相违的偏激言论。
娄氏兄弟因科名未能如愿,于是激起了满腹牢骚,即便呆在京师,他们也忍不住每常作些“自从永乐篡位之后,明朝就不成个天下”[1]112之类的议论,弄得兄长也听不过,怕惹出事,劝他们回了湖州老家。在姑丈蘧太守家烹茗清谈,说起宁王反叛之事,娄四公子又起了兴致:“据小侄看来,宁王此番举动,也与成祖差不多。只是成祖运气好,到而今称圣称神,宁王运气低,就落得个为贼为虏,也要算一件不平的事。”[1]112娄氏兄弟的牢骚偏激本缘于自视才高却又自认时运不济。比较一下娄三、娄四公子对成祖和宁王的议论,便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以看成祖的眼光,他们应该说宁王也是图谋篡位;如果以看宁王的眼光,他们应该称颂成祖英明。可是这兄弟二人不是如此,他们攻诘成祖,却为宁王鸣不平。这固然表现出不以成败论人的识见,不过也不能因此而高估了娄三、娄四公子的胸襟。他们实际上是在以运气论人,成祖运气好他们攻诘,宁王运气不好他们不平,这并不比以成败论人高明到哪里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娄三、娄四公子为何表现出不以成败论人的识见,却又陷于以运气论人的偏狭?不妨作这样的推测,娄三、娄四公子若以成败论人,那他们不能中鼎甲、入翰林,岂不是把自己也置于没才学、没本事的读书人之列了;可如果以运气论人,娄氏兄弟就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充分的可以沾沾自喜的理由了:我们兄弟没中鼎甲、入翰林不是因为没学问、没本事,而是因为运气不好。从这一角度看,娄三、娄四公子还真算是“高明”,原来是在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用宁王说事的确能够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只是太不谨慎、太过轻率了些。接着再看二娄后面的议论,更可以证明这种推测是合乎他们的心思的。蘧太守又对娄氏兄弟说起他的孙子:“自你表兄去后,我心里更加怜惜他,已替他捐了监生,举业也不曾十分讲究。近来我在林下,倒常教他做几首诗,吟咏性情,要他知道乐天知命的道理。”[1]112-113娄氏兄弟赞赏其高见,结果生出来的还是不无激愤之言:“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1]113二娄提起这样一句俗语,实则含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即:我们与其做一个斫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做一个有阴骘的通儒。再进一步讲,就是说:我们兄弟不是没有中进士的才,连做通儒的才都有,只怪我们运气不好。这样的话,要是在高翰林、施御史那里,肯定是不通的,所谓有操守的到底要从科甲出身。不过,存异求同的话,二娄实际上和他们也有一点是完全相通的,即都很看重科甲,不然,娄氏兄弟也不会对自己没能中进士、入翰林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像娄氏兄弟这样自感不遇于时而偏激怨恚的读书人,在科举时代不乏其人。王定保在《唐摭言》里就摭取了一些这样的读书人,王泠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王泠然,唐玄宗开元五年(717)进士,但一直未能得官,就向御史高昌宇、燕国公张说写信要求他们为自己谋得一官。《唐摭言》分别在卷二“恚恨”条、卷六“公荐”条辑录了王泠然的这两封书信。这里,仅以他写给张说的信为例述之。在给张说的信中,王泠然先以炫己:“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契、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2]1627接以责人:“天丧斯文,调零向尽,唯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知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2]1628甚竟至于诋难:“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2]1629《唐摭言》的作者王定保认为,对像王泠然这样不求己反责人的行事,非君子之儒所为,读书人应当反之于己,得失以道,而非望之于人,以至爱憎竞作[2]1593。不过,比较而言,王泠然的恚恨是为个人功名,虽怨天尤人,倒也直白,就是想做“相公一株桃李”,非徒为自炫;而娄三、娄四公子的偏激言论,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只为逞口舌之快,于事无补,于己无益,看来是显露自己不同于常人的识见,实则是对没能得中鼎甲之事耿耿于心,不免有藉惊人之论以搏取声名之嫌。
二
在娄氏兄弟身上,因科名蹭蹬而表现出的又一特征是:他们有极强的知音难觅之感,以至于妄认“同道”。
像娄氏兄弟那样对成祖和宁王所发的骇俗之言,自然很少有人敢公开地表示赞同,这是可能触忤朝廷的议论,可不是小事情。马二先生就曾被县里的差人唬得面如土色,托辞就是他的朋友蘧公孙忤逆朝廷,最终以此为要胁挤干了他身上的银两。其实,有娄氏兄弟这样看法的应该不乏其人,宁王和他的臣子就应该是想效仿成祖才起兵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势下,极少有人敢冒大不韪之险说出来。所以,长兄也怕惹出事劝他们回老家,刚好他们苦无知音,呆在京城也甚觉无聊。回到家乡,娄氏兄弟爱发议论的习气依然受到沮抑,姑丈蘧太守对他们妄言天下、非议朝政的行止,就正色提出告诫:“成败论人,固是庸人之见,但本朝大事,你我做臣子的,说话须要谨慎。”[1]112自己的一番卓识高见无人响应,娄氏兄弟颇有知音难觅的感慨。恰巧,府上的家人邹吉甫向他们谈起新市镇上有个杨执中,此人说过“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1]118这样的话。娄氏兄弟不由大惊,竟然还有和他们一样对永乐爷表示不满的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不想在乡间遇上了知音,就马上向邹吉甫探询这人的来历。又听说杨执中为人忠直不过,又好看的是个书,就将他认作了穷乡僻壤的读书君子。得知他因为欠债被收监,回家收拾停当之后,就派人救这位身陷囹圄的“同道”。
不过,娄氏兄弟将杨执中引为知音,实在是有些自作多情了。杨执中说永乐的坏话和二娄论成祖篡位,尽管都是对成祖永乐皇帝表示出些不满,实则有根本的不同,怀有不一样的心思。邹吉甫那番说酒汁淡与薄的话是从杨执中那里学来的,正可表示杨执中的意思,二娄也认为,乡下一个老实人,不会得知这些话。杨执中说永乐爷是将他和洪武爷相比,二娄论成祖是将他和宁王相比。二者拿来比较的对象不同,所表露的心思也就迥然有别了。如前所述,二娄说成祖和宁王是在以运气论人,是因未能中鼎甲而激成牢骚。杨执中则似乎是在以人情说世道,是抱怨永乐时的人情比洪武时的人情薄了。为什么杨执中有这样的抱怨?看看他的行止和他的家庭就可以明白了:东家因他为人“正气”,就托他管总,他却不肯用心料理,只管出外闲游或垂帘看书,凭着伙计胡弄,称他为“老阿呆”实在是没有枉屈他。家里又穷极,常日只好吃一餐粥,两个儿子又都是蠢人,既不做生意,又不读书,还靠着他养活,且时常在外面喝酒赌钱。如果说以娄氏兄弟论成祖和宁王也还不乏识见的话,那么杨执中这样又穷又酸的“老阿呆”不怪自己不做营生、不善持家,却怪永乐弄坏了天下,实在是不着边际,不免有些大言不惭。书中说永乐的还有一位杜慎卿,他说:“本朝若不是永乐振作一番,信着建文软弱,久已弄成个齐梁世界了。”[1]364搁下孰是孰非之辨,杜慎卿论永乐的气度要远胜于这位杨执中。总之,可以确定的是,杨执中和二娄议论永乐,本是缘于不同的遭际,基于不同的眼界。可是,娄氏兄弟一听到这位杨执中和他们一样说永乐的坏话,也就不论是不是抱有和自己相同的心思了,反正都是对永乐爷表示不满,肯定是志同道合了。正如卧闲草堂评说:“即有百口称说杨执中为不通之老阿呆,亦不能疏两公子纳交之殷也。”[1]127因为对娄氏兄弟来说,盼到这样的“知音”实在是太难了。由此也可见,二娄识人的眼光实在不能让人恭维。从后来的情形看,娄氏兄弟三顾草庐拜访杨执中,待他十分虔敬,又认他是个襟怀冲淡的人,其实他根本承负不起这番敬重,应该感到很惭愧。不过杨执中是不会惭愧的,他相与娄三、娄四公子本来就是想做个食客,蹭份不要钱的酒饭吃而已。鲁编修和娄三公子说:“这样的人,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我老实说:他若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只做这两句诗当得甚么?就如老世兄这样屈尊好士,也算这位杨兄一生第一个好遭际了,两回躲着不敢见面,其中就可想而知。依愚见,这样人不必十分周旋他也罢了。”[1]130有学问就得中了去,固为鄙陋之见;称杨执中是躲着不敢见,固是猜度之词;但他说杨执中之流“盗虚声者多,有实学者少”却也的确近情,他对娄氏兄弟的劝告也不失忠恳,不过鲁编修这“俗气不过”的话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后来,杨执中向娄氏兄弟荐举权勿用,称权勿用真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称他有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乃是当世第一等人,为投二娄之所好,不吝虚溢之词,以耸二娄之听闻,更是极不厚道。但娄氏兄弟不仅不产生怀疑,反而认为乡间真有此等人,这样自己又能结识一个有才而不遇于时的知音了,为此还专门将一个亭子题匾为“潜亭”,以示等权潜斋来往的意思。而权勿用其人实则是比呆头呆脑的杨执中还可笑的人,他不种田,又不做生意,坐吃山空,举止又怪模怪样,人品也上不了层次,至于在乡里的口碑更是糟糕得不行。从与杨执中、权勿用这些不呆即怪之人的际遇来看,娄氏兄弟真是盼知音盼得太着急了。
三
在《儒林外史》里,热衷于求名做名的并不少,但求名最终求出扫兴,做名最终做成笑谈的,还只有娄氏兄弟。
娄氏兄弟,因热衷求名做名,以至将自己遐想为历史上贤人俊士风云际遇的主角,结果一场豪举落得一场扫兴,“无限壮心”化做一时笑谈。应该说,娄氏兄弟还是确实有些经史学问的,只是因科名蹭蹬,一番功名事业心没个施为处,故转而求名做名。这主要体现在不断引起他们遐想的与杨执中的一段遇合历程之中。娄氏兄弟的遐想是从听知杨执中那番说永乐的话开始的。这遐想一开始,杨执中这个人物的行为做事,便在娄氏兄弟那里不断被过滤幻化,变得越来越崇高。起初,从邹吉甫那里听得杨执中的事,本来是杨执中不肯用心料理生意,只顾自己闲游看书,任由伙计乱来,亏空了七百多两银子,辜负了东家的托负,是个十足的“老阿呆”,娄氏兄弟却将他认做穷乡僻壤的读书君子,反责怪东家是守钱奴,杨执中是受了东家凌虐。接着,他们花了七百多两银子将杨执中救出,过了一月有余,杨执中却迟迟不肯来谢。二娄不胜诧异之际,想到了越石甫的故事,将杨执中想成了越石甫那样的人物,于是,更觉得他有高绝的学问和不寻常的人品,越发值得仰慕。只可惜这位杨执中并非其人,实际情况是杨执中根本不知道是谁救了他,也不想着去打听谁救了他,只是抱着不必管他,落得身子干净的心理,继续过他那不持家、不营生的“老阿呆”日子。倘若要知道娄府兄弟救了他,他巴不得连夜去相与。娄氏兄弟将杨执中想象成越石甫,其微妙的心思也颇可玩味。越石甫,又作越石父。《晏子春秋》卷五《内篇杂上》第二十四则、《吕氏春秋》卷十六《观世》篇、《史记》卷六十二《管晏列传》、《新序》卷七《节士》都载有晏子与越石父的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晏子去晋国的路上,途经中牟,遇到了敝冠反裘负刍的越石父正在路边歇息,看他是个君子,就将他从主人那里赎出,使他得免劳苦冻饿,并且“解左骖以赠之”,又载着他一起回去。“解左骖以赠之”,马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尊贵的馈赠之物,而赠以左骖更表示对受赠者的尊敬之意。越石父被晏子赎出,不再为人之臣仆,而且又给予这么尊贵的礼遇,依照常理,越石父应该表示感激才是,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颇出人意外:
至舍,不辞而入,越石父怒而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吾未尝得交夫子也,子为仆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赎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绝我之暴也。”越石父对之曰:“臣闻之,士者诎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彼功诎身之理。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晏子出,见之曰:“向者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之,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革之。”乃令粪洒改席,尊醮而礼之。越石父曰:“吾闻之,至恭不修途,尊礼不受摈。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晏子遂以为上客。[3]353
上面所列记有晏子与越石父故事的几部书中,除《史记》外,在记述完这个故事后,都载有托君子之口所作的论赞,论赞说:“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3]354论赞对晏子“免人于厄,反诎下之”的高尚道德不吝褒扬之辞。娄氏兄弟将杨执中遐想为越石甫,那么他们就自然可以与晏子同列了。不过,二娄欲礼贤求士,却又生出几多顾虑:四公子认为,虽然帮救了他,但仰慕他就应该先到他家相见订交,不能盼他来报谢,这是俗情;三公子则提出,“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若先到他家,就等于是要特地自明这事,也是俗情。去也俗,不去也俗,都无益声名,这让娄氏兄弟颇费了一番踌躇与权衡。最终还是抵不住对“高人”杨执中的想往,商定前去相访,在二娄看来,有这等极高品行的人,实在不忍因为这些缘故与之隔绝,错过一番际遇。天目山樵于此处将二娄与虞博士、杜少卿二人作了对比,评道:“虞、杜济人,情由中出,全是真诚,二娄则枝枝节节有许多计议,盖求为名高耳。”[1]122此正可谓是对二娄心思的洞鉴之论。
三顾草庐访杨执中的一段若遇若合之中的奇妙见闻,更让娄氏兄弟一片访贤觅士之心愈浓愈盛。杨执中俨然成了一位身处飘飘仙境中品高德重的高人雅士,他们自然也就俨然成了礼贤好士的信陵君、春申君一列的贤公子。正因为二娄油然生出的无限遐想,使得他们在审视杨执中的时候,怎么看怎么觉得此人非可等闲视之。其实杨执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早年补廪,乡试过十六七次,始终未能中得举人,到老了终得一教官,于是视若至宝。鲁编修只是当着娄氏兄弟的面说杨执中一句:“他果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他们就直说鲁编修是个俗气不过的人。杨执中辞了教官,报帖却还一直贴着,将他的这般作派与鲁编修相比,鲁编修固然俗不可耐,不过杨执中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雅人。但在二娄看来,鲁编修是俗气不过的,而杨执中是雅致不过的。这也许是在于:鲁编修说杨执中有学问,为甚么不中了去,正说到他们的短处,二娄正为自家运气不好没能得中鼎甲而愤激不平,最不喜欢听鲁编修这样的话,自然鲁编修是俗气不过的;而杨执中却和他们一样都是科名蹭蹬,正可同命相通,还有他们数月以来越积越浓的无限遐想,加上杨执中那番力辞教官不就的谈吐,以及亲临其境所见到的杨执中居处之地的小小草屋、一方小天井、几枝梅花、满壁诗画、一幅对联,不由得他们不将杨执中看作雅极了的高人贤士,自己当然也就飘飘如游仙境了。
各色人等聚齐之后,娄氏兄弟便做了一件极助声名的事——莺脰湖宴宾。这番聚会进行了一整夜,船上数十盏羊角灯映着湖光月色,照耀如同白昼,一派乐声大作,声闻十余里,惹得两边岸上的人,望若神仙,无人不羡。如此动静必定令娄氏兄弟雅名远播,他们也必定心满意足。莺脰湖宴宾,在娄氏兄弟,肯定觉得是一件雅极了的事,而吴敬梓对其场景的描写及最后的一句按语却分明透出笑谑:“席间八位名士,带挈杨执中的蠢儿子杨老六也在船上,共合九人之数。当下牛布衣吟诗,张铁臂击剑,陈和甫打哄说笑,伴着两公子的雍容尔雅,蘧公孙的俊俏风流,杨执中古貌古心,权勿用怪模怪样:真乃一时胜会。”
到后来,娄氏兄弟对杨执中、权勿用,尤其是张铁臂诸人的心思和手段也许有些察觉。比如,张铁臂得到娄氏兄弟赠送的五百两银子,丢下血淋淋的“人头”走后,娄氏兄弟在家等他回来。小说用了一段细致入微的笔墨绘写了娄氏兄弟将信将疑之下的焦躁情状,一个说:张铁臂他做侠客的人,断不肯失信于我,我们却不可做俗人。我们竟办几席酒,把几位知己朋友都请到了,等他来时开了革囊,果然用药化为水,也不是容易看见之事。我们就同诸友做一个“人头会”,有何不可?另一个说:想他在别处又有耽搁了。他革囊在我家,断无不来之理。娄氏兄弟已是将信将疑。可是在梦幻没有破灭之前,他们还是宁信其实不信其虚的,因为二娄遇到的那些场景正巧和他们依靠无限遐想编织起来的梦幻极为契合,他们也正准备着靠这些人“众星捧月”做一场“人头会”,为自己再添上一段“谁人不羡”的佳话呢。只是再后来,精心准备的“人头会”变做令他们面面相觑的“猪头会”,权勿用又被差人从家里带走,这些很失面子的尴尬事,应该能让他们先前远播的雅名化作人们的笑谈,娄氏兄弟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此闭门整理家务,休问世情。
四
最后还需要提出的是,在吴敬梓笔下,娄氏兄弟虽爱发牢骚、喜好做名,但他们的品行还是不错的。他们待人谦和,忠厚和平,绝无贵公子派头,断不做那些以功名富贵骄人傲人的事,也断不依仗家族势位横行乡里。如两公子初访杨执中途中,有人冒用他家名义耍横,他们也只是指说人家不应该在河道里行凶打人,坏娄家名声,并无怪罪,反倒告诉这家仆人不必向主人说起此事。可以说,娄三、娄四公子尚不失为贤者,倘若他们不为科名蹭蹬而牢骚不平,不热衷求名做名,而是出于真诚做些帮衬人的事,他们是可以和杜少卿同列的。因此,对于娄氏兄弟,吴敬梓在笔墨间流露的多是一种调侃而非讥讽。但是,这种调侃也足可以表明,吴敬梓不赞赏读书人因所谓“怀才不遇”而怨愤牢骚的名士习气,其所谓的怀“才”不遇,怀的也不是什么“真才实学”之“才”。
综上所论,《儒林外史》塑造娄氏兄弟正是为那些科举考试中所谓的“怀才不遇”者画像,同时小说又在不动声色地嘲谑和调侃中,显明了作者的态度:读书人科名蹭蹬,大可不必牢骚不平,也不必有什么知音难觅之感,若再热衷于求名做名,可能名未得到,却成为笑柄。如果与周进、范进、严监生,以及马二先生放在一起看,显而易见的是,吴敬梓通过科举考试下不同类型的读书人形象,意在反复告诫读书人:不必将科举考试看得太重,不能让举业功名迷了窍,读书人应当生活得不失尊严,而且读书人也有许多比举业功名更重要、更有意义、更能体现读书人价值的事情应该去做。
[注释]
①《儒林外史》第九回娄三公子对邹吉甫说:“我们从京里出来,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邹吉甫向娄氏二公子说:“我夫妻两个,感激太老爷、少老爷的恩典,一时也不能忘。”有论者据此以为,娄三、娄四公子的祖父是太保,因而说娄氏的祖、父、兄都是高官。这实在是误会了。按明清官制,太保不是独立的官职,通常是由德高望重的正一品官员兼任,相当于今天的荣誉职位。如果娄氏兄弟的祖父是太保,那至少也是正一品,也应当赐谥赐葬,但小说中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其实,“太老爷”在古代有一个用法是仆人对主人之父的称呼,在这里是娄府仆人邹吉甫称呼主人娄氏兄弟的父亲。“少老爷”这里指的是娄氏兄弟。再者,太老爷如果指娄氏兄弟的祖父,那么邹吉甫也不会只提娄氏兄弟和他们的祖父,而将他们官居大学士的父亲置之不提。因此,娄三公子说先太保、邹吉甫说太老爷都是指娄氏兄弟的父亲。
[1]吴敬梓著,李汉秋辑校.儒林外史汇校汇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王定保.唐摭言[M].//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2.
On the Characters of Lou's Brothers Shaped by Wu Jingzi
Gan Hongwei
Wu Jingzi shapes the characters of Lou's brothers,which represent the underappreciated scholars who liv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and intends to banter and ridicule them only in the chapters from 8to 13in The Scholars.If studying the characters of Lou's brothers with Zhou Jin,Fan Jin,Yan Jiansheng and Mr.Ma Er,we find that Wu Jingzi intends to warn that the scholars should not be obsessed by fame and live with dignity and do more meaningful things.
The Scholars;Wu Jingzi;the characters of Lou's brothers;imperial examination
李应青
I207.41
A
1673-1794(2014)03-0001-05
甘宏伟,河南城建学院中文教学部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明清文学(河南平顶山46703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科举制度与明清社会(11JJD750001)
2013-11-16